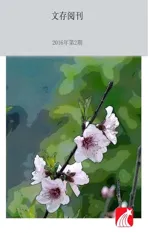唐弢对书话文体的实践与贡献
2016-07-20毛乐耕
毛乐耕
唐弢对书话文体的实践与贡献
毛乐耕

1920年代,在上海邮政局工作的唐。
书话这一文体和名称,起源于1930年代。
据姜德明先生考证,曹聚仁早在1931 年8月15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便发表了题为《书话二节》的文章,在8 月22日出版的《涛声》第二期上,又发表了《书话·2》。在1933年和1934年的《申报·自由谈》上,也有几位作者以“书话”的名义发表读书小品。到了1937年4月,阿英在《青年界》第十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1937年10月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前后,阿英又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一组《鲁迅书话》。(姜德明《唐弢书话·序言》)
这几位都是中国现当代书话最早的实践者和探索者,他们的作品,应是现当代书话的滥觞之作。
然而,现当代书话能够在写作方面长期实践,深入探索并努力加以弘扬的,则应首推唐弢。现在,一部《晦庵书话》,已经成为现当代书话写作的经典性文本,受到了许多书话迷的追捧,影响很大。
唐弢的书话写作,开始于1945年春天,最初是在柯灵主编的《万象》发表,接着,又先后在《文汇报》《联合晚报》《文艺复兴》《文讯》《时与文》等报刊发表,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写了一百篇光景”。(唐弢《书话·序》)
唐弢在1940年代写作的书话,对姜德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姜德明曾回忆说:“四十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塞”,“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版本一直诱惑着我”,“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唐弢书话·序言》)
由于有了这个深刻的印象,后来就促成了姜德明与唐弢在书话写作方面的合作。
1959年,唐弢从上海调往北京工作,当时已在《人民日报》副刊部任编辑的姜德明抓住这个机会,邀请唐弢为报纸撰写书话。唐弢当然愿意,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也有一些担心。他对姜德明说:“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姜德明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就和他一起商量,决定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所以后来唐弢在《人民日报》上的书话栏目一开张,首先谈的就是李大钊的书、鲁迅的书,然后再谈到国民党时期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这样,从1961年开始,唐弢又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书话总计有二十多篇。第二年,北京出版社就邀请唐弢编选一个书话集,这就是1962 年6月第1版的《书话》,署名为晦庵。这本书是唐弢出版的第一本书话集,也是后来颇负盛名的《晦庵书话》的前身。
二十年以后的1979年,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新时期文学开始兴起的历史时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邀请唐弢编选新的书话集,这就有了1980年9月第1版的《晦庵书话》。
新版的《晦庵书话》,将1962年6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书话》连《序言》带《附录》作为第一辑全部收入书中,同时又增加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等四辑新的文字,在篇幅上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唐弢又为这本书另写了新的序言。作者的署名也从《书话》的署名“晦庵”改为“直署本名”唐弢了(其实唐弢的原名叫唐端毅)。
《晦庵书话》的出版,产生了一个有趣的但也是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它的影响具有慢热型和持续扩大型的特点。这里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0年前后,正是新时期文学热的发轫时期,当时出现的文学作品,有的一经发表,就即时大热,形成了轰动性的影响,如1977年发表的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1978年发表的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以及后来陆续出现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晦庵书话》也是出版于这一时期,它的问世,在读书人中间固然也有一些影响,但与那些大热的文学创作却不能相比。然而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时间经过三十多年以后,新时期之初出现的许多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都已退出人们的视线,走进了文学的历史,可是《晦庵书话》却并不显得过时,虽然它在写作上也留有时代的痕迹,但依然在读书人中间具有影响,并且随着在一定范围内出现的读书热和书话写作热,已经多次再版,而且,这种影响力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就是《晦庵书话》的迷人之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弢的《晦庵书话》,对中国现当代书话文体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具有奠基意义。
唐弢写作书话,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三个基本的特征:一、作者写作的着眼点在书。唐弢说:“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书话·序》)二、唐弢探索的书话文体,其源头是中国古代的藏书题跋。唐弢说:“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晦庵书话·序》)三、书话文体是短文,具有篇幅短小的特点。
当然,唐弢对书话文体的实践,又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三个基本的特征上,他还能自觉地不停地进行多侧面的探索和追求,努力创造一种新型的受读者欢迎的书话文体。唐弢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追求意识和目标。
首先,唐弢写作书话起步比较早,持续时间比较长,经过不断的探索,反复的实践,使他在书话文体的写作中积累了作品,积淀了感悟,积聚了成果,扩大了影响。
唐弢的书话写作,始于1945年,至1980年出版《晦庵书话》,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多年。虽然这中间唐弢也因为有其它工作任务、写作任务以及一些客观因素,写作有时断时续的现象,但总体来说,他是始终坚持对这种文体进行探索和写作实践的,只要条件许可,他“一直没有放下《书话》的写作”。(《晦庵书话·序》)由于有了长期的坚持和实践,唐弢才具有了现在这样的成果和实绩。
其次,唐弢的书话写作,虽然在渊源上有继承,但他却并没有拘泥于传统,固步自封,而是有自己的创新目标和美学追求。作为一种特定的文体,唐弢认为“书话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去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在写作中要使书话的形式特点“更鲜明,更突出,更成熟,使特点本身从枯燥、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活泼和多样,而不是要冲淡它,调和它,使它淹没于混沌汗漫之中,落得一个模模糊糊的状态。”(《晦庵书话·序》)有了这样明确的目标追求,唐弢就努力地在实践中进行探索了。他说:“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书话·序》)
那么,什么是书话的散文因素呢?唐弢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晦庵书话·序》)
唐弢在这里的观点很鲜明,书话虽然含有材料的作用,却并不就是材料,书话应是一种独特的关于书的“散文”,书话要有感情,有热度,有艺术,有美感,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既能给人以知识,也要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唐弢对书话文体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去努力写作,探索和追求的。
在书话的写作实践中,唐弢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听取外界的意见,博采众长,修正和完善自己的书话美学观,以使这种新型的文体更臻完善,更加成熟。
例如唐弢早年的书话在《文汇报》副刊《文化街》发表的时候,有一次在开明书店遇见叶圣陶先生,叶圣陶对他说:“古书讲究板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叶圣陶的话点出了唐弢书话重视版本的特点,这是行家之论,自然引起了唐弢强烈的共鸣,使唐弢对书话写作需要版本知识,需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的认识更加坚定。
再如赵景深先生在读了唐弢的书话后对他说:“其实《书话》本身,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赵景深的话对唐弢也很有推动作用,更增强了唐弢将书话当成散文来写的信念。
现在,书话这一文体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欢迎,爱读书话,爱写书话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广泛的群体,每年全国许多出版社出版的书话类书籍也得到了众多爱好者的热捧。在当代书话写作日益发展和繁荣的今天,唐弢对书话文体开创性奠基性的探索和贡献值得读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