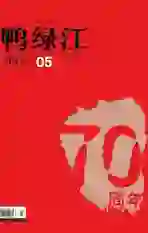桥头那地方
2016-04-29王重旭
王重旭
1
桥头那地方,我小时候就知道。
我老家是通远堡。我家对面有一户孙姓人家,生了六个女儿,一个比一个漂亮。
当时通远堡有驻军,一到星期天,他家总来一些当兵的,帮他家干活,有的还给他家买这买那。后来,听说他家大女儿嫁给了其中一个当兵的。不久,大女儿就随那个当兵的去了桥头,老头逢人就说,女婿提干了,当军官了。
我头一次坐火车去沈阳,便经过桥头。尽管沿途停靠很多站,但是桥头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这站,不仅火车停靠的时间要长一些,而且上下车的人中有很多当兵的,甚至还有让人生畏的军官和围绕他们的警卫。
直到后来上了大学我才知道,桥头虽是小镇,却很了得,威名赫赫的中国第一机械化师的师部就设在那儿,难怪我那位桥头的大学同学总是趾高气扬,人家见过世面,连军区司令都曾从他家门前经过。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本溪,你别说,桥头就更让我肃然起敬了,因为常常碰到好多机关干部都是桥头部队转业的。其实就连沈阳,不信你打听打听,也有好多机关干部是从桥头走出来的呢。这几年我常到沈阳开会,好多文友听说我是本溪的,就格外亲切,告诉我,“当年我在桥头当过兵。”
2
东北这地方,人们见面总喜欢相互打听:“老家哪儿的?”回答大都是:“山东的。”“山东哪的?”“登州府的。”“莱州府的。”“哎呀,老乡老乡。”
东北人大都是从山东过来的,按理说,闯关东那辈人,到现在最晚也差不多一百来年了,但是东北人奇怪就奇怪在这,表面看一个彻头彻尾的东北人,酸菜粉条,白肉血肠,但骨子里,血液里,还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根。
桥头虽然也历史悠久,虽然古籍中也有很多记载,虽然明清时也留下很多遗迹,但只要你打听,桥头人除了富、金、杨几个大姓外,大都是闯关东过来的。现在桥头还有一义冢,前竖一大石碑,名之曰“异乡碑”。那是在1917年由桥头异乡会出资修建的,快一百年了。那时候,闯关东的人并不是来到东北就进了天堂,好多移民因为战乱、饥饿、贫穷、疾病而客死他乡,死后无法魂归故里。桥头能建此碑,可见移民死亡并非个案。
也有幸运的,来到东北的黑土地上,种地的勤恳耕作,做生意的苦心经营,一些人一点一点地就发达起来了。当时桥头有一大户人家,姓刘,叫刘振邦,他的老家就是山东登州府的,清末的时候,父亲跨海来到东北,到他那辈,成为桥头富户。
其实,那年头,闯关东的这些人,从离开家乡那天起,大都不知道自己要到关东什么地方去。所以,从踏上关东土地的那一刻,就漫无目标地向前走啊,走啊。至于落脚何处,全看机缘了。那天,刘振邦的父亲走到这个叫桥头的地方,饥渴难耐,有一大户人家,给了碗饭吃。恰好这家又刚空出一个长工的位置,于是刘家就落脚桥头了。
有人说,“桥头”这名字不像一座古镇,此言不差。但东北就是这样,很多地名就是直来直去,尽管也很有些年头了。
不过,既然叫了桥头,那就总该有座桥吧?对了,这地名就是这么来的。明代的时候,因这里景色优美,细河蜿蜒,山上常有白云缭绕,故名白云寨。后来村寨繁荣,人口陡增,商贾频集,而且还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马市,于是便在村外细河之上修座石桥。东北人直截了当,不像南方人咬文嚼字,于是白云寨便被叫成桥头了。这名字,地理方位,一目了然。
3
我第一次到桥头是2013年。
当时我正陪一位全国著名作家在本溪采访。那天,我接到区文化局胡局长的电话,这位胡局长有些学问,尤其对本溪的历史文化、人文掌故颇有研究。我们是要好的朋友。那天他语气诚恳,对我说:“桥头正在进行全方位小城镇改造,好多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遗址都要拆除,实在可惜。作为区文化局长,责任所在,但人微言轻,无力阻止,你和那位作家来看看,帮着呼吁呼吁吧。”
桥头四面环山,细河蜿蜒,白云缭绕,一条铁路横穿小镇南北。远远望去,小镇安安静静地卧在群山之中那一片开阔的平地上。
胡局长对小镇了如指掌,带着我们仅半天多的时间,就把小镇浏览一遍。小镇有前街后街,还有一条当年日本人住的街叫洋街,尽管已经百年了,日本的那些建筑依然成片矗立着。胡局长每到一处,都细心为我们指点着,这是火车站,这是和田旅社,这是邮局,这是松中洋行,这是大慈洋行,这是日本小学,这片是日本侨民住宅。在铁路另一侧,胡局长还带我们看了日本铁道守备队的营房,队部、宿舍、食堂、浴池、校场等等一应俱全。接着胡局长又带我们看了满铁员工宿舍,他说,这里既为日本人提供住宿,又驻扎一个当时拥有最先进武器的日本机械化大队,这个大队在日本投降前,不知什么原因,就秘密调回日本了。
日本人在桥头足足待有四十余年,他们居住的洋街在当时已经很现代化了,他们修了自来水塔,在细河上还建了一个大游乐场。胡局长笑着说:“这些日本人一点都不见外,他们没把桥头看成是他们的临时住所,倒像自己的家园一样精心经营着。”是啊,你看那些房子,尽管至今已过百年,但依然保存完好,墙的红砖依然坚实光滑,没有半点风化的迹象,岁月的刻刀没能在它的身上留下多少痕迹。现在,这些房子里面住的都是桥头的老百姓,当年能住进这样的房子,也颇不容易呢。
4
这是一段让桥头的老百姓弄不懂的历史,其实何止桥头人,就是很多东北人也不明白,也搞不清楚的历史。关里那地方的日本人是靠枪炮打进去的,而桥头的日本人,不知为什么就随随便便、理直气壮涌进来了,而且来了就没想走,更没有人拦住他们问声为什么。
其实,说清这段历史,还真不容易。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失败,签下《马关条约》,日本占领了朝鲜和辽东半岛。这引起沙俄的不满,它不愿意日本独霸东北,于是联合法、德两国,逼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从此,日俄结怨。
后来,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而沙俄又趁机进入东北,并以“还辽有功”为借口,攫取了在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接着又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清政府说又说不通,赶又赶不走,打又打不过。怎么办?于是想到了日本。endprint
日本在甲午海战获胜后,野心膨胀,它想独霸东北亚,可是要实现野心,就必须铲除俄国这个对手。于是日本拿出惯用的流氓手段,在1904年那年,突袭俄国在大连旅顺口的海军基地。这下惹恼了俄国,马上对日本宣战。
日俄要开战,大清很高兴。于是大清王朝赶紧宣布中立,想利用日俄宿怨,让他们之间打,借助日本的力量,把沙俄赶出中国。于是清政府把辽河以东的广袤地域交给日俄,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所以,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还偷偷地帮助过日本人。
这场旷日持久的日俄战争,其惨烈程度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在桥头一带,日俄就有一场恶战,双方各出动十余万兵力,厮杀开来,炮火连天,血流成河。最后日军占领桥头,俄军溃败。战争结束后,日本还在桥头建了一座“大日本第一忠魂碑”及日本神社,纪念那场战争中战死的军人。
桥头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俄战争如此,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在桥头也有惨烈的争夺战。到此,读者应该知道,为什么抗美援朝过后,解放军的中国第一机械化师驻扎桥头了。
还说那场日俄战争。
为了尽早取得胜利,日本在没有得到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以运输作战物资为借口,擅自铺设了从安东(丹东)至奉天(沈阳)的铁路。后来经过美国调停,这场历经二十个月,打得筋疲力尽的日俄两国坐下来,签订了一个《朴茨茅斯条约》,其中第六条规定:俄国政府把长春以南,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线,以及铁道内所附的一切权利财产等,都转让给日本政府。就是说,没问中国同意不同意,就把东北一分为二,北面归俄国,南面归日本,于是就有了北满和南满之说。
这条日本人修的安奉铁路,由南向北,从桥头通过。
桥头有一座长长的隧道,两面的洞口上,分别有两个日本人的题字,一个叫桂太郎的侯爵,题了“其乐融融”四个汉字,一个叫寺内正毅的子爵,题了“其乐泄泄”四个汉字,后面都署了他们的名字。这两个成语典出《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说的是郑庄公杀了弟弟公叔段后,与母不和,发誓不到黄泉绝不相见,后来悔悟,为不食言,便挖一隧道,在隧道中母子相见。相见时,庄公赋诗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答曰:“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于是母子和好如初。
这个桂太郎何许人也?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他曾任第二任总督,并三度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那位寺内正毅呢?他担任过日本陆军元帅、朝鲜总督和日本首相。这两个人的题词,堂而皇之地刻在桥头的铁路隧道上,一方面可见侵略者肆无忌惮的炫耀,另一方也足以证明日本高层对桥头的重视。
虽然日本人蛮有中文修养,可是,被欺压的中国人,怎么能和这些强盗一起“其乐融融”“其乐泄泄”呢?在桥头,就曾有小学的老师领着学生,登上桥头北山,指着满载木材煤炭的火车,告诉孩子们,火车拉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国的,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由于铁路的修建,原本繁荣的桥头便更加热闹起来。日本宪兵来了,守备队来了,还有商人、铁路员工、家属,还有朝鲜人。他们修建军营、碉堡、官邸、学校、医院、洋行、旅店、酒馆、邮局、员工宿舍,还开办学校、修自来水塔、建水上乐园,甚至还开起了妓院。
从此,桥头不再是一个安静的桥头了。
5
就这样,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到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桥头的日本人已经待了快三十年了。如果算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人在桥头已经经营了四十余年。假设日本人刚来桥头时生的孩子,走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
原本就繁华的桥头,由于日本人的到来,更加热闹起来。人口陡增不说,日本人朝鲜人满街都是,穿和服的日本女人,酒馆里的日本浪人,大街上的日本宪兵,铁道上的日本警备队,日本话、朝鲜话,以及到处涂抹的“仁丹”广告,一时让桥头人蒙头转向,世道真的变了。
不过,桥头那两家日本洋行倒是很让桥头人喜欢,洋行里的商品全是从日本运来的。从烟酒糖茶到日用百货,应有尽有,不但样式新,而且质量好。像洋镐、洋锹、洋火、洋钉这些东西,甚至便所,许多桥头的老年人,现在还这样叫,改不了口。而且有些老住户的家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在日本洋行买的玩具,喷上大漆的木器什么的。洋行的日本人也很会做生意,不但对日本人,就是对中国人也是客客气气的。
这个时期,除日本的洋行,中国人的买卖也十分兴隆,有磨坊,有米店,有药铺,有饭馆,像天佑东、宝星楼、德元堂、福兴东等店铺远近闻名。还有,在细河沿上,有十几家香磨坊,以水为动力,以榆树皮、柞树皮和柏树皮作原料,经过石磨的研磨,制成老百姓上坟祭奠、寺庙拜佛用的香。其中也有日本人开办的香磨坊。
说到生意,就不能不说说桥头的砚台了。
起源于桥头的砚台,被称为辽砚。今天,到本溪旅游的人,莫不想带一方精美的砚台回去。可是,砚台虽然精美,可价格不菲,挑来选去,最便宜的也得五六百元,稍好一点的就得上千元、上万元。本溪人如果出门看朋友,携一方砚台上门,不但送者显得文雅,就是受者也满心欢喜,爱不释手。
这砚台就出自桥头。由于桥头盛产青云石和紫云石,明代时便有人用来制砚,到清代时,由于康熙皇帝钦定为“宫廷御砚”,使得桥头制砚业迅速发展起来。到20世纪30年代初,桥头已有孟家、方家、肖家、杨家、袁家等制砚作坊十余家,而且还有一家日本人开的作坊,叫“丸之砚台铺”。
有了这十多家砚台店铺,桥头可就热闹起来了。由于它是前店后厂,每天从凌晨开始一直到夜深,凿石之声不绝于耳,真是叮叮当当,当当叮叮,此起彼伏,奏乐一般。可惜,解放后,桥头的制砚业一度沉寂下来,直到1982年才逐渐恢复。现在,本溪地区有制砚作坊二十余家,已形成产业,其精美程度足以和端歙洮澄四大名砚相媲美。在全国有影响的制砚大师有紫霞堂的冯军、辽砚厂的章永军以及阿昌等人。2011年,辽砚还和岫玉、阜新的玛瑙一起,被辽宁省政府确定为辽宁 “三宝”。
6endprint
相比之下,桥头日本人的生活很优越,房子宽敞卫生,门前种花种草,穿戴整洁,上学的孩子都有制服。而且日本人还挺注重文化活动,桥头的日本小学有一个大礼堂,日本小学的师生和一些日本社团不时还搞些文艺活动,经常放映一些日本电影。来看的都是日本军人、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但是桥头人来看也是可以的。有时人多了礼堂装不下,就把银幕移到火车站的广场上,这样十里八村的桥头人就都来看了,一到放电影的时候,人山人海,像过节似的。
不过,桥头人也有自己的娱乐,他们组织了秧歌队,镇上的几家大买卖像天佑东、宝星楼等都出资赞助,组成了一个百十来人的秧歌队,这个队擅长舞狮;还有河东戴家堡子秧歌队,这个队擅长跑旱船;还有兴隆村秧歌队,这个队擅长耍龙。
每年的大年初一,吃完饺子,你就能听到外面的锣鼓声,孩子们早就待不住了,撂下筷子就往外跑,秧歌队远远地过来了,敲锣打鼓的,吹着喇叭的,有扮唐僧的,扮孙悟空的,扮猪八戒的,扮沙和尚的,扮妖魔鬼怪的,扮小媳妇的。孩子们最爱看的是那个扮傻柱子的。他们从前街扭到后街,再扭到洋街。日本人也跑出来看,日本的孩子也和中国的孩子一样跟着跑。秧歌队来到店铺前,领头的便说着快板讨赏钱:“秧歌队,来拜年,掌柜的,笑开颜。一笑今年生意红火财运旺,二笑明年好运长久赚大钱。来贺喜,来拜年,掌柜的慈悲多赏钱,给多给少都不嫌,谁叫咱们有情有义又有缘。”
于是掌柜的赶紧走出来,一边拱手一边递上早就准备好的赏钱。
这几个秧歌队从成立那天开始,一扭就是近百年。解放军进驻桥头的那天,桥头的秧歌队扭了一整天。桥头的秧歌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现在,本溪每年举办全市秧歌大赛,桥头的秧歌队都名列前茅。
我曾问桥头的老一辈人:“那时候,你们怕日本鬼子不?”他们说:“怕他们干吗?”
他们说,桥头有洋街,日本人住,有中国街,中国人住。但是日本人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倒也常常在一起玩,也常常打架。有一次,几个日本孩子撩闲,几个中国孩子气不过便追过去,一直追到日本守备队的门口,抓住那几个日本孩子就是一顿拳脚。可门口那几个日本兵却理都不理,还在那儿看热闹。
其实,那些日本兵为什么不来帮助日本孩子?如果你以为日本兵宽容,那就错了。这是日本人的习惯,他们就是让孩子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其实是挺可怕的。
7
到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成立了满洲国,桥头的形势便渐渐紧张起来,日本人对中国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客气了,桥头一带的日本人不断增加,驻军也多了起来。铁路沿线的警戒也严格起来,桥头的老百姓轻易不敢在铁道边行走。日本人还在桥头修了飞机场,有几架教练机,主要是训练日本的飞行员,偶尔也有几架战斗机停在这里。
桥头人本来对这个外来的日本人就没有什么好感,这下就更讨厌他们了,在桥头人的眼里,小鼻子和大鼻子都是一路货色,没一个好东西,尽管小日本一再宣称,东亚共荣,日满协和,王道乐土,但桥头人巴不得日本人早点滚他妈的蛋。
日本人在桥头虽然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可为了装装门面,这镇长还得由中国人来当。他们看中了刘振邦,逼他当了镇长,又派了一个日本人来当副镇长,而大权则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这个刘振邦,就是前面说到的“德元堂”的老板,他的父亲就是清朝末年从山东闯关东来到桥头的。
刘振邦的父亲在山东的时候,既是种地的好手,更识得几味中草药,会几个偏方。来到桥头后,挂起了“德元堂”的字号,因医德好,十里八村渐渐有了名气,日子慢慢地好了起来,五十岁时娶上媳妇,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刘振邦,字汉臣。
刘振邦是独生子,读过私塾,在日本人家里做过“小孩”(伙计),学会了日本话。十七岁那年,桥头成立邮局,因懂日语,便被选中做邮差。后来局长去了沈阳,就推荐刘振邦做了局长。
刘振邦出任“公职”后,在桥头成了头面人物。父亲去世后,刘振邦便子承父业,不仅德元堂药铺的生意兴隆起来,还经营了商店,又办了一个油粮加工厂。因是桥头买卖大户,又诚信经营,被推举为桥头商会会长。刘振邦性格豪爽,为人和善,常常赈济贫困百姓,当地人还为他送去了“急公好义”的金字牌匾。
刘振邦因为从小就在日本人家里做事,也善于和日本人打交道。所以,在他当镇长的那些年,尽可能与日本宪兵和那位叫植村的副镇长周旋,竭力替中国老百姓说话,甚至有时还和植村顶撞,这让日本人很不高兴。
表面看,刘振邦是在给日本人做事,其实,他骨子里却是一个爱国志士,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汉臣汉臣,汉家臣子。他仇恨日本人对中国的占领和掠夺,表面和日本人周旋,暗地里却支持抗联,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家里常有抗联官兵往来。
刘振邦有三个儿子,老大刘维藩,老二刘维坤,老三刘维箴。两个大的儿子都曾赴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身边只剩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刘维箴当时有十三四岁,他清楚地记得抗日英雄苗可秀等人常来他家,有一次还在他家住过一宿,刘维箴还见过他两次。那时苗可秀身穿便衣,带着手枪,中等个儿,不胖,看上去三十多岁,精神头十足。
刘振邦的行为,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其实,刘振邦因为支持抗联,家中常有抗联官兵往来,加之两个儿子在外常年不归,有抗日嫌疑,所以早被于泽普盯上了。于泽普是桥头警察署长,人品不好,欺压老百姓,投靠日本人,刘振邦瞧不起他,常常顶撞他,于是这个于泽普怀恨在心,便在暗中搜集刘振邦反满抗日的言行和儿子的去向。
一次,抗联的两个干部夜宿刘家,一个叫常伯英,一个叫关管羽。结果被于泽普发现。日本宪兵队迅速包围了刘家。虽然两位抗联干部早已闻声遁去,可是刘振邦却被日本宪兵抓走。
刘维箴清楚地记得,1938年4月23日,一帮人闯进桥头镇公所,抓走了父亲,押上九点那趟火车。后来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抓走父亲的是奉天省警务厅搜查班的人。他们把父亲押解到了凤城的赛马。在此之前,他们已抓了四五十人了。家里人不知所措,到处托人求情,可是没用。endprint
刘振邦被捕后,每次都是搜查班的头子井上亲自拷问,要他供出抗联线索,拷打中还一再问及两个大儿子的下落。刘振邦不愧是个汉子,受尽酷刑,宁死不屈。1938年4月25日,日本人将刘振邦装进麻袋,塞上木板,板上钉上铁钉,拧上了铁丝,从山上一直摔到山下,刘振邦被活活摔死,死时还不到五十岁。
一年之后,刘振邦的尸骨才被家人偷偷运回桥头,葬在了刘家坟地里。遗憾的是,因为刘振邦给日本人做过事,日本投降后被视作汉奸,直到四十多年后,本溪市人民政府才为他平了反,正了名,正式授予烈士称号。
8
说到刘振邦,就不能不说说他的大儿子刘维藩了。
刘维藩生于190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曾用名刘砥方,后改名刘仁。刘仁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一表人才。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加入高崇民、阎宝航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不久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刘仁在学习世界语时结识了世界语者、日本作家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两人一见钟情,不久结婚。
1936年的下半年,由于国内抗日运动空前高涨,刘仁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妻子绿川英子也一同来到中国。绿川英子在日本国内的时候,就是一个反战人士,曾因反对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而被奈良特高课列入黑名单。不久又以“具有危险思想的人”“共产党同情者”的罪名被逮捕,关进奈良警察署。
刘仁和绿川英子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目睹了日军的野蛮暴行,她痛恨不已,用手中的笔,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她写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烧弹,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封锁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主持工作,里面大部分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刘仁进第三厅从事资料编辑工作,绿川英子则进国际宣传处对日广播。
作为一个日本人,能公开参加中国抗战,绿川英子心情十分激动。1938年7月2日19时,绿川英子来到播音室,正式对日广播:“现在是中国广播电台对日播音时间,日军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你们可曾想过,这是罪孽,是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
绿川英子那柔和而流畅的女中音,随着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她用纯正的日语向日本国内人民,向正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大声疾呼:“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在为谁卖命?又是在为谁效忠?圣战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绿川英子的广播引起日本军方的愤怒,他们终于查清了那个操着流畅日语对日广播的绿川英子,就是长谷川照子。日本东京报纸《都新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登出了绿川英子的照片,骂她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和赤色败类”。
尽管日本特务在找机会除掉绿川英子,尽管绿川英子的父母受到迫害,但绿川英子的反战决心毫不动摇。有一次,重庆各界举办郭沫若五十岁生日庆典,周恩来当众人的面称赞绿川英子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骂你是‘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郭沫若还当场即兴在一块红绸上为绿川英子题诗一首:
茫茫四野弥黮暗,历历群星丽九天。
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抗战一胜利,刘仁夫妇便在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高崇民的安排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东北解放区佳木斯。正当刘仁和绿川夫妇满怀激情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时候,绿川英子因到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不幸于1947年1月10日逝世,年仅三十五岁。
刘仁与绿川英子感情笃深,恩爱有加,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刘仁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顿足痛哭,不忍离开绿川英子的遗体,“贫贱夫妻百事哀呀!”他边哭边喊道,“我真该死,我不该同意你做这个手术啊!”
自绿川英子去世后,刘仁不吃不喝,终日守着绿川英子的遗体,以泪洗面。由于过度悲伤和悔恨,刘仁的身心受到致命打击,仅仅三个多月,便追随绿川英子而去,年仅三十岁。
刘仁与绿川英子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尤其绿川英子,作为一个日本人,能够在我国的抗日战争中,不仅对日播音,做反战宣传,还写了大量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敦促日本军人觉醒的反战文章。这些文章大都登在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而且,刘仁和绿川英子凄美的爱情故事,更是让人闻之落泪。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和中国合拍了电影《望乡之星》,邓小平题写片名,日本著名影星栗原小卷扮演绿川英子,中国演员高飞扮演刘仁,其中部分镜头在本溪拍摄。
1983年,经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为刘仁和绿川英子重新修建了合冢墓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现在,重庆和武汉保留了两人的故居,重庆历史文化名人馆里有绿川英子塑像,哈尔滨、佳木斯等地的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展有他们的事迹、图片和遗物。
刘仁和绿川英子生有一男一女,男孩刘星,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可惜英年早逝;女儿刘晓兰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现已移民日本,取名长谷川晓子。
这些年,长谷川晓子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工作,她经常回到中国,回到父母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向父母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和女儿的思念。
现在,生活在日本的长谷川晓子常被人问及:“你喜欢中国还是喜欢日本?”还有人问:“你对中国的爱和对日本的爱哪个更深?”真的,对这个问题,她很难回答。因为在长谷川晓子的心中,中国和日本都是她的祖国,她对自己的这两个祖国的爱是没有区别的,她现在来到日本,就像当年她的母亲来到中国一样,当年的绿川英子并没有因为来到中国就不再爱她的日本。作为刘仁和绿川英子的女儿,她的身上流淌着中国和日本两股血脉,她希望这两股血脉能够在她的血管中,和睦地流淌着,而不再让她痛苦,不再让她纠结。
9
我第二次去桥头,还是胡局长陪同,这次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告诉我:“大家的呼吁起作用了,该保留的都保留了下来。这些东西,至少也是日本侵略的罪证啊。”他还说,现在桥头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一个是本溪市钢铁产业园落户桥头,另一个就是桥头的大台沟发现了一个世界最大的单体铁矿,储量巨大,可开采五十年。他说:“过几年你再来桥头,那变化可就大了。”
桥头的前景,让人很高兴。
不过,桥头的这些遗址保留是保留下来了,但是要继续保留下去却是很难,因为作为一个小镇,对这些遗址进行保护和维修,需要大量的资金,若没有投入,这些遗址将会和岁月一起消逝。
刘仁的老房子坐落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已近坍塌,好在还没有被拆除。那天看到刘仁的老房子后,我颇有一点庆幸,因为我还算看到了刘仁出生和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可是,说不定哪天,这座老屋就会从桥头这块土地上消失,就像刘仁和绿川英子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一样,那时我们再想寻找烈士的遗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千年古镇,百年沧桑。桥头人经历得太多了,战乱,和平,快乐;也有痛苦,屈辱,反抗。今天,桥头人最关心的是桥头的发展,最大愿望是日子一天天好起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