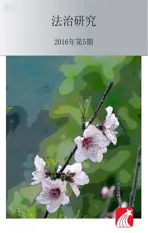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的法律适用评析*
——围绕新《行政诉讼法》第75条展开
2016-04-16黄涧秋
黄涧秋
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的法律适用评析*
——围绕新《行政诉讼法》第75条展开
黄涧秋**
《行政诉讼法》第75条修正了我国行政诉讼上诉判关系的不一致性,确认无效判决的效力和撤销判决并没有区别,法院应当严格地按照其条文含义遵循诉判一致原则。重大和明显违法作为两种司法审查的标准叠加适用: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行政行为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确认无效诉讼受到《行政诉讼法》起诉期限的限制,行政协议也不例外。将来,我国应当确立修正的无起诉期限制度,突破最长期限的约束。在我国行政实体法确立无效行政行为的一般制度之前,确认无效诉讼的功能定位只能限定在拓宽救济途径的视域之内。
确认无效 诉判一致 审查标准 起诉期限
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解释》)第57条第2款初步建立确认无效诉讼制度的雏形以来,各地法院逐步开始司法实践上的探索。在此基础上,2014年修正的《行政诉讼法》第75条正式设立了确认无效诉讼这一新的判决方式,从立法上补充了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种类的不足,成为新法的一大亮点。司法实践及其法律效果是新制度价值的试金石,在新法实施至今不长的一段时期,法院在确认无效诉讼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并进行大胆的尝试,已经涌现出一大批鲜活的案例。本文主要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最新案例为素材,从诉判一致、审查标准和起诉期限等三个方面对法院法律适用的逻辑和倾向进行梳理和归类,并以此观照《行政诉讼法》上确认无效诉讼的规范意义和制度功能。
一、确认无效判决的“诉判一致”原则
“诉判一致”的基本含义是指法院作出的判决种类应当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互对应,而不应当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和司法实践中,诉判一致原则并没有得到严格贯彻。①例如原《行政诉讼法》第54条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维持判决、确认合法或有效判决、情况判决、重作判决等,基本上都没有对应或者完全对应相应的诉讼请求。参见田勇军:《中国行政诉讼之诉判关系及其发展趋势探讨》,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但是,《行政诉讼法》第75条(以下简称第75条)首次对确认无效判决确立了严格的诉判一致原则:法院判决确认无效的前提之一是“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既然《行政诉讼法》仅在此条规定诉判一致原则,依反面解释进行推论,其他判决种类不一定要遵循诉判一致原则。最典型的例子是确认违法判决,当事人如果提出撤销行政行为的诉请,那么法院有权根据情况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第75条将判决类型与诉讼类型相互对应,架起沟通诉讼请求与判决方式的桥梁,在确认无效方面,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已经开启了将判决类型模式转变为诉讼类型模式的路径。在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体系内,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受到最为严格的制度约束。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确认无效诉判一致原则的适用还有一种反向情形:即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无效,如果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判决确认无效的情形,那么只能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不是作出其他判决。因此,原告在确定提起诉讼的类型时,就必须慎重地考虑和预测判决的结果。这种情形的诉判一致原则在《行政诉讼法》上没有特别规定,从第70条关于撤销判决的规定考察,撤销判决的作出并不受到诉判一致原则的约束。
在新法实施以后,各地法院有关确认无效的判决并没有完全遵守诉判一致原则。
(一)原告请求确认违法,法院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
在李欢与迁西县国土局注销宅基地使用证案中,②河北省迁西县人民法院(2014)迁行初字第3号。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被告注销其土地使用证的行为违法。法院认为:被告不具备注销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政主体资格,被告以本机关名义用通知形式注销原告土地使用证,因此该注销行为应属于无效行政行为。法院遂依据第75条的规定,判决确认被告注销行为无效。
综观该案案情,如果法院根据原告诉讼请求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由于此种判决并不涉及被诉行政行为的效力,原告被注销土地使用证的现状没有发生变化,确实不利于其权利保护。这可能正是法院变更判决方式的原因。但是,该判决的合法性值得商榷。第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而法院在判决主文径行变更为确认无效,明显有违第75条关于诉判一致的规定,而且对于这一变更,法院没有说明理由。第二,无效行政行为是需要由行政程序法予以确立的重要制度,我国并没有在立法上建立起统一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③参见叶必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探索》,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75条只是确立了确认无效这一判决方式,我们并不能以此反推其创设了行政程序法上的无效行政行为这一类别。法院将被诉行政行为定性为“无效行政行为”,但没有指明这一定性在行政实体法或者程序法上的依据。第三,法院如果为了充分保护原告在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应当作出撤销被诉注销行为的判决,原告土地使用证的效力因此恢复,即为已足。
(二)原告请求撤销,法院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
在刘晓龙与武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处罚决定案中,④甘肃省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金中行初字第22号。原告请求撤销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由被告的巡警大队作出,法院认为:巡警大队以自己名义对外公开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其执法主体资格欠缺,该行为无效。据此作出确认该处罚决定书无效的判决。该案的判决思路主要是基于被诉行政行为符合第75条“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情形,但是法院没有对为什么不按照原告诉讼请求而作出撤销判决进行说理。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法院强调处罚决定书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并因此在判决主文中不对原告提出判令退还罚没款项的诉讼请求进行回应。事实上,原告已缴纳罚款并被扣分,这一说理以及相关的漏裁明显与案件事实不符,这似乎隐含着确认无效判决对于被告来说,其涵摄的违法性程度低于撤销判决。
法院径行作出确认无效判决的情况在婚姻登记行政案件中尤为突出。这一类案件的事实较为特殊:一方面,行政机关在婚姻登记中已经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另一方面,当事人在申请婚姻登记过程中隐瞒相关事实。易言之,行政机关没有过错和违法性,而过错和违法性往往就在于现在诉请撤销的原告,那么,这种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登记行为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法院感到非常为难,其说理过程也显得捉襟见肘。例如在周连满与承德县民政局婚姻登记案中,⑥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2015)承行初字第00023号。法院认为,婚姻登记机关是在受欺骗的情况下作出的婚姻登记发证行为,“该行政行为形式上虽属合法,但因其有重大、明显的瑕疵”,显然不符合《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有关结婚登记的条件,该行政行为应当被确认无效。在袁辉、曹俊华与泰州市海陵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案中,⑦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5)泰海行初字第00014号。法院采用了相同的审理逻辑,强调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已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但由于两原告采用了欺骗的手段,提供了虚假的材料,导致被告为两原告作出了第二次结婚登记(即被诉登记行为)。有意思的是,虽然该案最终确认被告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无效,但同时确认“两原告采用欺骗手段造成登记行为的无效,应当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本文以为,该两个婚姻登记案件适用确认无效判决与第75条存在抵触: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条件是行政行为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被诉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是确认无效判决的基础。该两个判决均从客观角度强调涉案婚姻登记行为没有效力,虽然都引用第75条作为判决的基本依据,但都没有将案件事实与第75条的适用条件进行对应,难以自圆其说。
(三)原告请求确认无效,法院作出撤销的判决
在杜贤峰与萧县人民政府行政登记案中,⑧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宿中行初字第00079号。原告请求确认萧县政府为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无效。法院认为:一方面,被告具有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职权和法律依据,原告要求确认无效的理由不符合第75条的情形;另一方面,被告的颁证行为属于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遂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类似地,在六间楼八组与商水县人民政府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案中,⑨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周行初字第76号。法院认为:被诉颁证行为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以撤销。原告在诉请中要求确认被诉颁证行为无效,经审查被诉颁证行为不符合第75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不予支持。遂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
这两个判决的共同思路是: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撤销判决的情形,但不符合确认无效判决的情形,因此法院直接改判为撤销。法院有意在撤销判决和确认无效判决之间进行明确的界分,并且隐含着确认无效判决涵摄的违法性程度高于撤销判决,符合《行政诉讼法》设定确认无效判决的立法目的。如前所述,这种改判并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第70条关于撤销判决适用情形的规定,具有合法性的基础。
(四)小结
第75条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我国行政诉讼上诉判关系的不一致性,对于确认无效判决来说,其不仅涉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还进一步触及行政行为的效力,因此法院在适用时应当保持应有的克制和谦抑。⑩参见潘昌峰、孔令媛:《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7期。但是在新法实施以后,各地法院对于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采取了较为积极甚至激进的态度。在当事人没有提起确认无效之诉的时候,法院为了彻底地解决纠纷,罔顾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主动适用第75条而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这类案件中法院进行改判的思路不尽一致,但都明显违反第75条关于“诉判一致”的规定。本文以为,新法生效不久,对于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法院更应当严格地按照其条文含义予以把握,否则会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当事人的合理期待。如果法院认为由于当事人的知识局限未能适时地
⑪ 在江口县闵孝镇峰坝村岩董组不服江口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中,原告在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被诉登记行为无效,法院予以支持。参见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2015)江法行初字第00010号。根据案情提出确认无效的诉请,从而不利于其权利救济,法院也应当做好法律释明,引导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⑪
法院将撤销之诉直接改判为确认无效,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法院认为有的被诉行政行为不能适用撤销判决,因此只能适用确认无效判决。例如在姬晓明与金鸡乡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行政撤销一案中,⑫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15)隆行初字第00006号。法院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及行政原理,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对该无效行为无撤销必要,依法应作确认无效处理。故对原告的请求,本院直接予以纠正。”据此,无效行为既然自始无效,自然就不存在被撤销的问题,没有适用撤销判决的余地。
对此,本文以为:该法院过分强调撤销判决与确认无效判决在适用效果上的区别,这仅仅是学理上的一种论断,而缺乏实定法上的支撑。虽然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即认为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而可撤销行为嗣后无效,并以此界分确认无效判决和撤销判决的效力,但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上,两种判决都是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全面否定,都力求恢复到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行政行为的无效与可撤销之区分没有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⑬参见张旭勇、尹伟琴:《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三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事实上,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区分这两种判决的效力,如果某行政行为被法院判决撤销,其效力自然要追溯至其作出之时,否则就不会产生附带的国家赔偿问题。即使是在确立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制度的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其第118条明确规定:“违法行政行为经撤销后,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有限公定力,我国有学者提出严厉批评:有限公定力理论将立法上都难以客观确定的判断权交给当事人,同时也将错误判断的责任风险给予了当事人,反而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⑭参见黄全:《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之批判》,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6期。相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来说,我国目前缺乏当事人抵抗权制度,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权还是掌握在法院手中。“尽管命令无效,但除非要求法院作出判决,否则没有办法证实其无效性。”⑮[英] 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行政行为在被法院确认无效之前,其持续具有公定力,当然可以成为法院撤销判决的对象。质言之,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律体系内,确认无效和撤销判决的效力难分伯仲。⑯在新法实施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确认无效典型案例“俞飞诉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案”中,该案判决确认违法建筑行政处罚决定无效。在该案一审审理期间,涉案违法建设被行政机关强行拆除,因此,法院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已无撤销之必要,但如果确认违法,事实上又认可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最终选择作出确认无效判决。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170页。该案的案件事实表明:虽然法院最终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但即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仍然无法阻止被诉行政行为的执行力。该案的确认无效判决仍然是一种事后的否定性评价,在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上,较之于撤销、确认违法判决并无任何优势可言。当事人即使在撤销之诉中主张了属于构成被诉行政行为无效原因的违法情形,法院只要将其作为撤销诉讼进行审理也就足够了,⑰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并没有必要将其改为确认无效之诉。
行政诉讼的诉判一致建立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一致的基础上,如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一致,就会导致诉判关系的不一致。⑱参见邓刚宏:《我国行政诉讼诉判关系的新认识》,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5期。行政行为不合法不一定导致其丧失有效性,例如在情况判决的情形。上述两个婚姻登记案件中法院进行直接改判,则体现了另一种不一致,即行政行为合法,但又无效。法院在说理部分一方面强调行政行为合法,另一方面又将行政行为归结为无效,在行政行为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出现了乖离,但是这不能成为法院适用第75条作出确认无效判决的法定事由。第75条的核心适用条件是“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其判断标准按照通说,是该违法情形已重大明显到任何有理智的人均能够判断的程度。而这两个案件中,正是由于当事人在申请婚姻登记隐瞒了事实,而行政机关又难以发现客观事实,导致了错误的登记,此种情形,行政机关的明显违法从何而来?反之,结合该两个案件的事实,法院完全可以适用撤销判决中“主要证据不足”的法定事由,遵循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撤销登记行为的判决,而不是越殂代疱。
二、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
行政行为无效不是行政违法行为的一般后果,而是它的一种极端情形。⑲参见陈玉领:《确认无效判决司法适用论》,载《福建法学》2014年第2期。从逻辑上看,确认无效判决与无效行政行为相互对应,无效行政行为是行政实体法上的概念,而确认无效判决属于行政救济法的范畴。我国仅在《行政处罚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中零星地提到“无效”的行政行为,但是并未在行政实体法中构建出普适性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因此,在我国现行法律上,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事实上取代了无效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第75条将审查标准确定为“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按照文义解释,“重大且明显违法”属于审查标准的内涵,而“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两者系对其外延的例示性列举。⑳该两种情形的规定可能肇源于《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61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执法行为无效:(1)不具有法定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2)没有法定依据的。”易言之,如果行政行为构成该两种情形,原则上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
无效行政行为属于违法行政行为的一种,其法律特征同时也是区分其与可撤销行政行为的分水岭。日本在“二战”后就无效行政行为的特征提出“重大明白说”和“明白性补偿说”两种判断标准,前者成为通说。“重大明白说”不仅要求瑕疵的重大性,而且要求存在瑕疵外观上的形式明白。而“明白性补偿说”则认为明白性相对于瑕疵的重大性,仅仅是具有补充性的加重要件之一。㉑参见胡建淼、江利红:《行政法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明显性要件的基础在于信赖保护原则,即:既然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在外观上已经一目了然,法院判决确认其无效也不至于损害相对人和公众对它的信赖。㉒参见[日]南博方:《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类似地,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采纳“明显且重大瑕疵”标准,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1条规定:行政处分具有“重大明显之瑕疵者”为无效,并就具体情形作出列举。总体来看,重大且明显违法已经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审查标准。可以说,我国第75条正是沿袭了上述立法例。据此,对于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而言,“重大”和“明显”违法两者叠加适用。其中,前者侧重在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例如主体、程序、职权等方面;后者侧重于行政行为的外在判断主体,即任何人在具有一般知识的情况下即可判断其违法性,以此质疑其公定力。第75条有意从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确立确认无效判决较为严格的审查标准,以期与撤销、确认违法等判决各司其职。
(一)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我国法律上的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行政诉讼法》第2条虽然新增规章授权组织,但只是用于解决行政诉讼被告问题,而不是承认其可以成为行政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行政主体问题被判决确认无效的,包括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
1. 行政行为实施主体本身不是行政主体。在新法实施前的封氏农业生态科技公司与苏州市相城区农业局注销《动物防疫合格证》案中,㉓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2)相行初字第0005号。法院以被诉行政行为实施主体相城区兽医卫生监督所系未经编制部门批准的机构为由作出确认无效判决。在前述刘晓龙案中,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由武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巡警大队作出,而武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三定方案”中并没有巡警大队这一机构,被告也未能提供巡警大队的行政主体执法资格证,因此法院认定巡警大队“以自己名义对外公开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其执法主体资格欠缺”,确认其作出处罚决定无效。从各地实践看,巡警大队普遍可以成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而行使行政处罚权,但该案中的巡警大队和相城区兽医卫生监督所相同,连机构编制上都不存在其合法“名分”,更遑论其行政主体资格。
2. 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在查得保与南漳县城乡建设局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案中,㉔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2015)鄂南漳行初字第00009号。法院认定“南漳县城乡建设局没有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不具有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的行政主体资格”,因此判决确认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在张明希等与田氏镇人民政府确认集体土地使用证无效一案中,㉕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2015)滑行初字第53号。法院认定被告不具有颁发土地证书的相应职权,其“依法不具有相应的行政主体资格,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属重大且明显违法”。该两个案件的被告都是行政机关,但是作出的行政行为都超出其法定职权,因此被确认无效。
(二)没有依据
第75条中“没有依据”究竟是指没有事实依据还是没有法律依据,表意不明确。各地法院在适用这种情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时,对“没有依据”的理解出现五花八门、含糊不清的情况。
在康某某与皋兰县西岔镇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中,㉖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5)城行初字第12号。法院认定:“综上,被告西岔镇政府在征收房屋权属不清的情形下,即与第三人赵某某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证据不足,无事实依据。” 在河南隆源食品有限公司与确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确认案中,㉗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2015)泌行初字第00055号。法院认定:“被告确山县工商局依据虚假材料核准公司变更登记是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系该变更登记行为没有依据,属重大明显违法。”在这两个判决中,法院将“没有依据”理解为没有事实依据(根据)。
在李桂林与天津市北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案中,㉘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5)辰行初字第0035号。法院认定:“被告在没有确认原告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是否存续的情况下即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在李家祥与新津县花桥镇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协议案中,㉙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2015)蒲江行初字第22号。值得对比的是,在前述六间楼案中,原告提出确认无效之诉,法院也认定被告“视为被诉颁证行为没有证据、依据”,但最终认为此种情形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因此作出撤销判决。法院认定:“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也没有提供能与原告签订协议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故视被告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没有相应依据。”法院最终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确定被诉行政行为“没有依据,属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由于行政诉讼举证规则的作用,这种情形属于被诉行政行为全然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比较容易认定。
(三)小结
“重大且明显违法”审查标准说明:《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违法行为的框架内确定无效行政行为判断标准,法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不能超出这一红线的范围。在这一点上,第75条与《执行解释》第57条存在显著区别:后者将法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确定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实际上没有确立判断标准。这一多少带有“同语反复”之嫌的标准隐含着转致的功能,即诉讼法上的确认无效以行政实体法(特别法)的规定为依托,《行政处罚法》第3条“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的规定即为其典型适例。在第75条在行政诉讼制度上确立了统一的司法审查标准以后,法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不应当转致适用行政实体法(特别法)上的标准,而应当以“重大且明显违法”为最终判断依据。㉚在上述周连满婚姻登记案中,法院确认婚姻登记行为无效的主要依据是《婚姻法》第12条“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的规定。但是,该条调整的是婚姻民事关系无效问题,而《婚姻法》第10条关于婚姻无效的四种情形也并未指向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婚姻登记这种典型的民行交叉案件中,法院能否以民事关系无效作为行政行为效力的判断基准?本文的初步观点是否定的。
各地法院在第75条“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审查标准的适用中出现两种不同的口径,反映了法院在区分确认无效判决和撤销判决适用上的困惑。从《行政诉讼法》各判决方式适用条件的体系解释来看,第75条指的是完全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情形,而区别于实施主体有行政主体资格但无相应职权的情形。㉛参见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理解适用与实务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页。对于实施主体系行政主体,但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超越了其法定职权的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4项“超越职权”的规定,法院应当判决撤销。如果此种情形也属于确认无效的审查范围的话,那么,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范围将与撤销判决无法界分,前者也将失去其存在的独立意义。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1条将“缺乏事务管理权限”列为行政行为无效的事由之一,对此,台湾学者吴庚认为:该项事由的适用应当限缩于重大明显的情事,例如违背权力分立等宪法层次上的权限划分,或者教育部门核发建筑执照等明显超越权限的事例。㉜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其基本顺序是首先确定行政行为实施主体有没有行政主体资格。按照常理推断,如果被诉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连最基本的行政主体资格都不具备,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足以构成重大而明显违法情形,因此应当被确认无效。
上述刘晓龙和封氏公司两案的情形类似于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1条所列举的无效行政行为情形之(一)“:不能由书面处分得知处分机关者”,在台湾地区“行政法院”1992年判字第1259号判决中,工务局作出的行政处分通知仅仅盖有其内部单位建筑管理处的印信,被认定为“已欠缺形式合法要件,为违法之行政处分应属无效”。㉝参见许宗力:《行政处分》,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709页。我国的行政机构和其他公共事务组织体系较为复杂,有的纯属于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例如政府部门的科室,相对人比较容易判断其法律地位;而有的事业单位是否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相对人从其名称上较难确定。㉞例如上述刘晓龙和封氏农业生态科技公司两案中,实施主体均在执法文书上盖有自己的公章,刘晓龙之前因同一事由受到过凉州分局交警大队的处罚,故其在起诉时未对巡警大队的主体资格提出质疑,而相城区兽医卫生监督所的主体资格问题系机构职能划转而引起,前后过程较为复杂。在封氏公司案中,原告起诉其《动物防疫合格证》被相城区兽医卫生监督所注销,而先前的《合格证》上就是加盖了该所的印章,但被告相城区农业局在答辩中根本就不认可该机构的存在,这种主体资格问题对于原告来说几乎成了“无头公案”。因此,就行政主体资格而言,如果一概以“任何有理智的人均能够判断的程度”来判断是否构成明显违法,对于相对人来说确有勉为其难之虞。即使在无效行政行为理论较为成熟的德国,瑕疵明显与否,以一般理性、谨慎市民的合理观察视角来观察,仍有主观、抽象和不确定之嫌。㉟同注㉝,第709页。由此看来,第75条中“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审查标准应当属于对“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一种推定,而仅仅是实施主体超越职权,在一般情况下难以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
关于第75条中“没有依据”的适用,有的法院理解为没有事实依据,有的认定为没有法律依据。本文以为,参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61条“没有法定依据”的表述,并结合确认无效判决的独立性,“没有依据”应当理解为行政行为没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依据。“依据”一词通常对应于规范性法律文件,而关于事实问题,我们通常表述为“根据”。㊱例如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将“明显缺乏事实根据”与“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相并称。没有事实根据是指没有满足法律所确定的事实要件,此种情形,应当归结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第70条撤销判决中“主要证据不足”的事由。另外,上述李桂林案中法院所称“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审查标准,在文字表述上明显属于第70条撤销判决的法定情形。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指适用了不应当适用的法律,或者没有适用应当适用的法律,与“没有法律依据”不能等量齐观。被告如果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对法律理解的偏差;而如果没有法律依据,那说明被告根本就无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其违法的重大和明显程度高于前者,因此应当受到判决确认无效的否定性评价。
因此,第75条“没有依据”应当指全然没有依据,法院在审查中主要根据两种情形确定:一是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上没有引用任何法律依据;二是被告在应诉答辩过程中没有提供任何规范性法律文件。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中确定了原告在确认无效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但是,日本学者认为,原告的举证责任限于证明确认无效之诉不同于撤销之诉的例外情形(即重大且明显的程度),而行政行为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仍然在被告,包括被告已尽了调查义务。㊲同注⑲,第152页。这样,在庭审过程中,原告需要出示没有载明任何法律依据的行政行为文书,而被告应当举证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并对为什么事先没有载明法律依据进行说明,以避免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如果被告像上述案例一样没有作出任何举证,法院即可认定其“没有依据”。
三、确认无效之诉的起诉期限
起诉期限也是确认无效诉讼的一个特殊问题。自从《执行解释》第57条初步构建确认无效诉讼制度以来,学界和实务界关于确认无效诉讼是否适用起诉期限的限制一直争论不休。比较而言,认为不受起诉期限限制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不受限制论”以无效行政行为的自始、当然无效性为依托,进而推断无效行政行为从作出时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作出无效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得随时宣告其无效,行政相对人也可以随时请求行政机关和法院确认其无效。㊳参见金伟峰:《论建立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在立法上,《行政诉讼法》虽然正式确立了确认无效之诉,但并没有在起诉期限上为其作出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值得关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主编的新法释义书籍中秉持“针对无效行政行为的起诉,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而且也不受最长保护期限的限制”的倾向性态度。㊴同注㉛,第344页。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新法实施后各地法院在确认无效诉讼中排除起诉期限之适用,似乎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主流。
(一)确认无效之诉不受起诉期限限制
在孙晓惠与镇平县民政局颁发结婚证行为无效一案中,㊵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15)淅行初字第90号。原告请求确认被告于2000年12月20日为其丈夫和第三人办理的婚姻登记行为无效。该起诉如果适用《行政诉讼法》第46条中的5年最长期限,那就超出起诉期限。对此,法院声称:“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且不具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任何一个自始无效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通过期限的限制而获得一种确定力,本案中作为无效的行政确认行为之诉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期限。”法院的这一段说理几乎完全沿用了理论上关于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的基本论断,堪称涉及确认无效诉讼不受起诉期限限制的判决书的示范文本。其他法院在类似的案件中也采用了相同的说理。在申三军与隆回县民政局婚姻登记案中,法院更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上述释义书籍中关于无效行政行为不受起诉期限限制的表述。㊶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2015)隆行初字第27号。
这种主流模式的判决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排除起诉期限的适用上,并没有援引《行政诉讼法》的任何法律条文,而是以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的理论作为其法律适用的大前提,以被诉行政行为属于无效行政行为为小前提,继而径行得出不受起诉期限限制的结论。这种法治现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尤其值得关注和反思。
(二)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之诉不受起诉期限限制
行政协议在新法中被定性为行政行为的一种,但行政协议案件起诉期限的法律适用具有特殊性。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12条规定了行政协议案件起诉期限的两种制度:1. 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提起诉讼,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2. 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据此,行政协议的第一种争议具有明显的合同性特征,因而准用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但该种争议系对有效的行政协议的履行之诉,并不能涵盖对行政协议本身提起确认无效诉讼。《适用解释》第15条又规定:原告请求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那么,该条有没有确立确认行政协议无效起诉期限的特殊规则?
在柑洲坑村民小组与海城镇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合同纠纷一案中,㊷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2014)汕海法行初字第3号。原告以《征地协议书》未经全体村民同意为由请求确认其无效。在本案的起诉期限上,法院以行政协议案件的合同性为基点,认为“当事人请求确认行政合同无效是否适用起诉期限制度,在行政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和不违反行政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合同相关原则和法律法规予以确定……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请求确认行政合同无效,不应受起诉期限的限制。”据此,在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之诉上,该法院没有依据上述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的理论,而是“转致”于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则。该案判决书在有关起诉期限的说理部分没有引用《适用解释》。㊸该判决书虽然在最后援引《适用解释》第15条第2款,但是其援引的目的,从其上下文判断应当是指向其判决主文中的第2项,即判令原告返还被告征地款。
《适用解释》第15条是关于行政协议案件判决方式的规定,旨在针对行政协议这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参照合同法等法律增设恢复原状等特殊的行政案件判决方式,以补充第75条之不足。㊹参见江必新、邵长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辅导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易言之,第15条不涉及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起诉期限。《适用解释》第12条关于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也不适用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诉讼,这也正是该案没有援引第12条的原因。由此可见,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之诉的起诉期限在《行政诉讼法》上并不“享有”任何特殊政策。该案强调“可以根据合同相关原则和法律法规予以确定”起诉期限,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上没有明确的依据,其合法性存疑。
在民事诉讼方面,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依据是诉讼时效制度只适用于请求权,而不适用形成权。但是这一类型化原理并不能套用于行政诉讼中。在有关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另一个案件中,㊺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2015)蒲江行初字第22号。法院以“原告请求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属于形成之诉,不需另一方的同意或给付后即可实现”为由,主张“不受起诉期限的约束”。姑且不论我国行政诉讼法律有没有明确行政诉讼类型化的问题,确认无效判决应当属于确认之诉,而所谓的形成之诉最典型的就是撤销判决,其受起诉期限约束,自无疑问。可见,在确认行政协议无效判决的法律适用上,由于行政协议的特殊性,法院往往容易不恰当地受到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干扰。
(三)确认无效之诉受起诉期限约束
此类案件较为少见。在前述张明希案中,法院认为:“自原告知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时间2015 年9月1日至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2015年9 月22日),明显不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的起诉期限。”因此,对于被告提出超出法定起诉期限的抗辩不予支持。在另一个作出确认行政规划行为无效的判决中,法院也认定:“该争议涉及不动产,未超过20年诉讼期限。”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河县人民法院(2015)青行初字第1号。这些判决书都没有排除起诉期限的适用,但是由于案件事实都在法定期限内,其判决结果和排除适用实际上并无二致,很有可能是法院在法律适用上采用稳妥的路径。因此,我们很难推断法院在此是不是坚持起诉期限的适用,其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并不显著。
(四)小结
从以上司法实践可以看出,在新法实施以后,各地法院在起诉期限的适用上出现了超越实定法的现象。如果说在《执行解释》对确认无效诉讼制度初创时期,司法机关关于这一问题的导向出现摇摆不定,尚可理解。但是,既然《行政诉讼法》已经正式确立了确认无效诉讼制度,同时并没有将其排除在第46条起诉期限的一般规则之外,也没有为其设定任何例外情形,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逻辑,确认无效诉讼理所应当被涵摄在起诉期限制度之内。本文以为,无论从保护当事人诉权,还是从维护行政行为公定力的角度,起诉期限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其法律适用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定主义。如果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无权排除《行政诉讼法》起诉期限的适用。上述案件中某法院提及:“在行政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和不违反行政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合同相关原则和法律法规予以确定”,在本文看来,这一逻辑已经从根本上违反了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恰恰相反,《行政诉讼法》的起诉期限制度适用于所有的判决种类。无效行政行为究竟是否无限期可诉,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在学理上讨论。但是,既然现行法律对此问题已设明文规定,法院再纯粹以学理上的某种论断去裁剪法律适用,就显得削足适履,本末倒置了。
《行政诉讼法》没有纳入确认无效诉讼的无起诉期限制度,主要是考虑这种诉讼和判决在行政诉讼法律上是一种新制度,相应的起诉期限问题还要留待今后的司法实践积累经验。㊼参见童卫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释义与案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那么,如果今后我国继续修正行政诉讼法,究竟是否应当确立无起诉期限制度?我国学者在理论上提出无效行政行为不受起诉期限限制的观点,主要源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的立法和学说。由本文前面两节的分析可见,确认无效诉讼在判决后果上与撤销判决并无本质的区别。从确认无效诉讼类型化和独立性的角度看,该诉讼应当在起诉期限上有别于撤销之诉等其他诉讼,否则其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㊽有学者认为确认无效诉讼的特别程序应当包括三个方面:1.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2. 以行政确认为前置条件;3. 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同注㊳,第146页。本文以为,第二个方面的实现需要同时在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复议法上进行突破;第三个方面是对原告施加诉讼程序上的不利益,在确认无效判决的后果本身对于原告没有特别优惠的情况下,原告负有举证责任的制度构建最终只会对原告在选择诉讼请求上产生负面激励,从而消解确认无效判决的制度功能。相比较而言,无起诉期限制度可能是目前最为现实可行的“特殊政策”。例如在日本,通说认为确认无效诉讼的本质就是“乘坐定期公共汽车”而晚点的撤销诉讼。在我国确立确认无效诉讼的初始阶段,这种判决方式的独特价值就在于拓宽当事人的救济途径和降低起诉门槛。甚至有学者认为:在为其规定特别的起诉期限之前,法律上增设这种判决,没有任何实质意义。㊾参见张旭勇:《权利保护的法治限度——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的反思》,载《法学》2010年第9期。如果行政诉讼法把它在起诉期限上的特性给抽掉,那么确认无效诉讼的整个规则体系也将土崩瓦解。鉴此,对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目前的起诉期限体系,在立法完善上可以考虑将第46条第2款中5年或者20年的最长期限予以突破,也即确认无效诉讼不受最长期限的限制。㊿对照上述若干涉及到重复婚姻登记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在时过5年之后才突然发现自己或者其配偶“被结婚”了,而法律又不允许其提起确认无效之诉,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但是在另一方面,绝对的无起诉期限制度会严重损害法的安定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我国台湾地区法律没有为确认诉讼设定起诉期限的明文规定,因此属于无起诉期限制度,但基于该诉讼类型的后备性,有学者认为,确认无效之诉仍然必须在适当期间内提起。(51)参见蔡志方:《行政救济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37~338页。德国学者胡芬也认为:虽然确认无效之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期限,但是,如果原告耽误了进行法律上澄清的可能性,就可能缺少法律保护的必要。(52)参见[ 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按照起诉期限的法理,法律不应当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当事人,如果当事人已经知道有无效行政行为的存在,他应当在合理期限提起诉讼。因此,在原则上建立无起诉期限制度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正,即《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1款“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的起诉期限仍然适用于确认无效之诉。确认无效诉讼经由这种修正的无起诉期限制度的配套,既有利于行政诉讼发挥定纷止争,及时解决行政争议的功能,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我们可以设想:由于确认无效判决和撤销判决在事由的界分上存在模糊性,在绝对的无起诉期限项下,如果当事人因“过于自信”而在超出一般起诉期限之后提出确认无效之诉,但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仅仅符合构成撤销判决的事由,那么无论按照确认无效还是按照撤销之诉来审理,当事人均无获得胜诉的可能。
四、结语
新《行政诉讼法》的施行,开启了行政审判的新时代。(53)参见江必新:《开启行政审判新时代》,载《光明日报》2015年5月1日。作为一项理论先行的行政诉讼制度,确认无效诉讼已经正式走上司法实践的前台。理论是灰色的,如火如荼的审判活动激活了确认无效诉讼的制度意义。第75条的法律条文非常简短,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各地法院在第75条的法律适用上呈现出五花八门、南辕北辙的乱象,我们在呼唤制度创新的同时,不免产生一种隐忧。从《执行解释》到新《行政诉讼法》的发展脉络中,确认无效诉讼制度已经初步实现立法的“明定主义”,从而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规范化乃至法的安定性,但司法案例中折射出来的法律适用的任意性,反而会扼杀确认无效诉讼独特的制度功能于襁褓之中。在整个行政判决谱系中,确认无效诉讼制度推动了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同时增强了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复杂程度,因此,新制度实施伊始,法院尤其要以审慎、精密的专业态度去把握其法律适用,并注意廓清其与撤销、确认违法等判决类型的分工和衔接。纵观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发展进程,行政救济法总是领跑在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前面,确认无效诉讼制度被附加了很多超出行政救济法范畴的功能。但是,在我国当下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中,确认无效诉讼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并不十分彰显,其宣示意义大于实际适用效果。在我国行政实体法确立无效行政行为的一般制度之前,确认无效诉讼的功能定位只能限定在拓宽救济途径的视域之内。
*本文受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资助。
**作者简介:黄涧秋,苏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