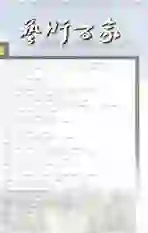佛学认知下的音乐表演理论探究
2015-07-07郏而慷
摘要:将佛学哲理应用于音乐表演实践的规律性研究,认为音乐作品与世间所有事物一样都是缘起有而“空无自性”,也即“法无我”,因而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诠释。人本身也不存在不发生变化生灭的实体,不存在独立自生的永恒不变的“我”,也即“人无我”。由此提出,音乐表演实践“直指人心”、“随心而为”的观点。基于音乐作品的“空无自性”,对以往音乐表演理论的相关研究冠以“忠实性”的概念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音乐艺术;佛学;音乐表演;空无自性;随心而为;美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
佛学认为,“有”是缘起有,世间一切“有”之现象尽皆众缘所生,都是由众多条件和合而成,是由这些条件决定它们的存在。并不是无缘而生、原本就有、自己成、自己规定自己,并具有实在、恒常之意,也即佛学所说的“自性”。因而,缘起“有”之本质为无自性,“有”不是原本如此,亦非实在、恒常的“有”。佛陀在《金刚经》中用一偈颂来说明对“有”之本质的透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1](p.74)
通常认为“有”的对立面是“空”,“有”是存在(者),空即不存在,既然“有”,必定不是“空”;既然“空”,必定不是“有”。然佛学所说之“空”并非断灭之“空”,与“有”并非截然对立的二元关系。因为是缘起“有”,故“有”之当下,就是自性“空”。《心经》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2](p.89),便是说明所谓“空”,不必在“有”之外,也非一无所“有”之断见,而是“有”“空”不二的辩证关系。《中论·观四谛品》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3](p.21)亦复如是。所谓“空”,实际上是指缘起“有”并不具有实在、恒常之意的意思。
一、音乐作品之“空无自性”
音乐作品当然在一切法(指世间事物)之中,由作曲家、作曲家之思想、时代背景、作曲技法等等因缘和合而成。乐谱只是具体音乐作品的略图,音乐作品只有在演奏时才真正成为音乐作品,当然,不是唯一的形态,也即佛学所说之“色身”。要使之成为音响,演奏者对于同样是缘起“有”的音乐音响,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问题也随之而来。在音乐表演实践中,一个毋庸质疑的客观现象是,不同演奏者对于同一音乐作品确实演奏出了不同音响,并不存在从外在音响形态到内在蕴涵意义完全相同的现象。同一演奏者多次演奏同一音乐作品亦复如是。既如此,是否意味着演奏者对音乐作品可不做任何研究分析而随意演奏呢?佛学认为缘起性空,但并不否定缘起假相,因此,对于问题的解决,还得着眼于对“有”的分析。
乐谱是音乐作品在生成音响之前的物质载体,即如佛学所说的文字般若,是对佛法在文字层面的权且设施,而并非实相般若本身。因此,对于音乐作品而言,乐谱只是音符般若,而非音乐作品本身。演奏者当然可以分析乐谱中的音乐语言而获得音乐作品内涵意义的一个大概框架。但由于音乐语言的多义性与不确定性,即便是放入大小语境中去分析研究,由于不同演奏者个体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有所差异及境界的不同,对具体音乐作品仍然无法获得唯一正确的诠释,而只存在有差异的诠释。如此,具体音乐作品的“真如实相”(唯一、正确的诠释)就如《金刚经》云“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1](p.43),何故?佛学认为,三十二相只是外在的虚妄之相,不可执著;反之,则不能认识如来的法身(指真实面目)。现象学通过在不同现象之间寻求贯穿一切不同现象之间的同一原因这一“本质还原”的方法,似乎“惟恍惟惚”[4](p.53)地看到了音乐作品的法身,可是由于人类语言的局限性却不能说,一旦表述就又是一个现象,法身即刻隐去。因为法身是无相的,就如人们无论如何也拿不出纯粹的“红”来,也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音乐作品的“真如实相”竟是如此的若隐若现,晚期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让其存在在去除隐藏之际已然保持遮蔽了,并且向隐藏有所动作了。”[5](p.9)海氏的意思是说,“存在将自身去除隐藏而开显出来,在存在的这样的敞开当中却又同时隐蔽了自身。”[5](p.8)也就是说显的当下有所隐,隐的当下有所显,《在通往语言之路上》中说:“那被言说的以多种方式源于那尚未言说的,它是一还没被言说的,是那不被言说的,亦即在这种意义上,它不给言说。”[5](p.17)海德格尔用不同于佛学语言的话语阐明了同样一个观点:包含音乐作品在内的一切存在①,即佛学所说的真如实相是“非空非有”的。
如此,音乐作品的“真如实相”无法以“就是这个”而“不是别的什么形态”来显现,也即“空无自性”。但这并非意味着演奏者就可随意而为,依然要研究分析“有”并获得一个蕴涵着法身的“色身”,也就是说,不可说的音乐作品之“真如实相”可以蕴涵在演奏者对作品的理解之中,也即海德格尔认为的,“在存在的这样的敞开当中却又同时隐蔽了自身”。它是“空”,是破除一切名相执著所呈现的真实,也即在不同现象之间寻求贯穿一切不同现象之间的同一原因。不同演奏者对同一作品的演奏音响都属“幻有”,是依当时因缘关系而暂时存在的现象,是在“空”的基础上因缘而生。既然演奏者面对的是“空无自性”的音乐作品,就没有实在、恒常之意义内容,也就是说具体音乐作品的唯一正确诠释对于演奏者来说根本就是了不可得。因而,有演奏者苦苦寻觅而不得的音乐作品之终极本体——“原作”,根本就不可以实相显现。它根本就是“一无所住”的“无相亦无念”,它是非个体化的无主体性的整体存在,而一切个体存在却要归之于它。同时,它又不时“惟恍惟惚”地显现于存在的敞开当中,也即演奏者对作品每一次心心相印的演奏。如此,“原作”就呈现为佛学所谓“有空不二”的状态。老子把不可眼观、不可触摸、不可言说的道表述为“无”,但又“常无欲以观其妙”,与佛学有相通之理。音乐作品之“真如实相”可以存在于无数个“妙有”之中——“空”即是“色”,无数个“妙有”也因它而起——“色”即是“空”,而其本身却是“无”、是“空”。如是,音乐作品的演奏音响便是“无中生有”、“藉空而显”。
二、音乐音响之“直指人心”
音乐作品之“真如实相”不可以形态显现,但音乐音响却又因它而起,并存在于无数个个体性演奏音响中。如此看来,经由分析音乐语言并结合于大小语境的研究,人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文字性表述的结果。只是这个结果因为语言文字的局限性而并无确定性,因而音乐作品之“真如实相”“在存在的这样的敞开当中却又同时隐蔽了自身”。如此,我们似乎无法进行理性的终极追问,也无法回答终极追问。可是在实践中,人们却总是在某个时期内一致承认并推崇大师们对具体音乐作品的演奏音响版本。这一现象又说明,对于具体音乐作品的演奏在人们心中还是有相对标准的,只是无法准确用语言文字表述,否则又生障碍。
佛学讲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释迦说法四十九年,却称“未说一字”,《金刚经》亦云:“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1](p.65)又如禅宗公案之“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这都表明对于佛法真谛而言,文字般若只是筏喻②,真正开悟还需“以心传心”。在音乐表演实践中,语言文字同样无法使演奏者真正领会作品要表现的精神性或情绪性的东西,语言表述最多也只是起到引导的作用。例如在教学实践中,当要求学生把某段音乐演奏得如行云流水般时,教师最多给予技术上的指导与“流动”二字的引导,但这种举措并非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奏效。有所悟的,音乐自然使人心动,那些音乐“根器”较弱的,即便技术很精湛,所演奏出的音乐仍然无法感人。禅宗二祖慧可“跪雪断臂”求师为其安心,祖师达摩一句“与汝安心竟”使慧可“立地成佛”;六祖惠能因听闻《金刚经》中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经文而顿悟成道。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学佛者成佛得道?悟了众生是佛,不悟佛是众生,佛与众生之间仅一悟之隔。音乐能否使人怦然心动也在于演奏者对音乐是否有所悟。悟了,作品之真如实相在音响中顿显耀眼的灵光;不悟,则是音高节奏的组合而无其他。
《金刚经》云:“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1](p.29)这段佛陀与须菩提的对话是要说明,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③的佛法,佛法也不一定就在佛经上,也不可执著于佛陀的说法,能表述出来的都是第二性的而不是其本身,就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一个固定的可说的法,但可说的也不能否定其对佛法开悟的引导作用。并且不同思想层次、不同修养的人对佛法的理解也是有所差别的。就如禅宗五祖为传衣钵命诸门人作偈,上座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惠能则作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因此偈获五祖传衣钵而成禅宗六祖。
音乐同样如此,执著于文字诠释反而落入障碍,某段音乐一说是欢快的,一说是跳跃的,一说是热情的等等,让你不知所措,真正领悟音乐背后的精神性与情绪性并在音响中表现出来后,上述诠释在不同欣赏者的表述中再次出现,真是无有定法。因而,佛陀说:“佛说般若波罗密,即非般若波罗密,是名般若波罗密”[1](p.43),意思是当佛说法时,只是假借语言而已,真正的佛法并不是这些语言。所以当说某段音乐是欢快,即非欢快,是名欢快,跳跃、热情等亦复如是。在音乐表演实践中也不可执著于大师的音响,一旦去模仿,灵光瞬间暗淡,且由于技术、技巧等方面差距的原因反而落个“东施效颦”的效果。音乐作品的“真如实相”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形态,它可以似如来的三十二相,也可以是六十四相,甚或更多。不同个体演奏者对音乐作品的“真如实相”即使有所悟,所表现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同一个形态,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不同演奏者具有不同的思想境界与音乐修养。不同之心,所悟者亦有层次上的不同,就如神秀与惠能。因而当其外化于音响时,不同演奏者对于同一音乐作品的演奏就出现了不同音响。这种不同可以是层次上的不同,譬如大师与一般演奏者之间;也可以是侧重面的不同,譬如大师与大师之间。演奏者对于音乐作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1](p.36),不住语言,不住大师之音响,不住大小语境之分析结果,用心去体会,用心去演奏,明心见性,直指人心。所谓“不住”是指不可执著,音乐语言之大小语境要分析,大师的音响可用于启发,语言诠释可作引导,但都是辅助,都是筏喻,都只落在文字般若的阶段,一如佛陀所说:“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1](p.27)真正演奏出闪耀着灵光并与众不同(事实上也不可能相同)的音乐,只能是挖掘“自家宝藏”,而不必向外求取并执著。马祖道一说的“自家宝藏”实际上就是学佛之人自己对佛法的证悟,就是演奏者自身的生活阅历、体验、对世界的认知、音乐修养等境界与音乐作品之“真如实相”之间的“心心相印”,这种会心只能用音乐音响来表达,而非别的什么东西,就如禅宗公案的不可言传,而是棒喝机锋,悟即悟了,不悟则莫名其妙。当然,这只针对具有“音乐的耳朵”的演奏者而言,就如学佛之人是否“根器大利”。如此,“话语停止的地方,便是音乐的开始”[6](p.137)。
都是“心心相印”,然心不同,对音乐的体悟则不同,其结果是同一作品出现了不同的音乐音响形态,这就体现出了音乐表演的本质——创造性。
三、音乐音响之“法无我,人无我”
音乐作品之“原作”不可以实相显现,演奏者却能与之“心心相印”,且不可言喻,似乎“玄之又玄”,那么,又如何判断具体音乐作品的若干音响形态确实不是随意而为呢?
《金刚经》中须菩提对佛说:“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1](p.145)佛学中的“实相”是指本体、实体、真相、本性等,但是世间所有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而起、变化无常的,没有永恒的、不变的自体,这就包含“空”之意义,也即世间万有的“真性”。所谓“实相者,即是非相,是名实相”,说明是人所生之“实相”并无“就是这个而非其他”的形态,也不可表述,只是名之曰“实相”,因此,实相实际上就是无相。佛学用“法无我”阐释了“实相”即“无相”的道理。
佛学中“法”有两种含义,其一指佛法,其二指事物和现象,“法无我”中的“法”指后者。“法,指轨持之意。‘轨是指有一定的范围与相貌,可使人认知;‘持是保持特性。综合起来,即是说有自身的特性、形象,能为轨范而使人理解、认识。”“‘我是既无集合离散,又无变化生灭的实体,是独立自生的永恒不变的主宰者。”[7](p.175-176)如此,“法无我”意思是说世间所有的存在(物)都没有独立自主且不变的实体,世间也无自我存在、自我决定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是相对的、暂时的。在佛学中,“实相”是指对佛学心有所悟,但并无固定的形态可显现,也无唯一的语言可表述。这也就是说,有形态可显现,有语言可表述的都不是“实相”,也即无相。因此,“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1](p.26)能与之“心心相印”并不意味着对象有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实相”;无固定形态,无唯一语言表述是指它本身“无相”,是“空”,但并非“断灭之空”,一旦开悟却可以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语言方式来表述。譬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则著名禅宗公案,历代著名禅师以“庭前柏树子”、“板齿生毛”、“云门干屎橛”、“麻三斤”……有的一语不发只做动作,甚或抬手便打作为问者的答案。答者都已有所开悟,若问者不开悟,答案对其则莫名其妙。
音乐作品只有在成为音响时才真正成为音乐作品。因此,演奏者成为了音乐作品的因缘之一,人心不同对音乐的体悟则不同,其结果是同一作品出现了不同的音乐音响形态,因而,作为“法”的音乐作品同样也是“法无我”。笔者曾认为:“在诸多演奏者不同的‘是什么中发现的,使这些不同的‘是什么发生的‘是,才具有作品的本质属性。它就是人们从作品的现象流中抽象出来的同一性的东西,胡塞尔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不同的现象流中的同一性,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8](p.109)可是,抽象出来的“同一性”还得用语言来表述,还是有“相”,它只是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共同认可的一个“相”而已,并不是那个无变化生灭的实体,也不是那个独立自生且永恒不变的主宰者。拙著紧接着从历时性的视角又认为:“从存在论的角度说,对音乐作品的理解与解释并不是一种被动的‘观照、‘反映关系,而是随着演奏者的生存境遇的变化而逐渐变化的存在过程。对于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很难说是克莱斯勒在1920年代的录音版本中的理解,还是穆特在2002年的录音版本中的理解更接近‘标准。……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作品唯一‘正确的理解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从现时的生存境遇出发,寻求对作品理解的相对标准。”[8](p.112)这就是说,上述从共时性中抽象出来的“同一性”在历时性中是发生变化的。即便是同一个演奏者演奏同一首音乐作品也不会出现相同的音响。笔者曾分析过谢林与穆特在不同时期演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各两个音响版本[8](p.155),仅速度这一因素的不同就足以证明两位大师各自对该作品的理解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差异。这一现象笔者认为是“对音乐作品的理解与解释……是随着演奏者的生存境遇的变化而逐渐变化的存在过程。”佛学则以“人无我”来说明问题。佛法认为,对于人之“我”,是依五蕴(色、受、想、行、识)合和而成。“色蕴”指肉体;“受蕴”指生理的感觉与心理的反应;“想蕴”指思维意识的思想作用;“行蕴”指身心活动;“识蕴”指心灵作用的精神本质[1](p.175-176)。“五蕴”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人之“我”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此,人本身也不存在不发生变化生灭的实体,不存在独立自生的永恒不变的“我”,是谓“人无我”。
共时性也好,历时性也好;不同的演奏者,同一个演奏者也罢;对于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我们从历代大师有差异的音响中无法判断哪一个是该作品“真如实相”的唯一化身,当他们音响中触及人心的耀眼灵光显现时,大师们对《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真如实相”便瞬间开悟。并且因为都是与音乐作品之“真如实相”之间的“心心相印”,因而,他们的演奏并非随意而为。
既然在音乐表演实践中实际存在着“法无我,人无我”之空性,对于音乐作品的忠实性又从何谈起?“忠实”,总是要问忠实什么?“忠实性”总是要问忠实某个“什么”到什么程度?可是我们始终不能确定那个唯一的“什么”。如此,对于音乐表演理论相关研究中是否还有必要提出“忠实”或“忠实性”的概念呢?
在音乐表演实践中,是否一定要追问类似号角声的音乐语言到底是战斗性的还是围猎性的?即便演奏者认为是战斗性而不是围猎性的号角,当成为音响时,听众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演奏法中并没有战斗性号角声与围猎性号角声的区别,号角声就是号角声。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号角声存在着音色及强弱变化而已。再如,为什么非要追问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歌唱呢?号角声音型、歌唱性旋律、跳跃似的节奏型等等音乐语言,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它只是与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运动相似而已,并且是一对多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非要通过各种手段把它们还原到作曲家作曲时意识中的那个瞬间原点,对于已故的作曲家恐怕是徒劳的,即便各种史料都可以佐证你的推理,也仅仅就是推理而已。
有学者认为,如果作曲家在世的话我们是可以确定作品唯一的那个真实面貌的。可是那只是语言而不是音响,此其一;随着人之“我”的变化,作曲家会不断修改其音乐作品,此其二;即便作曲家自己演奏,同样因为“人无我”的原因,不可能如放唱片似的每一次都毫无差异,此其三。柴可夫斯基为满足梅克夫人的要求把音乐形象勉为其难地写成了文字,但又在信中对梅克夫人说:“……这就是那部交响乐我能告诉你的一些物事。当然,我所说过的既不清楚,也不完全。”[6](p.26)
因此,不管具体作品的作曲家是否在世,作品一旦因缘合和而成,就不可能是实在、恒常的“有”,而只能是“空无自性”。其实所谓“空”就是不确定。那个曾经被笔者认为可以代表作品本质属性的“具体的同一性”,却在拙著第二章“忠实性生成研究”的小结中认为:“值得强调的是,在实践中演奏者并不是忠实于抽象出来的那个具体同一性。”[8](p.117)因为“那个具体同一性”是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若干音响中抽象出来的,因而渗透着演奏家个人的意识,而并非作品自身具有的。笔者并非否定自己对音乐演绎忠实性的研究,只是对类似的研究冠以“忠实性”的概念,如今认为还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笔者认为,对具体作品的演奏是否“随意而为”存在于两个层面。第一是乐谱层面。只要不改变乐谱中的音高节奏组合,不超出乐谱规定的速度、力度的范围值,就不能说随意而为。并且稍有音乐修养的演奏者是不可能把譬如表现为快乐的音乐语言演奏成痛苦的。如此,对具体作品的演奏就一定在其框架之内;第二是音乐内容层面。对于“随意而为”我们往往解释为不严谨,没有按一定标准操作。因此,判断对某事是否随意而为,一定要有“标准”作为参照系,否则就无法判断。经上文讨论认为,音乐作品根本不存在确定的内容,那么是否随意而为也就无从确定。在音乐表演实践中,演奏者能否对音乐语言及其在前后语境中的联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却是音乐表演的关键因素,在此前提下,对音乐表演如果逐字解释随—意—而—为,笔者认为恰如其分。这其中的“意”,正是个体演奏者的生活阅历、音乐修养、对事物认知的深度等等之集合体与音乐作品“真如实相”之间所产生的共鸣,或者如上文所说的与之“心心相印”,它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相同。
四、结语
佛陀在《金刚经》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1](p.26)所谓“不可得”并非不能得,只是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而不可停留。悲也好,乐也罢都将成为过去,成为“空”而不可得。对于音乐表演而言亦复如是,三心不得,唯有当下即是。音乐作品的“真如实相”通过当下开悟的“我”而呈现,当下演奏着的“我”就是音乐作品“真如实相”的载体,它如此自然地从当下的“我”心中“流淌”出来。过去、现在、未来的演奏都是那个当下的“我”在演奏,但却不可得,永无定法。由此,为着与一般意义上的“随意而为”有所区别,为着从佛学认知出发而讨论音乐表演理论,笔者认为,对“空无自性”之音乐作品的演奏,“随心而为”更为贴切。(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是指本质,“存在者”指现象。
②出自《中阿含·大品阿梨吒经》,比喻佛之教法如筏,既至涅槃彼岸,正法亦当舍弃。转引自陈秋平经、尚荣译注《金刚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页。
③梵语之音译,意指完成之人,故一般译为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觉、无上正遍知等。“阿耨多罗”意译为“无上”,表示佛陀所证悟的道是圆满无上的;“三藐三菩提”意译为“正遍知”,表明周遍正知最究极之真理,而且平等开示一切众生,令其达到涅槃。
参考文献:
[1]陈秋平、尚荣译注.金刚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陈秋平、尚荣译注.心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星云大师、南怀瑾等.般若莲花处处开[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4]饶尚宽译注.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A]//赖贤宗.海德格尔与禅道的跨文化沟通[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6]C.波纹.我的音乐生活: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录[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7]路浩青.心若莲花处处开[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8]郏而慷.音乐演绎的忠实性与创造性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