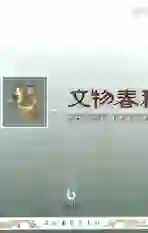侯家窑遗址2007—2012发掘地层的新认识
2015-05-30王法岗



【关键词】侯家窑遗址;许家窑遗址;许家窑文化;许家窑组;泥河湾层
【摘 要】本文回顾了侯家窑遗址名称的由来,报道了侯家窑遗址2007—2012年考古发掘对该遗址地层的新认识,新的考古发掘证实该遗址的文化遗物并非出自以往报道的泥河湾层之中,在此基础上对该遗址的时代、泥河湾古湖结束的时间、泥河湾层的上限以及许家窑组等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一、遗址概况
侯家窑遗址指许家窑文化遗址的74093地点[1],位于河北省阳原县东井集镇侯家窑村西南约500米处,地理坐标40°06′2.74″N、113°58′41.47″E,海拔970米。该遗址发现于1974年[2],随后及1976[3]、1977[4]、1979[5]年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该遗址与1973年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东北两叉沟附近的73113地点合并在一起,统称为许家窑遗址[6],与之相关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古人类化石、动物群也统称为“许家窑文化”“许家窑人”“许家窑动物群”等等。
73113、74093两个地点分属山西、河北两省(图一),相距较远,直线距离2300多米,在地层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而且 74093地点地处河北境内,是1974年以来历次发掘的地点,也是目前发表材料的主要来源,但发表资料使用了山西许家窑的名字。对此,部分学者[7]及河北的各级文物部门存在不同的意见,提出了将两个地点分别命名为山西阳高许家窑遗址、河北阳原侯家窑遗址,对74093地点在遗址保护标志名称、博物馆陈列展示解说以及出版的相关文字资料方面使用“侯家窑遗址”。本文在涉及到74093地点时,如无特别说明,统一使用侯家窑遗址。
二、本次考古工作背景
作为许家窑文化主要发掘地点及主要材料来源,侯家窑遗址丰富的早期智人化石,数以千计的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数量极多、比例极高的石球等极具文化特色,在现代人的起源、演化,旧石器文化演化、发展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该遗址的年代数据较多,但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1982年,陈铁梅等采用铀系法测定该遗址下层的马牙化石,测得其年龄大于10万年,应与距今10万年前的一个寒冷期相应[8],1984年又测量该地点地表以下8米处的犀牛牙,其年代值在10~12.5万年 [9];长友恒人等利用光释光测得文化层上部、中部的年代分别为60±8ka、69±8ka[10];马宁等采自文化层中部的样品采用光释光测得年代为大于13万年[11]。这些测年结果也基本与贾兰坡等根据地层、石制品特点和动物化石等推测其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之间[12]较为吻合。
1992年,刘椿、苏朴等通过对遗址周围剖面的古地磁测定,认为该剖面为距今10万年左右的布莱克极性事件,属晚更新世地层[13];后来,苏朴等通过古地磁的研究,对刘椿等的古地磁测定结果作出修订,并依据新的测定结果认为:遗址处于中更新世早中期,具体年代为距今四五十万年之间[14]。
对同一个遗址采用不同的测年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别达几十万年,超出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测年误差的范围.而对比上述测年方法的不同,古地磁测年的基础是地层沉积的连续性,文化遗物埋藏于泥河湾层之中。基于这些认识,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苏朴、樊行昭等[15]在遗址周围做古地磁测定时,就注意到遗址附近的湖相沉积物被后期河流的冲刷、改造、破坏较为严重,河流相与湖相沉积物成角度不整合接触,当古地磁年龄测定结果与铀系年龄存在巨大差异时,就怀疑埋藏文化遗物的地层是河流相的可能,认为:确定文化遗址年代所依据的U-Th绝对年龄样品是否产在湖相沉积物中是值得怀疑的。近些年,也有学者通过对该文化遗址周围地质、地貌的观察研究,直接提出许家窑文化的遗物埋藏于后期的河流阶地堆积中,而不是先前认为的泥河湾层,其地貌部位似乎应同于桑干河的第三级阶地,其时代为晚更新世,而不是中更新世[16]。
欲解决该遗址的年代问题,认定其文化层是否是泥河湾层就成为首要工作,为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织了2007—2012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三、考古调查
2003年以来,我们在侯家窑遗址及周围地区开展了地质、地貌及旧石器专题调查。发现梨益沟两岸泥河湾层堆积被后期河流侵蚀改造较为严重,站在梨益沟左岸(侯家窑村南)向对岸观察,可以看到梨益沟右岸断壁如图二所示:泥河湾层堆积被侵蚀成沟壑状,后期的河流阶地堆积呈楔状填充其中,而河流阶地顶面与保存较好的泥河湾层顶面在一个平面上,但从梨益沟两岸的断壁上观察,颜色及堆积物的差别特别明显,侯家窑遗址即位于其中的一个楔状堆积中。
在侯家窑遗址南侧大坡底沟北壁(图三)、长形沟两侧的断壁亦可看到相似的不整合接触面,结合使用探铲钻探的结果,各接触面在遗址西侧可以连成一线,呈西北—东南走向(图四)。该接触面以西为泥河湾层,以东为河流阶地,河流阶地以泥河湾层为基座,侯家窑遗址即位于河流阶地内,结合梨益沟自侯家窑遗址至入桑干河河口一带的地貌判断,该级阶地为梨益沟的第三级阶地。
四、遗址地层
为详细了解侯家窑遗址地层及文化遗物埋藏情况,2007年开始在上世纪70年代发掘区西北角划定约12平方米范围做小面积的考古发掘。2007年清理掉上部覆土,并发掘了部分文化层。2008年继续发掘,完成文化层的发掘。为了解文化层下部地层,在发掘区东侧发掘南北长2米、东西宽1米的探坑,发现厚2米以上的黑色泥炭层,并在泥炭层中发现石制品、动物化石,泥炭层未挖穿。2012年,为了解泥炭层中石制品、动物化石的情况,沿2008年发掘探方底面继续向下发掘,直至挖穿泥炭层,并少量发掘泥炭层下部的泥河湾层,发现泥炭层顶面自西向东倾斜,泥炭层中间的粗砂层中有比较集中的石制品、动物化石,泥炭层与下部的泥河湾层间有一清晰的不整合接触面,泥河湾层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与上覆地层不整合接触。
探方发掘总深度近16米,在距地表7.5~10米处发现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虽地层土质、土色有所变化,但文化遗物在地层中连续分布,无明显间断,无明显集中分布区,发现石制品、动物化石3000余件。探方内距地表约10.5米处与探方南侧70年代发掘区底面深度相近。距地表约13米处、泥炭层中的一层厚20~30厘米的粗砂中发现少量石制品、动物化石,动物化石保存较好,黝黑发亮。距地表14.5~15.5米处发现一不整合接触面,其下为原生泥河湾层,泥河湾层中未发现任何文化遗物。
依据发掘坑西壁,地层自上而下为(图五):
1 表土层,厚15~20厘米。
2 黄色细砂与粉砂质黏土的互层,含砂砾石条带,水平层理。厚200厘米。
3 砂砾石层,厚27厘米。
4 灰色细砂层,厚46厘米。
5 黄色粉砂质黏土,厚17~37厘米。
6 粗砂砾石层,水平层理。厚131厘米。
7 胶结砂层,厚5厘米。
8 灰白—浅灰色粉砂质黏土,弱水平层理,含大量粗砂条带,距层顶75厘米处发现动物化石一组。厚267厘米。
9 棕褐色砂质黏土,含大量铁锰浸染,为古土壤层,含石制品、动物化石。厚73厘米。
10 蓝灰色砂质黏土,含石制品、动物化石。厚30厘米。
11 棕色砂质黏土,含石制品、动物化石。厚135厘米。
12 黄褐—灰绿砂质黏土,含大量蓝灰色黏土块,顶部发现少量石制品、动物化石,底部含多层水锈。厚70厘米。
13 黑色砂质黏土,含大量云母片屑,顶面自西向东倾斜,为泥炭层。厚230~250厘米。
14 黑色粗砂层,地层自北向南倾斜,含石制品、动物化石。厚20~30厘米。
15 黑色—黄褐色砂质黏土,为泥炭层。厚120~150厘米。
16 蓝灰—浅蓝色黏土,呈透镜体状,探坑西北角处最厚,厚80厘米,在探坑北壁自西向东渐薄,东端最薄处仅28厘米,在探坑东壁厚8~35厘米,在探坑南壁仅在东端局部见到,北端不见,推测为坠落的泥河湾层堆积物土块。
17 灰黄—蓝灰色黏土,顶部不整合,为泥河湾层,最厚处70厘米。
18 灰白—灰黄色黏土,顶部不整合,为泥河湾层。厚20~30厘米。
19 灰白色黏土,为泥河湾层,发掘20厘米未到底。
依据1974年的发掘报告[17]和《“许家窑人”遗址志》[18],许家窑文化遗址的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来自距地表8~10米的灰褐色黏土或黄绿色黏土中的砂结核里,文化层基本上被破坏,但10~12米深处的黑色粉砂层中尚保留完整,下部的化石呈黑色,石化程度较低。依此描述,文化层堆积及下层文化遗物可以与2007—2012年发掘的剖面相对应,该遗址的文化遗物应位于黑色砂质黏土及以上的层位。
在该剖面上,2—6层具有明显的水平层理,基本为砂砾石层、粗砂、细砂、砂质粘土的互层,颗粒自下而上具有由粗渐细的特点,具有河流阶地二元结构的典型特征。9—15层相互之间整合接触,未发现明显的不整合接触面,为连续沉积的堆积物,底部有一明显的呈锅底状侵蚀面(参见图二)与第17、18层不整合接触(图六)。该套堆积物具有弱水平层理,颗粒较细,主要为砂质粘土、粉砂质粘土,局部见细砂、粗砂层,底部13—15层为黑色粘土、砂层,具有泥炭层的特点,应为静水或水流较缓环境下形成的堆积物。该套堆积在平面上呈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状,在横断面上呈锅底状与下伏的第17—19层的泥河湾层不整合接触,中间有流水搅动携带泥河湾层土块的扰乱层(第16层)。综合上述特征,该套堆积为牛轭湖相沉积,底部未发现明显的砂砾石层,但周围区域相似高度或稍低部位可见较厚的砂砾石层,综合判断剖面所在部位为河流的河漫滩堆积,而非河槽部位。
结合本次发掘探方黑色砂质黏土与泥河湾层之间的不整合接触面,以及周围的地貌地层关系,可以确认:侯家窑遗址的文化遗物埋藏于泥河湾层沉积结束之后的河流阶地中,而非以往认为的泥河湾层中[19],结合梨益沟至桑干河一带的地貌分析,应为梨益沟的第三级阶地,与桑干河的第三级阶地相当[20]。
五、相关讨论
侯家窑遗址的文化遗物埋藏于梨益沟的第三级阶地,而非以往认定的泥河湾层,为解决许家窑文化遗址年代的争议提供了一条新的有益思路。由侯家窑遗址文化遗物出自泥河湾层,且侯家窑遗址的时代为晚更新世,从而将泥河湾层的上限延续到晚更新世,由此提出的泥河湾层的许家窑组等都需重新考虑。
1.侯家窑遗址时代的讨论
侯家窑遗址年代的最大争议在于古地磁年龄与铀系年龄、光释光年龄以及古动物种群、古人类化石等反映的时代明显不符,古地磁的年龄给人以明显偏老的印象。
新的考古调查发掘证明,侯家窑遗址的文化遗物出自梨益沟的第三级阶地之中,而非最初认识的泥河湾层中,这种认识为年代差距巨大的原因提出了合理的解释。对该遗址进行古地磁测定的前提是遗址的文化遗物出自泥河湾层中,且这种湖相沉积有一个连续的沉积过程,新的材料证明遗址形成于泥河湾层沉积结束、河流侵蚀泥河湾层后再次形成的阶地堆积中,其时代要大大晚于泥河湾层沉积结束的时间。古地磁测定未考虑这个沉积间断,也无法预测沉积间断对年代的影响程度,其结果反映的应该是该区域泥河湾层沉积的时间,而不能正确反映该遗址的形成年代,遗址的时代要大大晚于古地磁测定的结果。
对比桑干河第三级阶地形成的时代、该遗址动物化石的种属、石制品的工业特点以及各种测年结果,我们初步推测:该遗址的时代应该仍为以往认为的中更新世晚期之末或者晚更新世早、中期,至于各种测年结果之间的差异,除其年代可能超出一些方法的测年范围,也可能与该遗址文化层较厚(最厚处达4米以上)、时代跨度较大有密切联系,这有待于新的系统取样测年及测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检验。
2.泥河湾层沉积结束时代的讨论
1924年,巴尔博对泥河湾村一带的地层进行观察后,将分布在泥河湾一带的河湖相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21]。其后,巴尔博、德日进等对泥河湾层的古动物化石进行研究,认为其中含有能和欧洲维拉弗朗期对比的化石,其时代为更新世早期 [22]。1948年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建议把维拉弗朗期作为更新世的下限,并建议将中国的泥河湾层作为中国早更新世的下界[23],从此泥河湾层作为中国早更新世的标准地层而被广大地质学者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所熟知。
1961年,杨景春根据1953年以来在大同盆地的教学实习成果,对这里的区域地貌、构造运动、火山活动及古地理等方面进行较深入的探讨,结论之一是泥河湾湖一直延续到更新世中期才消亡,泥河湾层下部属下更新统,上部属中更新统[24]。
上世纪70年代许家窑文化遗址的发现,特别是侯家窑遗址的发掘确认其文化遗物出自泥河湾层中,且其时代为晚更新世,距今10万年左右,又将泥河湾层的上限延续到晚更新世[25]。现在认定侯家窑遗址文化遗物出自梨益沟的第三级阶地内,而不是以往所认定的泥河湾层中,证明泥河湾层早在该遗址形成时即早已消失,其消失时代在中更新世以前,这也与该区域的光释光[26]、古地磁[27]测定结果相一致。
近些年,有学者认为在泥河湾盆地的中心部位,泥河湾层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早期,并提出了新的地层建议[28]。
由上述看,侯家窑遗址文化遗物的埋藏地层是否为泥河湾层,将对泥河湾层延续时代及泥河湾古湖消失时代的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许家窑组的讨论
许家窑组是指泥河湾层上部属于晚更新世的地层,因为许家窑文化遗址中有代表晚更新世时期的极其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所以采用“许家窑组”的命名[29]。
许家窑组的提出与许家窑文化遗址特别是侯家窑遗址的发掘密切相关。1978年,卫奇通过对泥河湾层上部地层发现的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特别是对侯家窑遗址等材料的分析,认为泥河湾层上部属于上更新统,为了把该组地层从泥河湾层区分出来,建议采用许家窑组命名,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1988年,陈茅南将泥河湾层划分为三个阶段:下更新统的泥河湾组、中更新统的小渡口组和上更新统许家窑组[30];2000年5月,第三届全国地层会议公布的地层指南中,建议将分布在许家窑一带的泥河湾层定为晚更新世许家窑组。
许家窑组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许家窑文化遗址的文化遗物出自泥河湾层中,且其时代为晚更新世,从而将泥河湾层形成的时间延续至晚更新世,其目的是为了将这组地层从传统认识的泥河湾层属于更新世早期的堆积中区分出来。此次在侯家窑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虽然证明其时代仍可能为晚更新世,但文化遗物并非出自泥河湾层之中,而是形成于泥河湾层堆积结束之后的河流阶地之中,其时代要明显晚于泥河湾层堆积沉积结束的时间,与泥河湾层堆积的延续时间没有直接联系。该遗址的时代不仅不能证明泥河湾层延续到晚更新世,反而证明泥河湾层结束的时间要早于该遗址的时代,而且新的古地磁测年数据证明该区域泥河湾层的时代为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早中期[31],与以往对泥河湾层时代的认识基本一致。由此看,许家窑组存在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存在,其目的也不能达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因而有专家建议取消许家窑组这一岩石地层单位[32]。
[1]王法岗,刘连强,李罡:《许家窑文化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文物春秋》2008年5期。
[2][6][17][19]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2期。
[3][12]贾兰坡,卫奇,李超荣:《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4期。
[4][11]马宁,裴树文,高星:《许家窑遗址74093地点1977年出土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2011年3期。
[5]吴茂霖:《许家窑人颞骨研究》,《人类学学报》1986年3期。
[7]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
[8]陈铁梅,原思训,高世君等:《许家窑遗址哺乳动物化石的铀子系法年代测定》,《人类学学报》1982年1期。
[9]陈铁梅,原思训,高世君:《铀子系法测定骨化石年龄的可靠性研究及华北地区主要旧石器地点的铀子系年代序列》,《人类学学报》1984年3期。
[10]长友恒人,下冈顺直,波冈久惠,等:《泥河湾盆地几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光释光测年》,《人类学学报》2009年3期。
[13]Liu Chun, Su Pu, Jin Zengxin. Discovery of Blake Episode in the Xujiayao Paleolithic site, Shanxi, China, Scientia Geologica, 1992(1).
[14][15][31]苏朴,樊行昭:《许家窑遗址磁性地层学研究》,地质出版社,2001年。
[16]谢飞,李珺,刘连强:《泥河湾旧石器文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年。
[17]卫奇:《“许家窑人”遗址志》,载贾兰坡,陶正刚等:《阳光下的山西——山西考古发掘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20]谢飞:《侯家窑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及文化遗物不是产自泥河湾层》,《中国文物报》2008年5月23日第7版。
[21]Barbour G B. The Deposites of the Sang Kan ho Valley, Bull Geol Soc China, 1925(1).
[22]Barbour G B. Licent E, Teilhara de Chardin P. Geological Study of the deposites of the Sangkan ho basin, Bull Geol Soc China, 1927(3-4).
[23]全国地层委员会:《中国的新生界》,科学出版社,1964年。
[24]杨景春:《大同盆地东部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1年1期。
[25][29]卫奇:《泥河湾层中的新发现及其在地层学上的意义》,载卫奇,谢飞:《泥河湾研究论文选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
[26]Zhao H, Lu Y C, Wang C M. ReOSL dating of aeolian and fluvial sediments from Nihewan Basin, northern China and its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 Quat Geochronol, 2010(5).
[27]左天文,成洪江,刘平等:《泥河湾盆地后沟遗址的磁性地层学定年》,《地球科学》2012年1期。
[28]夏正楷:《“泥河湾层”的时代归属及划分》,载《纪念袁复礼教授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93年。
[30]陈茅南等:《泥河湾层的研究》,海洋出版社,1988年。
[32]谢飞:《建议地质、考古学界不再使用“许家窑组”这一名称》,《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30日第7版。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