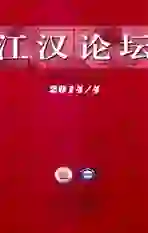苦难的代价论十七年革命叙事中的成长模式
2015-04-27姜辉
姜辉
摘要:在十七年的革命文本中,“成长”无疑是一种值得瞩目的叙事现象。这类成长叙事通常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基本线索,叙述其“成长”的艰难,藉此表现革命英雄从“天真”走向“经验”的艰巨历程。其成长模式背后隐藏的深层文化意义在于:革命者的成长既是个体生命成长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成长寓言。
关键词:革命;成长;苦难;生命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4-0097-04
的20世纪20-60年代的中国文学革命文本中,“成长”无疑是一种值得瞩目的叙事现象。从普遍意义来看。这类成长叙事通常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基本线索.叙述其“成长”的艰难,藉此表现革命英雄从“天真”走向“经验”的艰巨历程。其基本的模式是:作为历史主体的革命英雄(农民或知识分子)一开始处于天真或蒙昧状态.但在党的引导和培养下,历经劫难,备受考验.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本文拟从十七年文学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等文本进行分析,并将左翼文学文本以及解放区文学文本作为互文本,寻找上述革命文本中成长叙事的话语模式,探讨“成长”背后的深层文化意义。
一、成长仪式:分离——考验——再生
通常意义上,成长即指青春期的个体的生长与成熟。在原始社会,这种成长被理解为童年的死亡与成年的新生,并通过成年仪式来确定。美国人类学家巴巴拉·梅厄霍大认为,成年仪式“标志着每个人在一生的周期中所经历的各道关口:从某一阶段进入另一阶段;从一种社会角色或社会地位进入另一种角色、地位:它将生物定数如降生、繁殖后代与死亡和人类及文化经验统一起来”。换言之,成年仪式旨在创造人的文化状态和社会生命,使人拥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成年仪式一般遵循一个完整的程序模式:成长者与家人分开,被隔离在远离日常生活的边缘区域,即分离阶段;接受种种损伤肢体、磨练意志的考验,在考验中通常会受到一位长者的教导,或被给予新名字、新衣服,或被授予部落生存技艺与文化传统,即考验阶段或转变阶段;第三阶段,回归部落,被确定为再生,获得完全的成人资格。我们不难发现,成年仪式的一系列程序与十七年文学文本中革命英雄的成长模式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其原型意义也使成年仪式与十七年文本中的成长叙事有了连接的可能。
第一阶段:分离。在原始神话中,分离的目的在于“以特殊的禁闭性环境试炼少年的意志,净化其心灵,促进其更快地成长发育。而少女在被迫隔离期间,可能会得到与其天性更密切的接触机会”。《青春之歌》的林道静成长的起点就是对旧家庭、旧道德的反叛。文本一开始便叙述她拒绝母亲为她包办的婚姻,毅然离家出走,以一身素白、孤独、沉思的姿态出现在列车上。之后投亲未果,羁留异地,工作无着,又遭遇凶险。《红旗谱》则以朱老巩与地主冯老兰发生冲突后的含恨而死作为叙事起点,刚刚十几岁的儿子朱老忠深怀血海深仇外逃关东,历经多年的生活磨难,终于返回家乡,伺机为父报仇。
显然,在上述文本中,分离意味着离开家庭独自走向外界,并成为革命英雄成长的最初体验。因为处于年幼期的天真的革命者必须通过扩大自己的生活领域来获取走向广袤世界的经验,发展自己的生命。“所谓长大成人就是离开家庭,进入一个更广的文化领域”。因此,分离本质上就是一次初涉人世,是一种成长领域和生活经验的积极扩张。而在家庭成为摆脱对象的分离时期,守候他们的是随时的考验与试炼。
第二阶段,考验。成长仪式中的严酷考验在列维·布留尔看来,主要是“想查明新行成年礼的人的勇敢和耐心……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忍受痛苦和保守秘密”,同时也“给新行成年礼的人以‘新的灵魂”。朱老忠十几岁就孤身一人闯关东,“在长白山挖参,在黑河里打鱼,在海兰泡淘金”,与乡土分离使他无依无靠、一无所有,只能依靠自己与严酷的生活作殊死的搏斗:在历经数十年的江湖闯荡之后,不仅积累了生活的经验,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使他变得侠义豪爽、豁达自信、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而且也能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并成为锁井镇穷人的主心骨。在党的领导人贾湘农为他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之后,他意识到自发反抗和个体家族复仇的局限,开始进入革命者成长的逻辑进程。
不难看出,在这个阶段,对革命者的种种考验构成了革命成长中的主要事件。考验不仅展示了成长主体在复杂艰难的环境中挑战不幸与灾难的勇气,也表现了他们在肉体与精神上遭受的磨难。而正是这些磨难,使他们在认识和了解革命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的力量,从而为他们社会身份的改变打下了不可更改的显著印记。
第三阶段,再生。再生是成年仪式的最后阶段,是成长者成年的正式确立,标志着过去自然、生物状态的结束,而使人“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存在者再生出来”。而换装与获取新名字则成为再生仪式的一部分。标志着成长者成为与集体融合并拥有一切合法职能与权力的社会正式成员。《青春之歌》的结尾叙述林道静行走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示威队伍中,以一个宏大的集体仪式作为林道静“成长”的结束。林的“再生”还通过其政治身份的改变和个体身份符号的重新命名得到体现。在她出狱后,江华告诉她:“根据你在监狱里的表现,道静,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已经同意你入党了!”这标志着林道静在政治身份上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意味着她从此获得了革命的正式合法身份;之后,她向江华提出要求:“你替我起一个名字吧!我这个不好的名字是我父亲替我起的。你也像父亲一样替我另起一个好名字吧。”重新命名仪式的完成,无疑是个体在完成成长历程后获取新生的一种宣示。
至此,革命者完成了成人仪式的全部程序。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新生不仅意味着从“天真”到“经验”的跨越,也寓示着他们已经拥有“献给秘密的或神圣的东西的那一部分生活”。新生的革命英雄正式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员,以新的社会角色建立起全新的生命图景,担当起一个成熟革命者应负的职责。
二、话语重构:从失落到皈依
由于仪式在现代社会的式微,成年仪式作为一种稳固的文化体系对成长的限定也日显无力。因此,个体成长的路径和方式也日趋多元化。但“个体的精神生活中可能不仅存在着他自己所经验过的东西,而且可能在出生时就携带着种族发育根源的碎片这种原始遗产”。在这种情况下,原始成人仪式就有可能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进入现代人的个体成长,并在文本中体现为具体的叙事元素。在十七年文本中,不仅革命英雄的成长历程以模式化的三个程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原型结构,而且在整体的叙事话语上也大都包含了成长主体、成长过程、成长条件、成长归宿等具有普遍性的行动和结构要素。事实上,如果不将任何一种文本视为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在文本的相互参照中加以阐释,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在具体的主体性格和行动方式上存在差异和裂缝。但无论是在叙事主题还是在叙事话语的行动和结构要素上,上述十七年文本与左翼文学文本都有着惊人相似的共同之处。质言之,“成长”同样是左翼以来的大量革命文本的重要叙事主题,而这种主题性结构也同样通过积淀,演化成某种程式化的观念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具有明显独立特征的成长叙事模式。
十七年文学文本中的成长主体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前者如朱老忠,后者如林道静,而周炳则介于二者的灰色地带,集合了手工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征。而在20-30年代的左翼文本中,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同样是成长叙事的主人公。前者如蒋光慈《少年漂泊者》的汪中、王西彦《曙》的金小妹、茅盾《子夜》的陈小娥,后者如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的王曼英、茅盾《虹》的梅行素、丁玲《韦护》的韦护等。值得一提的是,两类不同的主体在成长叙事中的角色功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置换。工农群众在成长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引路人或助手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启蒙、教育和引导作用,如胡兴林之于金小妹、维嘉之于汪中;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又是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成长则是以回归工农集体以及知识分子的工农化为具体目标和归宿的。无论是王曼英、梅行素、韦护、美琳,还是以后的林道静、周炳,都无一例外地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显然,成长主体的这种角色功能的置换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了之后的十七年文本的成长叙事。
在左翼文本中,革命者的成长过程与十七年文学一样,也遵循的是“分离一考验一再生”的基本模式。正如有研究者概括的:“审视红色浪漫主义20世纪40到60年代文本,其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知识分子的还是农民的,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成长模式:农民英雄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经劫难,在党的教育下,经过磨炼,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尽管论者“审视”的文本范围只是20世纪40到60年代的文本,但如果将时间的上限延伸至20世纪20年代,其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如《少年漂泊者》以汪中的漂泊际遇为线索,叙述汪中在父母双亡后,经历入匪、学徒、做工等,最后结识了革命者维嘉,参加工人运动,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每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都必然会受到主观个性及其所处客观环境的影响,这些主客观的因素构成了成长主体的成长条件。主观个性既取决于主体的身份,同时也与自身的情感气质有关,因此,不同的个体,其特点也千差万别。而影响主体成长的客观因素,则主要取决于其经历的苦难以及遭遇的“引路人”。如前文所述,十七年文学的成长主人公,不仅都经历了苦难的磨炼与考验,而且都遭遇了对其成长起着关键作用的“引路人”。卢嘉川、林红、江华之于林道静,贾湘农之于朱老忠,张太雷之于周炳,即属此类。显然,没有前者的启蒙和教育,后者的成长就不可能发生。因此,主体的成长必须依靠外力的帮助。事实上,这种“引路人”在左翼文本中早就有迹可寻。《冲出云围的月亮》叙述王曼英在堕落的泥沼中意外与李尚志重逢,正是后者强大的人格魅力,不仅成为曼英情感救赎的源泉,也是其投身革命的精神原动力。胡也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的白华,在恋人希坚的帮助和引导下,克服了无政府主义在实际斗争中给自己带来的困惑,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实际的革命行动投身于工人运动。《韦护》巾的丽嘉也在韦护的帮助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虹》中的梅行素在共产党员梁刚夫的帮助下,看到了自己的无知和软弱,否定了个人主义,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鞋,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
成长主体的再生是所有革命文本成长叙事最为普遍的结局。一般表现为成长主人公最终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一个全新的社会生命由此诞生。从《少年飘泊者》汪中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直至最后战死沙场,到《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的白华放弃无政府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从《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洗净灵与肉的污垢,蜕变为一名纺织女工获得再生,到《虹》中的梅行素积极勇敢参加“五卅”示威游行,以战士的姿态迎接时代的暴风雨;以及之后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三家巷》中的周炳,其成长之路都可谓殊途同归。
从对以上叙事要素的分析可以得知,“成长”作为一种主题性结构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左翼文本之后不但大量涌现,而且一再被重复,这种主题性结构在革命文本中的积淀.已经演化成一条路线清晰的发展轨迹,并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与左翼文本形成较为明显的互文关系。可问题是,这种叙事元素在前后文本的互渗并不能完全遮蔽文本间的缝隙和裂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历史本身是无结构的,叙事的模式化并不意味着现实成长个体的模式化,个体成长的道路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独特的无法复制的唯一性。因此,成长仪式的最后完成,不仅其过程存在多元性,而且仪式终结后的再生也并不必然就是光明的结局。与革命文本成长叙事中无一例外的光明结局相比,中国现代小说不乏多元的成长叙事及其结局。叶绍钧的《倪焕之》展示的就是一个五四热血青年从辛亥革命到五卅惨案这一历史时期内的成长历程。文本中的成长主人公倪焕之从五四初期的理想主义到五四落潮后的无望挣扎,再到五卅惨案后的悲愤填膺与投身革命,到最后对革命的再次怀疑,都真实再现了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宁折不弯艰苦求索的精神成长之路。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组可谓倪焕之的精神孪生儿。文本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叙述了蒋纯组不断受挫、不断叛逆的成长过程,其最后结局是饱受精神苦刑的主人公带着对人生的困惑和痛苦在孤独与失意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上述文本中,成长主体的最后归宿不仅没有如革命文本中的成长者一样找到皈依和再生的力量,开启光明的人生,而且其本真、美好的理想也在现实苦难的挤压下被粉碎:精神的旅程不仅没有找列停靠的码头,反而变得更加漂泊无依。显然,这样的成长个体出现,不仅更具有个体生命的深层意义和丰富体验。而且显示出文本作者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所作的多元探索,同时也为一种新的成长模式的出现开辟了空间。
三、叙事隐喻:生命象征与历史寓言
在成年仪式中,原始社会的成长者必须与神合而为一,“经历一个无与伦比的魔力时刻,并且这种魔力聚召起一种和谐、有序的神圣理念,并以理想化的状态把每个人的成长纳入其间”。只有在被赋予了神的灵魂之后,青少年才能获得完整的生命,并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被部落所接受。显然,革命文本中的革命英雄从“天真”走向“经验”的艰难历程就是一种生命成长的象征。
在革命文本中,革命英雄大多在十几岁就离开家庭或故土,开始一段探索未知世界、寻求个人理想的艰难旅程。与原有生活秩序的分离,一方面使得年轻的成长主人公不仅获得了勇敢独立的契机和释放自身潜力的空问;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家庭的喂养和庇护,处于贫穷和饥饿中的儿女也被迫外出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藉此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朱老忠如果没有数十年的江湖历练,就不会有后来的成熟与练达;林道静如果没有逃脱封建家庭的牢笼,就不会走上革命道路,也就不会有作为革命者的林道静;周炳如果不是辗转于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就不会有以后清醒的阶级意识和坚定的阶级立场。正是因为物质的贫穷饥饿与精神上的匮乏,才使他们得以更新和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秩序或人生模式。但英雄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生命在其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磨难和考验才能真正成熟。成长者经历的诸如肉体的创伤、社会角色的卑微以及人格的屈辱等人生考验,不仅使他们得以见识到世界之大、社会之广、人心之狭以及自我力量之限,从而赋予他们或谦卑或热情地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也累积和蕴蓄了他们的生存技能、知识水平以及道德信仰和社会理念的基石。对于成长的青少年来说,肉体和精神的损伤给他们带来的无疑是一种严重的丧失,但也正是这种丧失,成为驱策他们为寻求身体与心理的完整而走向新生的动力之源。这样一来,苦难便成为成长者日后荣升为英雄的必要铺垫。在革命文本中,苦难更是作为革命英雄成长的必经之路而成为文本叙事的一个关键环节。林道静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后,被捕入狱,而遭受严刑拷打之后镌刻在身上的印记则铭写了林道静作为革命者的忠贞;周炳同样在敌人的牢狱经受酷刑的百般折磨而得以脱胎换骨;朱老忠面对的则是父亲的含冤而死,姐姐的受辱自尽,自己的腿被打伤,被迫离家漂泊独闯关东;汪中父母的惨死以及漂泊中所经历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欺诈和压迫,使他萌发了革命的种子;《苦菜花》中的柳八爷在由土匪成长为八路军战士的过程中。浴血奋战,几死一生,并失去了一条胳膊,终于完成了从草莽英雄到革命英雄的身份转型。
可以看出,无论是农民英雄还是知识分子革命者,他们在挫折和苦难中,都激发了自己抗击外在环境压力的能力,从而为进入革命战士的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下。这种受难经验甚至死亡体验既保证了成长者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壮健,同时也是对革命队伍中可能出现的弱者或背叛者的淘汰和摧毁。但肉体和灵魂的拯救与升华仅仅依靠苦难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通过剔除对革命信仰的怀疑,完成与党的形象和意志在意识上的完全合一才能得以实现。在原始神话的成长仪式中。这个过程被视为人神合一的“互渗”,即神的形象与意志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而这样的情感体验则恰好表明了这样一种人神关系,即人成为神的某种器皿,“人的生命被倾空,神的灵满满地进入”。而从此以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互渗”的意义在于促使成长的青少年体验到“圣物的权威”,拥有一种强大的心灵力量,从而“挣脱对父母权威的孩子气的依赖”,独立进入成年生活。而对于革命英雄来说,党则是通过“入党”等符号化的象征仪式,将自己的形象与意志编织成集体价值观和特定的阶级文化意象,深深地渗入并沉淀到此前懵懂无知的革命者的心智结构中,以此实现党对成长者革命身份的确认,完成成长主体与党的灵魂交接。而“成熟”后的革命英雄不仅其一切活动都打上了阶级文化的印记,个体的精神与意识完全被覆盖,其精神深处个体与集体的冲突、分裂与抗衡也在社会力量的审判或净化下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当然,革命文本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象征文本而存在。洪子诚就认为十七年文本“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做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主义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了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作为一种“叙事的历史”,“红色英雄的这种成长、转化历程具有线形的、进化的特点,因此,它又与历史相连结,而暗寓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文本的成长叙事构成的又不啻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寓言”。作为中国革命的两大力量,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历程,隐喻的是反抗与革命的历史关系.阐释了现代革命的自然性和合理性。作为工农出身的成长主体,他们的成长“起点”是为反抗压迫,表达的是受压迫的劳动者希望借助革命暴力来摆脱现实苦难的欲求。汪中与朱老忠都是因为父母被害死而背负着“为父报仇”的历史包袱走向革命,“家族复仇”最终转化为“阶级复仇”。这种反抗—革命的逻辑结构,隐喻社会民众反抗压迫的欲望成为革命力量的可能性,不仅赋予了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也赋予了革命作为苦难拯救者的身份。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便不难发现革命文本的成长叙事中“成长”外衣包裹下的暴力革命政治话语的内核。
而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成长者,主要是为反抗包办婚姻、追求爱情或爱情挫折而走向革命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的白华、《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虹》中的梅行素,以及林道静、周炳都属此类。但爱情只是成长的起点,上述主人公在对爱情归宿的做出抗拒或接受的选择的同时,也在做出对革命信仰和精神理念的选择。不同的爱情对象,事实上表征的是不同的精神理念和人生道路。以《青春之歌》为例,林道静对爱情对象的选择与其思想成长的历程呈现出高度趋同,从余永泽到卢嘉川再到江华,从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想到马列主义的理想信仰再到与工农结合的中国革命实践.每一个男性都是政治理念的具象符号,代表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样的情感历程投射的是知识分子对代表先进的社会发展思想的追寻,浓缩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精神成长之路。因此,成长主人公在生活道路和情感归宿的选择,不再仅仅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而是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的选择;个体的成长,也不再是个体情感经历和人生体验的历程,而是被置于宏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投注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之路。这样,个人生活经历与革命斗争历程的统一、个体情感命运与国家民族理想的统一便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情感和精神双重成长的重要前提和基本内涵,也是革命文本成长叙事的最终旨归。
至此,我们便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革命文本成长叙事隐藏的复杂意义,即个人成长的背后,暗含的是历史的成长,而历史的成长则导致了个人的成长。在这样的辩证关系中,成长个体便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人,而革命文本的成长叙事也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成长寓言。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