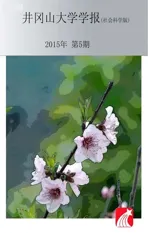清末官话教学的开展及其启示
2015-04-14梁尔铭李小菲
梁尔铭,李小菲
(井冈山大学1.教育学院;2.图书馆,江西 吉安 343009)
清末官话教学的开展及其启示
梁尔铭1,李小菲2
(井冈山大学1.教育学院;2.图书馆,江西 吉安 343009)
随着汉语地位的提高、切音字运动的兴起和统一语言成为共识,曾在清中期雍正年间推行过却没有成功的官话教学又在清末新政时期重新兴起,并进入了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体系当中。清末官话教学在课程设置、教科书编撰和师资培养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并取到了很大的发展。官话教学的重新兴起,不仅意味着统一语言的推行,更开了听说教学形式进入中国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先河,对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有着重大贡献。
清末;中小学;语文课程;官话;语言教学
官话一词起源于明代,是明清时期中华民族的区际共同语,也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①汉民族共同语有书面语与口语之分,文言一直在书面语中占统治地位,以官话为代表的白话则是明清时期民众日常使用的口语。由于官话只能用于日常交流而不能作为正式书面语使用,中国人对在学校教育中系统教授官话并不感兴趣,大家更倾向在社会交往中自行学习官话。官方虽曾于清中期雍正年间在闽粤地区有过一次推广官话的尝试,但这次尝试并没有取得成功。到了清末新政开展的时候,教育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官话教学适应社会需要重新兴起并出现在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体系当中,又是教育改革的一大亮点。在清末新政中,官话教学突破了以往官话教学范围狭窄的障碍,融入了当时的主流教育体系。它的开展,不仅使语文教育具备了统一语言的功能,更将听说教学形式带入了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当中,在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影响甚大。考察清末官话教学的发展,对今天我们推行普通话教育不乏借鉴和启示。学术界关于清末官话教学相关的研究,涉及到学制改革、语文建设、国语运动、中外交流等领域。②关于官话的研究状况,由于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的不同,研究者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王力、李新魁、耿振生、叶宝奎、李宝嘉、[日]平田昌家、[日]岩田宪幸、张卫东、黄灵燕等学者着重于究官话读音和官话标准音;吕朋林、陈泽平、岳辉、王永超、李无未、邸宏香、陈姗姗、[日]濑户口律子等学者留心中外各种官话课本;邓洪波、石美珊、吴永斌等学者着力于雍正年间在闽粤推广官话的运动;林焘、金丽莉、王理嘉等学者注重探讨官话的来由;崔明海、王东杰、李宇明、于锦恩等学者留意到官话在国语运动发展中的地位;郑国民、雷芳、史成明等学者从语文课程建设的角度关注官话的重要性;张虹、王钟翰、林家有等学者认识到满语衰落对汉语地位的巩固作用;胡瑞琴、王庆云、罗小东、张龙平等学者则研究了外国人学习汉语官话的情况。对于清末新政时期的官话教学,学术界多作为研究背景进行论述,而针对官话教学自身发展状况的探讨则较少。本文试图利用相关史料,对清末官话教学重新出现的原因、官话课程的设置、官话教科书的使用和编撰以及官话师资的培养、官话教学的意义及其局限等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对清末官话教学进行一个整体性研究,为今后深入探讨相关领域问题打下基础。
一、清末重新开展官话教学的背景
清代中国境内方言林立,虽然官话已经成为日常交流的通用口语,却依然有不少官员和民众习惯于使用自己的方言,尤以离官话区最远的福建和广东两省为著。雍正年间,福建和广东两省曾
根据朝廷的命令建立了许多正音书院来推广官话。只是科举考试和正式书面语言并不使用官话,因而通过正音书院推广官话的效果并不好,“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课制艺,广东则更无闻矣”[1](P439),这一场官话推广运动最终无疾而终。然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官话却又成了新式学校里教授的内容之一。与雍正年间那场推广官话运动相比,作为清末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官话教学,那时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中。
1.汉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奠定了官话教学的坚实基础。
清初满人入主中原以后,为确保统治地位并体现其民族优越感,将满语定为法定语言,大加推崇。由于满人掌握权力枢要,许多汉人不得不学习满语以便办理公务。然而满人生活在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中,因语言不通所带来的生活不便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许多满人在通晓满语的同时,也开始学习汉语。满族统治者起初对于满人学习汉语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雍正年间能够在闽粤两省推行官话教学正是得益于此。随着汉语在满族群体中的逐渐普及,许多满人慢慢不愿意甚至不能使用满语。到了乾隆年间,皇帝为了挽救日渐衰落的满语,不得不坚持“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强调满语的学习和使用。通过增加新词,丰富满语词汇,解决具体的语言问题,满语曾一度达到极盛状态。[2]
清朝统治者维护满语的国语地位,大大挤压了汉语的生存空间。不过语言毕竟是一种交流工具,使用频率低的语言终归会被使用频率高的语言所代替。乾隆后期,满汉两族交流日渐加强,不但关内的满人趋向汉化,就连东北辽沈一带地区的满人也开始习惯使用汉语。[3]随着汉文化优越性的显露,汉语的身影重新出现在各种正式场合。尽管统治者数次下谕要求保持满语的地位,但满语的衰落趋势已是无法挽回。[4](P265-266)汉语已经取代满语成为清朝的首要语言,文言重新成为主要的书面语,官话也成为官商交流的日常口语。在北京城内,“街上逛的人”和“到店里买东西”的人都“满嘴官话”,“说得清清楚楚”,就连闽粤两省“经过水陆大码头”的“行户、买卖人”,也“都会说官话”。[5]
到清末时,“北京官话是以北京官场为中心使用之语言,且为各地官吏及读书人所使用”,“凡官员因召见或引见而来北京进宫拜谒皇帝时,必须使用北京官话,故他们须学北京官话”[6](P473-474),官话已成为清朝官方通用的口语。满语地位的降低和汉语地位的上升,使汉民族共同语在政治层面上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语,为官话教学重新出现在官方视野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简便易学的切音字出现,提供了官话教学的辅助音标。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在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看来,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为了开启民智和普及教育,他们掀起了一场以 “言文一致”为口号的切音字运动。切音字创制者的本意是“要把象形、会意,而实非象形、会意的文字,改作拼音的文字,所以各地方拼音字母很多”[7]。只是汉字在中国流行已久,拼音文字的推行谈何容易。不过切音字的出现却无意中带来了另外一种功用,那就是用来拼写官话,为官话提供了辅助音标。
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一般不能凭结构直接读出它的读音,所以要给汉字注音。中国传统的注音方法主要有直音法、读若法和反切法三种。这些注音方法使用的工具都是汉字,对于没有受过较深程度教育的人来说是无法使用的。更重要的是,口语在几千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汉字在古代的读音与在清末的读音已经不同。如果用清末的读音去提取反切上下两个字的声母和韵母,得出来的结果与被切字在清末的读音很可能会不一样。中国传统注音方法的这些弊端,随着切音字的出现便迎刃而解。
切音字是一种拼音文字,有汉字笔画式、速记符号式、拉丁字母式、数码式和自造符号式之分。无论何种式样,都要比汉字简单,就连妇孺也能轻易掌握。而且切音字是以汉字在清末的读音为基础,因此可以用来拼写当时包括官话在内的白话。日后切音字运动衰落以后,切音字还保留着辅助音标的功用,民国初年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字母就是切音字的延续。切音字的出现,事实上为官话的拼读提供了有效的辅助音标,使拼写官话变
得容易起来,从而为官话教学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利器。
3.时局变化呼吁国语统一,制造了官话教学的舆论氛围。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在这场热潮中,教育领域的学习更加令人关心。在时人眼中,日本与中国在政体和国情方面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以日本为师进行教育改革能够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日本为师趋向的形成,为清末教育改革学习日本推广共同语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明治维新虽然结束了日本的分裂局面,但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造成了日本国内语言纷繁复杂的局面。民众不但交流困难,而且缺少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大力推广被称为“国语”的日语共同语,以期统一语言和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日本推广国语的力度相当大,只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做到了一切学校讲国语,一切公共场所讲国语。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曾在一次宴会上以另一日人阿多为例,向正在日本考察教育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介绍道:“即如仆信州人,此阿多君萨摩人,卅年前面对面不能通姓名,殆如贵国福建、广东人之见北京人也,然今日仆与阿多君语言已无少差异。”[8](P798)吴汝纶对日本推广国语的成效深有感慨,于是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指出:“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9](P436)由张百熙参与制定的癸卯学制中便采纳了吴汝纶的建议,在中小学语文课程中增加了官话教学的内容。
清末新政及其各领域的改革最重要的背景之一,就是现代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以吴汝纶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将语言统一的思想上升到国家与民族的角度,提出了国语统一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国语统一是再造新国民、消弭地域主义和加强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考虑,统一语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时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若不解决各地方言分歧的弊端,制定一个较为统一的语音标准,不但会影响各地区之间的交流,而且还会降低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时局变化呼吁国语统一,为推行官话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清末官话教学的开展状况
清末新政的开展使教育改革列入了议事日程,重要性日益增强的官话也被纳入新式教育的课程体系当中。清末的官话教学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使口语领域中的统一语言得以推行,听说教学形式也进入了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之中,对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1.清末官话课程的设置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公布,要求在初等小学堂设中国文字科,其它学堂设中国文学科。这是一种显著的变化,因为过去那种集经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和语言文字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语文教育将不再存在,代而起之的是单独设立的语文课程。更为重要的是,《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10](P207)高等小学堂从第一年到第四年皆习官话,“每星期一次即可”[11](P432),时限未定。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从第一年到第五年也皆习官话,次数和时限均未定,简易科亦兼习官话。[12](P675-678)优级师范学堂没有教授官话的明确规定,但事实上许多优级师范学堂也习官话,如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就曾在湖南优级师范学堂传授过官话。[13](P84)口语教学开始进入以往被书面语教学独霸的语文教育领域,这对于传统的语文教育来说是一种划时代的创新。
官话在各地学堂中的教学进行得较为成功,因此学部在1909年奏报分年筹备宪政事宜时,又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打算进一步扩大官话教学的范围。按照这项计划,到1910年,“所有省城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小学堂兼习官话”;到1913年,“所有府、直隶州、厅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小学堂兼习官话”;到1916年,“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习官话”,“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各项考试,均加入官话一科”[14](P49-52)。至此,在学部奏报分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上,官话教学已占了不少分量。然时任学部尚书荣庆犹不满足,认为“以我国版图辽阔,风土既异,语言亦殊,实为教育普及之一大障碍,非筹画统一语言之法,则声气不易相通,感情无由联络,而教育普及亦无办到之期。惟语言一端,关于各处之风俗习惯,一旦剧之改革,断难操切图功”[15]。在荣庆的主张下,学部
有意将官话教学继续扩大化,“拟先于各项学堂,增入国语一科,并通饬广设官话研究所,再由本部编订官话书籍,颁发各省,作为宣讲之用。庶渐染成习,或可同归一致云。”[16]官话教学进入到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当中,主要是因为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相对于文言书面语教学来说,官话教学处于次要的地位。在各级学堂中增设国语科,则意味着官话教学取得了与文言书面语教学同等的地位。此事影响面甚大,因而被搁置起来。
根据1909年制定的计划,学部在1911年颁布训令催促所有省城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小学堂兼习官话,并规定“各学堂应于正课时间之外添课官话时限,每星期二小时至三小时”[17]。当年7月,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会上又通过决议案,决定将官话教学扩充为国语科。然而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这项庞大的计划不得不宣告结束,清末官话教学就此告一段落。
2.清末官话教科书的使用和编撰
传授官话,刚开始并没有专门的教材。按照《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高等小学堂)习官话者,即以读《圣谕广训直解》习之”[11](P432);“(初级师范学堂)练习官话,即用《圣谕广训直解》,以便教授学童,使全国人民语言合一”[12](P670)。《圣谕广训》是一本雍正年间由清朝官方颁布并运用政治力量使之广为刊行的文献汇编,收录了康熙和雍正两朝皇帝的部分语录。《圣谕广训》颁布不久,陕西盐运使王又朴将其直译为口语,以《圣谕广训直解》为名刊布发行。《圣谕广训直解》文字通俗易懂,而且“其文皆京师语”,非常适合作为推广统一语言的教材。官话教学渐入正轨后,也有人另编官话辅助教材。如曾在广东公立官话讲习所任教的孔赞廷就于1910年编成《广东公立官话讲习所讲义》,其内容结合地方特点,包括了去弊法、预备法、正声法、辨似法、杂话名称法、杂话谈法、成段话法和分门别类话头等八项,是一本较好的辅助教材。[18]诸如此类的地方官话教材,当时各地还有很多。
上述的官话教材在语音上采用的是传统的读书音。由于传统的读书音与清末流行的口语音有很大的差别,以官话口语音为切音标准的切音字教材反而更受大众欢迎。王照的“官话合音字母”以京城口音为标准,“其法用支微鱼虞等字为母,益以喉音十五、字母四十九,皆损笔写之,略如日本之假名字,妇孺学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画,彼此通书”[9](P436),是一种很好的辅助音标。因此,王照的《官话合音字母》一书在当时较为流行。那时,“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传播很广,约遍于十三省的境界”,直隶甚至在袁世凯的支持下通令全省启蒙学堂传习“官话合音字母”,并将“官话合音字母”加入师范及小学课程中。[13](P28)到了宣统初年,王照因袁世凯倒台而受牵连,“官话合音字母”也被禁止传播。但劳乃宣编有《简字谱录》一书,其所提倡的“京音简字”异曲同工,亦可起替代作用。
1909年学部奏报分年筹备宪政事宜时,曾有打算在1910年“编订官话课本”,而在“此项课本未经颁布以前,均遵旧章讲读《圣谕广训直解》”,然后在 1911年再 “颁布官话课本”[14](P49-52)。到1910年2月,学部开始派员编纂官话课本,“于图书局暨审定科各员,择其宗旨纯正、深明教育者分担编纂,立限定程,一经脱稿,先由图书局长审阅,再送臣部丞参覆校。然后由臣等详慎检核,以臻周密,预计明年年内当可依限成书。”[19](P752-753)同年10月,官话课本已经完成初稿,“计年内可陆续成书”[20]。官话课本编纂期间,适逢劳乃宣亦在运动推广他的“京音简字”,希望将其纳入官话课本当中,并得到资政院通过议案,“将简字正名为 ‘音标’,由学部审择修订,奏请钦定颁行”。[21](P951)但学部对此并不热心,只将其交给不久以后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讨论。结果中央教育会虽然通过决议支持,但随着清王朝灭亡,最后此事不了了之,官话课本亦未能出版。
3.清末官话师资的培养
传统教育以学者为师,教员不用受专门的训练,凡具有某种知识或技能者即可充任教员。官话不是传统教育当中的正式内容,更谈不上专门的师资培养,因此官话开始在各级学堂教授之时尚没有完善的师资力量,只能采取因陋就简的办法,聘请一批熟悉官话的人员充当教员。当然,经费支绌也是各级学堂经常聘请不到合格的官话师资的原因之一,学部曾为此训令指出“此项教员,应准各学堂连合聘用,由提学使按照各地情形,明定每小时教授薪金数目,以期费省事举,便于推行。”[17]多所学堂合用一名官话教师,也算是当时的应急之举。但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来考虑,清末
的官话师资都难以满足中小学语文课程教学的需要。为了弥补官话师资的不足,学部和各省十分注意培养官话师资。
在清末实行的癸卯学制中,师范学堂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师范学堂的目标是为中小学堂培养师资,而中小学堂正是需要教授官话的地方,因此在师范学堂学生中培养官话师资至关紧要。学部指出,“至师范学堂官话一科,所关尤重,应由提学使切实督率办理,将来毕业日多,小学各项学科,皆可用官音教授,俾收统一语言之效”[17]。师范学堂培养官话师资虽为正道,但初级师范学堂学制五年、优级师范学堂学制四年,培养周期太长,而且开办数量不多。时间紧迫,仅靠师范学堂培养官话师资无疑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对官话师资的迫切需求,新疆、四川和广东等省为此曾自办官话讲习所一类的培训机构。各地设立的官话讲习所,大多数是独立设置,亦有附属于其它学堂的。学部也曾计划到1911年在 “京师设立官话传习所,行各省设立官话传习所”,又计划在1912年“行各省推广官话讲习所”[14](P49-52)。与师范学堂相比,以专门培养教授官话师资为目标的培训机构所需时间较短、要求条件也相对简单,是当时官话师资的重要来源,因而备受重视。
为了高效率地培养官话师资,学部召开的中央教育会在1911年8月通过议决案,对通过国语传习所培养官话师资的方法作了具体的要求:“先由学部设立国语传习所,令各省选派博通本省方言者到京传习,毕业后遣回原省,再由各省会设立国语传习所,即由前项毕业生充当教员,以次推及府州厅县。凡各学堂之职教员不能官话者,应一律轮替入所学习,以毕业为限。各学堂学生,除酌添专授国语时刻外,其余各科亦须逐渐改用官话教授。”[22](P142-143)此计划十分周全,只是尚未展开,清朝便已覆亡,计划未能实行。
清末官话教学对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影响甚大。1912年8月,民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采用切音字母方案》,决定先从统一汉字读音着手,实施国语教育。[23]1912年11月,民国教育部颁布《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也规定国文科“初等小学校首宜正其发音,使知简单文字之读法、书法、作法,渐授以日用文章,并使练习语言。高等小学校,首宜依前项教授渐及普通文之读法、书法、作法,并使练习语言”[24]。到了1923年6月,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为壬戌学制起草的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又将小学及初中、高中的语文课程一律定名为“国语科”,并规定语言是小学国语科教授的四大内容之一,由清末官话教学缘起的语言统一最终在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体系中得以确立。[25](P6-7)
三、清末官话教学的启示
汉语地位的显著提高为官话教学提供了前提保证,切音字的出现使得拼写官话变得更加容易,时局的变化为清末官话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官话教学在清末中小学语文课程中的迅速兴起。虽然受制于教材、师资和资金等各种因素,清末官话教学并没有发展到时人预想的程度就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暂告一段落,但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当今中小学语文教育仍有启示作用。
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必须在中小学语文课程中推行普通话口语教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广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在语文课程中推行普通话教学已经成为共识。然而各地在推行普通话教学的过程中却存在重书面语轻口语的倾向,很多地方依然使用方言进行教学。由于普通话的书面语与口语存在差异,致使学生能阅读普通话书面语却不能流利使用普通话口语。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种书面语与口语脱节现象在清末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中也有相似情形的出现。清末文言是通行的书面语,但人们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的口语却是白话。为了弥补书面语与口语相差太远的缺陷,《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专设中国文字一科,教授白话的书面语。[26](P418-420)由于各地白话存有差异,白话书面语无法在全国通行,人们在交流中往往存在着障碍,最后仍不得不借助文言书面语。官话教学的推行,恰好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它的目的就是通过统一全国各地的口语使人们之间的交流不再因方言区域的不同而产生障碍,既是语言统一思想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也推动了语言统一的进程。清末官话教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中小学语文课程中推行普通话口语教学是大势所趋。只有推广普通话口语教学,才能促进我国不同区域内口语
的统一,使得各地人们之间的交流不再因方言区域的不同而产生障碍。
另一方面,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需要更新和丰富中小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形式。当今中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普遍存在重读写轻听说的现象。实际上,由于“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与当时语言无异,此一定之理也”[27](P79-80),当时的语文教学中听、说、读、写等行为是协调一致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口头语言的变化速度远远大于书面语言,口语和书面语由此逐渐脱节。在这种环境下,古代语文教育变成了以书面语言教学为主,更倾向于阅读和写作训练。官话教学进入清末中小学语文课程后,改变了以往只注重读写不注重听说的教学模式。官话教学教授的是口语,要求学生能听和能说官话,因此听说的教学形式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使语文课程在两千多年以后重新增加了听说的教学形式,为后来听、说、读、写教学的一致性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虽然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其中的价值,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得到了普遍的实施。即使是民国成立以后,初等小学校(国民学校)依然保留着“练习语言”的规定,可见其影响之大。我们今天应该借鉴清末官话教学的做法,重视中小学语文课程中的听说训练,使中小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形式得以更新和丰富。
当然,清末官话教学也存在其局限性。与以言文一致为口号的切音字运动不同,官话教学主张的是国语统一。因历史原因而导致官话教学的终结固属可惜,但没有注意到言文一致与国语统一的关系更是官话教学的致命伤。大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言文一致的必要性,致使清末官话在标准音问题上产生了尴尬。由于文言文依然在书面语言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与其有密切的关系的传统读书音依然被认为是官话的标准音。但传统读书音离现实口语音太远,在日常教学中难以使用,各地在推行官话教学时只有以各地官话口语音进行教学,全国并无统一的语音标准。与此同时,人们没有意识到听说和读写在两个不同语言系统下所产生的矛盾,官话采用听说形式教授口语,文言采用读写形式教授书面语。两者各自都在全国通用,并行不悖。由于过分强调官话教学是为了口语统一,人们不能对听说教学形式在符合语文教学自身规律方面的重要性作出正确的认识,从而留下了极大的遗憾。清末官话教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些局限,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以保证当今中小学语文课程教育的正常发展。
[1]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
[2]张虹.简述乾隆帝对完善满语文的贡献[J].满语研究,2002,(1).
[3]王钟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A].清史新考[C].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4]林家有.试论满族文字的创制及满语满文逐渐废弃的原因[A].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民族史论丛[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5]高敬亭.正音撮要[Z].同治丁卯年(1867).
[6]服部宇之吉.清末北京志资料[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
[7]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J].教育杂志,1921,(13).
[8]吴汝纶.东游丛录:卷四[A].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三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2.
[9]吴汝纶.与张尚书[A].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三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2.
[10]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1]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2]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3]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4]学部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A].商务印书馆.大清宣统新法令:第三册[C].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
[15]荣庆.教育普及自划一语言始[N].盛京时报,1909-10-03.
[16]学部注意国语[J].教育杂志,1910,(1).
[17]中小各学堂一律添课官话[J].教育杂志,1911,(2).
[18]陈觉全.广州市推行普通话(国语、官话)史略[J].岭南文史,1996,(1).
[19]学部奏陈明年筹备事宜折[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0]学部奏第三年筹备事宜折[J].教育杂志,1910,(2).
[21]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序[A].倪海曙.清末文字改革文集[C].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22]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A].倪海曙.清末文字改革文集[C].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23]我一.临时教育会议日记[J].教育杂志,1912,(4).
[24]教育部通咨各省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J].教育杂志,1913,(4).
[25]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新学制课程纲要总说明[A].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C].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26]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27]王照.官话合音字母原序[A].王照.小航文存[C].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Mandarin Teach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LIANG Er-ming, LI Xiao-fei
(1.School of Education,Jingangshan University,Ji'an 343009,China; 2.Library,Jingangshan University,Ji'an 343009,China)
with favorable conditions including higher status of Han language,the rise of phonetic alphabet movement and consensus on language unification,mandarin teaching,an attempt failed in Yongzheng Reign, was held again in late Qing Dynasty Mandarin teaching in that time obtained great accomplishment at curriculum setting,schoolbook compilation and teachers training.The rise of mandarin teaching not only suggested a policy of uniform language,but also brought listen and speak into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which marked a breakthrough and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late Qing dynasty;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mandarin;language teaching
G529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5.05.013
1674-8107(2015)05-0080-07
(责任编辑:曾琼芳)
2015-03-27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民初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研究”(项目编号:13YJC880042)。作者简介:1.梁尔铭(1979-),男,广东高要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教育研究。
2.李小菲(1979-),女,广东高要人,馆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