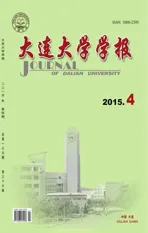《野草在歌唱》中的女性哥特艺术
2015-03-22王晓琪
王晓琪
(大连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野草在歌唱》中的女性哥特艺术
王晓琪
(大连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野草在歌唱》在种族隔离制度的社会背景中对非洲殖民地女性生活进行了细腻的描写。本文通过分析哥特元素——女性恐惧、禁锢、乱伦、沉默,结合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探讨莱辛如何在小说中利用哥特元素巧妙而深刻地展示女性遭受的压迫,鼓励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自我意识觉醒。
《野草在歌唱》;哥特;恐惧;凝视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1950年发表了她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2007年,多丽丝·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英国文学老祖母级”的小说家以史诗诗人般的女性视角、饱满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深刻的怀疑精神剖析了一种分裂的文明。近年来随着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有研究者从生态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主义,原型阅读及叙事策略等视角对小说展开全面的研究,从各个角度剖析了主人公玛丽具有典型意义的悲剧命运及其悲剧根源。但是鲜有论者从小说主人公玛丽所处的怪异环境,玛丽感受的女性恐惧与所遭受的禁锢以及她最后的精神崩溃等典型的女性哥特元素方面进行剖析。本文将通过分析小说的女性哥特元素,分析作者在小说中营造的诡异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环境,还原作者如何利用哥特元素展示女性遭受的压迫,鼓励女性在父权社会中自我意识的觉醒。
一、恐惧与幽闭
“哥特”一词源于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部落。在文艺复兴时期“哥特”被用来区分中世纪(公元5-15世纪)的一种暗色调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影响了文学,绘画,建筑和音乐。18世纪中后期,“哥特”一词发展成一种新的小说体裁。哥特式的小说充满了神秘、阴森和恐怖的气氛,向读者展示了沉闷、黑暗、情绪化的主人公和他们的生活。其中恐惧、死亡、古堡、癫狂和幽闭的空间等成为充斥在哥特文学中的标志性元素。哥特小说的出现是对极端的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反叛,它通过极端的场景设置和人物关系,试图向读者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和各种非理性因素。女性批评家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在她的著作《文学妇女》中将哥特视角引入女性批评。莫尔斯认为“女性哥特”这一概念被阐释为“体现以男权为主导的性别身份观对女性个体产生的影响的有效载体[1]71”,表现了在女性性别视角下女性作家以及女性人物的“恐惧”体验。女性哥特小说沿用了传统哥特小说中使人产生恐惧的各种神秘现象和幽闭的空间意象,同时强调“造成女性焦虑与恐惧的幽灵更多的来自现实生活中性别角色的禁锢性规定以及以性别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女性空间的束缚,特别是以男权为主导的家庭关系与婚姻制度等”[1]72。女性哥特小说自出现开始就是女性作家借助哥特小说中的典型意象来表达女性的痛苦与无助。女性哥特小说中给女性带来恐惧和焦虑的幽灵区别于传统哥特小说中的非人的神秘力量或者邪恶的家族史,而是社会对女性的禁锢性规定和对女性人际关系和生活空间的束缚。小说中玛丽的女性焦虑与恐惧正是源自她所生活的草原和铁皮屋这样的幽闭环境,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尤其是生育的恐惧,殖民地种族制度下父女乱伦的禁忌关系,以及小说所有的男性角色对她施加的禁锢和压迫。
玛丽生活在南部非洲。她的童年充满着灰色的回忆:爸爸总是“醉醺醺的,辛酸的妈妈,还有那座风吹得到的小屋子”[3]30。“她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在世上”[3]30,这种孤独的人际关系使女主人公禁锢自我,不愿长大。“她的朋友都把她描写成一个秀丽的金发碧眼的美人儿,因为她总是孩子气”[3]31。但是当她自由自在地“到了三十岁,生活没有一点变化”时[3]34,她无意间听见别人对她品头论足,谈论她的婚姻状况时,她陷入了来自社会对女性角色规约的恐慌。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她遇到了迪克,并且草率地决定嫁给性格懦弱的迪克,搬到了农场,住到了在草原的小房子里。非洲的乡村炎热潮闷,铁皮屋顶让这所小房子热得像火炉一般。“克莱尔·卡亨在《哥特镜像》中指出,哥特小说中的城堡构成了女性身体的隐喻;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身体使她感到不自在甚至是怪异的,因为它禁锢了女性的自我,给她带来恐惧”[1]73。小说中,玛丽一直想把这个铁皮屋顶换掉,她多次求助于丈夫迪克,而丈夫迪克每次都以家里没有钱作为托词而拒绝她。事实上,迪克会在别的事情上动辄花掉50英镑。小说中玛丽所处的环境——偏远的草原和密不透风的铁皮小屋,构成了小说中女性身体的隐喻。夫妻俩与世隔绝的人际交往,燥热潮湿的生活环境和捉襟见肘的生活境遇加剧了对玛丽的禁锢,使玛丽不堪忍受,让玛丽感到窒息。这既禁锢了玛丽女性的身体,也让她所有的女性幻想破灭。伊莱恩·肖沃尔特在研究美国女性哥特传统时提出,密闭的空间是美国哥特小说中普遍存在的意象,它象征着将女性禁锢在使其窒息的父权社会,同时这又是女性作家“表达女性内心隐秘的抗争、幻想和恐惧”[2]127的文学载体。作者莱辛对玛丽的家的描写运用陌生化技巧,使读者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只有铁皮屋顶的家和与世隔绝的草原农场就是玛丽的牢狱,在这个人为的牢狱中无助的女性无法逃脱男性权威的控制与禁锢,玛丽感到恐惧、愤怒,继而因为无力摆脱而逐渐癫狂。有评论家认为,女性哥特文本中的女性正是以“歇斯底里式的疯女人”的形象向读者展现无法言说的自我,向男性压迫做出无言地反抗,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反抗带来的常常却是女性的毁灭。
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迪克是男性形象的一个代表。正是与迪克的婚姻使玛丽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男性的压迫和对自己身为女性的恐惧和绝望。与迪克结婚之初,玛丽对生活寄予厚望。她希望通过婚姻能够摆脱生活的困境。但是迪克懦弱无能,意志薄弱,对玛丽的需求置之不理,这些都无法给她带来安全感和依靠。性格精明强悍的玛丽只有在丈夫病倒的情况下,才出外管理农场。这一度让玛丽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她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通过努力获得成功,实现自我价值。但是短暂的希望终究还是破灭了。玛丽发现自己在重复母亲的命运,或者说是在重复千百万殖民地女性的命运。女人仅仅因为其女性身份而遭受压迫和惩罚。玛丽发现自己在慢慢变成母亲,经历着和母亲一样痛苦的生活。这让她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她害怕被动地生活,像母亲一样遭受生活的惩罚。女性批评家William Meissner对“歇斯底里式的疯女人”表现出的偏执性格成因进行了细致地阐述。他指出,偏执性格的女性常见于权利关系歪曲的家庭。在男权制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女性毫无意外地沦为家庭权力关系中的弱者和牺牲品。她们没有自我意志,无法为自已言说。这样的权力关系和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身体引发了女性对自我身份、女性生理和女性生殖的恐惧和厌恶。小说中,玛丽来到农场后,感到自己并不是和丈夫开始自己新的生活,而是又回到了童年时母亲绝望的生活中。她好像“看到母亲无休无止地筹划家务,缝衣补袜。她突然跌跌撞撞地站起来,发了疯似地,好像是自己的亡父从坟墓里送出了遗嘱,逼迫她去过母亲生前非过不可地那种生活”[3]52。传统哥特小说中,女主人公被占有或被禁锢,但是在历经磨难后被一名强有力的男性拯救和保护,并最终找到幸福的归宿。作者莱辛将玛丽置于极端的困境之中。女性因为父亲的在场,被迫重复母亲的角色,女性因为其女性身份永远无法摆脱自身的困境从而走向癫狂。这正是女性哥特小说的主题特征。
玛丽害怕自己变成和母亲一样的人,更遭到了来自她周围所有男性的压迫和折磨。哥特小说中具有神秘力量的人通常以毁灭者的形象出现,将小说带入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对殖民地女性来说,黑奴摩西就是殖民地文学中白人小说家们所创造的具有神秘力量的“毁灭者”的代表。玛丽从小就被母亲灌输仇视“黑鬼”的教育。虽然玛丽成年后接受了民主思想,但种族歧视已经深深扎根于她的思想深处。她对黑人有着本能的敌意和毫无来由的恐惧。殖民地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懒惰野蛮”的黑奴形象显然是白人统治者的“他者”形象。但是莱辛为她的作品中的黑奴塑造了完全不同的性格和特点。首先“摩西”这个拯救者的名字使这个黑奴形象担负起拯救玛丽与水火的英雄人物。玛丽对摩西的感情是矛盾而复杂的。摩西身材魁梧,在玛丽遇见摩西的时候,“她觉得自己落入了这个佣人的掌握中,她感到一阵及其强烈的恐惧,一种深沉的不安,她没有一刻不意识到他的存在”[3]163。玛丽时常扬起鞭子抽打摩西,但是在她的心中会掠过一阵恐惧。但是在这个幽闭潮闷的生活环境里,摩西给玛丽她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他给予玛丽的安慰和希望又让玛丽沉迷其中。作者莱辛颇有用心地将传统哥特小说中的“拯救者”形象赋予了摩西这个带有“拯救者”隐喻意义的黑人。摩西强壮的身体和体贴的安慰慢慢唤醒了玛丽被压抑和禁锢的爱,使她的女性意识慢慢复苏。但是在殖民地种族背景下,玛丽无法摆脱压力而像对待狗一样地侮辱摩西。摩西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愤而杀死了玛丽。“拯救者”黑奴摩西无法真正拯救玛丽,而是将玛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作者莱辛将摩西和玛丽的角色置于复杂、对立的社会关系中:白人/女性/主人/受害者—黑人/男性/奴隶/拯救者(谋杀者)。玛丽对摩西有着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时而拒绝时而引诱,时而残忍时而充满感激,时而感到恐惧时而感到安慰。这种复杂多重的殖民地禁忌关系给读者营造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怪异、恐怖和陌生的气氛。
女性哥特小说中另一个常见的毁灭女性的男性形象就是“父亲”。在玛丽的童年生活中,父亲对玛丽的心理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童年的玛丽非常“憎恨自己的父亲”[3]2。父亲在玛丽童年是给她带来的精神创伤是玛丽对男性产生恐惧的根源。父亲酗酒、懦弱,使母亲在郁郁寡欢和极度贫困中死去。成年后的玛丽以为摆脱了父亲的影响,她有了自己满意的工作,和朋友交往得心应手。但是玛丽的衣着和行为与她的实际年龄明显不符。即使年逾30,却还是身着童装,仍然住在“女孩”俱乐部。在她决定改变现状,和男人接触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位老男人。那个老男人要和她亲热,玛丽觉得他就像父亲一样,让她感到恶心。父亲的影子笼罩着她的生活。在玛丽童年,父亲对母亲和玛丽的所作所为让玛丽对男性充满厌恶和恐惧。在玛丽昏迷的时候,她梦见了自己的父亲。自己与父亲正在做游戏,父亲把玛丽的头按在自己的膝盖上,让她抬不起头来。玛丽闻到了父亲身上散发出的不洗澡的肮脏气味,感到闷得透不过气来。这种明显带有性色彩的动作和所暗示的父女乱伦关系正是玛丽感到恐惧的原因。“窒息”是女性恐惧的具体表现之一。玛丽害怕重复母亲的命运和悲惨结局,害怕父亲与她发生乱伦关系。弗洛伊德指出,“文明的建立,就是一则哥特故事。不独是精神病患者,所有的人都有变态的、乱伦的、谋杀性的梦”[4]290。“乱伦”是人类文明中违反社会道德和伦理的禁忌话题。19世纪哥特小说中的乱伦情节正是使小说带有一种无名的恐怖和怪异的元素,是带给家庭和主人公毁灭的决定性力量和使人产生恐惧的根源。作者莱辛将“乱伦”这一哥特元素融入到玛丽与父亲,玛丽与黑人奴隶摩西的关系之中。梦中玛丽与父亲隐喻的乱伦关系和玛丽与黑人摩西发生的种族禁忌关系,使黑人摩西与白人父亲的形象合二为一。“土人慢慢地走近前来,那么猥亵,又那么强壮。他好像不止受着他的威胁,而且还受到她亡父的威胁。这两个男人合并成了一个。玛丽不仅闻到了土人的气味,还闻到了当年父亲不洗澡的那股味”[3]175。由此,作者莱辛完成了对传统哥特小说中乱伦主题的超越:女性仅仅因为性别而受到惩罚,无法逃脱性别规定给女性带来的毁灭。
小说中女主人公玛丽遭受了多重的压迫——幽闭的生活环境,遭受母亲一样的命运,男性带给她的压迫和伤害。这些都成为令她感到无法挣脱的恐惧,一步步使她走向崩溃和毁灭。
二、凝视与权力
萨特,拉康和福柯都对“凝视”进行过详细地论述。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就指出,凝视是构建自我主体性的过程。凝视者给被凝视者带来压迫,从而确立了被凝视者的他者身份。拉康探讨了凝视与欲望的关系。而福柯则以全景敞开监视理论探讨凝视与主体建构的关系。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凝视与权利、欲望和主体性构建等同起来。凝视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存在作为一种权利参照关系存在。那么男性作为主体的凝视和女性作为被动的客体的被凝视背后的权利关系,正反映了女性在男性凝视下彻底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力量和价值,是“为他的自我”,是男性奴役下的女性。小说中玛丽在男性角色的凝视之下,逐渐失去自我进而走向癫狂和毁灭。
父亲对玛丽童年时代的影响使玛丽病态地保留着穿童装的嗜好。玛丽与年龄不符的衣着打扮和羞涩天真的行为正是说明女性成为男性凝视下的他者的投射形象,女性仅仅是被物化了的他者的欲望对象。在玛丽遭遇生活危机时,玛丽去看电影的次数更多了。玛丽把自己隐藏在银幕之下,想通过看别人的故事来缓解自己的尴尬处境。玛丽试图通过凝视的行为而成为凝视的主体以求与男性的凝视平等,从而建立自己的女性身份。但是这一愿望却恰恰由于自己的女性身份而破灭。在男女权利关系中,女性是男性凝视下的符号和产物,是男性欲望的客体,女性的主体性被剥夺。小说中,玛丽始终无法逃避男性的凝视。迪克尤其厌烦电影,但是在他生活陷入困境时,他还是走进了电影院,试图通过看电影麻痹自己,逃避问题。“他呆望着各个出口处挂着的布帘,看到从上面什么地方投下一团光亮,照见了一个脸蛋儿和一头亮闪闪的浅棕色头发。那张脸蛋儿好像浮在空中,渴望向上浮去,在奇怪的绿色灯光之下,显得艳丽非凡”[3]42。“他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张可爱的、飘飘忽忽的脸蛋儿”[3]42。迪克迷恋起他所注视的女人。然而在他走出电影院之后,玛丽平淡无奇的面孔让他大失所望。这个被凝视的对象并不是玛丽本来的样子,而是来自迪克的想象。由此,女性自我就消失在男性的想象之中。在萨特看来,主体间的相互注视是不可能的;一个注视不能自己注视;我刚一注视一个注视,它就消失了,我只不过看见了眼睛。而凝视的主体与被凝视的对象二者之间的冲突是“为他存在”的原始意义,这就从本源上决定了凝视者和被凝视者之间的关系是冲突而不是对话,是压迫而不是平等。
这种凝视关系不仅体现在白人之间,也微妙地反映在玛丽与黑人奴隶摩西的权力关系中。玛丽刚刚遇见摩西时,“那黑人居然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玛丽,这实在使玛丽愤怒到极点”[3]151。白人女性成为黑人男性凝视的对象使女性遭受双重的压迫。在玛丽与摩西关系有了变化后,访客托尼看到“摩西站在她的身后,替她扣好扣子。瞧那土人的神态,宛如一个溺爱妻子的丈夫一般”[3]200。在此,玛丽成为第三者凝视下的被凝视对象,在这组像画中画一样的复杂的凝视关系中,女性沦为最底层的牺牲品。作为被他人凝视下的女性,玛丽总是在被男性凝视、被定义,最终逐渐陷入沉默和歇斯底里的疯魔状态。女性作为男性他者的存在,无法逃脱这个命运。小说结尾,玛丽骨瘦如柴,整日沉默不语,眼神涣散。这与小说开篇玛丽童年时所见的母亲形象如出一辙:母亲“骨瘦如柴,一双亮闪闪的眼睛病态,又含有怒意”[3]28。玛丽完完全全地复制了母亲的命运:女性失去自我,失去自我言说的权利。这种身体的残缺与精神的疯癫正是父权暴力的产物,是男性凝视下女性无法逃脱的结局。这种令人绝望的结局正是莱辛唤醒女性意识的有意安排。
结语
传统哥特小说中,女性主人公发现她所遭受的威胁和恐惧是毫无根据的。故事中的女性凭借自己的勇敢机智,或是英雄男主人公的出现,走向完美的结局。女性恐惧最终消失,女主人公摆脱恐惧而走向幸福。这种完美结局使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也得到解脱。但是,小说中,女主人公玛丽一生都陷入来自酗酒的父亲、懦弱无能的丈夫和黑人情人摩西的恐惧之中。这些人进而导致她的毁灭。莱辛将哥特元素融入到小说之中,真切地展现了女性所遭受的来自社会和男性的压迫而最终走向毁灭,以此鼓励女性在父权社会中重构女性身份的意识觉醒。
[1]林斌.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论女性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J].外国语,2005,(2):70-75.
[2]Elaine Showalter.Sister’s Choice: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M].Oxford: Clarendon,1991.
[3]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蔡满燕.男性凝视中女性的悲剧命运——重读《长日入夜行》[J].剑南文学,2011,(10):32-34.
A Female Gothic Art in The Grass is Singing
WANG Xiao-qi
(College of English,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00,China)
The Grass is Singing depicts the miserable destiny of a female character Mary in the South Africa in the apartheid.Some typical elements in female gothic novels,such as the closed environment,fear,incest,gaze under the males,are demonstrated delicately to persecute that women suffered and advocate the awakening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females.
The grass Is Singing;female gothic;fear;gaze
J64
A
1008-2395(2015)04-0052-04
2015-06-18
王晓琪(1976-),女,大连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