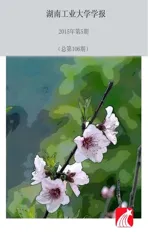“和解”难题与郑小驴的小说
2015-03-17刘长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刘长华,杜 凯(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和解”难题与郑小驴的小说
刘长华,杜 凯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 要]郑小驴小说中充分地书写了“和解”难题,总体表达了主体性与世界的分裂,其主要表现为:人际之间的心灵难以沟通,作为农村人共同的价值支柱——鬼魅崇信正在瓦解,个体在“无名”场域中的抗争之无效。其基于作者的生命体验,与文学史的血脉相连,具有思想史的深度,并由此显示出作者良好的诗学意向和创作前景。
[关键词]郑小驴;“和解”;人际关系;鬼魅崇信;个体抗争
杜 凯(1989-),男,四川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影视批评与创作。
这些年来,“80后写作”业已被固化成一个文学史范畴,其所指称的意义内蕴是明确与昭然的。毋庸讳言,“暴力书写”“血腥意象”等自是题中之义并几成人们指责这一文学群体或文学现象的口实之一。诚然,80年代中期出生的郑小驴也涉足过相关的题材与情节,譬如《赞美诗》《蚁王》《大罪》等等。但,以我观之,它们已经与通常的“荷尔蒙诱因”相去甚远或者说是对其实现了极大的超越,与其他相关的作品一道被统摄在“和解难题”之下,担负起作者对主体性与外在世界难以弥合这一沉重思考之职责。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探询自不待言既是亘古以来的文学主题,更是哲学母题,随着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勃兴,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马塞尔等在上面倾心耕耘,成果迭出。我不认为郑小驴与海氏等人的文本产品有着怎样程度上的交集,但这不妨碍他以体验的方式道出个人在生存论上的创见,并由是透射出作者不同凡响的思想穿透力和在主题挖掘上的深度。总揽起来,郑小驴在“和解难题”上的体验与思考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体现。
一
“古往今来曰世,上下四方曰界”,人文视域下的世界是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个板块组成。郑小驴在《少儿不宜》等作品中对原本和谐旖旎的自然环境与钟灵毓秀的温泉被商品经济鲸吞蚕食、“伤风败俗”、糟蹋不堪深表忧患。自不待言这也是主体性与世界分裂的表现之一,它正与小说中的一个细节——主人公“游离”在破庙中与“蛇”相安共处,即两块还不曾污染的心灵处女地形成鲜明对比。但他断断不忘将目光聚焦在人文和社会之中。“和解”难题在其小说表露出最为明显、最为直捷的精神形态就是人际之间的心灵难以沟通。
1.伦理关系的僵硬失和。“伦理是一种客观的自然法则,是有关人类关系(尤其以姻亲关系为重心)的自然法则”[1],确乎“伦理”更侧重于“姻亲关系”,这是它与“道德”的一大区别。在“亲亲”的文化语境中,“伦理”失和是大逆不道的。“五四”对“伦理”大加棒槌,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抨击,这可谓是最大也是唯一的缘由和表现,尽管上演的是“父子冲突”“婆媳矛盾”“兄弟情仇”……郑小驴小说中的伦理关系失和有缘于两代人观念抵牾的,但更有出于他因的,情感撕裂的图景庶几无处不在,一如海德尔格所谓的“烦”“畏”令“此在”无处遁逃[2]。《没伞的孩子跑得快》中的“父亲”对“叔叔”的愤懑,《少儿不宜》中的“伯伯”对“堂哥”的“恨铁不成钢”流溢出的是双方视高考作为改写命运的工具还是作为价值依托的意见相左,折射出附赘在当下教育制度身上的“罪与罚”。《等待掘井人》中讲述了农民阙国清身上由于被赂上“出身不好”的阶级印痕而吃尽苦头、备受欺凌,这是因为他父亲被抓为壮丁并最后和国民党政府一道溃退到了台湾。阙国清对乃父心生怨怼,小说中直抒胸臆:“阙国清恨他父亲简直恨入了骨”,就是垂暮之年的父亲终究叶落归根,回到他身边,在情感上、在经济上百般补偿与救赎,都难以销殒那些不平之气。肇造仇雠的帮凶有一言难尽的历史、无常的命运,但罪魁祸首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生存语境和思维模式莫属。小说隐喻这种隔阂、这种情感的焦渴到了上天都无法缝补和滋润的地步。《飞利浦牌剃须刀》中的儿子杜渊怨恨父亲杜怀民以至于发展到两人拳脚相加,咎其因由便是儿子埋汰父亲无能给他买起婚房。“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种种伦理关系失和不言而喻在郑小驴笔下无法一一呈现出来,但上述足以昭示出亲情的裂变、人性的蜕化在当下已经昭然若揭。亲人之间都无从沟通,源自天然的血缘关系被无情地割斩,意味着人之共性的稀薄和阙如,剩下来的当然只有孤独、异化、蜕退。难怪乎,秋红(《入秋》)面临着被养父强暴时,她由衷地感慨:“她不知道该往哪走,这个世界上又还有谁该值得她信任。”
2.他人的世界进不去。伦理是从与主体有着血亲关系的人那里切入的,没有这层关系的他人世界在郑小驴的笔下是完全进不去。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有延宕着卡夫卡的《城堡》、安部公房的《墙》等精神血脉的意味。《赞美诗》被不少评论者看好,也是郑小驴这一类主题作品中的佼佼者。小说中的“他”与“她”素不相识,意外地成为合租同住的孤男寡女。同在一个屋檐下,“他”生性自卑,由自卑而自持,“他总觉得,她和她们有些不一样,给人一种清新脱俗,干净透彻感。他喜欢这种与众不同的异质,仿佛为他而存在”,“她”简直就是一首赞美诗,令“他”灵魂飞升。两人就保持着距离、互不干涉,“他”从距离中获得无与伦比的美好遐想和精神净化。在“她”熟睡之际,“他”闯入“她”的房间,“她”的淡定和无暇让他“思无邪”,“她的裸露部分让他产生了不可遏抑的罪恶感。他为自己的卑湿感到羞愧”,让“他”只能心无旁骛地做着一个守护神。“他”的“守护”竟然“医治”好了“她”的“失眠”。这一切成为带有生理残缺的“他”在生活中努力找寻到生存的理由。“她”是“他”心目中的女神,然而,当“他”偷听到“她”在背后道出“他”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和毫不留情指出“他”的身体缺陷时,“他”被打回原形了,掉入尊严的冰窟之中——“她陌生得让他怀疑自己从未见过她。她和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切不过是幻觉”。说得多么透彻——“她和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确乎“他”就是“她”内心世界的“外省人”,留给他的只有假象,这就是反讽。与《赞美诗》异曲同工的《和九月说再见》,人如其名的女主人公瓦蓝对自己痴心相恋的男友钟楚独自干了那么多令人咂舌以至于羞于见人的事情毫不知情,钟楚作为“青青子矜”的大学生其内心已是复杂莫测得到了匪夷所思之地步。《枪声》中的公安老郑明白自己被郑时通愚弄后,发出感慨:“我以为我是最懂他的人呢……他娘的这世界谁也不可能懂谁”,并向小娄怒吼道:“你懂我吗?你懂我吗!?”这同样是注解,到了令作者不能不代言的地步。《秋天的杀戮》中的“博”同样让人看不懂,故事虽然是在写史但更在讽今。
3.对于别人的“证求”不以为然。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罗杰斯认为,“真实”“接受”和“移情性理解”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三大条件[3],进而才能自我确证、自我实现。问题是在当下,这些条件都一一沦陷,所以现下就信任危机泛滥,孤独个体就此蔓延。人际关系的恶化是与自我的证明和寻求理解互为表里、呈恶性循环的,这点弗洛姆也有同感。郑小驴笔下的老李《石门》在某些行为上就和这些心理学观点相当共鸣,其标题“石门”笔者认为其寓意心扉封闭、难以敞开自我。老李曾上演过非常态的“爱的神话”,他和阿莲的爱恋跨越了国界,跨越了世俗是非,也跨越了生死。老李在战场上不是出生入死的英雄,但他为了“人鬼情未了”,却主动踩踏地雷,以除阴阳两隔,他是在用生命诠释“爱”的本义。人没有死成却落下了终生残疾。他并不甘心,他与阿莲举行了“冥婚”,让阿莲来陪伴着灵魂孤独的他。老李的这一“英雄”事迹起初令人动容,也给了当下那种建立在金钱物质等基石其实脆弱不堪的爱情一记讽刺。问题是老李在有过不轨的举动之后,无论老李怎么自诉身世和寻求人们的同情与理解,人们再都难以相信他了,判定他是鬼话连篇。孤独中的老李只好采取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手段来解救自我的封闭与凄然。因此整个过程就滑入恶性循环的陷阱之中,老李失掉本有的生存轨道。他越想向人家证明点什么,得到的是更大的不被信任。与《石门》堪称姊妹篇的是《让所有的猪都活着》。该小说中的“姑父”本是警察因涉嫌刑审过当,由于心生忏悔和戒意,脱离岗位并落下心理障碍。后来面对别人的挑衅,他都不敢正当防卫,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亮出自己的警察身份,希望能起到警示作用,但效果适得其反,他越是强调自己是警察,别人越是觉得他是胡说八道、以谎言来行骗和壮胆,最后逼着“姑父”不得不再次就范——动粗。
二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郑小驴小说中的鬼魅叙事是比较丰沛发达的[4]。大家注意到郑小驴小说与鬼魅叙事的联姻很大程度上是由巫楚文化、梅山文化的撮合使然。巫楚文化信奉鬼神,这是它的特色和魅力,表现出难以遏抑的生命冲创力,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纳在“赋魅思潮”之列。郑小驴说他自己见过鬼,在一次访谈录中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见到过鬼的情形。[5]在其描述中,鬼不但不可怕,似乎还挺慈爱的。鬼魅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是深沉的并有着非同寻常的寄寓。确乎,鬼魅在巫楚文化中起着准宗教或原始宗教的效用,作为一种信仰,它以价值体系方式的存在,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也部分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非常态的方式起着承担一些人的精神支柱之作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问题在于20世纪同样是一个“祛魅”[6]的时代,在功利主义、所谓科学与理性、非常态的人文语境高歌猛进的大潮中,鬼魅信仰的价值空间变得越来越逼仄,一如《少儿不宜》中的“游离”一把大火烧掉了“南岳庙”那样;而另一方面社会病患和心灵困惑骤增起来,“和解难题”自在兹列。
1.迷信科学与“祛魅”之间的困惑。当代“祛魅”的最强的动力是科学和理性。科学和理性所释放出无与伦比的能量与它们一往无前、君临天下的精神姿态,导致人们对科学产生新的崇拜。但无论从逻辑还是实践而言,科学都不是万能的。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曾在《科学史教篇》《破恶声论》等就明言过,所以他最后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7]。在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上,郑小驴是有着强烈的生命体验的,他对科学是存疑的。在他看来,科学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一把利剑,问题是它极有可能成了双刃剑,给人与自然关系上带来新的矛盾和困惑。在《等待掘井人》中,作者藉助小说人物阙国清之口说到:“现在的人都不信神信鬼,都只信自己,这一世过好就好。”该小说安排了一个故事背景,即“石门”处于空前大旱之中。“算命的李瞎子曾说,石门之所以大旱,是因为这地方的风水被人破坏掉了”,“风水”观念是与鬼神崇拜相连。大旱的原因果真如此吗?果真如此。其理由就在于由于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不惜伸手向大自然索取。阙国清家安装了空调和冰箱等现代科技产品,以这些来消暑避夏。而这些科技产品恰是需要以水发电来支撑,科技产品所耗排出的热气热量定会加剧整个气候升高、旱情升级的。所以,“等待掘井人”也就意味着大家都在竞相开发地下水资源,都是以“负性”对抗“负性”的思维方式展开,整个本是“顺其自然”的生态链条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不正是“风水遭破坏”的表征?科学与自然之间的“和解难题”,大约正是存在主义哲学曾指出的“深渊意识”的具象之一。小说“残忍”地设计阙国清去死,医学再发达也不能最终解决生命中的一些问题。“赋魅”建立在对自然有所敬畏的之上,建立在人与自然相安共存之上;亦大约正是出于作者这种意识,《大罪》中小马吓唬那些抓泥鳅小孩的话是“水稻田有鬼”,《枪声》中打猎的郑时通死在闹鬼的“猫耳朵”茶山里。
2.人性裂变与“鬼气”附体的胶着。郑小驴的写作青春期并不拒绝与生理青春期同步,作品总回响着初涉人世者对世界的复杂性和莫名状的讶异、领悟甚至无奈感。《弥天》中写道“我”偷吸旱烟:“那是一种世界上最醉人的味道,令人麻木不醒。我的脑海中空白一片,晃晃悠悠穿过陌生的阁楼长廊,有一种声音悄悄地提醒着我,瞧,世界就是这个鬼样子。”从中是道出他对“鬼”与“醉”之间关系的理解,此“醉”可诂为复杂与茫然等,表达了青年人常有的那种心理状况。现代社会莅临,科学与理性大行其道,“鬼魅”被日趋挤兑,人们不再奉信,正如郑小驴在《最后一个道士》《蛮荒》中以悲怆的笔调所叙述到的;与之相反相成的是,人性却变得让人难以捉摸起来,甚至荒诞透顶到了正如上文中所分析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在郑小驴看来,这正是“鬼气”附体之时,从而显现出思想深度和对生理年龄的精神超越。文化上“祛魅”与心灵上的“赋魅”胶着,压夹在中间的正是“和解难题”。《枪声》凝聚了这一环节上的思考,小说在结尾部分写到:“小娄本是不怕鬼的”,确乎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一个逻辑推断训练有素的警察而言,一切本应如此。问题的是郑时通表面上光鲜正常,但他逼着别人睡他的妻子,他在想别人给他圈套,他犯有家暴……总而言之,他整个人生的背面是荒诞不经、莫名其妙的,所以情同手足的老郑最后感慨系之:“他说我是他唯一的朋友的……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而警察老郑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说自己对女性毫无兴趣了,却又在和人家偷情。对于这些谜团,小说从中给出的解释就是撞鬼、鬼魂附体了。周遭一切如此扑朔迷离,小娄“感觉到一股从未有过的陌生感从心底流过”,张开颤抖的眼睛,似乎真有鬼影幢幢了。多一份对“鬼魅”崇拜,内心就简单一份和踏实一份;内心多一份复杂,“鬼魅”就多一份附体,搅得你心神不安。问题是现代人的复杂多方、裂变扭曲已成常态。
3.珍爱生命与崇信“鬼魅”错位。生命与“鬼魅”从字面来看势不两立的,种种关于“鬼魅”勾魂、吃人的想象与传说一路流传明证了这点,人们崇信“鬼魅”,就是希冀藉以保全生命,“崇信”是生命与“鬼魅”之间的润滑剂,起了调和作用。但在某些特殊语境下,珍爱生命与崇信的“鬼魅”之间脱节。不言而喻,个中的责任无疑就是要由语境来承担了。在郑小驴的文学世界里,这个语境就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郑小驴的重要写作题材,诸如《我略知一二》《入秋》等多篇小说均有涉足。《鬼节》更是集珍爱生命、崇信“鬼魅”、计划生育等三位一体予以思考的结晶。“鬼节”按照湘西南农村的风俗是农历7月半,祖宗鬼魅回家,活人子孙就得烧纸衣纸钱来祭祀,祈求祖宗保佑。在这个节前节后,到处笼罩着一派神秘诡谲的气氛。小说中的“母亲”梦见自己和死人在抢东西了,担心自己老命不长了。于是乎更心急火燎地请道士给自己做法事。而正是这个时候,负责计划生育的村支书八伯闻到了风声,得知“我”大姐已经“非法”身怀有孕,他便像幽灵一般地闪忽出入在“我”家里外,并似乎藉此要挟“二姐”和“母亲”与他家成婚,他才是真正闹得大家不得安宁、心怀不轨的“活鬼”。如此一来,“大姐”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躲”计划生育,以至于最后“躲”到地窖了。“大姐”在地窖与蜈蚣作伴、与缺氧为伍,受尽磨难,最终几乎葬送生命,流产了。一个不曾见天日的生命就在鬼节中被死亡带走了,成为新鬼。信奉鬼魅的“母亲”没能如愿——保全外孙的生命,这与鬼神崇拜的本旨背道而驰。说到底,根本原因就在于“鬼”不再是阴间的,恰是那些别有用心、心术不正的“活鬼”利用极其不正常的语境,糟蹋人们的信仰,也扼杀人们的生命。这种“人”“鬼”颠倒的世相无疑只能导向“和解难题”的不归之路。
三
鲁迅通过自己独到的生命直觉,发现了“无物之阵”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独有奥秘。它“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和仇,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这就是‘无物之阵’”[8]。这是一种“荒诞”意识,也是一种深渊体验,与存在主义哲学是有着深刻的精神共振。与这种意识和体验十分近邻的是,郑小驴也是深刻地感受到了个体在“无名”即难以名状、难以把握的场域中的无能与无奈。个体可能有所抗争,当最终往往是无效,以悲剧性地收场,要不是被迫归顺,要不是直接被吞噬消弭。个体抗争当然是对“和解”反动,但它的根本意向是对主体的捍卫和葆全。而这种抗争的无效则更是“和解难题”的衍射和深化,对某一具体的主体残忍地剥夺和残杀,事实上这才是最难愈合的鸿沟。这类主题在残雪的《民工团》等作品中也有所表现。
1.“生活在别处”的希冀与幻灭。列维那斯曾说过:“我们在厌倦中怀念着一片更加晴朗的天空,希望逃离存在本身”[9],当下种种以生存体验为基础的存在的确令人们想逃离。这种体验也令捷克作家昆德拉写下了《生活在别处》的经典。逃离主题在郑小驴小说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不少小说的主人公甚至都以“宿离”(谐音“疏离”)“游离”等为命名。《没伞的孩子跑得快》中的“宿离”厌倦了父亲以及他周围的庸俗势力的生活环境,叔父的人格理想令她神往,她付诸逃离,但最终被收领回。“游离”(《少儿不宜》)和“宿离”所面临的生活环境还要复杂,高考、孤独、红灯区、父亲的责骂、网吧、物质诱惑等构成了他的生存,逃离是他本能性的选择,最后他放弃目下的一切,去深圳打工,从而印证着他先前的一席话:“我想当个无忧无虑的小和尚儿……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用去想,就这么晃荡来,晃荡去。”而实际情况是,他“去投靠溜子那位靠卖六合彩坐庄的表兄”,寓意此番逃离绝非是“换了人间”。郑小驴对“生活在别处”的集中性描述与思考便是《可悲的第一人称》。坦言之,该作品是浸染过《鲁滨孙漂游记》《瓦尔登湖》等“梦土”色彩的,也是士人“桃源”情结的吐露。在这片南陲之地上,“我”自食其力,刀耕火种,在不曾开垦的处女地上自由呼吸着远离都市文明的新鲜空气,逐渐淡忘那些痛苦的记忆——因无力在城市里购房和安顿家业,不得不与女友堕胎和分手等。这是“逃离”之后的新生,当然在这片无人区里“我”也是遭遇过生活的荒凉、物质的匮乏、死亡的威胁。没想到护士小乌居然找到了“我”,解救了“我”的生命和危机。两人在这个世界里重新点燃起新生活的曙光,但小乌慢慢就无法忍受这停留在“原始时代的生活”,“她”重新回到北京。尽管“我”誓言:“死我也要死在这里,死在我的地里。这儿是我最后的阵地,是我的战场。我了无牵挂,坦坦荡荡。那些财富,信仰和爱情以及尊严,在这场百年难遇的大雪面前,贱得像个婊子”,但问题是信基督教的小乌怀上了“我”的小孩。“基督教”、丈夫身份、为父责任等因子将“我”拉回现世的“烦忙”之中去。“生活在别处”化为泡影。
2.守望沦为绝唱。通常意义下的守望是对从众心理的抵抗,是对理想的坚守,是对自我个性的捍卫。这个过程是艰难困苦的,这种姿态本身是拒绝“和解”的,但这种守望最终坍塌下来,被裹挟在“平均化”的洪流之中,这正如上文中所说的将形成一个更大的难题。《最后的一个道士》中的道士老铁离群索居,不从流俗,用自己的清苦在书写着对民间宗教的坚信和传承,他收留了子春作徒弟,子春悟性很高,是传承衣钵的不二人选。老铁对此寄寓很高。但子春在岁月的催熟下,选择了下山去遥远的西北当兵,起初还与老铁鸿雁往来,老铁望眼欲穿,总期冀子春早日归来,再造慧根。后来音讯渐稀,子春退伍后,直抵沿海地区以打工为生,彻底斩断了老铁最后一丝幻想。老铁是在用自己的信仰与功利主义、世俗人生作抗争,子春是他的全部希望所在,但最终等来只是一场空无,充满反讽意味。此乃当下的某种象征和真实写照,笼罩着几分凄凉和几分悲壮。这种守望还表现在《1921年的童谣》中的陈云青老人身上。虽然这是一篇“新历史叙事”,但从中所表达作者的创作理念完全是当下的。祖母陈云青气质蕙兰,吟诗作赋,内心高洁。她是有自己的爱情理想和生命追求的。但时运不济,由父母之命,首先是嫁个一个田姓人家,田姓男人不能识文断字,天生大老粗,两人毫无沟通可言,祖母的那些衷肠和孤独无处诉说,唯有付诸泪花点点的诗词,两人还不曾留下子嗣。祖母在建国后改嫁“我”祖父,祖父虽然聪慧,但心性浪荡,他的聪明才智都只属于草根文化,祖母的“雅”与祖父的“俗”依然风牛马不相及,祖母内心之哀苦依然得续写。虽然膝下有了儿女,但遭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她受尽凌辱甚至来自亲生的儿子。祖母内心的超凡脱俗只能在自缢中获得永恒。那些字字珠玑、句句令人动容的诗词表达和见证着“祖母”对生命的守望,但只能化成“此恨绵绵无绝期”。《弥天》的“爷爷”和《赞美诗》中的“他”在某种程度都与“祖母”有着精神血缘,其结局也惊人的相似。
3.“恶”众对主体直接性地“围猎”。鲁迅笔下的“看客”“庸众”是构成“无物之阵”的重要资源,他们好像是具体的但在本质上绝非如此,因为他们具有“穿越时空”的禀性,因为他们更是一种文化习惯的凝结和具化。郑小驴笔下的“恶”众大约也有如此特点。《大罪》中的小马身为一个警察,本应享受体制带给他的恩惠,其人也是一身正气,但他最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燃烧起怒火,杀了人也自杀,诠释了一场“大罪”,但“大罪”的真正罪魁祸首是谁呢?值得追询和深思。警察小马这种“以暴力追讨正义”的缘由是出于一个场域:工资收入与工作强度成反比、房价奇高与廉价拆迁相向、女友分手与无力购买同源、校长贪腐与学校混乱一致等等构成了置身其中令人生不如死的“软陷阱”,众人都像头头看似无形实则有力的恶狼在围盯着他。暴力抑或是杀出重围的突破口,显然这种“和解”是别无选择的,更是恶化版的。《青灯行》《蚁王》等则描述了青少年在成长道路上所遭遇不良环境,这些环境就是就制造问题少年的温床,譬如小马出于良知和江湖义气,找到杀害哥们独生子的凶手了,没想到这个豪不起眼的小孩竟然嗜杀成性,把小马击倒再地,其杀人的理由很简单——“老子还未满十四岁,杀人不犯法”。在作者看来,法律在这里也成了帮凶与教唆。《让所有猪都活着》在我看来就是作者基于对一个强者、一个健康的主体被来自外界的冷暴力胁迫而导致心理病变的体验和想象。“他企图用暴力使这些天真孤傲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改变一切的年轻人屈服”,“以暴制暴”道出了身为警察的姑父的想法,也是道出了年轻人的普遍心理,更是道出了整个社会的潜意识和显意识。问题是“以暴制暴”并不能“让谁屈服谁”,“姑父”失败了,或许这仅仅能吓唬小孩而言。四处充满肉体和精神的“暴力”,四处都是以“暴力”反“暴力”,每个人都活着这个“暴力”的中间。
海德格尔认为,人为自己的主体地位而斗争,“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10];马塞尔指出,造成人们相互隔离的原因是“抽象的观念”和“对象化”[11]等等,存在主义把关于“主体”与“世界”关系的思考推入到了西方思想史中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郑小驴作为成长起来的80年一代,在生存道路上历经过计划生育、农村留守、城市膨胀与高房价、就业难等等,使得他深刻地体悟到了“主体”与“世界”难以“和解”的问题。所以,在他笔下表现出来的世界其分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表达出他对“主体”非常态的忧思,正如他自己所言:“那一刻,我和世界的所有不快,通过写作都达成了和解”。[12]在这点上,郑小驴不自觉或下意识地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碰撞出了火花,这也是他对文学史血脉的承接,因此表现良好的诗学意向和创作前景。这已然无法用“暴力写作”去涵盖其特质,他已经不属于他同时代的文学,他的小说是当下国人生存状态的一面鉴镜。当然,郑小驴强调的“世界”是与“主体”或“个体”对立的,这不同于存在主义所标示出的“主体”,是在“世界”中的“主体”,凸显承担意识。但不必苛求,毕竟他还年轻,毕竟他只是小说家。
参考文献:
[1]姚建宗.法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64.
[2]赵敦华.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09.
[3]单中惠.外国教育思想史[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88.
[4]金 理.郑小驴的鬼魅叙事[N].文艺报,2013-05-13.
[5]谢 琼,郑小驴.为写作和生活的关系而苦闷[J].文学界,2009(5):27-30.
[6]姜智芹.经典作家的可能:卡夫卡的文学继承与文学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95.
[7]鲁 迅.破恶声论[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8.
[8]钱理群.心灵的探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3.
[9]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M].吴蕙仪,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4.
[10]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91.
[1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587.
[12]范亚湘.郑小驴:忧郁的80后[N].长沙晚报,2014-07-18(3).
责任编辑:黄声波
“Reconciliation”as a Hard Nut to Crack and Zheng Xiaolv’s Novels
LIU Changhua,DU Ka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410081 China)
Abstract:Zheng Xiaolv’s novels are in full writing of the“reconciliation”as a hard nut to crack and in overall expression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the world's division.Its main representations are:difficul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deep heart and soul;collapse of worship of ghosts which is the common value of the rural people;invalid resistance of the individuals in the field of“unknownness”.Based on the author's life experience,his novel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deep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And this shows that the author has a good poetic intention and creative prospect.
Key words:Zheng Xiaolv;reconciliation;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worship of ghosts;individual resistance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5.05.001
作者简介:刘长华(1978-),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学难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母题书写”(13YB246)
收稿日期:2015-02-02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5-0001-07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7.425
[主持人语]郑小驴,本名郑朋,1986年出生于湖南隆回。曾任《大家》《文学界》编辑,现就职于海南省作家协会和《天涯》杂志社。2007年开始尝试小说写作并发表,至今已在《收获》《十月》《人民文学》《花城》《山花》《南方周末》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选载,入选多种权威年度选本。著有长篇小说《西洲曲》,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痒》《少儿不宜》《蚁王》,随笔集《你知道的太多了》等。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毛泽东文学奖、湖南青年文学奖、希望杯·中国文学创作新人奖、上海文学新人佳作奖等奖项。长篇处女作《西洲曲》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2013)。其作品得到韩少功、残雪、毕飞宇等众多名家好评,系评论界公认的80后重要作家之一。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位实力文学青年的创作,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郑小驴专辑”,特邀请山东师范大学张丽军教授、西南大学熊辉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刘长华博士等几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小说予以深入解读和论析,以确实增加和推进我们对郑小驴这样一个“80后”重要作家的认知和了解。(主持人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长华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