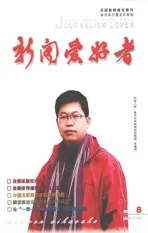知人论世,清通简要——读《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2015-02-27□李彬
□李 彬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这两年,随着网络的勃兴,一种新的学习方式也盛极一时,这就是慕课。由此想到一种类似的形式,即笔录名家授课内容,然后公开发行,如章太炎的《国学概论》、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堪称此类学人向慕的“慕课”。章太炎1922年开讲国学时,并未想着出版,若非一位听课的有心人记录下来,就不可能有《国学概论》传世。这位有心人,就是时年22岁的曹聚仁,中国现代名记者。由于记录《国学概论》,得到章太炎赏识,只有六年师范教育背景的曹聚仁,受聘为复旦大学等名校教授,他的一位哲嗣曹景行也成为当代名记者,并兼职任教于清华新闻学院。与此相似,《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是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期间,由弟子万绳楠记录下来的课堂笔记。
提起陈寅恪先生,总会联想到一些流行的奇闻轶事,如教授中的教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梁启超向清华校长举荐他的理由:他的几页纸抵得上我著作等身。于是,在世人心目中,陈寅恪俨然一位神话人物,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仅看他的名山事业,如巍峨的高头讲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柳如是别传》等,没有一定学问功底的确很难接近。不过,翻开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课堂讲演录,则别是一番风味了,用俗语说是娓娓道来、条分缕析、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用魏晋南北朝的雅言可谓:“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吴均)或如《世说新语》的隽语所言:“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先看一例。唐诗宋词的妙处之一在于声律,为什么汉语诗词不早不晚会在唐宋臻于完善呢?一般解释离不开齐梁文学。作为宫廷艳曲的靡靡之音,齐梁文学在思想内容上自来乏善可陈,《玉树后庭花》更是成为亡国的象征。不过,这些空虚颓唐的文字,在诗歌形式上却玩出了不少新花样,如声律、对偶、练字等讲究。那么,为什么偏偏是齐梁文学对这些格外敏感呢?陈寅恪说,是因为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广泛传播与影响。佛教讲经弘法对声音有特殊要求,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这种社会氛围培育、强化、推动了汉语诗词在声律方面的精雕细刻,如陈先生所讲的四声:
南朝文学界极重要的发明为四声。四声,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的入声以外,复分别其余之声为三声——平,上,去。之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声,是依据并摹拟当日转读佛经的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的三声……中国文士乃据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三声,合入声适成四声。[1]
再看一例。陶渊明《桃花源记》千百年来深入人心,桃花源在哪里也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陈先生旁征博引地指出:真实的桃花源不在南方的武陵,而在今天的洛阳或灵宝(弘农),桃花源人说自己的先人避秦乱的秦,也不是秦始皇的嬴秦而是十六国时苻坚的前秦。当时北方大乱,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囤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2]。这种堡坞如同近代北方的“土围子”,董卓的郿坞庶几近之。所以,陈寅恪的结论是:“在纪实上,《桃花源记》是坞壁的反映,在寓意上,《桃花源记》是陶潜思想的反映。”[3]
中国古代有两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汇流的高潮,一为春秋战国时代,一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前者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从而以一系列文化原典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根基;后者形成儒释道的兼容并包,从而以闳放与雄廓气象开辟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两次高潮也适逢两次乱世,国家多故,天下大乱,翻开这段历史,触目所及不是远交近攻、合纵连横,就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而无论社会政治的崩陷还是文化思想的交融,也不管是礼崩乐坏还是凤凰涅槃,魏晋南北朝又比春秋战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人口的大流动、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碰撞,都在这三百年间达到空前规模。按照马克思精神交往思想,社会层面的物质交往必然激发精神层面的文化交往,魏晋时期就是一个典范。
说起魏晋南北朝,常人难免头大,除了天翻地覆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等大事变——谁人记得八王及其次序,以及五胡十六国、宋齐梁陈、东魏西魏、北周北齐等一系列朝代的错综勾连、犬牙交错,还有一大堆令人目迷神眩的民族及其关系:匈奴、羯、氐、羌、鲜卑、柔然、敕勒、高车、丁零、吐谷浑……面对这样一幅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纷繁图景,陈寅恪先生的讲述却显得风烟俱净,清通简要,让人再次领略了举重若轻的大手笔。借用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的评价:“陈先生把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和文学等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作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纪念陈寅恪先生》)
苏东坡有一句称道王维的名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听陈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程,也仿佛在观赏大画家作画,但见胸有成竹,气定神闲,先是从容地由一点轻轻落墨,然后一笔一画渐次展开,有些笔墨横溢斜出,仿佛可有可无的闲笔,但随着整幅作品一点点展现出来,就看出作者的匠心独运了,原来每一笔、每一画都有讲究,最终凝为浑然一体的神品。吾生也晚,无法亲聆大师的耳提面命,但通过课堂笔录,也能多少领略大学者的风姿,以及有学问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问之魅力。这里,陈先生以通家的慧眼,扭住历史的关键问题,沿着历史的潜在脉络,不仅勾画各色人等的所作所为,而且揭示其间的有机联系与内在动因,就像恩格斯对历史的经典论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4]
有人或觉疑惑:陈寅恪怎么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了呢?他不是一向对此敬而远之吗?坊间不是流传他对“毛公”毛主席的吁请,允许他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吗?的确,作为心无旁骛的纯粹学者,陈寅恪一生对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但并不意味着他不讲政治。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没有不讲政治的,从柏拉图到亨廷顿,从司马迁到陈寅恪,不讲政治也不可能成为大学者。因为学问学问,无非知人论世,而政治就是人事之核心,用孙中山的说法,政治是“众人之事”。陈寅恪也不例外,身处书斋、心系天下。他的政治意识与政治情怀,一方面体现于他的“遗民”姿态,即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指出的所谓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是针对民国;一方面体现于他的学术著述,如代表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正如冯友兰所言,陈寅恪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他游学欧美,转益多师,不图文凭,但求真知,不仅开阔了学术视野,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而且对现代学术的理论与方法也了然于胸,包括唯物史观及其认识论与方法论,故他的学问与研究,“远远超过封建时代的水平”(冯友兰)。一部魏晋南北朝史课堂讲授,可以说就是陈寅恪用鲜活的而非教条的唯物史观审视社会历史大变局的典范。比如,他开篇就用阶级分析法,从曹魏与司马晋的阶级关系讲起,而记录这一授课内容的万绳楠成为新中国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万绳楠的记录时间是在1947年至1948年。当时,陈寅恪已经年届花甲,双目失明,但在学生的记忆中,他一堂课也没有缺过。全部课程一共二十一篇,如同二十一章。第一篇是“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附论吴、蜀)”,第一节是“魏晋统治者社会阶级的区别”,开头与结尾讲道:“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在于: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旺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儒家豪族阶级不得不暂时隐忍屈辱。但乘机恢复的想法,未尝一刻抛弃。曹操死后,他们找到了司马懿,支持司马懿向曹氏展开了夺权斗争。袁绍是有后继人的,他的继承人就是司马懿”。[5]然后,接下来讲西晋政治社会的特征与曹魏大相径庭,而原因正在于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不同。如西晋的选官用人制度——九品中正制,否定了曹操唯才是举、简拔寒门的政治路线,使贵戚子弟入仕晋升得到保证。而他们做官只是为了攫取一己私利,盛行的清谈之风不过是为了猎取“名士”的美名,“既享朝端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陈先生称之为“历史上名利并收的最显著的例子”[6]。在这种“金玉满堂,妓妾溢房”的贪鄙淫僻之风盛行下,西晋政治大坏,危机四伏,于是第二篇就顺理成章谈到西晋灭亡及其直接原因——八王之乱,而八王之乱的直接原因又在于分封诸王的封建制度,以及相应的罢黜州郡武备问题:“州郡由皇帝控制,封国属于诸王。八王之乱所以乱到西晋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无武备,而封国则有军队。”[7]至于西晋之所以选择分封权贵的封建制度,追根溯源还在于司马氏所代表的大贵族、大士族及其阶级利益。第三篇“清谈误国”,承续上述清谈思路,分析西晋灭亡的另一原因。清谈,是魏晋时代的时尚,当时与后世往往目为超然物外,高蹈清远,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而陈寅恪以唯物史观,抽丝剥茧地揭示了清谈背后无所不在的现实政治与思想背景,如血淋淋的司马氏与曹氏的“阶级斗争”。
西晋覆亡,五胡乱华,这些天崩地坼而眼花缭乱的问题,在陈先生循循善诱的讲解中珠箔银屏迤逦开,其间的大脉络、大关节同样一一清晰地展现出来。先是汉代直至魏晋,边地各路戎狄的“内徙”,由此形成中原周边多民族混杂的状况,于是由此涉及五胡的种族以及胡族的汉化、胡汉分治、胡汉融合等问题。再下来,自然谈到五胡乱华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口流动与社会变故。这些内容构成了讲演录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南北朝局面的形成及其来龙去脉。讲演录的后半部分即第十一篇到第二十一篇,则分别讲述南朝与北朝。而无论南朝还是北朝的变动,归根结底还是源于社会阶级以及相应政治集团的分合演化,包括南方士族、六镇问题、关陇集团等。对这些问题的讲述与分析,不仅处处展现了陈先生治学的清通简要,而且也显示了现代学术思想如唯物史观的烙印。比如,他讲“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的”[8]。接着分析三条迁徙的路线与方向:东北、西北和南方。南方一线又为两途,一至长江上游,以江陵为中心;一至长江下游,以建业为中心。长江下游的北方流人,有上层阶级,如“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王谢诸家;有中层阶级,如宋齐梁三朝的开国帝王刘裕、萧道成和萧衍;有下层阶级,如陈霸先。而江陵一线的南来北人,“是原来居住在南阳及新野的上层士族,其社会政治地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辈,他们向南移动自不必或不能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可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这不仅是因为江陵一地距胡族势力较远,比较安全,而且是因为江陵为当日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为占有政治上地位的人群所乐居”[9]。这一上层集团的地位在南朝后期日益上升,梁元帝迁都江陵是其最盛的时代。随着西魏灭梁,这一士族同遭遇侯景之乱而从建业逃到江陵的士族一同成为俘虏,随征服者北迁,“北方上层士族南渡之局遂因此告一结束”[10]。再如,他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指出,南朝商业城市发达,士族喜居都邑,都邑一旦攻破,士族也就被摧毁了。而北方宗族与农业土地关系密切,士族除了在京城与地方做官,都不在都市,因此,北方士族的势力可以延续下来,从而影响此后的历史进程。我们在隋唐的史籍中,还能看到北方崔姓、李姓等士族,而南方王谢堂前燕,早已飞入百姓家。总之,陈先生按照阶级分析法,将南朝历史分为三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宋、齐、梁由北来中层阶级的楚子与南北士族共同维持,陈则是北来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握政权的朝代。 ”[11]
南朝如此,北朝亦然。陈先生是个语言天才,按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的详实介绍:“先生对历史语言学下过功夫。于汉语文之外,还通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满文、新疆的现代语言和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20多种语言。”所以,陈先生对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游刃有余,而北朝的关键恰在民族关系。他于纵览南北对立形势之际,首先抓住的就是这一问题。比如,既然北朝比南朝强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兵力强悍,为什么不能一举并吞南朝,统一天下呢?他一语挑明,“主要在于内部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北朝统治者是胡人中的少数胡人,绝大多数的胡人与汉人都是被统治者,这一尖锐矛盾构成北朝社会政治问题的主因:“北朝整个胡族不及汉人多,统治者胡人又不及被统治者胡人多,以此极少数人统治极大多数不同种族的民族,问题遂至无穷。”[12]苻坚淝水之战一败涂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就是著名例证。而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化解都需要时间,即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逐次融合:“当北朝民族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则南北分;一旦解决,则南北合。因为这个问题一解决,北朝内部便无民族冲突,北朝潜在的强有力的经济与武备力量,遂能发挥出来。这是南朝抵挡不住的。”[13]
北朝的民族问题,主要体现为胡汉之分。由于胡人以征战为业,汉人以农耕为主,胡人是军队的主力,汉人是生产的主力,因此,胡汉之分也就成为兵民之分、兵农之分。经过数百年的演化与融合,这种对立至隋文帝时代逐渐消弭,唐代著名的府兵制就是兵民合一的体制。而这一演化轨迹,正体现了社会的汉化与胡化相互交织的过程:“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族,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都在汉化,虽然深浅不同,也不是整齐划一,但表明了一种倾向,即胡族与胡族之间的融合让位于胡汉之间的融合;以地域区分民族让位于以文化区分民族。”[14]以文化而非地域与种族区分民族——这一见地不仅新人耳目,而且把握了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的民族关系的命脉。中华民族与西方近代历史中形成的民族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中华各族在数千年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中不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血脉,彼此间的区别与差异主要不在地域人种,而在文化习俗,如李唐王朝就是胡人后裔,而每个中国人身上也不知混杂了多少不同的民族血统。所以,陈寅恪明确指出:
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划分,而非以血统来划分。少数民族汉化了,便被视为“杂汉”“汉儿”“汉人”。 反之,如果有汉人接受某少数民族文化,与之同化,便被视为某少数民族人。……在研究北朝民族问题的时候,不应过多地去考虑血统的问题,而应注意“化”的问题。[15]
以北齐皇族高氏为例,他们本为汉人,由于高谧、高树和高欢祖孙三代都在北方边地,“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即鲜卑化了,“高齐皇室自认为自己是鲜卑人,原因即在已经鲜卑化”[16]。如今习以为常的“中华大家庭”,原是有着深厚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大家庭内部无论怎么南腔北调,也不管多么风俗各异,实际上早就“化”在同一个中华大熔炉之中了,也就是费孝通说的“多元一体”。千百年来,大家庭内部即便发生龃龉甚至冲突,最终还是兄弟姐妹,还是中华一家亲,这是一种谁也无法割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血脉!
在南北朝三百年民族交融、文化交会的大潮中,迎来了中华文明第二次辉煌灿烂的高潮,宗白华将其称为第二个哲学时代。大眼一望,满目琳琅: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祖冲之的圆周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文选》,范缜的《神灭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以及一批大文豪、大诗人,包括三曹父子,竹林七贤,王粲、刘桢、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五四诗人、美学家宗白华激情洋溢地写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宏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一曲美不胜收的《敕勒歌》,足以成为魏晋南北朝秾丽多彩文化的一个象征。鲜卑人后裔、元代大诗人元好问为此赞叹道:“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现代诗人流沙河在他的诗话中浓墨重彩地论及这首敕勒族的民歌:
最妙的是结尾的画面:“风吹草低见牛羊”。前面画的是大自然,茂草无边,不见人影,一片寂寞荒凉。天助诗人,忽然吹来一阵猎猎长风,低偃的草丛间显现出点点斑斑的生命来,那是牛羊!这些点点斑斑的活物,或啃或眠或戏,给观众带来了多少温暖!敕勒族的儿女真聪明,赞美自己心爱的乡土,竟不说半句赞美之词,只画画,比我们这些写诗的聪明多了。[17]
范敬宜在清华开设新闻与文化课程时,还专门讲授《文心雕龙》。我在协助他推动毕业生以新闻作品代学术论文的改革时,也要求学生一方面认真研习中外新闻经典,一方面广泛涉猎古今叙事名作,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历史》,从史诗般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到寥寥数笔而形神毕肖的笔记小说,如《世说新语》。如同《文选》《水经注》《文心雕龙》等经典,《世说新语》也是魏晋时代一朵不朽的奇葩,千百年来风行宇内,光耀人间。作品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写,萧梁时代刘孝标为之作注,从而相得益彰,开篇第一则就显得气宇轩昂、不同凡响 (小字为刘孝标注):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贤传曰:“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有室荒芜不埽除,曰:‘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值汉桓之末,阉竖用事,外戚专横。及拜太傅,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反为所害。”
今本《世说新语》有上、中、下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赏誉、容止、伤逝、任诞、简傲等三十六门,总计一千余则故事。其中,记人则流光溢彩,叙事则摇曳生姿,许多生动的轶事或“段子”更是家喻户晓,一些成语就出自其中:难兄难弟、割袍断义、拾人牙慧、咄咄怪事、空洞无物、渐入佳境、望梅止渴、身无长物、肝肠寸断、一往情深、卿卿我我、我见犹怜……对新闻记者来说,《世说新语》不妨作为枕头书,随时翻看品赏一段,不仅涵养心性,浸淫文化,而且也能不断获得新闻写作的点滴启发。因为《世说新语》的一大特征就在于语言精练含蓄、隽永传神。明代学者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鲁迅先生称道:“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拙著《中国新闻社会史》还引用了两则世说故事:
魏武(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容止第十六》)
谢公(谢安)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续晋阳秋曰:“初,苻坚南寇,京师大震。谢安无惧色,方命驾出墅,与兄子玄围棋。夜还乃处分,少日皆办。破贼又无喜容。其高量如此。”(《雅量第六》)
无论曹操的英雄气概,还是谢安的大将风度,无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再看下面一段故事,用“刺、掷、蹍、啮、吐”等动词,将一个人吃鸡蛋、性子急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使人好像活生生看到一个急脾气人的气急败坏: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忿狷第三十一》)
如果说《世说新语》是魏晋时代的私人叙事,那么《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则是宏大叙事。无论私人叙事,还是宏大叙事,都在于知人论世。央视某主持人接受南方某报采访,将新闻的核心归结为一个“知”,即知道、知晓。窃不以为然,新闻怎一个冷冰冰的“知”字了得。但若将此“知”字曲解为“知人论世”,则不失为真知灼见。没有深切的知人论世,如何真切地把握时事、报道新闻,如何展现时代风云、影响社会人生呢?说到知人论世,年轻时往往觉得不算什么,自以为是、信口开河,而阅读日多,阅世日深,才渐渐体会了“却道天凉好个秋”的人生况味。当然,记者不能也不应欲说还休,新闻毕竟属于大说特说快说的行当,而要说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或曰实事求是,更需要知人论世的功夫。比如,众所周知,记者离不开采访,采访离不开明辨,因为采访不是你说我记,不能听风就是雨,而需要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拿下面这段世说故事来看:
王孝伯(王恭)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如果仅听他说的,并信以为真,弄不好就被忽悠了,以为名士不用读书,只要熟读《离骚》痛饮酒就行了。余嘉锡先生在其《世说新语笺疏》里就此所作的剖析可谓善听者也,也正是记者采访所需的本事:“(《世说新语》)《赏誉篇》云:‘王恭有清辞简旨,而读书少。’此言不必须奇才,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王)恭之败,正坐(因为)不读书。故虽有忧国之心,而卒成祸国之首,由其不学无术也。”
陈寅恪的南北朝课程讲演录,不仅让人领略了大家的学术思想,而且也提供了知人论世的典范,至少有两点值得记者借鉴。其一,拨云去雾,抓住要害,也就是政治家办报以及审时度势的要求。其二,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也就是讲好故事的本领。概而言之,一曰清通,一曰简要。
[1]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307.
[2]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20.
[3]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27.
[4]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5]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11.
[6]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50.
[7]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38.
[8]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04.
[9]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11.
[10]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13.
[11]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29.
[12]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96.
[13]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201.
[14]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91.
[15]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248.
[16]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249.
[17]流沙河.流沙河诗话[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5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