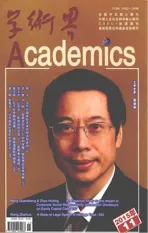从“生之谓性”到“生生之谓性”——先秦主要几种人性论检讨
2015-02-26○吴勇
○吴 勇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江淮论坛杂志社,安徽 合肥 230051)
人性即人的属性,人性论是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有一个“以生谓性”的传统,也即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1〕,是从先天的既成性角度来说人性,虽然孟子反对告子的这一说法,但这一传统当以孟子性善论为代表,他以“四端”之情反推本善之人性,至宋明理学发展为复性论。而成性论由荀子肇始,但荀子明谓“人之性恶”,人要为善就离不开后天的“化性起伪”,但从根本上来说,人性本质上仍然是先天的,没有脱离“生之谓性”的传统。由荀子一路至张载提出成性论。先秦各家人性论基本上都在“生之谓性”的框架内,且以善恶论之。
然而,人性并不单单指先天的自然属性,它还应当包括后天的社会属性。人性首先应当包括自然属性,这是人性概念与人的本质概念的区别。从这一角度来说,以善恶这样的伦理概念指称人性是不周全的。人又是社会性的存在,单从生物性角度无法区别人与自然物,孟子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2〕,这“几希”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传统人性论所重视的人禽之分,且指向理想人格。正如人性的自然性内容包含了所有的自然属性一样,人性的社会性内容也不能仅仅指善恶,它应当包括人的一切社会属性。如果说传统的人性论是在“生之谓性”框架下展开的,那么,同时包含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性论就应当在“生生之谓性”的框架下展开。
一、何为“生生之谓性”
“生之谓性”指人的自然属性,它具有既成性的特点;“生生之谓性”,生生,意为使生者生,涵容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兼具既成性与生成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相互联系的。相较“生之谓性”,“生生之谓性”能够更好地反映人性的内容和指向。
在对中国传统人性论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是在传统固有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也有学者直接把人性定义为人的本质。但在对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反思中,学者们注意到了人的本质与人性的区别和联系。按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也即人的本质是后天的社会属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在这一点上,国内学术界不存在争议,但人性到底是人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人性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意见却有分歧。因此,对“生之谓性”需要在现代话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话语背景下检讨。
俞吾金先生认为,应该用马克思的差异分析方法来分析人性与人的本质,人性只能是人的自然属性,是先天的,不可以善恶论人性,人性的基本内容就是“食色”,人性与人的本质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4〕针对俞先生的观点,张曙光先生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不能简单地把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生理属性。如果把人性仅仅归结为人的生理属性,我们就没必要特别讲人性了,人性无非就是吃喝拉撒睡,和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5〕
从汉字字源上看,性的本字是生,“生之谓性”是有合理性的。现代语言中,性有性质、性能的意思,是物质所固有的属性;但性也含有本质的意思,因而人性与人的本质也是相通的。因为人是社会的存在,人性如果含有本质的意谓,必然有其社会性的一面,但从其根本意义上讲,人性也是人生而即有的。若只承认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那么与人的本质便没有区别,且与“人性”一词的本源不合;若只承认人性是先天的自然属性,那么就只能从生物学意义上区别人与其他动物,孟子说所“几希”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哲学上就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用“生之谓性”来界定人性有先天的不足,而人性与人的本质也不能等同。
俞吾金先生认为,人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吃、喝和性行为”,即告子所说的“食色”,但与动物相区别的是,“食色”在动物是唯一的和最后的目的,而在人则非。俞先生事实上承认了人性是具有社会性的。〔6〕纯粹的先天生理属性的“食色”是包括人在内的大部分动物共具的,而传统人性论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使人性狭化为人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反对告子的人性论。但作为人的自然属性,“食色”处于基础性地位,应包含在人性的内容中。马克思所说的“吃、喝和性行为”正是“人的自然的行为”〔7〕。人与其他动物的这种自然的行为最终指向是一致的,即生命的延续,既包括个体生命的存续,也包括个体和种族生命的延续。要达到这一目的,人之外的其他生物依靠本能和物竞天择,而人则依靠自觉的行为,使人从动物界超脱出来。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人类。中国传统哲学则强调“生生”,生生既是天地之大德,也是人特具的品质。
在中国传统哲学,一切存在者的本性是“生生”,即使生者生。向世陵先生说:“‘生生’具有多样性的内容,从宇宙论的角度看,包括从无到有的创生和有自身延续的化生。”〔8〕创生和化生正是个体生命存续和个体及种群生命延续的两个维度。但这是在把宇宙整体和宇宙万物均看作生命现象的基础上言说的,即从创造之真几的角度而言。若非如此,单从类的不同性来说,自然生命中,无生物没有生命,谈不上生生;人之外的生物的生命延续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本能,它们不会自觉地“使”生者生。因此,人之外的生命的本性可用“生”来界说,即生命的存续和延续。但在人类,生命的存续和延续固然也是目的,但不同于其他生物,人会自觉地维护这个目的,并努力不断提高生命的质量;不仅要针对自己,还要针对家族、社会和整个人类的生命。就是说,人要使自己、他人,乃至人类的生命延续,这“使”的方法在人而言,决非“吃、喝和性行为”可以概括,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行为,这些自然的和社会的行为都是“生生”。可见,“生”比“吃、喝和性行为”更准确地概括了生命的自然属性,但只有“生生”才体现了人的生命的本真属性。
“生生”观念见于《易传》,《易经》六十四卦以乾坤始,阴阳爻的变化便会产生新的事物,每一卦不同爻位又象征着事物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样,事物是变化发展的,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所以说:“《周易》之宇宙是生命宇宙,是一个大化流行的生命世界,宇宙生命之理展现在个人生命之上,个人生命之则契合于宇宙生命之流,二者是融为一体、相互见证的生命整体。”〔9〕《易经》揭示了生命的本性是“生”,生命不是静止的和孤立的,发展、变化是生命的常态。因此可以说,“生”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本性,也构成了人性的自然性内容。区别在于,人之外的生命是受天道驱使的,它没有自觉。人类则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并努力维护它和延续它,在行动上与人之外的生命就有了区别,即人的行为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因此,人与自然物的区别在于,正是通过劳动,人具有了类的主体性,不断地通过创生和化生证明着人的属性,使自己成为超越性的存在。
《易经》初为占筮之书,它的卦、爻辞大多有“吉凶悔吝”等断语,用以指导人们是否行事和如何行事,它背后的预设逻辑就是,人是趋吉避凶、趋利避害的,趋利避害从而成为人的行为的特征。动物的行为也有趋利避害的特征,但它们的行为主要的是依靠本能,动物在行动之前不会有谋划和构想,而人的行为主要依靠知识和智慧的指引。先民讲“无疑不占”,在知识和智慧也不能指导行动时,还可以依靠占卜以求得上帝的指导,因而,人的行为的趋利避害就不纯然是盲目的、本能的,与动物的行为有着根本的区别。人摆脱盲目性所依赖的知识和智慧源自实践,而实践只能是社会性的。趋利避害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
从根本上讲,“生生”首先是人的自然属性,创生、化生体现为人的实践,人的实践具有趋利避害特点,这就决定了人的“生生”品质同样具有社会属性。以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生生”来概括人性的内容,比“食色”或善、恶更为根本,“生生”不仅涵盖了“食色”这样的基础行为,而且指向社会实践。
二、先秦“生之谓性”框架下的人性论检讨
在先秦人性论中,大致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和性可善可恶论等。
道家老庄人性论属于自然人性论。老子推崇婴儿状态,没有社会化的婴儿只有自然属性。对于已经社会化了的成人,老子要求通过无为而治等手段,使其复归于婴儿。在小国寡民的社会里,人的社会化程度也是比较低的。在庄子那里,即使是小国寡民也是不可取的,他要求“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10〕,从而使人完全像动物一样回归自然,智慧、创造性都应该放弃,与他人语言上的沟通都被怀疑,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可能性。在传统语境里,这样的人性是无所谓善恶的。如果说这只是道家理想状态下的人性,那么在现实社会里,人是有欲望和智慧的,智慧的使用是为了满足欲望,但智慧并不足以满足人无止境的欲望,于是,争斗不可避免。老庄有见于此,才要求人回归自然。然而,回归自然状态的人类,真的会避免争斗吗?动物尚且有争斗,甚至社会性的动物还会打群架,人又如何避免?在道家人性论中,自然性的“生”之本性在起始点被忽略了,结果却是要人回归自然的“生”之本性。“生生”首先就是要保障个体生命的存续,面对有限的资源,争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本能,也是万物保持平衡的自然法则,即使是实现了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的无为状态,老庄所批判的争仍然不能消灭。
儒家的人性论滥觞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1〕之说。相近的“性”只能是先天的,也即人的自然属性。人在现实上是千差万别的,这是“习”的原因。孔子的“性”相当于人性的自然属性,“习”就是人的行为因趋利避害而做出的选择,选择的千差万别导致人与人之间相去千里,这一部分是人的社会属性。作为先天的自然属性的人性,无疑是相近的,甚至是相同的,但后天的社会属性并不一定都是“相远”的。在孔子那里,“习”与“远”的关系,并不是“习”必定导致“相远”,而是说“相远”是“习”导致的,但“习”也可能使人保持“相近”。因此,后世以人性论为出发点的政治哲学,都是要通过教化和修养等后天习染使人人“相近”乃至“相同”。
孔子以下,孟子持性善论,认为仁义礼智发乎“四端”,即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恻隐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端”人皆有之,意即“四端”是先天的自然属性,由此反推出人性善的结论。孟子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2〕能够“去之”“存之”的不是自然属性,或者说主要不是自然属性。可是,没有仁义的庶民难道就没有人性、在人禽之辨的意义上庶民就不再成其为人么?这在事实上是讲不通的,解释只能是,性善指的是人的社会属性,同时,孟子的人性指的是应然状态,而不是当然状态和必然状态。因此,虽然孟子也注意到人性中的自然属性,但他以“性命分立”排除了这一部分:“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13〕从孟子的理由来看,人的生理欲望能否得到满足受外部环境的制约,具有偶然性(“命”),而君子、贤圣之行仁义是内在的,不受外部环境干扰。孟子在这里忽略了一个事实,仁义礼智和伦理道德必然以利他为指向,而利他若非专指贤圣,最基本的是满足他人的物质需求,精神上的满足要建立在生理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孟子自己设计的井田制目的也在此。可见,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并不能截然分立。孟子反对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固然不错,但以善为人性内在的先天规定同样不能成立。
从“生之谓性”的角度来说,告子所说的性是没有善恶的,也即没有社会性的内容,与公都子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世硕的“人性有善有恶”论类似,先天的性无所谓善恶,善恶是后天引导的结果。
《易经》说小牛在长角之前要对它进行束缚,防止角长出来之后因为不舒服而顶人。牛因为长角不舒服而顶撞一些东西是它生理发育的结果,顶人并非有意选择,但一旦与人有关,人对牛“顶人”这一行为便有了价值判断,因而需要预防和引导。同样,人性如果与他人无关,便永无善恶之分,但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的行为可能自利利他,也可能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属人的行为因而进入价值领域,才有善恶的判断。因此,善恶并非先天的。
《荀子·礼论》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14〕《荀子·性恶》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为伪。是性伪之分也。”〔15〕荀子以“伪”为改造、完善人的方法,其前提是“明分使群”。人不仅是群体性的存在,也因社会分工而有不同的身份,相互之间需要配合才能最大程度地自利利他。很明显,这种分和群最初是人在社会中通过“争”自发形成的,分和群的规则则是不断完善的,大多数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则,也即大多数人是善的。通过博弈形成的社会相对普遍的善虽然是人一生下来即面对的既成事实,仍然不能错误地以善为先天性的存在。
荀子认为人必有争,关键在于是否“顺”这种争,从而发展了礼学,强调通过教化的路数使人人向善。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显然认为教化过于软弱和不可靠,“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16〕。管子和韩非子都认为人是好利恶害的,韩非子认为,好利恶害是人天然的条件决定的:“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17〕韩非子认同趋利避害是人性的内容,“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18〕,但并不能据此认定他持性恶说,好利只是人性自然性的内容,“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19〕,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好利可以为恶,但也可以为善,因此,好利恶害本身无所谓善恶。韩非子依据人性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认为必须依靠法这种强制手段来调节人们的利益关系。但是韩非子对人性的态度偏向悲观。人并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还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文化使得人可以超越自然的束缚,从而并不只是追求自我的幸福,还有更为根本的终极关怀。这是德性、文化和社会的力量,也是人性社会性的内容和人性的光芒。
在《易经》,趋利避害首先体现在个人的行为上,因而人的行为首先是自利的,人因为这种自利性,在与他人相遇时,便少不了争,荀子有见于此而谓人性恶。从《易经》的角度来看,没有这种“恶”的本性,人类恐怕无法存在,这也是《易经》顺应这种本性、指导人们行事的价值所在。显然,如果每个人都只以牺牲自我而利他为能事,看起来是每个人都“善”了,但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如果人没有自利之心、没有个人利益,利他便无从说起,也没有价值。那么,利他何以可能?这必定是趋利避害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利他能带来自利,另一方面,利他有利于族群、种群生命的延续。因此,利他表现为善,恶则只能为个人带来利益,却损害了他人和族群的利益,甚至也损害了个人的利益。从“生生”自然属性的角度来说,损人利己是最切近和最短视的选择,即使是在动物,损他也可能招致损己,因此,损人不可能是最佳选择。从社会属性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利他是利己的最佳选择,同时也是种群生命延续的最佳选择,善恶由此分界。
三、先秦人性论的价值与启示
先秦人性论固然有失误,但它的价值也是巨大的。
1.人的自觉和以人为本。对人性的讨论是人的自觉的结果。夏商两代上帝崇拜极盛,没有足够地意识到人的地位和作用,周建立后才认识到天命不可信靠,提出“敬德保民”,人的地位开始上升。《易经》固然是人向上帝寻求帮助,但人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同时,寻求上帝的帮助也是以人为中心,是利用上帝的力量来处理人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人殉逐步被废除,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20〕人的活动开始以人为中心而不再以天为中心,老子说人是“域中四大”之一,《易传》认为人是与天、地并列的“三才”。这些思想的产生是人的自觉的反映。当人不再匍匐在上帝的脚下时,便要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等这样终极性的问题,孟子终于清晰地发出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之问。虽然此类终极关怀是每个民族共同的,但华夏民族较早地摆脱了上帝对人事的管控,宗教战争从而成为不可能。“人”的意识的觉醒,使人与天地的关系问题、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人何以为人的问题较早地发展起来,所有人事都以人为本。此后,性与道的关系始终是传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也使得中华民族始终关注着现实的人类社会的建设,把精神家园建基于脚下而不在上天,这又是传统独特的人性论的贡献之一,它塑造了我们民族爱好和平、追求理想的品格。
2.伦理道德。传统人性论以善恶为中心议题。不管是性善论、性恶论,目的都在于导人向善,可谓殊途同归。对伦理道德的高度关注也是人摆脱上帝控制的一个结果,人要自己管理人类社会,凭自己的力量立足社会,从而需要社会美好、个体品质符合美好社会的要求。社会美好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和谐、物质生产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在这样的社会,绝大部分的普通民众都应当是善的,否则社会就会大乱。个人的善体现在行为上就是利他,而内在的善就是仁。这样,人性之善便指向两个维度:个体修养与政治。一方面,个人要努力使自己成圣成贤,另一方面,统治者要施行善政。当儒家哲学成为传统哲学的主流时,建基于性善论基础上的儒家政治哲学便对国家机器有了强力制约作用。但恶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法家的存在事实上正好可作儒家的补充,起着坚守底线的作用。
伦理道德对社会利益起调节作用,这种调节是依靠道德的个人自律和道德他律完成的。纯粹的道德不具有强制性,因而,它强调个体的修养,希望每个人都能成贤成圣从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在传统社会,道德他律建基于道德自律的基础之上,因而比较强调利他,道德个体对自身利益的损害和放弃被认为是高尚的和值得推崇的,义利之辨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展开的。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道德高标,普通人要实施这样的道德行为往往是可望不可及的,如果强行,自身合理利益就会受到不必要的损害,这显失公平。道德的制约作用还有主观性和随意性的弱点。道德的行为原则主要是以心比心,所谓“忠恕之道”,就是要换位思考、合理估量自己与他人的利害关系。这种估计即使没有客观的事实依据也可以说是道德的,对他人的道德评价也主要依靠个人推理和人之常情。显然,这种主观性面对纷繁的个体行为,避免不了随意性。主观的和随意的道德他律可能不恰当地高估某些行为,也可能严重地损害某些无辜的人,从而失去调节利益的作用。韩非子说:“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21〕法家认为用道德来息争不太可靠,转而依赖规则,使人们的行为有章可循,使判断是非的标准明晰化和统一化。
3.正义。因为人是趋利避害的,个体利益多样,如果纯任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人们就会估计利害,那些急功近利的行为、损害他人和集体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无法保障,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即“私行立而公利灭矣”〔22〕。因此,从自利、自为的人性出发,韩非子认为既不能放任人性无限度的发展,也不能依靠高标准的道德教化来治国,必须把人们的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从而保障个人和国家的利益。法兼顾个人和国家二者的利益,明确人们的行为标准,因而具有正义性。虽然法的正义性也是有局限的,有时避免不了对个人利益的损害,但这种损害相较自然状态下人们的争斗来说要小,比“理想”状态也更为明确和可预期。在个人幸福、正义和善这三个层次中,正义比善和个人幸福都更为重要。
正义固然最为重要,但只依凭法治仍然不可长久。法以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最后目标,但以承认和保障个人幸福为前提,因而,法不能无视个人的自由,并以社会整体的善为最高境界。韩非子的思想为秦所用,而韩非子思想是以君主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对国民个人利益无限度打压、对道德无比怀疑,整个社会人人自危,在一时的成功后用来治理“天下”就只能归于失败。韩非子法的思想承认了人性的自然属性,但他没有认识到人并不仅仅是要活着,还要活得越来越好,而人性的发展要以社会发展为前提,法也必须兼顾个人和社会。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子治下的齐国,其法治思想就是非常成功的。《管子·七法》说:“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23〕“法德并举”就是管子思想与韩非子思想的主要区别。管子“以民为天”,强调“因人情(欲利避害)而治”,必富民而后强国。法可以规定利途,而要达到更高的目标,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发展从而实现比较理想的社会,德的作用就不可忽视,管子说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认识到了善比法处于更高的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德并举”一方面保证了个人幸福实现的正义途径,在最基本的层面保证“生生”之人性的实现,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人类最大共同体的利益,也就为个人幸福的实现提供了最优的外部环境。这样,“生生”既可以在生存的意义上展现,也可以在文明的意义上彰显。时至今日,德与法仍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维度,不管是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离开德与法的保障,都将成为不可能。历史的经验还证明了,良法与善德离不开对人性的正确体认。
注释:
〔1〕〔2〕〔12〕〔13〕《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737、567、567-568、990-99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4〕俞吾金:《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去魅与重建》,《中国哲学年鉴2010》,2010年,第52-70页。
〔5〕张曙光:《聚焦“人性”论》,《哲学分析》2013年第1期,第22页。
〔6〕俞吾金:《再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去魅与重建》,《哲学分析》2013年第4卷第1期,第26-35,197页。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8〕向世陵:《生与生态——从屈伸相感看生生与平衡》,《江汉论坛》2013年第3期,第66页。
〔9〕李振纲、张乃芳、魏彤儒:《〈周易〉生命哲学观的“生生”之维》,《学术论坛》2011年第3期,第27页。
〔10〕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336页。
〔11〕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5页。
〔14〕〔15〕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366、436页。
〔16〕〔17〕〔18〕〔19〕〔21〕〔2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369、145-146、98、274、461、448-449页。
〔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395页。
〔23〕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