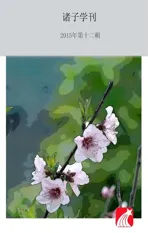朱熹《中庸章句》的生態觀*
2015-02-07樂愛國
樂愛國
朱熹《中庸章句》的生態觀*
樂愛國
朱熹在對《中庸》所涉及天人關係作出深入分析和詮釋時,特别强調人與物各有其本性而各有其道,因而提出要通過“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並進一步“贊天地之化育”,達到“與天地參”,從而在“致中和”中實現“天地位”、“萬物育”。顯然,這裏藴含了具有現代價值的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中心的生態觀。
關鍵詞 朱熹 《中庸章句》 人與自然和諧 生態觀
中圖分類號 B224.7
朱熹重視《中庸》,以為“《中庸》是直指本原極致處”*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四),《四部叢刊》初編本。,論及天人合一之道。因此,在詮釋《中庸》時,朱熹不僅討論了人道,而且還深入分析了其中所涉及的天人關係。尤其是通過對《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分析,朱熹强調人與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時又有各自不同的道;其中包含了人與自然萬物相互平等的思想。而且,又通過對《中庸》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的分析,朱熹提出要通過“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並進一步“贊天地之化育”,達到“與天地參”,實際上是要求通過“致中和”而實現“天地位”、“萬物育”;顯然,這裏藴含了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中心的生態觀。
一、 人、物各有其道
對於《中庸》所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鄭玄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説》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修,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傚之,是曰‘教’。”孔穎達疏曰:“‘天命之謂性’者,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天命自然,故云‘謂之性’。‘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於道理,使得通達,是‘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於下,是‘修道之謂教’也。”*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五十二,《中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25頁。顯然,在鄭玄、孔穎達看來,《中庸》講“性”、“道”、“教”是就人而言的,講人之性源自天,循性而有人道,君主修行此道而教化百姓。
與此不同,朱熹《中庸章句》的注釋從人與物統一的層面展開,指出: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頁。
相對於鄭玄、孔穎達,朱熹的注釋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僅就人而言,後者則將人與物統一起來,具體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發明: 第一,認為人與物都得自天所賦的共同之理,而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時又由於氣稟的差異而有“氣質之性”的不同;第二,認為人與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而有各自不同的當行之道;第三,認為“修道”在於依據人與物各自不同的“道”,對人與物作出不同品級的節制和約束。
問題是,《中庸》講“性”、“道”、“教”,既没有專就人而言,也没有兼人、物而言,朱熹以為兼人、物而言,其文本依據何在?《中庸》第二十二章講:“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裏講“性”,既講“人之性”又講“物之性”。此外,《中庸》第十二章説:“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這裏所謂“君子之道”並非只是人道,還包括了天地之道。而且,《中庸》第二十六章還專門闡述了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 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顯然,《中庸》所謂天地之道,是指天地之間的物之道。由此可見,朱熹注《中庸》“性”、“道”、“教”兼人、物而言,是有充分的文本依據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注釋中,朱熹既講人與物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又講人與物有氣稟的差異,所謂“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朱熹還説:“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黎靖德《朱子語類》(一),卷四,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8頁。人與物由於氣稟的差異而有了人之性與物之性的不同。朱熹甚至説:“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五十九,第1378頁。
關於氣稟的差異而導致人之性與物之性的不同,朱熹《孟子集注·告子章句上》注孟子所謂人之性不同於犬之性、牛之性,曰: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第326頁。
在朱熹看來,人與物,就氣而言,似乎没有差别,但由於氣稟的不同,所得仁、義、禮、智之性就有全與不全的差别。
對此,朱熹門人黄灝問:“《中庸章句》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或問》亦言‘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理則未嘗不同’;《孟子集注》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二説似不同,豈氣既不齊則所賦之理亦隨以異歟?”朱熹回答説: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朱熹認為,人與物同為一原,但氣稟有粹駁不齊,所以“理同而氣異”;人與物,雖然所稟的氣相近,但理有偏全之異,所以“理絶不同”。朱熹説: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朱熹《四書或問·大學或問》,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頁。
在朱熹看來,人與物都為陰陽五行所造化,因而有着共同的“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同時,人與物又都由氣聚而有形,人所稟之氣“正且通”,物所稟之氣“偏且塞”,因而造成人之性與物之性的差别,以至於貴賤的差别。另據《朱子語類》載: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黎靖德《朱子語類》(一),卷四,第57頁。
朱熹認為,人之性只是明與暗的差别,可以由暗使之明;而物之性或偏或塞,“偏塞者不可使之通”。所以,在朱熹看來,人之性與物之性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很大的差異。
在朱熹看來,既然人之性與物之性有很大的差異,那麽由“性”而自然派生出來的“當行之路”,即“道”,也不相同,這就是朱熹《中庸章句》所言:“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中庸或問》也説:“‘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朱熹《四書或問·中庸或問》,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六册,第550~551頁。
同時,正是由於人與物有其各自不同的道,所以聖人要依據人與物各自不同的“道”對人與物作出不同品級的節制,所謂“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這就是《中庸》所謂“修道之謂教”。就物而言,朱熹説:
“先王所以咸若草木鳥獸,使庶類蕃殖,如《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六十二,第1495頁。
關於“修道之謂教”,朱熹特别强調必須依據人與物各自不同的“道”。朱熹《中庸或問》在對“修道之謂教”作進一步解説中指出:
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唯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朱熹《四書或問·中庸或問》,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六册,第551頁。
在朱熹看來,一方面,人與物由於氣稟的不同而存在着差異,“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所以,需要“為之品節防範”;另一方面,人與物由於氣稟的不同而導致“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修道”是“因是道而品節之”,“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所以,“修道”是依據人與物各自不同的“道”而作出不同品級的節制。由此可見,朱熹《中庸章句》把“修道”解説為“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其中的“所當行者”並非僅就所有人與物的共同之道而言,而更多的是就人與物各自不同的道而言,是從人與物各自不同的道入手。
從朱熹對於《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詮釋可以看出,朱熹在人與物統一的層面,强調人與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時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據人與物各自不同的“道”對人與物作出不同品級的節制,顯然包含了人與自然萬物相互平等的思想。先秦儒家重視人,從人出發建構了以人為中心的宇宙觀。朱熹《中庸章句》則進一步從人與物的統一出發,實際上建構了更廣大的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統一的宇宙觀。
二、 既要“盡人之性”又要“盡物之性”
《中庸》第二十二章講“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對於其中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朱熹《中庸章句》注曰: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32~33頁。
在朱熹看來,所謂“至誠”是指“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朱熹門人陳淳也説:“‘至誠’二字,乃聖人德性地位,萬理皆極其真實,絶無一毫虚僞,乃可以當之。”*陳淳《北溪字義》卷上《誠》,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頁。由於聖人之德與天道為二而合一,所以,“至誠”則能够盡其性,盡人與萬物之性。所謂“盡性”,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就是要體察天賦於的内在本性,並推展至事事物物,而無所不盡;其二,是要根據其本性,盡可能合理地予以對待和處置。這就是所謂“察之由之”,“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能够“至誠”而“盡性”,就能够無人欲之私,所謂“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朱熹還注《中庸》第三十二章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曰:
唯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38~39頁。
朱熹認為,只有“至誠”、“盡性”而“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才能真正“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他還説:
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朱熹《四書或問·中庸或問》,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六册,第596頁。
在朱熹看來,只有像聖人那樣至誠而“無人欲之私”,才能“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按照天地之道,贊助於天地之化育,而這樣的“人之所為”實際上也就是“天地之所為”。
在《中庸》第二十二章看來,要達到“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除了要“至誠”、“盡性”,還要“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那麽,如何“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呢?朱熹認為,人、物為天地所化生,人、物之性源於共同的“天命之性”,所謂“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而要盡人、物之性,先要“盡己之性”。他説:
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六十二,第1490頁。
朱熹還説:“至誠唯能盡性,只盡性時萬物之理都無不盡了。故盡其性,便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便盡物之性。”*黎靖德《朱子語類》(二),卷十七,第381頁。同時,他又認為人之性與物之性“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因此要求在“盡己之性”基礎上進一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從而達到“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
在盡人、物之性方面,朱熹首先要求“知之無不明”。他推崇《中庸》第二十四章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並注曰:“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33頁。據《朱子語類》載: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虚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僞,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卻不能見也。”*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六十四,第1575頁。
可見,在朱熹看來,聖人至誠,“無一毫私僞”,所以能够知萬物之變化,達到“知之無不明”。
朱熹不僅要求“知之無不明”,而且更强調“處之無不當”,要求根據人、物之性的不同而使之各得其所。據《朱子語類》載:
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若只明得盡,如何得與天地參去?”*同上書,卷六十四,第1569頁。
可見,在講盡人、物之性時,朱熹較多地講“處之盡其道”。他説:
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他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六十四,第1568頁。
至於盡人,則凡或仁或鄙,或夭或壽,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所。至於盡物,則鳥獸蟲魚,草木動植,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宜。*同上書,卷六十四,第1569頁。
朱熹還特别强調“盡人之性”與“盡物之性”二者之不同。他説: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它,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它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同上書,卷六十四,第1570頁。
在朱熹看來,人與物都具有天賦的“善”性,但氣稟各有不同;有些人雖然稟得濁氣,但“善”性仍然存在,可以開通,所以聖人用教化去開通它;物稟得氣偏了,無法開通,也不能教化,然而,聖人可以根據它們不同的物性,合理地加以處置和利用。
關於“盡物之性”,朱熹還説:
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同上。
朱熹認為,“盡物之性”就是要讓自然之物各順其性,各得其宜,而不是依據人的主觀模仿想象。他説:
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 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唯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黎靖德《朱子語類》(一),卷十四,第256頁。
在朱熹看來,要使萬物各得其所,就必須“因其性而導之”,就是要根據自然物的不同物性,順其性而為,合理地加以開發和利用,“取之以時,用之有節”;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先要“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知得萬物之性。
朱熹特别强調對待自然物的“取之以時,用之有節”。他的《孟子集注·盡心章句上》注“仁民而愛物”中的“愛物”曰:“物,謂禽獸草木;愛,為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第363頁。認為“愛物”,就是對動、植物的“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他還説:
愛物……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黎靖德《朱子語類》(八),卷一百二十六,第3014頁。
所以,朱熹非常讚賞並引述張栻所説:“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絶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六册,第751頁。認為保護自然應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要像孔子那樣“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既要反對“窮口腹以暴天物”,也要反對“禁殺茹蔬、殞身飼獸”。
由此可見,朱熹講“盡物之性”,要求對自然物“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取之以時,用之有節”,從廣義上講,就是要在認識自然的基礎上,對自然物做出合理的開發和利用;“知之無不明”,就是要深入認識自然;“取之有時”,就是開發自然物須按照時令;“用之有節”,就是利用自然物須有所節制。顯然,這種“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的思想藴含着深刻的生態思想。
三、 “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在《中庸》看來,能够“至誠”、“盡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所謂“天地之化育”,朱熹《中庸章句》注“天命之謂性”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17頁。認為天化生萬物,氣以成形,並將“理”賦予了人和物,於是就有人、物之“性”。由此可見,“天地之化育”就是指天地對於人以及萬物的形體與先天本性的化生和養育。
關於“贊天地之化育”中的“贊”,鄭玄注曰:“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孔穎達疏曰:“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化育。”*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五十三《中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第1632頁。朱熹注曰:“贊,猶助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33頁。顯然,無論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中庸》還是朱熹《中庸章句》,都把“贊天地之化育”的“贊”注釋為“助”,即“贊助”。
與鄭玄、孔穎達把《中庸》“贊天地之化育”中的“贊”注疏為“贊助”不同,程顥説:“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個誠,何助之有?”*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二程集》第一册,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3頁。對此,《宋元學案》載楊開沅案:“參、贊皆是同體中事。如人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不可謂耳有助於目,足有助於手。”*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第一册,卷十三《明道學案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63頁。以為天人一體,無所謂“助”。
對於程顥“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朱熹《中庸或問》認為,“若有可疑者”*朱熹《四書或問·中庸或問》,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六册,第595頁。,並且指出:
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同上書,第595~596頁。
朱熹認為,程顥鑒於當時人們對“理一”“多或未察”,而較多地講天人一體;但是,就“分殊”而言,天與人各有不同的職分,天人之事是各不相同的;正因為天與人之不同,所以人對於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助而言。
關於“贊天地之化育”,程颐曾説:“‘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二程集》第一册,第158頁。朱熹贊同程頤的説法,指出:“程子説贊化處,謂‘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説得好。”*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六十四,第1570頁。朱熹還説: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卻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説非是。*同上。
在朱熹看來,天與人“各自有分”,有天所為之事,有人所為之事;而人所為之事,就應當是“贊天地之化育”。所以,他明確把“贊天地之化育”之“贊”詮釋為“贊助”。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還把“贊天地之化育”之“贊”,進一步詮釋為“裁成輔相”。所謂“裁成輔相”,源自《周易·泰》所引《象》曰:“天地交,泰,後以財(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朱熹《周易本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頁。關於“裁成輔相”,二程説:“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上,《二程集》第一册,第280頁。可見,“裁成輔相”就是根據天地之道,教化百姓依道而行。朱熹説:
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卻自做不得,所以生得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卻須聖人為他做也。*黎靖德《朱子語類》(一),卷十四,第259頁。
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朱熹《周易本義》,第58頁。
朱熹認為,天地間之萬事萬物固有其不完善之處,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使之完善。據《朱子語類》載:
問“‘財(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 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製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一作: 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黎靖德《朱子語類》(五),卷七十,第1759頁。
“財(裁)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同上書,第1760頁。
應當説,朱熹對“贊天地之化育”以及“裁成輔相”的詮釋,既是針對人類社會,也是針對天地自然;就後者而言,朱熹的詮釋包含了兩個重要思想: 其一,由於“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應當積極主動地在與自然的互動中,通過彌補自然之不足,以滿足人的要求,而不是消極而被動地適應自然,甚至畏懼自然;其二,在與自然的互動中,人只是起到輔助自然的作用,只是補充自然的不足,而不是肆意破壞或“改造”自然。正是通過這種人與自然的互為補充,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需要指出的是,在朱熹那裏,“贊天地之化育”並不是從人出發,而必須是“盡物之性”,“因其性而導之”。朱熹還説:
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於外也。*朱熹《西銘解》,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十三册,第141~142頁。
在朱熹看來,“贊天地之化育”就是要對於不同的物,要給予不同的對待,應當“若其性、遂其宜”,也就是要根據自然物的特殊性,合理地予以對待,而不是外在的强加。這就把“贊天地之化育”與“盡物之性”統一起來。
《中庸》講“贊天地之化育”,並且同時指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對此,朱熹注曰:“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33頁。認為人在“贊天地之化育”中,就可以達到與天地和諧並立。顯然,在朱熹看來,“與天地參”,實現人與天地的和諧,是人類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標;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通過人與自然的互動,並在輔助自然的過程中,達到與自然的相互補充、相互協調。
關於“與天地參”,戰國時期荀子也有過闡釋。《荀子·天論》講“明於天人之分”,但較多强調人對於自然的作用,指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認為人與天地參,是指人治天時、地財。可見,荀子反對放棄人力而順從天地,因而要求“制天命而用之”。
與荀子不同,朱熹則要求通過“贊天地之化育”,輔助並順從天地自然,達到“與天地參”,强調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追求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人與天地的合二而一。由此可見,朱熹對“贊天地之化育”的注釋,雖然講人對於自然的作用,但是又認為,人只是輔助自然,只是補充自然之不足,並以此達到人與自然的相互協調,而最終的目的在於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四、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根據朱熹《中庸章句》,《中庸》所謂“至誠”、“盡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實際上是對“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詮釋,是對“致中和”如何能够達到“天地位,萬物育”的回答。
對於《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正義·中庸》有孔穎達疏曰:“致,至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其養育焉。”*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五十二《中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第1625頁。顯然,這是從人的性情的角度講“中”、“和”,並認為,人君的性情能“致中和”,就能使“陰陽”和諧,從而達到“天地位”、“萬物育”。
一般而言,“陰陽”既可指人體内的“陰陽”,也可指天地中的“陰陽”。人的性情會影響到人體内的“陰陽”,但是不可能影響到天地中的“陰陽”。《禮記正義·中庸》中所言“陰陽”均指天地中的“陰陽”,所謂“天地陰陽,生成萬物”*同上書,第1634頁。。《禮記正義·中庸》在對“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詮釋中引入了“陰陽”概念,但是並没有就人君的性情“致中和”如何能够使天地“陰陽”和諧,並達到“天地位”、“萬物育”,做出明確的説明。尤其是,這種詮釋與漢唐時期流行的“天人感應”思想十分相似。
關於“天人感應”思想,漢代董仲舒多有論述。他説:“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鍾肇鵬《春秋繁露校釋》,卷十三《同類相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4頁。又説:“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同上書,卷十《深察名號》,第671頁。所以,在董仲舒看來,人的性情會影響到天地陰陽。他明確指出:“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静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摇盪四海之内。”*鍾肇鵬《春秋繁露校釋》,卷十七《天地陰陽》,第1085頁。雖然不能完全肯定《禮記正義·中庸》對“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詮釋,依據的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但該篇的確包含了“天人感應”思想。比如,孔穎達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曰:“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國家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文説》:‘禎祥者,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又疏“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曰:“妖孽,謂兇惡之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為妖傷之征。若魯國賓鵒來巢,以為國之傷征。”孔穎達還説:“聖人君子將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將興,禎祥可知。而小人、愚主之世無至誠,又時無賢人,亦無至誠,所以得知國家之將亡而有妖孽者。”*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五十三《中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第1632頁。顯然,這本身就是“天人感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注“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静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18頁。
《中庸》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又講“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慎其獨”;朱熹則把二者結合起來,並明確認為,君子戒慎恐懼乎其不睹不聞,即“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同上書,第17頁。,是“未發時工夫”;君子慎其獨,即“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尤加謹焉”*同上書,第18頁。,是“專就已發上説”*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六十二,第1505頁。。所以,《中庸章句》講“致中和”,從戒慎恐懼和慎獨講起,以為“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静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就可以“極其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就可以“極其和”。朱熹還説:
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朱熹《四書或問·中庸或問》,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六册,第559頁。
朱熹認為,“致中”就是要自“未發”時戒謹恐懼,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且又能“守之常不失”,進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致和”則是要於“已發”之際以謹慎,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且又能“行之每不違”,進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
在朱熹看來,要使得“天地位”,就必須“致中”;要使得“萬物育”,就必須“致和”,所謂“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五《答李時可》(一),《四部叢刊》初編本。;而“致中和”之所以能够達到“天地位”、“萬物育”,這是由於人處於天地萬物之宇宙系統的中心,即所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因此,要達到“天地位”、“萬物育”,關鍵在於“致中和”。
關於“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朱熹《中庸章句》注“天命之謂性”而認為,人與物都得自天所賦的共同之理,而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所以,人的先天本性,即天地萬物之理,二者是同一的,本為一體,這就是所謂的“性即理”。應當説,朱熹講“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强調人與天地萬物的同一性,與陸九淵講“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二十二,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3頁。以及王陽明所謂“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册,卷二《傳習録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以為天地萬物本之於人心,是有明顯差别的。
按照朱熹所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之説,喜怒哀樂未發的“中”與發而中節的“和”,本身就是天地萬物之理;也就是説,喜怒哀樂未發的“中”,即超越千變萬化的自然現象之“天下之大本”;發而中節的“和”,即自然現象千變萬化之“天下之達道”。换言之,“致中和”不僅是要讓性情的“未發”之“中”與“已發”之“和”達到極致,而且要在這一過程中,把握天地萬物之理和變化規律。這是實現“天地位”、“萬物育”的前提。朱熹還説:
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静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静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朱熹《四書或問·中庸或問》,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六册,第559頁。
在朱熹看來,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乃“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乃“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就能達到“静而無一息之不中”而“吾心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而“吾氣順”;“吾心正”、“吾氣順”,則能够與天地萬物和諧共處,即所謂“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因而能够達到“天地位”、“萬物育”。據《中庸或問》所述: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朱熹《四書或問·中庸或問》,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六册,第559~560頁。
在朱熹看來,天地自然萬物的變化,雖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往往與人有關,且與是否“致中和”有關。對此,王夫之作了進一步闡釋,指出:“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可得而正也。以之秩百神而神受職,以之燮陰陽、奠水土而陰陽不忒、水土咸平焉、天地位矣。何也?吾之性本受之於天,則天地亦此理也,而功化豈有異乎?吾之氣順,而萬物之氣可得而順也。以之養民而澤遍遠邇,以之蕃草木、馴鳥獸而仁及草木、恩施鳥獸焉,萬物育矣。”*王夫之《四書訓義》(上),卷二《中庸》,《船山全書》第七册,嶽麓書社1990年版,第108~109頁。
需要指出的是,《中庸章句》注“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講“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並不同於漢唐儒家的“天人感應”。朱熹説: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今人不肯恁地説,須要説入高妙處。不知這個極高妙,如何做得到這處。漢儒這幾句本未有病,只為説得迫切了,他便説做其事即有此應,這便致得人不信處。*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六十二,第1519頁。
朱熹認為,漢唐儒家是用“天人感應”來説明“致中和”即有“天地位”、“萬物育”,而重要的是,要説明“這個極高妙,如何做得到這處”。
朱熹門人周謨注“致中和”云:“自戒謹恐懼而守之,以至於無一息之不存,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謹其獨而察之,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並且還説:“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戒謹恐懼所以守之於未發之時,故無一息之不存而能極其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必謹其獨所以察之於既發之際,故無一行之不慊而能極其和。天地之所以位者,不違乎中;萬物之所以育者,不失乎和。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者,蓋如此。學者於此,静而不失其所操,動而不乖其所發,亦庶幾乎中和之在我而已。”對此,朱熹説:“其説只如此,不難曉。但用力為不易耳。”*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周舜弼》(十),《四部叢刊》初編本。顯然,朱熹重視的是,如何通過“致中和”而達到“天地位”、“萬物育”。
所以,在朱熹看來,“天地位”、“萬物育”不是“致中和”感應出來的,而是要通過“致中和”,使得“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行之每不違”,進而達到“天地位”、“萬物育”。而且,朱熹還認為,要達到“天地位”、“萬物育”,不僅要“致中和”,把握天地萬物之理和變化規律,同時還要“因其自然之理以裁成輔相之”。因此,他明確指出:
“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六十二,第1519頁。
如前所述,朱熹把“贊天地之化育”之“贊”,詮釋為“裁成輔相”;而在詮釋“天地位,萬物育”中,又講“裁成輔相”,由此可見,要實現從“致中和”到“天地位,萬物育”,必須通過“贊天地之化育”,即“裁成輔相”的過程。
張栻門人胡季隨説:“‘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若就聖人言之,聖人能致中和,則天高地下,萬物莫不得其所。如風雨不時,山夷谷堙,皆天地不位;萌者折,胎者閼,皆萬物不育。就吾身言之,若能於‘致’字用工,則俯仰無愧,一身之間自然和暢矣。”朱熹説:“此説甚實。”*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隨》(六),《四部叢刊》初編本。顯然,在朱熹看來,“致中和”而達到“天地位”、“萬物育”,是就聖人而言的;就一般人而言,需要在“致”上下工夫,就是要通過戒慎恐懼以及慎獨,而達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發皆中節之“和”,並且把握“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達道”,把握天地萬物之理和變化規律,這樣才能達到“天地位”、“萬物育”。朱熹還説: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致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潜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説道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説得前一截,卻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到極處也。*同上。
朱熹認為,“致中和”而達到“天地位”、“萬物育”,這是恒常的道理。因為“致中和”,就是要通過“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無一事之不盡”,從而實現“天地位”、“萬物育”。而且在朱熹看來,“致中和”必須達到“天地位、萬物育”,才是“推致極處”,達到最高境界。
由此可見,朱熹《中庸章句》對“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詮釋,其豐富内涵在於,朱熹認為,將人的喜怒哀樂未發的“中”與發皆中節的“和”推到極致,並據此體會人的先天本性以及與此具有共同性的天地萬物之理和變化規律,進而“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贊天地之化育”,就可以實現“天地位”、“萬物育”;而這與對《中庸》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的詮釋是完全一致的。
五、 從生態的角度看
現代人所謂的“生態”,是指人在與自然的相互關係中,通過各種途徑、各種方法保護自然環境,實現與自然的和諧。從這一角度看,朱熹《中庸章句》藴含着具有現代意義的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中心的生態觀,大致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自然萬物有各自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規律。在朱熹看來,人與物雖有共同的來源和本性,但是,由於人與物的“氣”的不同,所以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乃至物與物之間存在着差異,以至於他們的本性各有差異,因而各有不同的“道”。所以,人有人的生存方式、物有物的存在方式。就物而言,動物、植物以及非生命物各有自己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規律。因此,人與自然萬物相處,必須依照它們各自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規律,而不是依據人的主觀想象,更不是違背自然萬物各自的存在方式和規律,以至於造成對於自然的破壞。
第二,在與自然萬物的相處中,人處於主導地位,但必須尊重自然。在朱熹看來,人與物的最大差别在於人是萬物之靈。但是,作為萬物之靈的人並不可以任意宰割萬物,掠奪自然,破壞自然。朱熹説:“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别?”*黎靖德《朱子語類》(一),卷八,第132頁。在朱熹看來,人如果將自己視為高於萬物而任意宰割萬物,就會將自己等同於禽獸。也就是説,在與自然萬物的相處中,人處於主導地位;正因為如此,人不僅對自己,而且對自然萬物,都負有同樣責任,必須給予同樣的對待、同樣關心、同樣的尊重。
第三,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的道德素質至關重要。為此,朱熹不僅講“至誠”、“盡性”,而且還講“致中和”,還説:“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六十二,第1519頁。從現代的角度看,在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中,人始終占據主導地位。自然的和諧要靠人來保護,而自然和諧的破壞往往來自人的肆意妄為,人的道德素質和行為直接影響到人與自然關係的解決。因此,人的道德素質和行為以及作為其基礎的人的性情修養,對於自然的和諧至關重要。不可否認,要保護自然的和諧,制止對自然和諧的破壞,需要有制度的建設,但是也離不開人的道德素質的提高。
第四,尊重自然,就是要認識自然,並按照自然規律對待自然,順應自然。朱熹强調要讓自然之物各順其性,各得其宜,而不是依據人的主觀模仿想象,同時又要根據物的不同的本性,給予不同的對待,合理地加以處置,“若其性、遂其宜”,“使之各得其宜”。而且,在朱熹看來,要使萬物各得其所,就必須“因其性而導之”,“取之以時,用之有節”;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先要“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知得萬物之性。
第五,人與自然的和諧,是最高的目標。《中庸》講“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要求通過提高人的道德素質,達到自然的和諧。《中庸》又講“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要求通過輔助自然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這是儒家所要達到的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最高境界。朱熹《中庸章句》對此所作的詮釋,則進一步反映了這種對於人與自然和諧的一貫的和持續的追求,以及在這樣的追求中所形成的文化傳統。
顯然,這是從人與自然的和諧出發,要求尊重自然,而不是從“人欲之私”出發;從對自然的認知出發,要求在把握自然之理的基礎上,合理地對待自然,而不是從人的主觀願望出發;其目的在於輔助自然,在於實現人與自然的相互補充、相互協調,而不在於為了人的利益干擾、改變和改造自然。由此可見,這不僅是為了人,而且也是為了自然。從生態的角度看,這不是單純的以人類為中心,而是一種通過人與自然的互補與協調而達到和諧的生態觀,是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中心的生態觀。
當然,朱熹《中庸章句》在闡發這樣的生態觀時,把論述的重點放在如何“至誠”、“盡性”以及如何“致中和”上,至於如何“贊天地之化育”,實現“天地位”、“萬物育”,並没有做出更多具體而深入的討論。因此,朱熹《中庸章句》所藴含的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中心的生態觀,實際上並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闡釋,在理論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比如,朱熹《中庸章句》對“贊天地之化育”的詮釋强調人對於自然的輔助,其根據在於認為自然有其不足之處。問題是,這種“不足”是相對於人的需要而言的,是人對於自然的不滿足;那麽,如何才能保證對這種“不足”的彌補不會像《莊子·應帝王》所説,為“渾沌”鑿七竅*《莊子·應帝王》載: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窍,七日而渾沌死。那樣而超出對於自然的“輔助”?又比如,朱熹《中庸章句》以“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人與萬物之性都源自“天命之性”予以論證,雖然也强調人與物所賦形氣之不同,“盡物之性”與“盡人之性”、“盡己之性”有差别,但問題是,如何才能保證在“盡物之性”過程中做到客觀意義上的“知之無不明”和“處之無不當”而不受人的主觀願望和主觀評價的影響?儘管朱熹《中庸章句》對於如何“贊天地之化育”實現“天地位”、“萬物育”的回答還有種種不太圓滿之處,但是,其中所藴含的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中心的生態觀,是一種與當今備受質疑的人類中心論所不同的生態觀。這既是我們今天需要繼承的具有現代價值的生態觀,同時也為我們今天構建新的生態理念,提供了思想資源。
[作者簡介] 樂愛國(1955— ),男,浙江寧波人。1983年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本科畢業;1986年復旦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畢業。現為厦門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中國朱子學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中國哲學、朱子學、道教思想史以及中國古代哲學與科技關係的研究,著作有《朱子格物致知論研究》《朱熹的自然研究》《宋代的儒學與科學》《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王廷相評傳》《道教生態學》《管子的科技思想》等。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朱熹《中庸》學研究”(12FZX00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