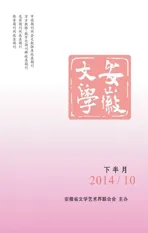后殖民视角下的中国民俗
——论《雪花秘扇》中他者化的民俗演绎
2014-12-12丁良艳
丁良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后殖民视角下的中国民俗
——论《雪花秘扇》中他者化的民俗演绎
丁良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美国作家邝丽莎《雪花秘扇》一经出版便风靡美国,成为华裔文学中引入中国元素的又一部力作。然而在以女书、老同及裹脚布为背景的故事叙述中,作者演绎裹脚布带给妇女的苦痛的同时,却不曾想到作为美的枷锁的裹脚布和现代的高跟鞋从本质上的一致性。作者渲染着老同之间的超越友谊爱情的姐妹情谊,却在性的描绘上不遗余力地展示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猎奇和想象。作者反复地演绎女书的书写和内容,在彰显古中国妇女聪慧、轻盈与男权对抗的勇毅的同时,恰恰落入了女权主义者的书写模式。于是,作者在夹杂着自身文化思维模式的同时关照和演绎中国文化元素,其最终塑造的只能是似是而非的他者化的中国形象。
裹脚布与高跟鞋 老同与女同 女书与女权
萨义德《东方学》一书中定义东方主义为“一种思维方式”,“东方”只是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而非事实。长久以来,充满异国情调、神秘色彩的东方一直充当了西方人认识自我、验证自我的“想象性他者”,“是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①小说《雪花秘扇》中,邝丽莎笔下的中国民俗正是这样一种“想象性他者”。在讲述晚晴湖南瑶族村寨以女书传情的两名女性的故事中,大量中国文化元素的史诗式的堆砌和演绎,固然有作者故国溯源的努力和身份认证式的平铺叙述;然而商业化的写作模式和西方话语,使其在展现中国文化元素时不可避免地带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以及为博取眼球而刻意凸显的似是而非的东方情感和文化表征。在笔者看来,作者在努力还原女书、老同及裹脚布的文化符号时,无论是描述的视角、措辞还是情感表达,都不可避免地带着西方的思维眼镜,字里行间展现的不过是他者化的中国。
一、美的枷锁:从裹脚布到高跟鞋
中国历史上,裹脚布的由来很久。早在五代时期,陶宗仪《辍耕录·缠足》便讲道:“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②可见裹脚一开始便是女人爱美与取悦男人的修饰工具。在脚上大做文章以博取郎君目光并非只是中国人独有的专利,当今社会,风靡全球、五光十色的高跟鞋在我看来与裹脚布异曲同工。关于高跟鞋的起源,相传是法国路易十四为弥补自身身高劣势而特意定做的增高鞋。而自从女性穿上高跟鞋以后,高跟鞋慢慢就成为美与时尚的代名词。所有镁光灯下的女性无一不与高跟鞋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男子喜欢三寸金莲和高跟鞋走出的风摆杨柳的姿态,认为它能产生一种美感,激发男人保护女人的欲望,激发男人的快感”。③这样的美,很大程度上只是迎合了时代对女性的全新的束缚。
裹脚问题俨然成为旧中国的最具代表的陋习,也成为早期来华者集中关注的焦点。从托马斯·胡迪《茶杯之幻想》到赛珍珠的一系列小说,中国美人的三寸金莲,“几乎看不见的小脚”,④一直成为西方人文学记忆中不断强化的文化符号。《雪花秘扇》中对裹脚的描绘也挣脱不了持续以来的固化的西方表达。
其一便是对苦痛的极度渲染。《雪花秘扇》中提到裹脚女子的死亡率近乎10%。雪花、百合以及美月在裹脚之前对裹脚心怀着莫名的恐惧和排斥。然而她们无法拒绝。对裹脚女子遭受苦痛的过度的描绘恰恰反映了西方话语中对东方落后、野蛮形象的隐性的强化。自文艺复兴彼特拉克等人高举人文主义大旗以来,人性的自由与解放一直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旋律。而这时的中国,居然以这样一种反人性的残酷的手段戕害妇女的身体,这是一种怎样的野蛮的行径。而西方人在以这种异样的目光关注中国妇女的小脚的时候,却极少将这带给妇女苦痛的裹脚布与高跟鞋联系起来。现代妇女在适应高跟鞋的过程中遭受的痛苦被他们轻易忽略了。
其二,审美的对象过度局限于小脚。三寸金莲在中国的由始主要为了取悦君王,提升女子地位。古代男子在赏悦女人的小脚之时,绝非将目光停留在小脚本身的纤巧与玲珑,步履的轻盈与身姿的曼妙共同构成审美的对象。金莲第一次出场时小说中描写道:“往下看尖翘翘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做处风吹裙边。”⑤可见除了一双纤纤细足,那种风吹杨柳的神态和步履共同构成引发男人性幻想和迷恋的极致诱惑。然而在《雪花秘扇》中,雪花地位的提升完全靠了自己那双无与伦比的美足。脱离了步履与身姿的小脚之美,在笔者这样一个中国读者眼里显得是如此的单薄和瘦削。
其三,对小脚妇人骄傲与满足感的忽略。裹脚这一传统从出现到成为习俗是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根据唯物史观来看,如果缠足带给妇女的仅仅是苦痛,那么它必然要遭到抵制和抛弃。裹脚从最初一开始的爱美之心引发,继而带来的是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改变,这其中固然有对男权社会对女人异化、压迫的批判,而女人在这种强制的压迫之中,逐渐内化为对缠足的接受并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中国的妇人们对缠足有一种内在的主动性。成功的缠足是她们傲人的资本,这种内心的满足感以及物质上的回报足以抵消掉之前所受的苦痛,成为她们一生受享不尽的福报。雪花嫁得富贵人家后再面对百合其实内心是有优越感的,正是这样的优越感使她难以设身处地地为自己的老同考虑,并在百合提出分手后勃然大怒。雪花很清楚自己生活的改变靠的是什么,所以在回忆曾经裹脚的疼痛经历时也是略带一丝淡淡的甜蜜。而这淡淡的甜蜜,却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二、老同的名号,女同的视角
同性恋在近现代的西方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种种或支持、或反抗同性恋的社会运动在欧美层出不穷。在解放人性的呼声中成为自由主义者和性解放运动人士的社会标签。同性恋关系中居核心地位的是性爱,在性爱基础上建立两个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支持的情感。而老同,根据李虎《壮族社会的拟亲属关系研究》的定义,更多的是基于家长制的社会结构中,一系列亲属关系的延伸。《雪花秘扇》中,两个同年同月生的同性女子,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仪式,结为老同;从此在一生中都保有对彼此的如爱情般忠贞和包容的情感。邝丽莎深入挖掘和描写老同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勇气是可敬的,然而在充斥着大量同性恋禁忌和宣扬的西方文化氛围中,作者在描写老同的同时也不时地带上了女同的视角。
其一是对性的关注。当今时代,全球范围内对同性恋问题褒贬不一。学术界对同性恋问题属于疾病范畴抑或文化范畴依然争论不休。而唯一毋庸置疑的是同性恋关系中居核心地位的便是性爱。这种或隐或显的性关系对维系同性恋之间的情感及生活是不可缺失的。而中国的老同,从诞生开始,便与社会生产关系密切相关。无论男性老同还是女性老同,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发挥着如同亲人般协同劳作的作用。《雪花秘扇》中在描述雪花和百合的私生活时,对两个人之间懵懂的性冲动的描述是一大突出点。尽管作者一再彰显的是两人之间的姐妹情谊,而时不时的关于两人之间性行为的想象和描写完全暴露了作者同性恋思维下的猎奇心理。
其二是对彼此间个人情感的极度铺陈。结老同现象一开始固然离不开两个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和彼此欣赏,然而在历史的发展中,老同渐渐成为一种文化习俗后,对个人情感的关注便逐步地褪除;相应的老同关系与社会生产关系交织一起,成为封建家长制下亲属关系的自然延伸和补充,对维系两个部落乃至族群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晚晴时期的瑶族村寨,其盛行的老同民俗无疑是一种文化现象。其老同关系的历史真实应是强调生产、生活中的协作而非单单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倾吐。《雪花秘扇》故事中,从头至尾充斥的都是雪花和百合通过女书互诉衷肠和相思之情,似乎老同更多是朋友与闺蜜的升级。小说中对两个人生产劳作的场景描述甚少。在西方文化背景中长大的邝丽莎,尽管一度以华裔作家身份自居,其对华夏文明的理解终究是冰山一角,管窥蠡测。在叙述老同情谊时,不可避免地站在一个现代西方人的立场,用极大的人文主义情怀去关注老同之间的个人情感。剥离了社会生产背景的老同,在邝丽莎笔下异化成了多愁善感、心思细腻的女子之间的灵魂伴侣。而这他者化的老同关系在作者的话语霸权下一再被强调,被重述,被重写。
三、女书与女权
《雪花秘扇》从小说到电影,对女书这种专属于女性的书写文字的大力强调与挖掘,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女书的存在恰恰迎合了“女权主义者们寻求作为“真理讲述者”而独立存在的理想”。⑥只在妇女间流传的女书,既能连接女性情感又能躲避男性的监控,为男权社会下女性之间的相互交流关爱提供了天然的屏障。《雪花秘扇》中,雪花和百合,从相识之初便与女书结下了解不开的渊源。从婚丧嫁娶到家庭中的一切变故,两个人始终通过女书将自己的境遇传递给对方。一切面对亲人爱人不能说的话,不能表现的情感,却可以通过女书,这种男人完全看不懂的文字倾诉给自己的老同。从精神分析学看,这样的倾诉为保持封建男权制压迫下的女性的心理健康是极其重要的。在国际女权主义者看来,女书的出现就是受压迫的女子对抗男人的工具,是张扬自我、争夺话语地位的有力武器。“就女书而言,追求独立于男性之外的话语,讲述真理是摩根等女性主义者的理想;她坚信,妇女是真理讲述者,她们可以用未被修辞的外交辞令话语讲述事实。”⑦而在古代的中国,女书的出现恰恰是男女不平等地位的一种极端反映。女子自古极少读书识字,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文字似乎天然就专是男人的游戏。被无形剥夺了文字权的女性在种种封建压制的夹缝中为自己发明了女书,这种发明从一开始便自矮三分,“把它变得更女性化”,⑧男人们对此丝毫没有任何兴趣。而到了邝丽莎的笔下,女书的形象难免不与女权者心中的奉为对抗武器的女书形象相交织。女书的世界里,男人成了缥缈的背景。殊不知,正是男人的不屑和鄙弃,才为女书的存在争取了空间和机会。男人自动地远离女书,不过是封建男权社会下少有的对女性的尊重和包容。
华裔文学中,在尽可能地描绘、还原旧中国时期的女书、老同及裹脚习俗等文化习俗上,《雪花秘扇》无疑是成功的。邝丽莎成功地唤醒了西方社会对古代中国的遥远而又模糊的记忆,激发了西方人对古代东方文化的浓浓兴趣和关注。然而由于文化背景、个人经历等的不同,作者在醉心于中国文化书写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摒弃自己的文化认同。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洋洋洒洒地演绎裹脚布带给妇女的伤害和苦痛,却不曾想到作为美的枷锁的裹脚布和现代的高跟鞋从本质上的一致性。作者用娟丽的笔调奋力渲染着老同之间的超越友谊爱情的姐妹情谊,却在性的描绘上不遗余力地展示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猎奇和想象。作者用温婉的笔法反复演绎女书的书写和内容,在彰显古中国妇女聪慧、轻盈与男权对抗的勇毅的同时,恰恰落入了女权主义者的书写模式。于是,作者在夹杂着自身文化思维模式的同时关照和演绎中国文化元素,其最终塑造的只能是似是而非的他者化的中国形象。
注释
①(美)爱德华·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②陶宗仪.辍耕录·缠足[Z].
③尹志红,陶辉.论男性视阈下的女性的审美价值取向[J].艺术百家,2012(12).
④ Mimi Chan.Through the Western Eyes: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Z].Joint Publishing Co.Ltd.HongKong,1989:104.
⑤(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二回[M].
⑥范若恩.“全球姐妹情谊”的幻与灭——《雪花秘扇》后殖民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解读[J].北京电影学报,2012(4).
⑦Morgan Robin.Sisterhood is Global[M].Harmondsworth:Penguin,1984:821.
⑧(美)邝丽莎(LisaSee),.雪花秘扇[M].忻元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3.
[1](美)爱德华·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美)邝丽莎(LisaSee).雪花秘扇[M].忻元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尹志红,陶辉.论男性视阈下的女性的审美价值取向[J].艺术百家,2012(12).
[4]范若恩.“全球姐妹情谊”的幻与灭——《雪花秘扇》后殖民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解读[J].北京电影学报,2012(4).
[5](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二回[M].
[6]Mimi Chan.Through the Western Eyes: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Z].Joint Publishing Co.Ltd.HongKong,1989.
[7]Morgan Robin.Sisterhood is Global[M].Harmondsworth:Penguin,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