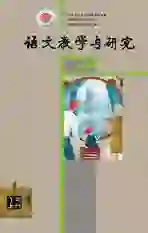狼·蝇子·阿随
2014-07-26周晓明
鲁迅为人,在我看来是很痛苦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
鲁迅为文,在我看来更加痛苦——一种鲁迅特有的痛苦。它是“孤独”、“无奈”和“失落”的混合,并充满悖论。
于是鲁迅说:“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影的告别》)
一.《孤独者》:“受伤的狼”
鲁迅曾经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①
就我个人而言,鲁迅的小说中,我最喜欢《孤独者》②。原因之一,我觉得它表达了一种灵魂深处的孤独、寂寞乃至绝望,且与鲁迅独特的人格精神气质非常契合。当年鲁迅与胡风谈到《孤独者》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③
鲁迅就是一个孤独者,并把孤独上升为人生的处境或普遍生存状态:“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再不会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
鲁迅的《孤独者》,写的就是“孤独”;或者说,写的就是“受伤的狼”似的孤独者的孤独。
首先,可以看到:“孤独者”是“异类”;而“异类”注定不被理解,须承担孤独。有时,真正的异类往往并不寻求理解:他们独往独来,甚至寻求孤独。从这种意义上讲,孤独者的孤独,首先源自于孤独者自己。
鲁迅本人就是一个异类,他一生都在“走异路,逃异地”,一生都在“与黑暗捣乱”。他“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独自承受“自以为苦的寂寞”和“独战的悲哀”。
小说的主角魏连殳也是一个异类,所以孤独。鲁迅以第一人称叙事,在“我”的回忆中,讲述了一个身为异类的孤独者的故事。例如,小说的第一章,由“听到”而至“去看”,在“异”与“同”的对比中,写孤独者的“古怪”;第二章则通过“第三次相见”,在“冷”和“热”的对比中展开,进一步揭示孤独者异于常人的行为方式以及灵魂深处的“冷”与“热”。
其次,可以看到:孤独者的孤独,也来自环境。——他永远为俗世所不容,不仅得不到理解,而且无法生存。在小说的第三章中,鲁迅通过“失业”,包括失业后世人态度的变化,着重描写了魏连殳的穷困、孤寂和悲哀。在第四章的前半部分,鲁迅进一步描写了孤独者的生存困境。
最后,还可以看到:孤独者的孤独,还来自于一种更普遍、更深刻的生存悖论——为生而生,向真、善、美而生,不得其生;为死而生,缘假、恶、丑而生,反可求活。于是,身体与灵魂不得不分裂,人须以杀死自己的方式生存,或作最绝望的报复与抗争。
小说的第四章后半部分至第五章,通过“来信”、“送殓”,着重描写了魏连殳在世俗绞杀中的“自我毁灭”,以及毁灭中的精神抗争和痛苦。
例如,鲁迅通过魏连殳给“我”的一封来信,写出了这样一种人生困境甚至是悖论——想活的时候无法活下去;不想活、不配活着的时候,却似乎活得很“好”。还如,在“送殓”部分,鲁迅还写出了这样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情景:魏连殳善待自己和世人的时候不被善待;而作践世人的时候反被迎奉和恭维。因此,他至死都在“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包括这个世界。
每当读完《孤独者》,“一匹受伤的狼”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并与魏连殳、与鲁迅混融在一起。
魏连殳是“一匹受伤的狼”:他闯入了“只需要驯服的狗而视狼为异类的环境中,孤独、挣扎、嚎叫、绝望,直至死亡”。④
鲁迅也是“受伤的狼”:他一生“与黑暗捣乱”,“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独自承受各种痛苦、伤害:“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实在受不了时,就发出自己的长嗥。
他的《孤独者》,就是他的“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二.《在酒楼上》:“蝇子停在一个地方”
周作人曾经称赞《在酒楼上》⑤是一篇“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鲁迅的一些同时代人,包括鲁迅的好友,也很推崇这部作品。但可能由于年龄的缘故吧,我过去并不怎样的喜欢它。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与这部作品有一种共鸣。
如果说,《孤独者》主要写“孤独者”的孤独;那么,《在酒楼上》则主要写“无奈者”的无奈。因此,《孤独者》的核心意象是“受伤的狼”——它在荒原中独行、独战、奔突、哀嚎、挣扎而至灭亡;而《在酒楼上》的贯穿意象则是“蝇子”——它在尘世中苟活,“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然而孤独也罢,无奈也罢,其自身或在鲁迅看来,仍都是一种痛苦——因为鲁迅对这两种痛苦都有深切的体验,包括记忆。《在酒楼上》写的就是这种“无奈的痛苦”;一篇关于“绕了一点小圈子的蝇子”的现代寓言。
所谓“无奈”,汉语字面义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它既是一种处境,也是一种心境。在很多情况下,“无奈者”不是“异类”;或虽然曾经是“异类”,而现在则沦为“同类”。因为“异类”是“战士”,是反叛者,他们往往特立独行、不顾一切;而“同类”则多为“庸众”或“失落者”,他们往往心灰意懒、苟且地活着。
《在酒楼上》的第一部分(1-7自然段),写第一个无奈者“我”的出场。
首先,可以感受到:无奈是一种疏离、空虚、懒散和寂寥。其次,还可以发现:无奈,也是一种人生的无根状态和漂泊感;一种精神上的失落或别无依傍。两者导致的都是孤独。
“无奈”,既是一种处境,一种心境;更重要的,也是一种痛苦——对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无能为力。事实上,许多“无奈者”,都曾经是“有为者”:他们曾有意气风发的过去,曾经想飞得更远;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现在再无力抗争,“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于是,这样的无奈或许更痛苦。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也清醒现在;只是无法改变现在。
《在酒楼上》的第二部分(8-20自然段),随着第二个无奈者吕纬甫出场,这样的无奈及其痛苦被逐步揭示和展现。endprint
“无奈”的痛苦,不仅仅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无法改变现在;还包括他们往往以清醒而认真的方式,顺从现在,并在顺从中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这实际上是一种“心死”的状态。庄子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⑥从这种意义上说,吕纬甫之无奈,在于他自己或旁观者,都是一种大悲哀。
《在酒楼上》的第三部分(21-42自然段),主要讲述了两件所谓“无聊的事”,以表现吕纬甫的“心死”状态。第一件“无聊的事”,是吕纬甫为了敷衍母亲,于深冬之际,千里南下,为三岁时死去的幼弟迁葬。第二件“无聊的事”,是吕纬甫为了安慰自己,南下时沿路搜求购买两朵“剪绒花”,打算送给先前邻居的一个女儿顺姑。
通过吕纬甫讲述的这些“无聊的事”,我们看到了无奈者的一种生存状态:认真的敷衍,清醒的麻木。而正因为有这种“认真”与“敷衍”,“清醒”与“麻木”的对立和矛盾,竟能在一个人身上相安、共存而且无事,使我更震惊于一个“无奈者”究竟可以怎样的“无奈”。
对于这样的“无奈”,就连同为“无奈者”的“我”也感到无奈了:“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一切“都织在”“不定的罗网里”——人生是这样的空虚、无助、无价值。于是,无奈者的无奈,在这篇小说中,被鲁迅推到了极致:吕纬甫还活着,有时还极认真地做着一些无聊的事;但他的魂灵已经死了——无聊、无奈,只是已死魂灵的在现世的痕迹。
鲁迅在谈到果戈理《死魂灵》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⑦
与《孤独者》写“特别的悲剧者”不同,《在酒楼上》,写的就是“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由于太平常,我们甚至不能觉察它们的存在,尤其是它们存在的普遍和残酷。
然而它们确实存在:过去这样,现在这样,或许将来还会这样……
三.《伤逝》:“阿随也将留不住了”
根据鲁迅日记,《伤逝》完成于1925年10月21日(即完成《孤独者》4天后)。关于《伤逝》的主题,历来有多种说法。
过去一般认为:《伤逝》的主题,是探讨情感、家庭,尤其是新女性的出路,包括“女性经济独立”问题;并常用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来阐释《伤逝》。
周作人则认为:《伤逝》是鲁迅“为自己而写的”。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还进一步指出:“《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但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彻底决裂是1923年7月;而《伤逝》则完成于两年后。其间是否真有联系还缺乏旁证。
也有人认为:《伤逝》与鲁迅和许广平的恋情有关;主要写“鲁迅对生命中的两个女人(许广平和朱安)的心灵感观”。从写作日期看,倒是很切近。但是,也存在疑问:如果鲁迅、许广平确实是1925年10月20日晚关系明朗化;那么,鲁迅为什么于“定情”当晚写出这样一篇“解构爱情”的小说?
其实,鲁迅自己也曾明确否定《伤逝》是写自己的事:
“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⑧
我的基本看法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契机和生活体验往往并不单一;其主题也往往具有多义性。此外,完成后的作品更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不同的读者,解读出来意义很可能相异。因此,作者的本意固然有价值;但阅读的体验尤其重要。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伤逝》主要写“失落”。“逝”者,“去也”;“逝”之“伤”,即对“过去”或“过往之事、之人、之情”等一切“失落”的感伤。
“失落”的逻辑前提是“曾经追求”、“曾经拥有”。否则,无从“失落”、“逝之”。因此,《伤逝》的第一部分,主要从“现在”——包括“现在的失落”出发,写“曾经的追求和拥有”:涓生与子君当初曾勇敢相爱、大胆同居。
“失落”也是一个过程。它可以突然降临,也可以逐渐发生。《伤逝》的第二部分,主要写 “曾经的追求和拥有”,是如何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消磨、消退,失去往日的光彩。小说先是写涓生眼中子君的改变:她日益世俗化,失却往日的清纯、美丽和勇敢。接着,在继续描写子君变化的同时,写涓生自己的改变:日益不堪生活的重负,且与子君产生精神隔膜。
《伤逝》的第三部分,主要写随着“人”的改变,“情”也被改变:涓生和子君之间,出现感情危机,并愈趋严重——爱情也走向死亡:小说先写涓生对阿随的遗弃及其影响;接着写两个人之间的精神冷战;再写子君挽救情感的努力,以及涓生终结情感的试探。
《伤逝》的第四部分是“结局”:一切都失去了——包括子君的生命;留下的,只是无尽的失落乃至悔恨。
先是子君的离去——去得那样的无奈而决绝。接着写子君之死——死得那样的孤独和绝望。最后,写涓生的无望的期待、忏悔和灵魂的自我拷问: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读完《伤逝》,像读完鲁迅许多其他的小说一样,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沉痛。因为我觉得它写的绝不仅仅是爱情悲剧,也包括种种其他的人生悲剧。
换言之,《伤逝》有两个关键词:“伤”是一种精神、心理、情感状态,如“伤感”、“伤悲”、“伤悼”等等。“逝”则可以是一切“不在”或“不再”的东西。在《伤逝》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无论美丽、纯洁、善良,还是爱情、婚姻、家庭;无论理想、追求、奋斗,还是承诺、决心、誓言,都不一定是永恒的存在——它们或最终将改变颜色,萎谢、枯黄乃至逝去。
于是,存在的本质就是“虚无”;“逝”之“伤”,其实是“存在即为虚无”之伤。
于是,爱情的“伤逝”,就上升和推演为存在的“伤逝”;而“逝”与“伤”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人生宿命与轮回。
又于是,“失落”、“无奈”、“孤独”,就成为相互联系、相互纠缠、相互阐释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命题。
(注:本文系《现代中国经典作家阐释》未刊书稿《痛苦鲁迅》章节之节录。原作于2006年)
①鲁迅:《〈自选集〉·自序》,见《南腔北调集》;本篇最初印入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②写成于1925年10月17日。当时未发表,后收录于《彷徨》(1926年8月)。
③胡风:《鲁迅先生》, 《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④闫玉刚:《改造国民性:走进鲁迅》,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年第83页。
⑤写于1924年2月16日,原刊1924年5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后收入《彷徨》。
⑥《庄子·田子方》。
⑦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8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旁。
⑧鲁迅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书信。
周晓明,本刊顾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责任编校:晓 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