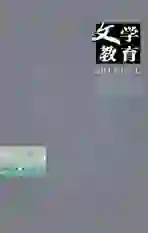《钢的琴》:温情悲悯的时代挽歌
2014-06-30苏也
这几年总有朋友问我,最近最好的中国电影是哪一部?面对这个问题,我总感到很为难。想了半天,我说,不知道它是不是最好的,但我觉得它是最打动我的,张猛导演的《钢的琴》。大部分时间,听者都会反问道,什么?哪个电影?什么导演?或者表示自己大概在网上看过这个电影,但是对于其故事情节的印象不深。
的确,对于中国影院的整体观众而言,这部电影是陌生的,是被忽略了的。张猛导演的名字还没有进入主流视野,而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里,除了秦海璐之外,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再加上这部电影基本没有任何的前期宣传,《钢的琴》在全国院线只上映了两周,就因为票房不济和档期考虑被撤了下来。除此之外,这部电影很难用一种固定的类型去加以定义,在文艺、喜剧、商业、剧情等关键词中左右徘徊,观众很难对这部影片产生一个清晰的观感。所以,《钢的琴》的票房窘境既有制作方本身的原因,也有大环境的不利影响。但这些商业收益的成功或是失败并不能定义这部电影人文意义的成功与否。也许,正是因为种种与时代心理不适应的现状才更加反映了这部作品的社会思考。电影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理想主义情怀的幻灭,而这部电影自身的市场失败似乎也在现实生活里证明了这种看似华丽的理想情怀的悲剧命运。
电影的故事并不算新奇,用一句话说就是一群下岗工人自造钢琴的生活小品。前几年,这样的故事在文学和电影领域里层出不穷,拾荒者造飞机,农民拍电影,小人物的一腔激情和荒诞的创造力似乎总能博得一些眼球。《钢的琴》顾名思义,就是小人物试图用钢铁制造钢琴,这种简单语言结构的拆分既解释了剧情,也在逻辑上隐喻了这种简单拆分的不合理与滑稽,似乎是在暗指这场激情事业的失败结局。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地点在中国北方的某重工业城市。这个城市在剧中并没有向观众点明,但由演员的口音可以分辨出他们来自东北地区。这样的安排似乎也表明了创作者的理解:这类的故事和情感也可以同理地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土地上,发生在不同口音但相同身份的人们身上。主人翁陈桂林原本是当地钢厂的技术工人,他下岗后凭着会拉手风琴的本事,独自组建起了一支小型乐队,每天奔波在婚丧嫁娶、店铺开业的各种零碎散活之中,勉强维持生活。他的妻子小菊几年前离家而去,如今已投怀送抱于靠卖假药发财的商人怀里,按照陈桂林自己的话说,“她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生活”。这次小菊光鲜亮丽地回归,是为了要与陈桂林离婚,还要带走他们唯一的女儿小元。陈桂林爱女心切,但又唏嘘于自己的经济实力。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钢琴家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女儿买一架钢琴,以此博得女儿的抚养权。于是,捉襟见肘的陈桂林开始了“圆梦之旅”,从借钱买琴,到找人偷琴,连连失败,走投无路,最终开始了气势恢宏的造琴事业。
在这一场由亲情包裹的小人物之悲喜剧里,镜头通过“借钱买琴”,“合伙偷琴”再到“齐心造琴”的三个环节,向观众刻画了一个逝去的大工业时代,以及一系列形象生动的底层人物。除了主人公陈桂林之外,故事里还有他的好朋友,丧偶多年、为人老实的王抗美,留俄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汪工”,狡猾、爱占小便宜的“胖头”,犯过事儿、但讲义气的“快手”,留着毛式发型的旧时代大人物“季哥”,还有陈桂林的女朋友,能歌善舞、为人热心的淑娴。他们这一群人都来自过去辉煌一时的工人阶级,性格行为上都各有各自的毛病,家庭生活中也有各自的烦恼,但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显得有血有肉,似乎就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人。再加上电影背景里常常出现的那两根厂房大烟囱,横移的镜头让人们看到了上世纪末改革开放后,重工业时代褪去后的生活风情画。
这种对于时代风情画的描绘以及怀旧情绪的渲染出现在电影的多处场景里。电影一开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笔直地站着出现在镜头前,他们各自望向不同方向,虽然在相互对话但都没有扭头看对方一眼。陈桂林和妻子小菊用这样子的方式出场,既体现了他们分崩离析的感情关系,也在画面上制造了一种戏剧冲突。小菊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陈桂林答,“别拿幸福吓唬我。”这种小品式的对话风格充满了浓郁的东北味儿,但也契合了这种视觉上的戏剧感。电影画面里的三层内容分布也多次运用在此片中,以开场而言,画面远景里慢慢拉出的那两根巨大的工厂烟囱,一方面在形式上对应了一男一女的视觉构成,达到了一种观感上的和谐之美,同时也在心理上暗指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年代,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心理情绪和故事走向。冒着稀疏烟圈的烟囱如地方神仙一般地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男人和女人,各家的悲欢离合都净收它的眼底。但它只是默默地看着,不做任何评价。因为它知道,自己已经是时代的淘汰品,而土地上人们所经历的欢笑或泪水也不过就是时代转型时期里的必经过程。这过程不能说其好坏对错,只能远远地看着,多读出一份温馨,试着用笑去化解泪的苦涩。
另一个时代风情画的描绘发生在陈桂林拜访汪工之前,他来到潜水池塘旁边炸鱼,想用不要钱的鱼作为见面礼去请教汪工。对于这个画面我个人十分有感情,作为八十年代后期生人的我们都没有机会亲眼见到这样的场景,但这种炸鱼吃鱼的活动充满了父母亲对上一辈人的描绘里。我的外公也是一名金属冶炼厂的工人,在母亲的回忆里,父亲带着孩子们去荷塘里炸鱼补贴家中伙食的故事既是心酸的过去,但也是甜蜜的记忆。陈桂林炸鱼的这片水塘已是荒草丛生,毫无生气,眼看就是这段靠天吃饭的时代尾声。这里的自然环境已在奄奄一息的边沿,看来再过几年,经济发展带来的工业污染就会将这水塘里的鱼消灭干净,甚至那时这里还会不会有水塘都是个问题。陈桂林站在溏边捂着耳朵抽着烟,看着泛着白肚皮漂上水面的几条小鱼,似乎在思考些什么,但也许什么也没想到。画面的远景里,水泥高架桥上一列绿皮火车吐着浓烟轰轰隆隆地驶过,打破了这看似平静的画面。靠天吃饭的时代已彻底被“不劳而获”的时代所取代了。马上,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将不再是只要你劳动就可以致富,反而是那些靠着钱生钱、或是钻时代空子的行为才会占去既得利益。陈桂林看着那几条死鱼,也看着属于自己的工人时代的死去。endprint
这种对一个过去的工业时代的刻画其实出现在电影的每分每秒里,很多时候,导演甚至是在用破坏画面的方式去打破叙事常规,为了突出展示一些遥远而沉默的东西。在《钢的琴》里,讲故事、表情感的,不仅是前景里的男人和女人,还有中景里的房屋街道、过往人群,更还有远景里的绿皮火车,无声无息的大烟囱。这些镜头的设计十分讲究,有时内容完全居中,有时人物就出现在镜头的黄金分割点上,这种近乎舞台剧的构图设计让那个时代的风貌完美地呈现在了一幅幅画面里,看上去甚至不像是电影,而更像是对于一张张珍贵的泛黄老照片的动态想象。
而有的时候,在某些动作镜头里,人物甚至已经跑出了电影画面,但创作者对于时代背景的关注和留恋甚至超越了对于人物关系或者动作的描述。在很多转场切换中,镜头对于背景和环境的表现成为了主要任务。似乎相较于人物间的矛盾关系、爱恨情仇,导演张猛在更多的时候,是在电影里表达了对那个时代和环境的怀念和不愿离去。镜头长久地定留在那里,注视着没有人物的空镜头,深情地望着远处的背景,目送那个时代的消逝。
在这种特殊的时代风情画的表现上,打破常规的淡化前景、突出背景的手法,自然会遭受到专业人士的诟病。而这种过度情绪化的艺术手段也使得这部电影在后半段的叙事结构上显得不够紧凑,情绪的连接性不强。但是换个角度看,这种选择性的“错误”也正是这部电影的魔力和情怀所在。
相较于陈桂林涂满发胶的发型,小元对于钢琴的热爱,我相信,让观众们印象更深刻的是那炸鱼的荒草河滩,灯光昏暗的歌舞厅,用红色油漆刷写的简单招牌,桌球室里吸烟的叛逆少年,绿漆墙壁旁置放的烤瓷保温瓶,还有那成为主角的大烟囱。这一些看似可有可无的背景都充满了那个时代的风貌,饱含我们父辈对于过去生活的记忆,再现了一段文化在一个时期里标志性的视觉表象,勾起了我们现代人关于过去美好的想象或回忆。
除了在视觉上突出工业时代的印迹,《钢的琴》在统一而温暖的怀旧情绪下,还在音乐上表现了创作者对于工人阶级的悲悯怀念,以及对于那个大时代的复杂情感。大量的俄国老歌和革命歌曲的使用把观众一下子拉回了那个年代。例如在一开始夫妻决裂的夸张亮相之后,整个电影就被苏联民歌《三套车》的悠扬旋律占满。在这电影主线情绪的铺陈开张之时,导演选择用一场雨中的葬礼介绍这个怀念过去的故事。陈桂林和他的乐队成员在雨中套着廉价的黑色塑料垃圾袋挡雨,一起歪歪扭扭地吹拉弹唱着。这种带着点儿诗意的写实叙事中,一种戏剧的夸张和小品式的黑色幽默怪异而温馨地结合在了一起。《三套车》的曲调在两根大烟囱做背景的画面里诠释了悲剧中的喜剧因素。最终死者家属对这首“太过忧伤”的歌曲的叫停,《三套车》被《节节高》的欢快音乐所取代的桥段也强化了这种悲剧意味的喜剧效果。这样,此片对于旧工业时代和工人阶级辉煌时期的怀念与歌颂,用一种极其自嘲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动人而不造作煽情。这种在如今看来显得有些卑微的存在,却在一种具有缅怀意义的舞台性叙述里显得崇高而伟大。
尽管这并不是导演本身的用意,但开篇的雨中乐队让很多影评家读到了前苏联电影大师库斯图里卡的名作——《地下》。在那部堪称完美电影里,也有一支贯穿镜头始终的,看起来歪歪扭扭的乐队,一直演奏着戏谑的乐曲,看似与剧情毫无关系但又从未离开。同样是用普通人的演绎来描绘一个时代的风貌,《地下》则更多的表达了一种民族的、时代的、集体的命运和坎坷,而《钢的琴》则是用一种小人物的、个体命运的、日常点滴的关怀展现了那个失去了的美好年代。其实,这种前苏联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的东北地区,无论是在文学艺术还是在音乐上,都受到前苏联的巨大影响。曾经的苏联“老大哥”对我们在科学知识、政治军事、文化生活上的参与和启蒙其实是影响了中国的一整代人。我们怀念着“中俄友谊”时期的美好,也是在怀念那种伴随着革命激情和理想主义时期的简单和纯粹,一种在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的光环笼罩之下,所有的艰难困苦都附上了金色的外衣。那种相信世界是共和大同的,人人都是平等博爱的,生活是付出必有所得的年代是值得怀念的。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乡愁伴随着《三套车》的曲调,牵动了东北、甚至是中国大部分人的情感,那种父辈对共产主义年代的生活理想也饱含在了那悠扬而忧伤的旋律中。今天,尽管我们的社会生存法则已经改变,但我们只要听到那个年代的那些革命歌曲,似乎还能回忆起那些对于共产时期的集体主义的理想画面。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化的快速生活里,还是有一群人对于苏联时期的文学,音乐,电影充满了浓浓的感情。他们怀念的也许并不是那个中俄共产时代,而是自己活在那个梦境中的甜蜜滋味。
于是,在那两根象征着过去共产革命、工人阶级辉煌的大烟囱下面,一首首苏联民歌从手风琴里拉出,从淑娴的嘴里唱出,从“造琴队伍”的大合唱中喊出,伴随着一些情绪复杂的泪花,那些歌曲传达出一个沉默许久的群体的声音。破旧的厂房,生锈的车间,不卑不亢的下岗工人,他们还活在“工人阶级敢想敢做”的美好梦境里,即使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变迁,自己的辉煌不再,但他们还是用一种可笑到可爱、执拗但执着的精神,完成着自己一个集体的、满怀深情的文艺梦。用一种近乎穷途末路的智慧,荒诞而壮烈地唱着一曲时代的挽歌。
导演张猛自己坦言,这是一部拍给工人阶级的电影。他们的褪去发生的太快,四十年前他们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里,还担当着革命家和主人翁的角色,而如今,用“下岗”这两个词去概括这整个阶级的状态也不为过。他们现在是怀揣梦和理想的社会弱势群体,曾经最大程度地承受了社会改革的阵痛,却不得不再次接受被时代所抛弃的事实。导演张猛面对这个阶级人群的现状,自身充满了复杂的感情,而在反思上得不到最终的结果。所以这一部弥漫着小品式的黑色幽默电影里,其实体现了一种虚无、颓废的“反励志”、“反正能量”的精神感悟。这种有关怀旧的惆怅,以及对于现实的无奈使得这部电影在情感上避免了廉价媚俗的煽情,用一种自嘲的手段化解了这一社会问题原本的沉重和伤感。endprint
这种自嘲的伤感在电影的结局上体现的十分明显。在淑娴的提醒下,陈桂林已经意识到窘迫的自己虽然是更爱女儿的人,但也许并不能在经济上给女儿一个更好的未来。他赌气地说,“你们啊,都一样,太现实了!”面对这个现实的社会,小小年纪的女儿已经意识到资本的力量,所以她选择,谁给我买钢琴我就跟谁。所以,最终即使陈桂林造好了钢琴,也留不住女儿。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个结局,认清了社会的现实,看到了所谓理想的不堪一击。
现实中,导演张猛的境遇和剧中的陈桂林颇有几分相似,他何尝不是一个在做理想主义之梦的人呢?几年前在沈阳,张猛去铁岭评剧团里找木材,发现了一台斑驳破旧的木质钢琴,至今还能发出声音。人们说,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群文艺工作者为了省钱,自己画图纸,联合动手造出来钢琴。之后张猛在沈阳钢材市场买建材时,发现了许多已经下岗的钢铁厂工人,他们各个身怀绝技,车、钳、铣、铆、电、焊一应俱全。这两件事情一直在张猛的脑子里打转,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他想出了《钢的琴》这个故事:走投无路的父亲为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找了一帮三教九流的下岗工人一起来自造钢琴。简单的剧本只有三十多页纸,电影预算五百万人民币。张猛拿着上海国际电影节给的30万奖金、韩国方面提供的50万后期制作费,拉着秦海璐、王千源,就在东北红旗拖拉机厂开机了。开机两周后,人们才知道,剧组的账上只剩下47块钱。
最后这部电影硬是在导演四处借钱,剧组处处省钱,演员自己掏钱的状况下拍摄完成。张猛终于在2010年造好了自己的《钢的琴》,也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大奖,但进入国内院线却没法挣钱。张猛就跟陈桂林一样,终于意识到了社会的现实,资本的力量。电影结尾处,造好的钢结构钢琴在车间被缓缓吊出,那气势如虹的现身,如森林之王一般的气质让人动容,虽然弹出的声音和高级钢琴的音准和音色都有差别,但这架钢的琴还是如梦如幻般地完成了。结果,这激情的事业完成后,女儿还是没能留下;在激情的文艺情怀的实现中,观众还是没有用票房留住这部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票房过百亿的传说中,《钢的琴》和工人阶级的时代一样,被市场快速地淘汰了。
对于中国的电影产业而言,现在的确是一个气势磅礴的大时代;但对于《钢的琴》这样的非主流的诚心之作而言,这一定不是一个最好的年代。我不知道导演张猛对于他这腔热情的滑铁卢会作何感想,但在电影里,陈桂林发现偷琴行动失败后,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选择在雪夜里,独自浪漫地在钢琴上演奏一曲。这种极其不合常理,没有逻辑,荒诞滑稽的行为也许是一种口号,一种情怀,一种理想。此时坐在这里给自己演奏的,不仅是陈桂林,也是张猛本人。
最后引用剧中汪工对两根大烟囱的讲话来描述这种对已逝的理想主义,和辉煌不再的工人阶级的怀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些话语可以看作是对工业时代生活印记的告别,也可以看做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独白,最终也成为了《钢的琴》这部好看但不卖座的电影挽歌:“这两根大烟囱,在我看来,他们是某些人成长的记忆,也是某些人回家的坐标,但他们更像是两个被我遗忘的老朋友。我不知道是应该极力地挽留,还是应该默默地看着他们离去。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忧伤,似乎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时光荏苒,社会变革,如今为了时代的发展进程要求他们离开,我们总还是要试着做点什么。如果我们成功,他将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如果我们失败,他们也将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
但愿时间能证明这部电影的价值,《钢的琴》里所描绘的那个年代的生动人文风情画必将成为我们电影历史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苏也,生于中国武汉,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