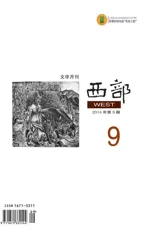周边小说四题
2014-04-06捷克埃米尔赫鲁什卡拓芙译
[捷克]埃米尔·赫鲁什卡拓芙译
周边小说四题
[捷克]埃米尔·赫鲁什卡拓芙译
埃米尔·赫鲁什卡(1958-),捷克小说家。出生于捷克西部城市姆拉达-博莱斯拉夫,在捷克与德国巴伐利亚州边境地区度过青少年时期。1996-2003年期间在斯科达公司比尔森分部工作,2004-2009年间在布鲁塞尔任欧盟议会议员助理,现居比尔森。赫鲁什卡以法律工作为生,以时事和历史评论为乐。自1996年在慕尼黑出版诗集《紧急状态》后,有诸多关于二战史和捷德关系的文章书籍以捷克语与德语见诸于世,此处的《旅途》出自短篇小说集《一人双棺》,其余三篇以少年的眼光诠释六十年代的“苏台德”地区,出自短篇小说集《我们这些苏台德的男孩》(德国出版时以《降落伞下的马》为标题,经作者同意中文译作《异故乡》)。

异故乡
“格鲁纳,来块口香糖!”梅查洛斯下了命令。
格鲁纳个头不高,脸色苍白,一双红通通的奇特招风耳。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小片口香糖递了过去,包装纸上印着“箭牌薄荷”。大家都知道:格鲁纳一家又收到了西德寄来的包裹。
“你会德语?”我问梅查洛斯。教育程度怎么可能高成这样!梅查洛斯的爹在林子里赶马拉木头,成天醉醺醺,娘就是个纱厂扫地的。他自个儿留过两次级,这才跟我们成了同班,读六年级。
“啥?”
“老伙计,过来快活下。”
“你这鬼头!”
格鲁纳被宽宏大量地放过了。梅查洛斯黑不溜秋的,长相无愧于他那东方血统。他优雅地把口香糖放进了嘴巴,然后意味深长地抬起胳膊,手指间夹着包装纸。这东西可是我们当年的热门收藏品。
“谁想要啊?”
“我出两个克朗!”
“我出弹弓皮筋!”
“温尼托②的画片!”
“去他妈的吧。”梅查洛斯傲慢地说道,撕掉了包装纸。
天将傍晚。我们走在村中间的鱼塘边。水面点缀着一簇簇黄色的萍篷花,宁静得像是夜晚。路上要是碰到德族③同学,我们就招呼“kriskot”④,要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或罗马尼亚人,就招呼“brejden”⑤。这寻常得就像太阳打东边出来一样。我们创建了典型的复合文化社会,尽管对这多年后才出来的词,我们当时还一无所知。
“老博莫娃搬走了。”梅查洛斯宣布说。
这真是草泥马的要闻,就算我们其实老早就全都知道了。博莫娃这个老寡妇投奔德国亲戚去了。西德,不然还能是哪?他们是开车来接她的,只带走两个随身箱子。其余财产在亲戚们看来只是一钱不值的破烂货。他们锁上屋门,钥匙交给了地方民族委员会。这在当时是常事。德族人要是战后几年内没赎回自己的房子,房子就自动归国家了。
六十年代末,我们村里许多本地德族人纷纷搬去西德。其中也有我们的若干同学和伙伴。不久后格鲁纳也消失了。还有弗里德里希、拜尔、波尔和罗斯迈纳。他们再没回来,我们只是时不时地在他们的亲戚那里听到点什么。要么从此就断了音讯。
“我们瞧瞧去。”司令官梅查洛斯下了命令。
小屋斜插在鱼塘边的斜坡上,依着条小径。放学后我们常从这儿走,往博莫娃的硬铁皮屋顶上扔松果和石头来吓唬她。房门紧锁,窗户紧闭。地下室的小窗户也关着。小屋左边墙上贴着个又窄又高的板棚。
“你,钻进去,瞅瞅里面的状况。”梅查洛斯指挥着。
我顺着梯子爬了上去。里面光线昏暗,乱七八糟地堆着陈年的干草、木头和坏掉了的农具。顶上有个小窗户通往屋子阁楼,打得开,别说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就连十三岁的男孩都可以不费多大力气就钻过去。
“找到了,这里!”我喊道。
我们四个陷入了陌生的屋子里,久无人居、久未通风。这种奇特的感受直到今日我仍记得,每当我们偷偷钻进被遗弃的陌生屋子里,同样的感受就会再次浮现。警惕,胸骨下面的颤抖,有点想解大手的感觉。
我们走下了阁楼,那里没啥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也曾搜过老施杜克家的阁楼,那才叫有货呢!比方说何尼查就在大梁后面发现了本相簿,名叫“KRIEGSERINERUNG”⑥。贴的每张照片上都写着点什么。有士兵、少女、汽车和加农炮。还有被吊死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士兵们站在这些人旁边,笑着看镜头。后来何尼查把照片揭下来,把它们重新命名为印第安人或者歌手。大炮被称为冯德拉奇科娃⑦,吊死的人们变成了英勇的阿帕奇⑧。
下面是厨房、卧室,还有个小杂物间。到处都弥漫着霉菌、灰尘还有天知道什么鬼东西发出来的奇怪气味。
厨房里的老旧碗橱里满是玻璃制品和瓷器。大玻璃杯、小玻璃杯、绘着花纹的杯盘、贴着德文标签的香料。这些我们都不感兴趣,我们要找的是武器、德国钢盔、刺刀、匕首和战时徽章。
瓶瓶罐罐……
“开火!”梅查洛斯下令。
四把弹弓向橱柜的玻璃门一阵齐射。子弹是钢质螺母。然后又是,乒!乒!老博莫娃的瓶瓶罐罐全都化为碎片。乒!普洛瓦兹尼克打下墙上镶着玻璃的圣人像。乒!桌上的花瓶。乒!窗户。好吧,其实窗户不是故意的。
旁边的房间里有夫妇两人铺着床垫的床,还有衣柜,里面是些陈年破烂货。我没有因为嫌弃它们而掉头走掉,于是终于有了第一份收获。柜子底下藏着个精巧的小型手持角磨机,还带着磨盘。
“嘿,给我。”梅查洛斯诱骗着,把角磨机从我手上拽了过去。
“草泥马,”我说“,上次我想要那个手电筒,你给了我吗?屁!手电,你家里倒有不下五个。”
遭受冒犯的梅查洛斯消失在那个黑暗的小杂物间里。叮叮当当、咯吱咯吱、。
“那儿有啥?”普洛瓦兹尼克朝他喊道。
“就是些旧瓶子。”
“可回收的?”
“不是……”
搜查渐近尾声,没啥货了。我们从阁楼窗户钻出来,下到斜坡上。老博莫娃的家我们已经抄过了,尽管卖给来度假的人好了。
“那你还是不给咯?”梅查洛斯朝我俯下身来。
“没门儿。”
“那你瞧瞧这个好了!”梅查洛斯从运动衫底下摸出一条卷着的军皮带,皮带扣上刻着十字和“MEINE EHRE HEISSE TREUE”⑨。党卫军皮带!铁定是在那个小杂货间里找到的!王八蛋!
这条皮带我想得要命。
“那好吧。”我说。扫荡来的物件就换了主人。
天黑了下来。
一年后,博莫娃又回到了她出生的小村子。是亲戚们开车载她回来的。她想要一个人去看看自己的屋子。亲戚们在熟人家里等她。博莫娃走到房门紧锁、青苔满布的屋子旁,驻足站了一小会儿,然后向鱼塘走去,淹死在了那里。漫长的公务交涉之后,他们把她,联邦德国入籍一年的新公民,埋在了我们村子的墓地里,那儿是她的归宿。
半老公的风流韵事
卡鲁金是俄罗斯人,不光他的姓这么提示,名字也一样:尼古拉;费舍洛娃,从姓推断可能是个德意志人,她的名字则给这推测添了些准头:丽赛罗特。这两人一起生活,没结婚,因为费舍洛娃显然不想放弃那份从西德给她寄过来的战争遗孀补贴。
卡鲁金一文战争补贴也没有,尽管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开着驱逐机到处飞,最后甚至飞出了个苏维埃英雄的称号。不过这头衔后来又被摘了:45年他在卡罗维发利⑩喝得正高兴,有个同伴据说是泄露了卡鲁金所谓的犹太血统,触了霉头,被他开枪崩了。但若没有这个头衔,卡鲁金现在也不会安卧在寡妇费舍洛娃身边,最轻也会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哪个角落里去吹西北风(再说天知道,兴许在俄罗斯旷野把她丈夫送上了天的正是他)。乖张的命运让被撤了官职、踢出部队的卡鲁金留在了捷克,更古怪的是他居然来到这么个被人遗忘的边境小村。但事儿就这么发生了。
卡鲁金喝酒,酗酒,酗得对得起真牌老毛子的身份,几乎每天都醉醺醺的。但那种哥萨克的本性,小村小职员松松散散的工作,以及丽赛罗特无微不至的德意志式关怀,把他的酒精主义变成了某种换成本地话就是“沙龙行家”。尽管在曾经的“苏台德”地区一呆二十年后,卡鲁金除了出身之外已经跟苏联半毛关系都没了,人们还是把他当作活生生的圣体光座,一有重要的公共政治活动就请他去参加,好让他来上一通简短却攻击性十足的俄语,然后再跟乡干部或州干部一起喝个昏天黑地以示犒劳,因为友好嘛,友好。
丽赛罗特出人意料地爱着她的飞行员,而他大概也爱她。这俩人只为他们自己个儿而活。卡鲁金除了一家当地小酒馆哪儿都不去,(值得一提的是,以边疆酒馆的水准来看,这家店还算过得去,甚至还提供热菜)他不在家时,丽赛罗特就去拜访自己的德意志族女友们。需要透露一点的是,她的女友们要么嫁给了外族人,要么像丽赛罗特一样跟着外族人过活: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斯拉夫人。大部分德意志人被驱逐后,这些人搬过来填上了坑。纯粹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家庭属于“精英”,那个圈子已经不接受丽赛罗特了。
从这些女友嘴里传出消息,说丽赛罗特家起居室的墙上挂着两个大相框。一边是身着德国国防军军士服的胡戈·费舍尔,表情肃穆;另一边是戴着若干勋章的少校卡鲁金,满脸笑容。两位先生中间挂着耶稣受难像,好让他们看在神的意志上别打起架来,不过也许压根儿就没这危险,至少卡鲁金对他的前任没什么成见。
唯一有可能搅扰丽赛罗特和她的俄罗斯英雄关系的,是卡鲁金的不忠。要知道嫉妒会暴露出丽赛罗特的软肋。不过这软肋藏了许久,因为没机会——有谁会看上醉鬼卡鲁金!
可是村里搬来个新屠夫,接替去世了的维柯卡先生。这位屠夫,也就是鲜肉和香肠小卖部的头头,瘦得出奇,高个儿,光头,坑坑洼洼的大鼻子上架着副硕大的眼镜。他叫查达克,年近五十,妻子比他小上十五岁还不止。查达科娃女士黑发,胖乎乎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对人非常友好。首次必要的社交活动中,也就是说拜访小酒馆时,这对夫妇就自然而然地碰上了卡鲁金。于是查达科娃女士和俄罗斯英雄之间擦出了火花,点燃了火焰。然后仿佛又有谁给火里浇上了海量的莫洛托夫鸡尾酒⑪。
把干“那事”的卡鲁金和查达科娃女士逮个正着的,就是屠夫查达克。一对爱人正在肉铺后面以身相许,查达克通常就在那儿剁肉剔骨绞香肠。这地方看起来什么样、闻起来什么味也就可想而知了,但卡鲁金和查达科娃的其他感官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据说最开始查达克是想干掉卡鲁金的,但曾经的红军上校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自己的情敌。不过他并没有伤害查达克。如果说当场真有什么血迹的话,那也千真万确只是猪血和牛血。而查达克,在卡鲁金昂首挺胸离开之后,至少给了自己的妻子好一顿耳光,然后就是一通张罗,好让整件事传到寡妇丽赛罗特的耳朵里。
事儿是周日晚饭时出的。星期天,丽赛罗特总会在起居室两位英雄的相片下摆好餐桌。卡鲁金喝完了汤,品尝着奶油兔肉,打发丽赛罗特去厨房拿瓶啤酒。丽赛罗特进了厨房。回来时手上拿的不是冰镇啤酒,而是一把锋利的厨刀。然后她大嚷一声——听不出内容的可怕吼叫声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怒——用尽全身力气把刀插进了卡鲁金的后背。上校和椅子一同倒在地上,抽搐着,身子下面流出了一大滩血。这一刀仿佛唤醒了迷梦中的丽赛罗特。她奔出屋去,哭喊着求助。医院保住了查鲁金的命。
几个月后县法院对丽赛罗特·费舍洛娃进行了审判。法庭若干次提请证人卡鲁金注意,要说实话,不要如此明显地偏向被告。审理的高潮是查鲁金宣称,伤是他喝醉了酒自己弄的,当时他正在切洋葱,摇摇晃晃摔倒了,背部着地,而在摔倒前他想用刀尖挠背上的痒痒来着。
丽赛罗特被判了五年。坐了三年号子后假释回家。而这三年中卡鲁金靠酒精排遣忧伤和孤独,身子已经全垮了,爱人回来两个月后就死于心肌梗塞。他是在家里去世的,就在起居室他自己的和国防军军士的相片下面,弥留之际手一直被握在丽赛罗特的手中。
卡雷尔·法贝尔之死
卡奈特往笼罩在小酒馆的沉默中扔了句:“唷……已经两年了,正好是今天。”气氛当下多云转阴。
“为啥是两年?什么两年?”法贝尔沉下了脸。
“弗朗塔·布尔塔茨⑫离开我们升往永生已经两年了。”卡奈特意味深长地答道。
卡奈特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后,直接来到了边境地区,挣扎着逃离战争找了条活路。他在建筑工地上做帮工,以一种仿佛是庆典但同时又很实际的奇特方式沉迷于死亡。大家都说,在经历了毛特豪森集中营⑬后他已经不正常了。死亡已经灌进了他的生命,这辈子是甩不掉了。他也靠给村子管理墓园来挣点外快。他的第二项嗜好是创作诗歌,业余到不能再业余。他用沉重的手把自己的作品乱划到小纸片上,喝醉后再在酒店尿斗旁念给他的酒友们听。
“啊,我们的朋友被死亡带走,”卡奈特挺身而起,用雄浑的声音朗诵起来,“我们爱他,但那婊子……在周日那天到来。弗朗塔以为他这样就不会孤独,终局却是被埋进墓地。”
布尔塔茨另外的三个朋友也站起身来。诗歌朗诵声一落,就响起了啤酒杯的碰撞声,然后沉浸在悲伤中的男人们艰难地坐下。
“是个好伙计,”抑制着激动心情的玛利尼亚克微微点着头。“好伙计,不像某人那么抠门。每次他都借我钱,每次,真格的!”他一拳捶在啤酒杯之间,呜咽了起来。
法贝尔要了四大杯朗姆酒。“五杯,你也跟我们一起喝吧,为弗朗塔。”他指示酒店老板说。
“好像我还看到他坐在那儿一样。”酒店老板舒尔茨晃着脑袋。他体格健壮,长着一张电影演员的脸。
酒店老板他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命运之路,却没给自己造出点什么来。还是个小伙时他就加入了武装党卫军。55年从俄罗斯战俘营归来,居然回到了他出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小村庄,他在这儿已经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回来不久他就被逮了起来,判决为战犯。五年号子后奇迹再次发生——获释的他没被迁到西德,他自己对此也没兴趣。他又搬回了出生的小屋,从46年起那儿就没人住了,家什已被洗劫一空。他修好屋子,娶了老婆,最后还生了两个儿子。妻子是个年轻漂亮的捷克姑娘,民族安全委员会地区委员的女儿。老丈人因为女婿被迫告别了制服,愤而断绝了父女关系,搬回到梅尔尼克区的什么地方去了。
“再来五杯,算我的。”贝克施坦因冒出一句。和同桌那些人相比,他算是个老苏台德了。但他却非常骄傲于自己的身份:他不是苏台德德族,而是“帝国”德裔,生在斯图加特⑭。
假如说村子里存在什么种姓之别的话,也是那些未被迁出的当地德裔们依照着某种古怪的规则自己搞出来的。所谓的帝国德意志人高于苏台德德意志人,纯血的“苏台德”又高于他们那些混着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天知道什么血的同胞。
已经死掉了的布尔塔茨大概是匈牙利人,但到底是不是也没人知道。战后他娶了德族女子施密托娃,但几年后她便离开他投入斯洛伐克人拔嘉的怀抱。此后布尔塔茨便和他的酒友们混得更近了,尤其是和众人敬畏的法贝尔。
伐木工人法贝尔力大惊人,身为捷克人,娶了个斯洛伐克老婆。另一个酒友诗人卡奈特据说出身于波兰,但事实肯定不是如此。他那个温顺的妻子卡奈托娃不识字,是个吉卜赛人。玛利尼亚克的斯拉夫血统则不容置疑。他妻子是个德意志族人,她的家族据说在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三百年,如今再三对玛利尼亚克施加压力,恳请他一起搬去西德。玛利尼亚克殊死不从,家里因而成了地狱,他便靠喝酒来逃避苦难。这些怪异组合生出来的孩子们却早已和平共处了。父母的民族属性他们并不在乎。
钟点数在涨。舒尔茨用软铅在陶瓷酒杯垫上画的道道也一样⑮。可阴霾不但没有散去,反而更浓了。酒店柜台右手边的那桌客人一致决议去举行一场独特的悼念活动。
“再给我们来……三瓶朗姆酒。”法贝尔要求道。
“这可够贵的啊!”酒店老板诚心劝告说。
“去他妈的!”
快到子夜时,他们出发去了墓地,也带上了酒店老板。五个跌跌撞撞、说着醉话的人影荡过静寂的小村。管理人卡奈特亲自打开了巨大的铁门。
“衷心欢迎来到我的王国!”他做着请进的手势。
过往与现今在墓园里古怪地掺合在了一起。德意志人的墓碑和十字架——上面最早的纪年还在19世纪——和战后新搬来人们的坟墓混杂着。高级林业官奥托·莱茵纳(1855-1907)的左手边是卡特日娜·科奈奇娜(1902-1963),右边则长眠着约瑟夫·斯帖特卡(1915-1951),他因摩托车事故死在了村子的正中央⑯。
不受欢迎的教师克维托斯拉夫·里布卡(1892-1962),斤斤计较、胆小懦弱,对小孩子却又凶又狠,躺在早先的家庭纺织作坊工人马丁·采德勒(1849-1916)的坟墓里。卡奈特只消刨出早已烂透的棺材残渣,从保留下来的金属十字架上摘下写有采德勒名字的小牌,换上里布卡,活儿就成了。里布卡由两个女人拥着:德意志女子罗莎·法斯宾德(1888-1945)和斯洛伐克人玛利亚·奇日玛罗娃(1900-1959)。德意志人的坟墓大多无人料理、难以为继,因为战后他们的许多亲属和熟人都从小村里消失了。
布尔塔茨的坟墓同样没人管。他的棺材上方如今还耸着一堆土,杂草丛生、无人平整,总有一天这堆土也会没入周遭。布尔塔茨的头上插着木制十字架,配着椭圆形的铁皮铭牌,上面写着:“这里躺着弗朗蒂谢克·布尔塔茨。愿你睡得香甜!”
贝克施坦因固执地拔掉了布尔塔茨十字架周围蔓生的杂草,用弄得黑乎乎的结实手指在十字架前刨出一个坑。他把嘴巴凑到坑前喊道:“嗨,弗郎茨,听见吗?你在里面吗?“
“给他喝点,这样他还会醒过来。”法贝尔建议道。
贝克施坦因往小坑里倒了点朗姆酒,然后自己喝了一大口。“敬你,弗郎茨!”
“弗朗茨,你这老伙计,回来吧!没有你这儿狗屎都不算!”法贝尔呼喊着,也往坟上倒着烈酒。
“倒这儿。”玛利尼亚克从他手上抽出瓶子,贪婪地把朗姆酒倒进自己嘴里。
布尔塔茨的伙伴们倒伏在坟头四周。酒瓶在一只只手里轮转,不时有人把酒让给布尔塔茨。微风将不连贯的话语和高呼带过墓地的院墙。
夜深,朗姆酒喝光了。玛利尼亚克消失在了别的什么地方,舒尔茨在墓园里缓缓走动,不时坐到坟墓旁,用低沉的声音唱起哀伤的歌谣。贝克施坦因和卡奈特睡了,拥着布尔塔茨的坟。
法贝尔坐在旁边坟墓的石头上,呆呆凝视着碎云遮蔽下的月亮。大概凌晨两点时,他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从墓园走回家里,点亮了厨房的灯,从代替食品储藏柜的古董衣橱里摸出一瓶没喝完的松子酒。他把酒瓶放到桌子上,规规矩矩地把酒倒进用来装芥末酱的小玻璃瓶,一口气喝干,然后又回到衣橱旁。这个衣橱是他从房屋曾经的德意志主人那里“继承”过来的。同样“继承”下来的还有一把7.65口径瓦尔特手枪,是在阁楼梁木后发现的,如今藏在腌黄瓜罐后面。枪维护得很好,擦得干干净净,上了机油。法贝尔抽出保险,把枪管放进自己嘴里,扣下了扳机。
旅途
他报了假名:有可能一切都因此而起。
他不是计划着要撒谎,甚至没有这么做的理由。但当那位仪表堂堂的先生在火车站问他,他是不是谁谁谁的时候(他确实就是,兴许是和那位先生在儿时或当兵期间打过交道),他回答道:“抱歉您认错了,我叫诺伊曼⑰。”然后就跑着去赶火车了⑱。
火车开出比尔森⑲时已过下午六点。
他选了个顺行驶方向的靠窗座位,然后把箱子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他的全部家当都带在了身边:外套、衬衫、内衣、鞋子、洗漱用品、一台小收音机、几本小书,加上最重要的词典以及证书:出生证、离婚证、高中毕业证、大学毕业证。
肩上背着的皮包里装着一点吃的,一升容量的水杯里盛着茶,还有翻过了不知道多少遍的书:恰佩克的《故事》⑳。
他的家当里缺了一些身为当代社会人的标志性物件。
没有手机,故意不要的。尽管周围环境逼得他工作时用计算机,但私人电子邮件他不用。他甚至连辆机动车都没有。也是故意不要的,跟节省没一点关系。他从来就不和那些过江之鲫们混在一起。避之不及。这是他的基本生活原则,出于直觉而遵守,而不是出于故意留心。
“您尽管晚上来好了,”人家在电话里这么告诉他。“说不定这样还更好点儿。安顿下来,然后第二天一早就上班去。其实您随便什么时候来都行,哪怕半夜也没问题。”
当时他还做了个鬼脸,因为这番话挺出乎他的意料。
也就是在乘车离开的这一天,他收拾好了自己的房间,那个曾经属于过他的房间,然后把钥匙交给了曾经的妻子,那位从未属于过他的妻子。
钥匙一交,退路烧掉:他的脑袋里冒出来这么一句。他时不时会爱上句格言,尤其是自己脑袋里冒出来的那种。
这份工作是在插页广告上找到的。
“洪水”农场招经济专家。未婚或离异者包住。工资高,环境美,自然爱好者之福。
他在地图上找到了淹没在密林之中的农场,距德国边境也就几公里。
对他来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反而更好。他还年轻,有时间经他折腾,向着新生活折腾。嗯……要是还能折腾到就好了。
列车每停一站,他都留心着站名。
他得在“下跑马地”下车,然后沿着蜿蜒的公路步行爬坡数公里,再拐上林间路(据说会有指示牌),最后才能到达农场:“洪水”农场。
和他一起下车的只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目测已退休,采购归来。薄暮初临。火车站的建筑让人忆起了第一共和国㉑。
车站值班室亮着灯。他敲了敲门。
是个女人,黑发,粗壮,三十来岁,屁股肥大,脸却漂亮得一塌糊涂。
“麻烦您了,去‘洪水’。能指个路吗,怎么走?”
她一言不发地盯住他看了几秒,然后从值班室出来,一言不发地指了路:一条栗树大道通往某个未知的地方。指完后她走回自己的房间,砰地一声带上了门。
“多谢!”他在她背后喊着。
一开始他感觉还不错,可一爬起坡来,就歇得越来越多。爬着爬着,天就暗了。
下跑马地的尾巴上还亮着灯,接下来他就不得不摸黑了。他盼着能碰上辆车,好请人家搭他一段,但连个车影儿也没有。一路上没车也没人,只能看到高大树木的轮廓和头顶上模糊的天空,斑斑点点透过些星光。
他再次停下脚步。走得越远,脚步越沉。他大声喘着气,在两只手间倒来倒去的行李磨得手掌像被火燎了一样生疼。
他在行李箱边站定,点上一根烟。
他思索着,心中生出些许不安,路到底对不对?之前走过的部分并没有看到岔路,除了前行别无可能。还剩下多远?五公里?
该带上手电的,他想。哼,手电,见鬼!不过据说“洪水”的指示牌是白色的,很明显,大概不会错过它吧。
他扔掉没抽完的烟,抓上行李箱,继续向前。终于看到了指示牌:一只巨大的白色箭头,上面写着“洪水”。顺着箭头所指的方向,他拐上公路右手边的砂石路,继续步行前进。
要是没记错地图的话,现在他只消再走上三公里,费不了什么周折就会到达农场。“洪水”农场。连农场主的名字他都不知道。
除此以外,就连在电话里跟他商量前往农场事宜的那位女士的名字,他也不记得了。还是说她压根就没告诉他?
歇过几次之后,路分了岔。
天已经黑到家了,他只能根据头顶上稍微亮点的带状天空来认路,而现在天空分了岔。
他从口袋里掏出地图,但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万分地确信,这条路上压根就不该有岔道。但现在怎么办?见鬼!向左?向右?他心底燃起无名怒火。该死的自己,该死的路,该死的混帐“洪水”!
直觉领着他再次选了右边。
走走,歇歇;再走,再歇。前方现出一点亮光,他加快了脚步,即便他已经累了,非常累了,麻木在逐渐取代怒火。
前方越来越亮,一片宽阔的平地,尽头紧挨着大片黑色森林,在那里他瞧见了灯。“洪水”!终于还是到了!
大楼底层流溢出昏暗的灯光。
这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农场?牲口圈在哪里?饭堂在哪里?拖拉机在哪里?
大门两边靠墙跟叠放着自行车。旧式的,结实笨重,大概有六辆。
一楼的左手半边亮着灯。窗户大都离地不高。他往屋里瞅了瞅。上帝啊,居然是酒馆!
黑色屋梁上吊着三盏大灯,目测是煤油的,下面摆着两张长桌,桌旁坐着些男人,他们抽着烟斗或烟卷,用样式古怪的深色酒罐喝酒。打酒的柜台大概是在屋角,在巨大的石头壁炉左边。
当下正从那儿走出个矮胖店主,给客人送上杯鲜啤。屋里传出低沉的谈话声,听不出在说些什么。
他用目光在门和窗户上方寻找着。招牌在哪?没找到。只有一点毋庸置疑,他是站在家小酒馆外面。说到底——招牌又有什么打紧?
他抓住门把,推开门走进了黑暗的走廊。
厕所的臭味扑面而来,大概来源于走廊尽头那边。他在酒馆门上摸索着钥匙。找到了。他打开门,走了进去。
“晚上好。”他打着招呼,然后把箱子放到地上,关上了门。
屋子里一股烟草和啤酒的味道,就是那种酒馆常有的味道,但又有点不同,跟他所习惯的酒馆味道不同。怎么不同,又说不出来。
他的到来让酒馆沉寂了下来。
这个乡下酒馆连装饰家具看起来也像是在战前。结实粗糙的深色木桌椅,煤油灯(要么是煤气灯?),墙上的窗户间挂着巨大的耶稣受难十字架,简单粗糙的打酒处,既没有闪光发亮的柜台,也没有啤酒商的广告。
就连屋里的人看起来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他数了数,一共七个男人,全都穿着深色衣服,完全算不上得体,其中三个连帽子都没摘。绝大部分抽着烟斗,有几支是那种皇帝时代㉒的长烟斗,还有几支短的。味道可有够冲的。
他在长凳上坐下,位置紧靠着门,与最近的临桌还隔着三米的样子。
男人们沉默地上下打量着他,无人回应他的招呼,连店主也没有。
“能上杯啤酒吗?”他问,“一杯酒,麻烦了。”他向店主打着手势。
压在平顶帽下的矮短粗农夫店主把酒罐放到龙头下,打满一杯酒,然后沉默着送到他面前,再走去另一张桌,跟坐在那边的人们嘀咕了些什么。一个字他也没听懂。词语尽管是嘀咕出来的,听起来却粗糙嘶哑。也许压根儿就不是捷克语:他冒出了这个念头。
店主仿佛拆去了由陌生人的到来而建起来的壁垒。连他这张桌子上的人也加入了低声的交谈——与其说是低声交谈,还不如说是嘶哑的耳语。
他喝了一口啤酒,又惊讶地拿开。这啥酒啊?
酒冰镇得很好,浓郁、劲儿足,比他时不时喝的比尔森12度㉓还要凶。就他的口味来说稍稍有点苦,但总体说来相当不错。他大口喝着,嘴巴很干,很快就喝下了半罐子,然后规规矩矩地拿手帕擦了擦嘴。
现在他已确认其余客人嘀咕的是德语。大概是德语。确切地说是某种古怪的德语,粗粝地窝在喉咙里,又像是用鼻音。在他听到的只言片语中,他一个词儿也没搞明白。
那些人鬼鬼祟祟的低语和他们看他的眼神叫他颇不舒服。
但这么说还不确切。他是发慌了。起因与其说是他那些奇怪的同桌,毋宁说是那种不明不白的气氛,那种他尽管努力尝试却又解释不清楚的气氛。
所有这一切,裹挟上他的疲倦和巨大的失望感,都成为他胸口那种强烈不适感的来源。
“Noch einmal.(再来一杯。)”㉔他放胆喊道。
酒馆再次沉寂了。
店主慢慢蹭了过来,拿走了空酒罐,也不冲干净,就重新往里灌了一杯鲜啤。
还没等店主拿过酒来,隔壁桌的一个男人起身坐到了他对面。
两人沉默着互相打量。
男人大概五十多岁。散发出一股烟草、森林、汗液和泥垢的味道。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乱七八糟、油腻不堪,鹰钩鼻,胡子拉碴。而目光却是小心的、探寻式的。少顷后男人开始难以置信般地揉头,似乎面前看到的不是个疲惫的年轻人,而是什么怪兽或者呆瓜。
“晚上好。”他低声说。
男人沉默着。
“晚上好,要么,guten Abend. (晚上好)。”
男人站起身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开始热烈地和自己的同桌们争论起什么来。
他的脑子里冒出了卡夫卡。他喜欢《城堡》,超过《审判》和别的作品。或许他现在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土地测量员”㉕?卡夫卡的那个测量员至少还能打打电话。对啊,打电话!
他向店主招了招手。
“您这儿有电话吗?电话!”
农夫店主摇了摇头。那堆男人中的谁大笑了起来。
他一下子就蔫了。
“吃点啥。吃的。Hunger.(饿)”他用手比划着送食物进嘴的动作。
店主转过身,消失在柜台后面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片刻后回来,在他面前放上一块显然因为上了年头而变了色、却擦拭得很干净的木砧板㉖。再加上一把刀,巨大的木头刀柄,窄窄的刀口已被磨得很粗了。
木砧板上摆着一块熏肉和两根硕大的酸黄瓜,还有两片切下来的面包。熏肉闻起来香极了,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手切,一手送,时不时浇上点啤酒。他不再关注剩下的客人了,虽然他们还继续盯着他看。他们全都仔细地瞧着这个陌生人:如何把吃的送进嘴,如何使用刀子,如何下咽。
吃的喝的一扫而光。
店主拿走了木砧板、刀子和酒罐,不言不语地又往里面灌了一杯啤酒。
他感觉还不错。酒足饭饱。高度啤酒弄钝了他的神经,由不确定和失望带来的紧张感慢慢平息。
突然之间,他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喏,也许可以在这里过夜,明天一早去农场。什么事儿也没有,很快他就可以开始工作,齐活儿。而他呢,还一直在为也许根本不存在的问题瞎担心。
他向店主招了招手,后者正和旁边那张桌子上的男人们窃窃私语着。
“Bitte, Herr Neumann?(诺伊曼先生,要什么吗?)”农夫店主问。
听岔了?诺伊曼?
“再一杯。”他把酒罐递了过去。
“Noch einmal?(再一杯?)”店主问道。
“Ja,(嗯)”他顺着说,“Noch einmal.(再一杯)”
男人们的咕哝像异族的蛛网般层层结在天花板下,还蒙着袅袅烟雾的纱。
他已经不再关心他们时不时斜着瞅过来的眼神。他回撤到自己的世界里,惬意地舒展手脚坐在长凳上,把所有的思绪都抛到远远的什么地方,抛到这个古怪的小酒馆之外。
四杯酒下肚,醉意略起。
他又朝店主招了招手。
“Schlafen...hier?(睡……这儿?)”㉗他极力组织着自己那点可怜的德语。话不够,手势凑。
“Ich... hier schlafen?(我……这儿睡?)”他指指自己,然后又往屋子里指了指。
“Nein. (不行。)”店主决然回答。客人们又沉默了,全神贯注地盯着看。
“结帐。”他困窘地说。“Ich...alles... bezahlen.(我……全部……付账)”
“Nein!(不行!)”店主提高了声音,摇着手坚决拒绝。其余的客人们则再次用审视的眼光看了过来。
他耸了耸肩,从皮背包里拿出钱夹:“付账。Bezahlen!(付账!)”
他抽出一张五百㉘。心中算计着这样损失大概有多少。超过两百?
他把纸钞递给店主。后者面带惊奇上下打量着钞票。
“Was ist das?(这是个啥?)”
他表示无法理解地摊了摊手,然后用捷克语补充道:“五百块。还是说太少了?”
店主走了一圈,把纸钞展示给两张桌子旁的人看。其中有些笑了起来,剩下的则仔细地打量着钞票。钱在众人手中轮转。
最后店主把钞票拿了回来,就像人们玩牌时那样,啪地一声拍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Scherze beiseite, mein lieber Freund.(别开玩笑,我亲爱的朋友。)”店主大声说,“Ich bekomme dreiundzwanzig Kronen, aber kein solches...dummes Falschgeld.(我收二十三克朗,但决不是这种……傻瓜假钞。)”
从桌子那头站起个宽肩膀的矮胖子,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两手撑在桌上,逼到他近前,一声不吭地盯住了他的眼睛。这人散发出一股烟草、森林、汗液和泥垢的味道。
店主话音刚落,矮胖子就把拳头往桌上一砸,喘着粗气说:“付账,诺伊曼,付账!马上!要不然……”然后就把奶牛心脏那么大的拳头晃给他看。
他的倦怠感瞬间消失。
他们这是干嘛呢?难道是个玩笑,新来的客人都要经历一遍?
但他们的脸色看起来可不像是在开玩笑。板着的脸上一片阴沉。他的心里害怕起来。
他小心地捡起被退回来的五百块,像要展示给所有人看一般地举了起来。

然后又打开钱夹,抽出一张两百,像要展示给所有人看一般地举了起来。
“Zweihundert Kronen.(两百克朗)”
接着又展示了绿色的一百。
“Einhundert Kronen.(一百克朗)”
群情激愤。酒客们开始嚷嚷,语气凶恶愤怒,嚷的什么却听不明白。
那个醉醺醺的人从他手里拽出纸钞——纸钞像树叶般飘落——然后动作麻利地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桌边拎了起来,腾出右手,一拳打在他肚子上。
他倒在木头地板上,倒在污垢、泥浆和松针的混合物上,痛得蜷起了身子,没法呼吸。
又一个客人从桌边站起,推开笨手笨脚的店主,把沉重的靴子踢向新来者的脊背、肚子。然后又一下,又一下,但他已经感觉不到了。
他昏了过去。
醒来时已是大白天。
他完全搞不清状况,既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当下何时。
他也不知是什么唤醒了自己,是寒冷还是浑身剧烈的疼痛。
他试着站起来,没成功。
背上和肚子的疼痛如此剧烈,以至于他重又倒回了潮湿寒冷的青草上。他侧躺着,吃力地解开了裤子。尿憋得紧,紧到他害怕会直接尿在裤子里。
尿完后他害怕了起来。尿里有血,这一点他确定无疑。
恐惧激活了他的感官。
酒馆。里面的客人们……他的随身物品、皮包、箱子都到哪去了?他张望了一下四周,什么行李也没有。随后他听见了拖拉机的声音,树木组成的屏障后,有谁在干活。
他花了很久才站起来。倚着树挪了几步,然后又不得不停下休息。
疼痛简直没法承受,但似乎步子挪得越多,痛觉就越为退让,逐渐削减。他就这样挪到了林子边缘,两个男人正在那里把锯下的木材装上拖拉机后的挂车。
他们停下工作,瞧着他。他能想像得出,自己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子。
“麻烦了……”他说,“麻烦两位,能送我去农场吗?”
那俩人对视了一眼。
“什么农场?”带着平顶帽、高高瘦瘦像根麻杆似的小伙子问道。
“喏……‘洪水’啊,还能是哪?”
又是那种眼神,仿佛在说:“当心,是个疯子!”
“您这是耍我们玩呢!”另一个人粗鲁地回答。他大约五十来岁,穿着黑乎乎的工装裤,挺着个大啤酒肚。
“您大概是在林子里什么地方把头撞到树上了,是吧?”那个瘦子说,从口袋里掏出盒“起点”㉙,点上了一支。
“你看哈,你这……游客,”瘦子接着说,“洪水遭了火灾,大概是在……二十……年前?”他转向自己的同事。
“二十二年前。”
这番疯狂的、不真实的、却让人痛苦万分的冒险,怎么就没个尽头啊!
“抱歉……那,那里现在是啥?怎么说那农场反正是存在的啊!”
那俩人又对视一眼。
“您以为还能有啥,尊敬的阁下?废墟一片,别无他物。”
冷场。他跌坐到地上,脊梁已经撑不住了。
“那那边的酒馆又怎么说?林子里的酒馆。林子里什么地方确实有个酒馆来着,不是吗?那边是有个酒馆吧?”
“您瞧,”高个子说。“我们还得工作,累得要死要活的,您的那些疯话我们可没时间听。”
他扔掉了没抽完的烟,掉过头继续干活去了。
“很久很久以前,”另一个说,“据说在‘洪水’那边曾经是有过个小酒馆,还是在战前。但那里现在已经毛都不剩了。您要是想喝杯啤酒,得到跑马地去。那个方向。”
他放弃了。
“抱歉……我是在林子里瞎逛来着,掉到个什么坑还是沟里来着。麻烦能载我到跑马地去吗?”
他在司机后面的小凳上摇晃着,浑身疼,对面是那个五十来岁的啤酒肚。
后者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目光让他想起那个小酒馆的酒客们,他们窥探的目光,还有那个奇怪的梦。虽然发生了,其中的一切却都不存在,除了他自己,还有身上的疼痛。
“您瞧,”啤酒肚在马达的轰鸣声中大声喊道。
“您瞧!您是不是凑巧是当地人?您不是出生在这儿的吗?”
他摇了摇头。
对方停了片刻,然后说:“我只是……我只是觉得,您很像某个诺伊曼。那时候……那时候在‘洪水’农场烧死了的诺伊曼。”
注释:
①德语发音、捷克语拼写的德语句子,含义见下。
②温尼托,德国作家卡尔·迈探险小说的主人公。
③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意志族人,拥有德意志血统、说德语,但非德国公民。二战前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聚居地为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奥地利和波兰接壤的边界地区。作为二战前奏的慕尼黑协定即是将德意志族占多数的苏台德区划归德国。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大部分德族被驱逐至奥地利和德国,60年代再次允许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族迁往德国,本文涉及的即是这一时期。
④德语GrüB Gott的捷克语拼写,意为“问候上帝”,是宗教信仰较为深厚的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常用问候语。
⑥德文:战争回忆。
⑦捷克著名歌手。
⑧阿帕奇族:数个文化上有关连的美国印地安人部族的总称。
⑨德语:吾之荣誉即忠诚,纳粹口号。
⑩捷克西部温泉城市。
⑪土制燃烧瓶的别称。
⑫弗朗塔是后文出现的捷克名字弗朗蒂谢克的爱称,弗郎茨则是弗朗蒂谢克的德语写法。本文中全指的是布尔塔茨。
⑬位于奥地利的纳粹集中营。
⑭斯图加特无论战前战后都是德国城市,而苏台德地区仅仅在1938-1945年期间属于德国,当地的德意志族居民自动获得第三帝国国籍。
⑮啤酒杯垫上的道道表示喝掉的啤酒杯数。
⑯奥托·莱茵纳是典型的德意志男性名字,而卡特日娜·科奈奇娜和约瑟夫·斯帖特卡则分别是斯拉夫的女性和男性名。下文中的维托斯拉夫·里布卡和马丁·采德勒分别是斯拉夫和德意志男性名。
⑰诺伊曼为姓氏,在捷克和德国等国家都有使用,在德语里的意思是“新人”。
⑱捷克的火车系统属于开放式:没有出入站检查,验票工作由检票员在车上完成,绝大部分火车车票与座位不绑定,因此乘客可以直接进入车站和站台,并随意选择空座位。
⑲捷克西部城市,距德国国境约两小时车程。
⑳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故事集:《一个口袋里的故事》和《第二个口袋里的故事》。
㉑指1918-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㉒1918年以前捷克仍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受奥地利皇帝统治。
㉓捷克比尔森市出产的啤酒。
㉔此处为德文,从此以下对话德文捷克文掺半,德文均保留原文,翻译在括号内标出。
㉕《城堡》与《审判》均是弗朗茨·卡夫卡的作品,《城堡》描述了自称被城堡聘请而来的土地测量员“K”试图进入城堡却永不得其门而入的故事。虽然使用德语写作并被划归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却出生并长居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目前在捷克的知名度也远胜于其他德语作家。
㉖将肉类放在木头平板上属于捷克传统上菜方式。
㉗这里的德语有语法错误。由于动词没有变格,此处及后面的句子都既可理解为主语为“我”(陈述式或疑问式),也可以理解为主语为“您”(命令式)。例如此处既可以是“(我)睡……这儿?”,也可以是“(请您)睡……这儿?”
㉘五百克朗的纸钞,约合人民币150元。
㉙起点,捷克斯洛伐克香烟品牌,60年代开始出产,2013年此商标已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