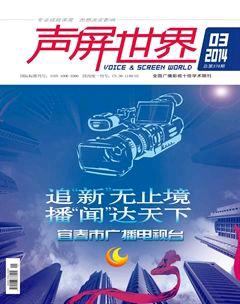制度意义上的价值转轨
——从《中国好声音》的制度创新谈起
2014-04-01商建辉赵利圆
□商建辉 赵利圆
制度意义上的价值转轨
——从《中国好声音》的制度创新谈起
□商建辉 赵利圆
制度影响变革,更影响未来。大至国运兴衰,小至组织变革,制度带来的影响都历久弥新。面对信息革命带来的比特级竞争,新的市场环境下,广播电视的制度创新与制度选择,对中国电视的未来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不仅有“好声音”,而且有好制度
对于业界探索已久的制播分离来说,2013年夏天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再次带来一笔好生意的同时,也为节目制作的模式创新与制度创新带来了一缕清新的变革之风。业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电视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制播分离。相较于以往制播分离中的一口价承包,即电视台以一次性费用承担购买相关公司的电视节目,《中国好声音》在制播分离上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承包制度——对赌式协议。
业界所谓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份“风险协议”,指的是灿星制作和浙江卫视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约定。灿星制作和浙江卫视之间有一个约定,即“收视率低于2,灿星制作赔偿播出损失,收视率高于2,二者分红”。 ①
在旧有制播分离中的节目购买模式上,一次性的费用交换意味着对于节目制作方来说,收入是固定的,如果要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只能朝控制自身成本的方向努力。灿星制作参与电视台广告分成的制播分离模式,避免了过去的恶性循环。为了赢取更多的利润,制作单位会竭尽全力制作出最好的节目来确保收视率。②“以前的利润是电视台给的,现在的利润是市场给的”,此项利益激励机制的形成让市场的调控能力发挥到最大,作为逐利并寻求市场空间的制作主体,自然会全力以赴。
“好声音”的好制度似乎只是个例
从好的向度上看,《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意味着制播分离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在制度创新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可谓是“好声音”的一小步,中国电视业界的一大步。但从反向上看,这也意味着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电视台把电视剧制作交由社会专门的制作公司开始,过往中国电视业的制播分离实践大多只是走在 “成功的路上”。换句话说,并不是每一次对于制播分离的探索都在赚的盆满钵满的同时赢得满堂喝彩,更多的时候,业界对于制播分离的尝试总以失败或草草收尾告终。
即便本次《中国好声音》的制度创新在制播分离上一定程度取得了成功,但并不标志着制播分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得到了本质性解决,毕竟《中国好声音》开创出的对赌协议只代表着对节目制作方有了更有效的激励,更好地保证了节目质量。对于节目制作方来说,可谓是风险与机遇并存——优者胜,劣者汰,由此形成的正向激励与竞争也将促成节目制作市场步入更为良性的发展轨道。
不过以上环节仅仅考虑了如何激励民营节目市场中的内容提供方,对于把控内容平台的渠道方,即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电视台在制播分离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制播分离的本质意义在于充分利用市场的竞争在激发活力的同时创造更为丰富的内容市场,为文化事业的市场化改革奠定相应的物质基础。《中国好声音》中“对赌协议”的创新仅仅是将压力加在市场化的节目制作商身上,活跃的是与此对应的节目市场,对于体制内关于节目制作的原有方面无法触及。“好声音”模式创新所起到的作用,至多只是通过体制外活力迸发的节目市场带动体制内的部分改革。因此,“好声音”带来的好制度只是对特定领域的特定节目具有借鉴意义,无法对制播分离下的场域形成普遍性影响。
制度保障的缺失是制播分离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是什么造成了制播分离雷声大、雨点小的实践困境,又是什么让业界的探索止步不前?笔者认为,制度保障的缺失在制播分离来回逡巡而不得前进的过程中起着主要的阻碍作用。
首先,制度缺失滞延人事改革。对于“企业化经营,事业化管理”的传媒业界而言,体制内人员收入与生活相对平稳,福利保障也更为完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故而集聚了大部分精英人才。在制播分离的具体实践中,业界管理层试图从体制内剥离出部分人员参与体制外公司化运营,但对未来模糊不清的政策导向与安全感的缺失以及“铁饭碗”的打破都让这一设想阻力重重,即便对于探索较为成功的“上海模式”仍不可照搬照用。按照我国“四级办电视”的原则,各台之间人员、资金、管理情况差异很大,与底气十足的东方卫视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对于改革中关联到的体制内人群,建立相应完善的制度保障机制势在必行。
其次,制度缺失影响公平竞争。在制播分离的具体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此类问题。节目制作若在体制内或与体制有牵连,则是“小姐命”,若在市场外,则是“丫环命”。对于体制内已然形成的固化阶层来说,很难不利用手中原有的影响力对播出平台施加影响,进而波及最后的决策。有地方台人员认为,在市场交易中,节目制作机构和播出机构的不对等也是矛盾所在,尤其是民营电视机构在与国营公司之间进行竞争中存在双方收益不平等、风险不共担、权益不对等的问题。③如何建立在第三方评审基础上的节目选择机制,最大可能规避主观选择与主观影响,使体制外节目能够和体制内节目公平竞争,制度的探索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制度缺失易致媒介垄断。《中国好声音》节目的成功并非偶然,对于节目质量的要求,可以用严苛来形容。幕后总指挥田明解释,一组组数字证实着节目制作的不易:8000万的制作成本,2000万的音响设备、80万一把的导师转椅;提前4个月,6个导演组到全国各地寻找2000个好声音;游说那英和刘欢三四个月,往返京沪十余次;邀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响总工程师金少刚担任音响总监,零点乐队王笑冬领衔的一线大明星巡演乐队,在一个2000平方米的录影棚里,打造出可供3万人享受的音乐效果;现场有26个机位,每期96分钟节目的素材达1000分钟……④如此巨额的投入显然不是实力一般的体制外中小公司所能承担的,这对体制外民营节目制作公司形成了隐形资金壁垒。高门槛带来的不是自由市场中多元意见、多彩节目形态的共存,而是在马太效应的促使下形成新的寡头垄断。在寡头垄断的背后,实质上涉及到的将是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政商背景财团。如何完善相应的制度机制,如何在保证自由竞争与维持多元意见市场中求得平衡,制度的设计完善不可或缺。
解铃还须系铃人:转轨由制度始
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念是: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效率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⑤制度产生的全局性影响无论在传媒产业与外部环境的宏观层面,还是在广电产业体制规划中的中观层面,抑或在业界具体操作实践上的微观层面都影响深远。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电视台把电视剧制作交由社会专门的制作公司开始,中国电视的制播分离至今已走过了20多年历程。90年代曾迅速发展,特别是国办发【1999】82号文件提出的 “网台分营”的要求,标志着以国家为主导的中国电视制播分离改革大幕的正式开启,但改革进展缓慢,未见显著成效。2003年12月30日,国家广电总局颁布 《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再次提出 “制播分离”和“电视产业化”的概念,直至2009年8月,广电总局66号文印发了《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为制播分离提供了政策指引,“制播分离”由此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再度成为热门话题。此后,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制播分离的讲话和政策,带动了国内广播电视制播分离的快速发展。
由此,制播分离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政策先行,是拉动和确保制播分离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引擎与保障。⑥如今,改革已进入深化期,各种关键性的矛盾和问题也更加突出。这一时期,战略性的制度考量比具体的战术性实践更为重要,制播分离的效益首先应在制度改革中产生。对于当前制播分离中出现的探索困境来说,转轨需从制度始。
结语:在实践中进行制度创新
没有人会嘲笑呀呀学语的幼童,成长就是如此,需要在不断地尝试中探寻成功的路径,而点点滴滴的有益进步都是为质的飞越做好量的积累。无论怎样,《中国好声音》都开创了一个历史,它的尝试注定在制播分离摸索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特有脚印,对于顶层设计抑或管理层既定的目标来说,这个脚印的内涵依然意义不凡。在制度设计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基层创新与高屋建瓴架构出的理论模型同样重要。毕竟,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四川省荣县宣传杂志社)
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释:
①李 翔:《一份“风险协议”带来的电视节目制播的启示》,《当代电视》,2013(4)。
②蒋秀丽:《中国好声音红遍中国的秘密》,《中国联合商报》,2012年11月26日。
③商亚南,苑志强:《城市台制播体制的改革的困局和突破》,《南方电视学刊》,2011(2)。
④蔡芳芳:《总指挥田明揭秘〈好声音〉走红:仅制作成本就8000万》,《现代快报》,2012年9月12日。
⑤盛 洪:《现代制度经济学 (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9页。
⑥张 雷:《制播分离的体制性障碍及其突破路径》,人民网传媒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