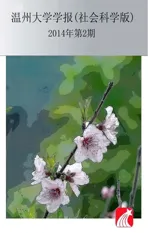礼乐文化当代意义下的反思与重构
2014-03-19陈其射
陈 思, 陈其射
(温州大学音乐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礼乐文化当代意义下的反思与重构
陈 思, 陈其射
(温州大学音乐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礼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对中国的民族意识和审美心理都具有深刻影响。它至始至终包含了巫术礼乐、治国礼乐、儒家礼乐三个文化层面。当代礼乐的重构从巫术礼乐中汲取的是对信仰的坚贞,从治国礼乐中汲取的是对爱国精神的崇尚,从儒家礼乐中汲取的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当代社会若能脚踏实地地将这三者内化于我们的思想和实践中去,复兴和传承礼乐精神将会大有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将会与日俱增。
礼乐文化;巫术礼乐;治国礼乐;儒家礼乐
“礼乐之邦”的礼乐文化,法天地序人伦,治社会度情感,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其本质特征是追求文明。礼乐之礼是音乐化的行为规范,礼乐之乐是礼制化的音乐情感和伦理美感。乐之礼,是精致的政治、善化的行为、审美的情怀;礼之乐,是规范的艺术、伦理的宗教、神话的道德。礼是以人本身的一套程式化动作(或表演)为符号载体,而乐是以有声符号“音乐”来表达象征性内容。中国古代社会“无礼不乐”、“无乐不礼”,非礼之乐和无乐之礼从来没有得到古之哲贤的认可。中国礼乐文化本于先秦,其发生发展经历了不断深化的三个历史阶段,即原始至商代的巫术礼乐阶段;西周的治国礼乐阶段和春秋战国的儒家礼乐阶段。这三个阶段也代表礼乐文化内蕴的三个文化层面,即精神层面、政治层面和伦理层面。精神层面开启了后世礼乐精神的基本路向;政治层面突出了国家意识和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伦理层面构建了后世汉民族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三个阶段显现的三个层面各有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巫术礼乐顶礼膜拜的是人格化的神灵,礼乐宗旨是礼序神鬼,巫和觋“歌舞事神”表达的是人与神鬼的关系;治国礼乐是周人强化血亲和宗法等级秩序,以达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政治目的,是礼序人伦的礼乐,是人之间的关系学;儒家礼乐是礼乐内在精神的光大,是理性化的思辨,它把社会伦理的“仁”实践到人的意识之中,“从而把原来是外在强制性的规范,改变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1]。礼乐文化三个层面的内容在当代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它的孑遗现象,在当代意义下对此如何反思与重构,是学界同仁们需要认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巫术礼乐、治国礼乐、儒家礼乐在当代遗存现象的反思,以期从古代礼乐文化浩大的宇宙精神、谨严的伦理要求、崇高的审美意趣中汲取教训、传承精神,为当下的时代灌注生气、提升人心。
一、巫术礼乐当代意义下的反思与重构
礼乐文化的源头是巫术礼乐,巫术礼乐起源于祀神,故礼字从示、从豐[2]。它含有皇天上帝崇拜、太阳太阴崇拜、生命生殖崇拜、祖宗鬼神崇拜的意义,初始便奠定了礼乐的社会功能特点,其后扩展为对人的崇拜,再后扩展为吉、凶、军、宾、嘉五种仪制。事神仪式礼与事神歌舞乐的结合,就是“礼乐”的初义。在巫乐中,乐曲对应神灵,乐律对应天象,乐器对应方位,化妆反映内容,祭仪的用乐规范依靠音乐的器用和形式,使音乐充满着象征、暗示、超越和征服的意味。虽然巫术礼乐的疯癫痴狂和超凡脱俗早已远去,但其精神内涵和表现样态却一直延续至今。在今许多地方,伴随着神人对话、天地交流、驱瘟避邪、蜡祭求雨和祈福求子等活动,巫术礼乐之生命依然强劲,其实质就是人们对天、神和图腾的盲目信仰和崇拜,无理智地将自然界或人世间各种变化莫测的因果关系归结于超自然力的神,将自然物和自然力人格化,将领袖神灵化,用咒语、祷词、舞蹈和音乐等手段进行膜拜。当这种膜拜仪式按定时、定格方式反复举行后,就会成为一种制度和习俗。这种制度和习俗常常不因历史和社会变迁而消亡,却以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于后世,成为一种民俗或民族的标志,有些因素还以遗传基因的形式存活在民族民间音乐和舞蹈之中。
巫术礼乐当代的孑遗形形色色,有些是带象征意义的巫术礼乐,有些则是直接意义的巫术礼乐。对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举出值得反思的例证:象征意义的巫术礼乐,如我国“文化大革命”中的造神运动[3]所表现的“礼”之行为和“乐”之形态;直接意义的巫术礼乐,如当下屡禁不止的大操大办的信神和丧祭活动中的畸形礼乐现象。前者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宗教仪式化”[4],领袖之语一句等于一万句,将领袖变成了神,图腾标志是红太阳。后者是当下信神和丧祭活动中显现的古代巫术礼乐的孑遗现象。除了边僻农村仍有神人对话、祈福求子、驱病避灾等巫术礼乐外,即使在比较发达的城市也出现了巫术礼乐的孑遗。尤其是原始积累丰厚、暴发户较多的地区,人们不惜重金雇用巫师与神对话,与之匹配的背景音乐却是当下的流行音乐。许多阔老为敬神烧新年第一柱香而一掷千金、彻夜不眠。做道场、法事等人神交通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宗教音乐在这里不但起到了仪式的标识和营造气氛的作用,也通过音乐表达出象征性的宗教内容和情感。
在当代意义下对这两种不同层次、不同意义的巫术礼乐进行反思,教训惨痛,发人深省。文革造神运动中象征意义的巫术礼乐是个人崇拜、文化专制、践踏民主的结果,致使音乐等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除直接的造神歌曲和语录歌外,“样板戏”音乐、器乐作品以及其他体裁音乐都烙上了象征红太阳的固化音乐符号的时代印记。当下的信神和丧祭活动,则与当代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科学社会、和谐社会极度不协和。
巫术礼乐是礼乐文化的神话时代,“其深层结构,已含蕴华夏文化之精神方向”[5]。当代社会的礼乐重构,在巫术礼乐层面上决不是对“盲目信仰”的重构,而是积极地吐故纳新,扬弃迷信,反对复古、崇古、遵古,从巫术礼乐深层蕴积中汲取有益于当今社会发展的和谐因素、情感因素和心理因素,从巫术礼乐的精髓中升华出新的人文精神,重构出与时代吻合的新的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音乐。在当代意义上透析这种深层结构的精神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坚贞信仰的刻骨铭心,对信仰义无反顾的坚执。当下,人浮于事,不少人早已将共产主义信仰抛至脑后,不少人的人生追求方向是五子(票子、房子、车子、妻子、孩子)登科,有些老共产党员也随波逐流,甚至腐败堕落。在当下信仰危机的情势下,坚定信仰,从心底信服和尊重共产主义,用科学人生观规范行为,从“自我”中升华,融入更广大、更深邃、更丰富充盈的“大我”之中;充分发展个人理想,并使其不断闪烁民族之光、生命之光和动力之光,这是重构新礼乐的急切和迫切的要旨。与信仰危机行为相辅相成的是糜糜之乐,它是以情爱和性爱为主题的新淫声。重构就必须打破以缠绵为主体的音乐格局,改变整体音乐成份,增大与坚定信仰相匹配的音乐比重。使追求美好人生,崇尚自律、自爱和自强等高尚人格的内容成为音乐的主体,将强弱反差大的脉冲式律动、重音同位的强有力节奏、积极向上的动性旋法等音乐表现形态作为音乐审美的主体,使音乐能够与时代脉搏同步,能够振奋人心、高昂意志、催人向上。
二、治国礼乐当代意义下的反思与重构
西周摆脱了神权的桎梏,用理性精神对待礼乐传统,是神权让位于政治、神坛走向世俗的历史进步。“周人贵亲而尚齿”①参见: 戴圣: 小戴礼记[M]. 郑玄, 注.,用血亲关系来维护宗周统治,与这种政治措施相应的是各种礼仪和音乐的等级规定。各种礼仪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用不同雅乐曲标识宗法的等级秩序,使礼乐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治国方略,成为礼序人际关系的手段。治国礼乐扩大了礼乐的社会功能,使礼仪充斥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除五礼之外,礼乐又细化为“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九种礼事,这些礼仪多有相应的音乐配合,根据不同的等级有相应的用乐规定,使人的社会行为、思想感情乃至政治关系完全消融在礼和乐的文化氛围之中。“礼”已被视为人的道德、伦理、修养;“乐”已被视为人的情感、思想、欲念,将这些无形的道德、伦理、修养、情感、思想和欲念外化为有形的礼乐形式,使无形有形化、抽象具象化、意识形态化。这种有形的礼乐亲和、约束和控制人们的道德、伦理、修养、情感、思想和欲念,等级秩序、宗法伦理、社会政治、君臣父子等完全被束缚在礼乐之中。同时,礼和乐被固定化、模式化,这既不符合人的本性,也不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到头来只能走向“礼崩乐坏”。
虽然西周治国礼乐的等级秩序、宗法伦理、社会政治约束和控制人的思想和欲念的内在功能早已烟消云散,但其外在形式仍可在当代礼乐中寻觅到它的孑遗。笔者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例证说明之:一是当下的官方礼乐,它早已形成一套程式化的礼仪行为和与之相应的符号性的音乐;二是当下的民间礼乐,它是早已根深蒂固地以血缘、师生、战友、亲朋、同学和同事等因素结成了人际关系的礼乐。前者追求的方向与西周礼乐是一脉相承的,试图将礼乐纳入意识形态上的治国方略之内。后者更与西周礼乐的表现形态同型同构,它将西周“礼序人际”的治国方略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斥于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人为地将社会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形诸于礼仪,表现为当下“关系社会”中形成的各种礼乐形式。西周之后,中国社会数千年一直处于礼序人际的文化氛围之中,这种礼序人际的礼乐早已凝冻成一种“关系社会”“人治社会”的意识形态,人人都在这种“关系网”的制约之下。其外在形式表现在婚、丧、嫁、娶、谢师、庆生、贺寿、开张、节庆等方方面面。当下这些礼仪场合,“礼”要求所有“关系人”必须到场,否则就是失礼。礼仪用乐虽因地而异,但除少数民族外,用乐已有约定俗成的趋同和固化的现象存在。
在当代意义下反思这两种不同层次的治国礼乐,感慨颇多。
一是在官方礼乐上所形成的程式化礼仪行为和与之相应的符号性音乐早已与西周治国礼乐表同实异了。西装革履的礼服早已标识了“礼”外在形式,西洋的铜管音乐早已固化了礼乐的用乐形式。中国人找不到具有民族标识的服饰,全球化趋势的典礼用乐更不允许采用不同音色的民族乐器,官方礼乐从外在形式的礼服到内在精神的音乐早已远离了民族传统。相比之下,我们周边的印度、巴基斯坦、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等国家不但有体现民族身份和文化传统的礼服,也有不少不用铜管而用民族乐队的仪式场合。韩国甚至在国家重大的典礼(“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开幕式)演奏国歌时,堂而皇之地用上了纯民族乐队[6],乐队中的伽倻琴、筚篥、奚琴、大笛交响映衬,别具一格。反思当代中国典礼用乐,在许多人眼里,用民乐是不可想象的,是丢人、丢面子的事。这是由于 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音乐观念和行为早已全盘西化。在西化的急风暴雨下,人们接受了“欧洲文化中心论”,一时间崇拜西洋成了时尚,导致了民族乐器的大规模改造,许多民乐器除失去了原本最值得骄傲的音色特质外,也失去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二是在民间礼乐上,延续了西周礼序人际的治国礼乐,突出地将人际关系网放到了首位,这是否就是长期以来我国推行法治社会的国策步履艰辛的原因呢?笔者认为:当下民间礼乐与起源于西周,发展于其后数千年的人际关系网形成的“人治社会”关系密切。当代人一仍旧惯,早已习惯了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纳入“礼”的系统(人际关系网)之中,不自觉地延续了中国古代礼序人际的宗法文化,人们无法摆脱人际关系的制约,许多不正之风均与此关联。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早已视人际关系为第一要素。对通过“关系”而获得晋升、提职、评优和获奖等早已习以为常、习非成是。在当下“以法治国”的口号下,对许多问题的处理虽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但在执法过程中往往遇到了西方人难以想象的阻力。阻力的来源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人际关系网,许多人深信这种“礼”的外化形式早已凝冻成中国人的人性,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然而,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却一刻也离不开法治。为改变中国人人性的丑陋面、我们必须加强以法治国,必须群策群力,提升全民守法的自觉性;必须循序渐进地治心易俗、善化教育,从情感和心理两个层面接受法治,使关系网形成的人治现象逐步萎缩,代之而起的是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
今天我们重构治国礼乐,乃复兴其精神,非拘泥其形式,是追怀其功能而非摹仿其仪礼,可借鉴其学理而非神话其意义。自古以来,治国礼乐的精神要旨就是以国家为核心。当下治国礼乐的重构就是要重塑中国人的“人格精神”,就是要将“国家精神”放到首屈一指的地位,自觉地提升民族身份的认同意识,自觉地维护作为中国人本身的尊严和价值意识。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美治国,人人都能为建构和谐人格、和谐社会而竭尽全力。因而,提升国家意识、发扬爱国思想就是当下“礼乐”的最大之“礼”,以此为核心构建的音乐等艺术就是当下“礼乐”的最好之“乐”。即以爱国主义作为一切“礼”的行为规范标准,以爱国主义作为各色“乐”的精神核心。众所周知,好的音乐不但可以荡涤乐之邪秽、饱满乐之意志,也可以动荡乐之血脉、流通乐之精神。在当今“郑声”横行、人心浮躁、工具理性独擅而人文精神萎靡的时代,治国礼乐的重构和复兴更显重要,我们更应该重构治国礼乐,以修养国家、民族、时代之德,纠救人文气质之偏。
三、儒家礼乐当代意义下的反思与重构
西周礼乐制度不过是文化领域内的一次社会实践,真正将这种制度理论化,使之成为一种思想体系而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儒家礼乐。儒家礼乐从礼乐的内在精神入手,从伦理学、哲学和实践三个维度对礼乐作了思辨性解释,这种解释给礼乐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即将“礼”和“乐”的精神归结为“仁”,从而使“礼乐制度合情化、合理化,使礼乐在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的支持下获得了普遍的社会意义”[7],使礼乐成为构建崇高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的教育手段,这也使礼乐生长出一套完备的音乐伦理学说。《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8]。儒家礼乐同时认为,遵循天地(自然)之序,尊重天地(自然)之和是最大的礼乐,从而使礼乐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节剂。
在当代人类学的视野下,所谓“礼”乃是社会的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行为;所谓“乐”,是配合这种行为的另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行为。若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礼”可泛指人的行为规范,“乐”可泛指人的精神修养。当下这两方面值得反思的地方实在太多。总体观之,中国人的善恶、是非观念与从前比较淡漠了许多。中国人性丑陋的恶性膨胀较少有内省约束力的控制,因而可以频频见到抢、盗、奸、杀、拐、黄、赌、毒和骗等罪恶的报导,也可频频见到为富不仁、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贪赃枉法和忘恩负义等贪婪邪恶的丑陋人性的曝光。而人的善性萎靡较少有道德内省力的激发,因而频频听到当下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上的勾心斗角、口是心非、面和心不和等人事内耗的情况出现。当然,见义勇为、仗义疏财、救死扶伤、鞠躬尽瘁的人也大有人在,但袖手旁观、冷目视之者众多,甚至有人视义勇者为傻人。孔子将礼乐精神归结为“仁”,后世儒家又将其发展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八德”成为中国人的处世之道,也是礼乐之邦的美德,然而近百年来“八德”几乎丧失殆尽。反思这些珍贵遗产的丢失,我们发现其主要原因与近百年来两次革命运动关系密切:一是1919年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次革命运动使中国传统礼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摧残,中国人由此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了,找不到做人的准绳了,丢失了的确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礼乐精神。其严重程度正如管子所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9]。除此之外,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教训也是刻骨铭心的。当儒家礼乐被粉碎得无影无踪之时,“改造自然”,“战天斗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破坏生态的跃进口号便顺理成章了。改造自然的结果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带来的却是接二连三、无穷无尽的惩罚。上述种种现状使不少人直面遍体鳞伤的儒家礼乐而悲天悯人,但灰心地认为当代礼乐的重构前途渺茫。
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10]无疑,这一成为世界共识的宣言给主张重构新礼乐的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成就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将会不断地从孔子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创造文明、发展未来。我们更应将孔子“仁”所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尽快地实践到每个人的行动中去,用儒家礼乐之“礼”规范人的行为,提升社会秩序和正义,引导人们向善,将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追求彼此相爱的社会和谐;用儒家礼乐之“乐”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协调世间万物,使人们各安其位、相互提携、和谐相处;用音乐陶冶心性、增长修养、提升人格、使人生快乐安宁,生命长久。除此之外,当代礼乐的重构还应像孔子那样强化“乐教”功能,突出“乐”在礼乐中的功能意义。西方国家对孔子乐教早已心领神会,如美国就用《教育法》的形式将音乐等艺术列入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11]。我们应该像美国那样用“国家标准”的形式将音乐教育普及到全社会,实行全民音乐教育,使音乐等艺术成为终身教育的主干课程,使人人都能用同样水准的音乐符号交流思想和情感,以达到“以乐教和,大音陶情”[12]、熏染品行、荡涤邪秽、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之目的。当代礼乐的重构还要加强以德治国的力度。正如《礼记》所云:“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①参见: 戴圣: 小戴礼记[M]. 郑玄, 注.儒家礼乐将“民悦”放到社会和谐的首位。这是儒家礼乐“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的核心价值观。当下社会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尊重,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但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当代礼乐的重构还需大力倡导自我修养,自身顺和了,社会岂能不和?当代礼乐的重构必须将儒家礼乐“和为贵”的核心价值从过去的贬斥声讨中解放出来,重构“和为贵”的评价体系。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作为化解社会冲突,化解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矛盾的原则,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使人心有所归属和安顿,实现心灵和谐。当代礼乐的重构必须复兴儒家礼乐的“孝”、“善”的传统美德,造就孝亲睦邻、敬业乐群、尊师敬长和礼贤下士的行为规范。当代礼乐的重构还要使“卑己尊人”的儒家之礼成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夫礼者,自卑而尊人”,“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当代礼乐的重构还需要按照“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的儒家礼乐原则,遵循天地之序,尊重天地之和,使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成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
综上所述,礼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它至始至终包含了巫术礼乐、治国礼乐、儒家礼乐三个文化层面,当代礼乐的重构从巫术礼乐中汲取的是对信仰的坚贞,从治国礼乐中汲取的是对爱国精神的崇尚,从儒家礼乐中汲取的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当代社会若能脚踏实地地将这三者内化于我们的思想和实践到我们的行为中去,从历史中汲取可资借鉴的经验的教训,复兴和传承礼乐精神就不会是梦,这样,国家和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必将与日俱增,中国礼乐文化的思想魅力和精神活力必将会永存后世,也会放射全球,成为世界文化的核心价值。
[1]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50.
[2]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9: 32.
[3] 梁茂春. 中国当代音乐[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3: 19.
[4] 梁茂春. 中国当代音乐[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3: 17.
[5] 罗艺峰. 礼乐精神发凡并及礼乐的现代重建问题[J].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97, (2): 3-7.
[6] 张振涛. 国歌音色[J]. 北京: 人民音乐, 2010, (10): 82-83
[7] 薛艺兵. 论礼乐文化[J]. 北京: 文艺研究, 1997, (2): 53-64.
[8] 吉联抗. 乐记·乐论篇译注[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2: 11.
[9] 梁启超:管子·牧民[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 17.
[10] 李锁华. 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N]. 北京: 人民日报, 1995-6-30(4).
[11] 刘沛. 世纪末美国音乐教育动态术评[J]. 北京: 中国音乐: 增刊, 1990: 18-20.
[12] 陈其射. 音乐教育新机智[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36.
The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CHEN Si, CHEN Qishe
(School of Music,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Being the cor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aesthetic psychology. It encompasses the three cultural levels of the ritual and music of witchcraft, ruling ritual and music, and Confucian ritual and music.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ritual and music draws the firmness of faith form the ritual and music of witchcraft, the advocating of patriotic spirit from ruling ritual and music, and the pursuit of social ideals from Confucian ritual and music. If contemporary society can make the three internalized in our mind and practice really, renaissance and imparting of the ritual and music spirit will be helpful enough, and our country’s inner national cohesion will be grow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Ritual and Music of Witchcraft; Ruling Ritual and Music; Confucian Ritual and Music
J60-152
A
1674-3555(2014)02-0094-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2.015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3-05-30
陈思(1975- ),女,安徽阜阳,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