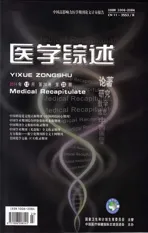冠状动脉植入支架术后发生支架内再狭窄的影响因素探究
2014-03-06张婧娴综述刘同库审校
张婧娴(综述),刘同库(审校)
(吉林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 吉林 132011)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发病率逐年上升。自1977年Gruentzig开展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plasty,PTCA)以来,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发展迅速,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己成为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主要方法,显著地改善了患者的远期预后。但支架内再狭窄(in-stent restenosis,ISR)的发生成为目前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降低ISR的发生率就成为支架植入术后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了解支架内再狭窄的临床影响因素有助于判断支架植入的适应证以及降低支架内再狭窄的概率。近年来,众多学者已分别从以下方面针对ISR的临床影响因素做了不同研究,研究人员主要关注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年龄、吸烟、体质量、高血压、糖尿病、总胆固醇、心肌桥、支架因素、患者或疾病本身因素、术前血管狭窄程度、血管狭窄部位及类型、术前影响因素等。
1 糖代谢异常因素
目前,国内糖尿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糖尿病作为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其糖代谢异常与冠心病发病的关系也日益受到重视。
1.1糖尿病 需应用胰岛素才能将血糖水平控制达满意程度的糖尿病患者,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再狭窄率会显著增加。而Scheen等[1]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发生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危险率约是其他因素的2倍。但上述是针对植入支架的所有长度及支架直径进行的综合研究结果。将冠状动脉直径<2.75 mm的血管称为小血管,当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小血管发生病变时,应用药物洗脱支架(drug-eluting stents,DES)的再狭窄率会显著低于金属裸支架[2]。当冠状动脉直径>4.0 mm时,糖尿病患者应用药物洗脱支架相对于应用金属裸支架(bare metal stents,BMS),其再狭窄率均有所降低,但仍高于非糖尿病患者;而非糖尿病患者应用两种支架的再狭窄率近似。因此,非糖尿病患者应用BMS可以节约治疗费用,是值得推广的。
1.2胰岛素抵抗 国内外众多研究已证实,在糖耐量受损及空腹血糖受损阶段大血管病变就已启动。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当空腹血糖>6.1 mmol/L时称为空腹血糖受损状态。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胰岛素抵抗与ISR显著相关[3]。糖尿病患者发生ISR可能是由于胰岛素抵抗所致内皮功能受损,诱导血小板聚集并激活生长因子,加速平滑肌细胞和炎性细胞的增殖,促进细胞外基质形成,从而使冠状动脉内膜增生活跃。在目前100多种抗高血糖药物中,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可以明显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瘦素水平,从而改善胰岛素抵抗和内皮功能,进一步降低ISR的发生率。但因其价格较高,国内应用较少。吡格列酮是噻唑烷二酮类胰岛素增敏剂,它可以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及迁移。由于部分非糖尿病患者也存在胰岛素抵抗,因此有研究显示它不仅可以降低糖尿病患者的ISR发生率,也可以降低非糖尿病但存在胰岛素抵抗患者的ISR发生率[4]。
1.3术后用药 冠状动脉介入术后,抗血小板聚集是预防支架内血栓发生的关键。有研究发现,部分患者存在阿司匹林抵抗和(或)氯吡格雷抵抗,而发生支架内急性或亚急性血栓。而西洛他唑与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组成的三联抗血小板治疗可以显著降低支架内血栓的发生率及主要不良心脏事件的发生率[5-6]。针对有关糖尿病相关临床因素与支架内再狭窄的文献进行阅读后发现,糖尿病是导致ISR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当PCI术后出现糖代谢异常即要对血糖行早期干预,而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则要严格控制血糖。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降低糖代谢异常患者PCI术后发生ISR的概率。
2 血脂异常及他汀类药物因素
血脂代谢异常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密切相关,血浆中脂类的总称即为血脂,主要包括三酰甘油、磷脂、胆固醇及其酯,以及非酯化脂肪酸等,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C(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C,LDL-C)的升高已成为动脉粥样硬化和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生、发展的必备条件。众多研究表明,凡是可以使血浆LDL-C的水平降低,即可以降低冠心病的发病率及病死率。而他汀类药物是目前发现最有效的降低LDL-C的药物[7]。不仅如此,在冠心病的Ⅰ级预防和Ⅱ级预防中,他汀类药物的有效性已经得到公认。有报道称,他汀类药物还可以降低PCI术后ISR的发生率[8]。Sun等[9]认为,阿托伐他汀不仅具备降脂功能,而且还有利于支架处的再内皮化。与阿托伐他汀相比,瑞舒伐他汀在长期使用后仅降低了术后心绞痛的发生率,而对于预防ISR的发生与阿托伐他汀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国外有报道指出,强化降脂要将高危患者LDL-C降至<2.0 mmol/L,极高危患者LDL-C<1.8 mmol/L或LDL-C水平降低50%。只有大幅度降低LDL-C的水平,才能显著减少心血管事件,而慢性炎性反应也会随即减轻或消失[10]。血脂指标中的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C(non-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C,non-HDLC)反映了含有载脂蛋白B的脂蛋白数量,包括LDL及脂蛋白A,所有这些成分都促进了胆固醇在动脉壁内的蓄积[11]。徐凯等[12]对行PCI术3~6个月后复查冠状动脉造影的94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ISR患者non-HDLC水平的变化值与ISR程度显著相关,而随访时血清non-HDLC水平升高是再狭窄的预测因素。因此,PCI术后持续服用他汀类药物可能会减少再狭窄的发生,这一作用可能与血清non-HDLC的降低有关。针对血脂相关因素,血脂中载脂蛋白B与ISR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而他汀类药物通过降脂降低了ISR的发生率。
3 年龄、性别、体质量、吸烟因素
国内有一组针对住院的150例老年冠心病行PCI的患者进行年龄因素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老年患者中年龄不是再狭窄的相关因素[13]。这与王强等[14]对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所做的回顾性研究的结论近似,指出年龄、性别、吸烟、体质量非ISR的预测因素,但同时指出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也非ISR的预测因素,这与众多研究结论不相符,可能与其所研究的病例数较少有关。高血压、糖尿病等冠心病危险因素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支架内再狭窄主要是因为内膜、平滑肌增殖,两者机制并非完全相同。
4 心电图、心脏彩超及其相关因素
有关患者入院时的心电图表现,如ST-T的改变与支架内再狭窄的相关性报道甚少,并且择期手术的患者心脏彩超的相关数据与支架内再狭窄关系的相关研究也较少。而对于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学者们研究更多的是使用何种支架能使患者在长期应用中收获“低投入高回报”的疗效。
5 支架因素
众多学者对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应用不同类型的支架获得的疗效进行回顾性总结。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治疗的关键是尽早、尽快再灌注、开通梗死相关血管、挽救濒死心肌,改善预后。冠状动脉支架已由最初的BMS逐步发展为DES,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无论何种支架,都可以改善心肌供血,保护心功能。在临床上,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的应用较为广泛,其主要作用机制为:雷帕霉素进入细胞后和FK506结合蛋白12受体蛋白结合形成复合物,从而抑制蛋白激酶TOP(TOP是细胞循环过程中的重要调节物)的活性,阻止细胞周期G1/S期的转换,从而抑制细胞增殖[15]。国内外研究已证实,药物洗脱支架再狭窄率显著低于金属裸支架[16-17],近年来,国内研发了数种不同类型的药物洗脱支架,临床证明部分支架效果较好,且国产药物洗脱支架的价格较低,这也成为国产药物洗脱支架的优势。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使用国产支架会有更好的性价比。因此,支架的植入数量逐年递增。已有的临床试验都证实,双支架后再狭窄率高于单支架[18],而双支架或多支架再狭窄多发生于无支架覆盖区[19]。
6 病变血管因素
6.1心肌桥 通过冠状动脉造影可见,前降支中远段出现心肌桥的概率较大[20]。在有心肌桥存在的情况下,当心脏收缩时冠状动脉严重扭曲,可致内膜损伤、内皮细胞受损,在此情况下促进了血小板聚集、血栓形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当有支架植入时,可能会加速上述过程的发生,形成恶性循环[21]。吕树铮等[22]、苏永才等[23]通过对不同地区合并有心肌桥的患者行支架介入治疗后再狭窄的发生进行回顾性分析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合并有心肌桥的患者再狭窄发生率显著高于无心肌桥的患者。
6.2病变部位、病变类型 有关病变部位及病变类型与再狭窄的相关性报道较少,而苏永才等[23]通过研究后指出,不同病变部位及病变类型与再狭窄无明显特殊性,最终通过分析数据后提出心肌桥是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的独立预测因素。而韦艳[24]的一项研究指出,前降支是ISR的主要部位。两者结果不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统计。
6.3病变血管直径 Sahara等[25]研究指出,通过血管内超声检出的软斑块是ISR的独立预测因素,但血管内超声检测手段在国内的使用率较低。也有学者指出,当病变血管直径<2.8 mm时其冠脉支架内再狭窄率明显升高[24]。
7 血流动力学
有学者提出,频繁的ISR发生不仅和支架与血管的变形、支架与血管的顺应性失配有关,也和支架后局部血流动力学变化引起的内膜增生有关。由于目前还没有一种理想的支架其顺应性可以与正常血管相比,因此当前运用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建立支架后冠状动脉的个体化模型,是研究冠状动脉分叉处血流动力学形象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现有分析分叉冠状动脉再狭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26]。
8 不稳定型心绞痛及抑郁症因素
目前人们更多致力于探究影响ISR的术后因素,而忽略了术前因素。从疾病预防的角度出发,术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在行PCI的患者中,除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以外,多数为不稳定型心绞痛的患者。有研究表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与炎性因子C反应蛋白密切相关,而Bankier等[27]提出,随着C反应蛋白水平的升高,冠心病伴抑郁症的发病率也逐渐增加。因此,有学者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后指出,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发生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机制可能是由炎性因子及抑郁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8]。
9 结语和展望
目前多数研究具有局限性,对于ISR的预测因子的研究更需要多中心、随机、双盲的前瞻性研究以证实各可能预测因子的预测价值。引起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临床因素众多,行PCI的绝大多数患者都同时合并多个可能导致ISR发生的因素。只有对ISR的影响因素进行认识,采用多因素共同干预的手段降低ISR的发生率,才能提高支架术后远期疗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因此,全面认识ISR的影响因素任重而道远,有待继续研究。
[1] Scheen AJ,Warzée F,Legrand VM.Drug-eluting stents:meta-analysis in diabetic patients[J].Eur Heart J,2004,25(23):2167-2168.
[2] 苗军,崔连群.药物洗脱支架对糖尿病小血管再狭窄的影响[J].山东医药,2006,46(31):44-45.
[3] 魏广和,刘立新,王铁成,等. 吡格列酮降低非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药物洗脱支架再狭窄的研究[J].临床心血管病杂志,2012,28(6):445-448.
[4] Nishio K,Sakurai M,Kusuyama T,etal.A randomized comparison of pioglitazone to inhibit restenosis after coronary stenting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J].Diabetes Care,2006,29(1):101-106.
[5] Douglas JS Jr,Holmes DR Jr,Kereiakes DJ,etal.Coronary stent restenosis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cilostazol[J].Circulation,2005,112(18):2826-2832.
[6] Lee SW,Park SW,Kim YH,etal.Comparison of triple versus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after drug-eluting stent implantation (from the DECLARE-Long trial) [J].Am J Cardiol,2007,100(7):1103-1108.
[7] 马文学,江志羔,古玉燕,等.瑞舒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脂、超敏C-反应蛋白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再狭窄的影响[J].中国当代医药,2012,19(19):30-33.
[8] Mulder HJ,Bal ET,Jukema JW,etal.Pravastatin reduces restenosis two years after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plasty(REGRESS trial) [J].Am J Cardiol,2000,86(7):742-746.
[9] Sun ZS,Zhou SH,Guan X.Impact of blood circulation on reendothelialization, restenosis and atrovastatin′s restenosis prevention effects[J].Int J Cardiol,2008,128(2):261-268.
[10] Robinson JG.Models for describing relations among the various statin drugs, low-de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owering, pleiotropic effects, and cardiovascular risk [J].Am J Cardiol,2008,101(7):1009-1015.
[11] 王惠珍,刘德文 .血清非高密度脂蛋白脂固醇在冠心病合并高脂蛋白血症中的诊断意义[J].中国动脉硬化杂志,2000,8(1):67-69.
[12] 徐凯,韩雅玲,荆全民,等.他汀类药物减少冠心病患者支架术后再狭窄的影响因素及意义[J].中国动脉硬化杂志,2005,13(5):607-609.
[13] 佟翠艳,刘剑立,刘雪虹.老年冠心病冠脉支架再狭窄相关因素调查[J].解放军保健医学杂志,2007,9(4):215-217.
[14] 王强,陈建昌,李晖,等.冠脉支架术后患者支架内再狭窄原因的回顾性研究[J].中国血液流变学杂志,2012,22(2):241-243.
[15] Marx SO,Marks AR.Bench to bedside: the development of rapamyci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tent restenosis[J].Circulation,2001,104(8):852-855.
[16] Abbott JD,Voss MR,Nakamura M,etal.Unrestricted use of drug-eluting stents compared with bare-metal stents in routine clinical practice: fi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Dynamic Registry[J].J Am Coll Cardiol,2007,50(21):2029-2036.
[17] 胡承恒,杜志民,罗初凡,等.CypherTM支架治疗冠心病的疗效观察[J].中国动脉硬化杂志,2006,14(3):230-232.
[18] Murasato Y,Hikichi Y,Horiuchi M.Examination of stent deformation and gap formation after complex stenting of left main coronary artery bifurcations using microfocus computed tomography[J].J Interv Cardiol,2009,22(2):135-144.
[19] 刘修健,蔺嫦燕.冠脉分叉病变及支架后再狭窄的血流动力学研究进展[J].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2012,31(3):446-450.
[20] Ge J,Erbel R,Rupprecht HJ,etal.Comparison of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and angiography in the assessment of myocardial bridging[J].Circulation,1994,89(4):1725-1732.
[21] 王宁夫,潘浩,童国新.心肌桥和心肌桥近端合并严重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介入治疗疗效观察[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5,33(8):684-686.
[22] 吕树铮,陈韵岱,陈欣,等.真实临床条件下CypherTM支架的应用效果评价[J]. 中华介入心脏病学杂志,2005,13(2):67-70.
[23] 苏永才,张小乐,吴剑胜,等.心肌桥对冠脉支架内再狭窄的影响[J]. 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2007,5(11):813-815.
[24] 韦艳.冠脉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现代医药杂志,2011,13(11):91-92.
[25] Sahara M,Kirigaya H,Oikawa Y,etal.Soft plaque detected on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is the strongest predictor of in-stent restenosis: an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study[J].Eur Heart J,2004,25(22):2026-2033.
[26] Taylor CA,Steinman DA.Image-based modeling of blood flow and vessel wall dynamics: applications, metho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Sixth International Bio-Fluid Mechanics Symposium and Workshop, March 28-30,2008 Pasadena, California[J].Ann Biomed Eng,2010,38(3):1188-1203.
[27] Bankier B,Barajas J,Martinez-Rumayor A,etal.Association betwee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C-reactive protein levels in stabl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J].J Psychosom Res,2009,66(3):189-194.
[28] Armstrong EJ,Morrow DA,Sabatine MS.Inflammatory biomarkers 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partⅡ: acute-phase reactants and biomarkers of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J].Circulation,2006,113(7):15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