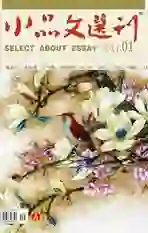蝉
2014-01-16厚圃
厚圃
蝉为什么叫知了?有人说是因为与它的发音相近,其实听听又不大像,或许是某地的方言吧。近日才又听到另一种说法,蝉的发音同“禅”,禅在佛教里是指静思,故戏称它为“知了”。
夏天到了,树上的蝉逐渐多起来,叫声日益密集,此起彼伏,给人一种比实际温度还要躁热的感觉。天刚放亮,就有蝉在叫,叫一阵歇一阵,待你微微合上双眼以为可以睡个回笼觉,它又更加欢畅地叫开来,真让人生气。不过蝉的叫声虽令人厌烦,我却对它另眼相看,须知它曾是我童年的玩伴。那时候的乡间,树木比现在的城市要多得多,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绿,如果有大片大片的红,那一定是凤凰花。听到蝉的叫声,我们就到修自行车的小摊去,要一块从报废的内胎上剪下的橡胶皮,或者从穿烂了的“人字拖”上取下那根用橡胶做成的带子,点上火,看着它烧化了嘀嘀嗒嗒地滴成一滩,再掺上蜘蛛网(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蛛网的作用至今我仍没弄明白),拿瓷片将它刮起来敷药似地敷在竹竿尖上,拿去粘蝉。粘到的蝉被剪去部分翅膀,这样它就飞不掉,但是它自己并不清楚,依然急促地拍打着翅膀转着圈圈,那样子既好笑又可怜。在那些炎热的日子,每个小孩子手里都有一只蝉,只需轻轻捏一捏,它就会放声歌唱。伙伴们围在一起,说一二三,都捏一捏,瞬间便能听到蝉的大合唱。几乎落入孩子手里的蝉都活不到第二天,死了的就丢给鸡吃,或者弃于某个角落,才眨眼功夫,就被蚂蚁团团裹住最终掏成像蝉蜕那样空空的壳子。也有的蝉是被大人弄死的,掏掉肠肚,泡一遍盐水,再塞进去几粒黄豆和一小块猪油,搁在火钳上伸到到灶坑里去烤,给孩子解馋,虽夹带着一丝糊味,但吃起来还是酥酥脆脆的,香喷喷的,颇受孩子们的喜爱。广东人没有什么不敢吃的,这话颇有几分道理,到北方念大学时我就碰到一个什么都敢吃的老乡,夏天一到,他便拿着电筒,招呼我们几个同学满校园找蝉。他熟知蝉的一切习性,知道它们的幼虫只有天黑才会出现。对于那些刚从蝉蜕里挣脱出来、绿盈盈的幼虫,我是不大敢动手的,我害怕抓大青虫时那种软绵绵的凉丝丝的感觉。那个老乡却像个种地的好把式,眼睛发亮,摘豆荚似的捉到一只,便利索丢进塑料袋里,嘴里不停地发出兴奋的哇哇声,我想他大概也是知道蝉是个“极聋的聋子”吧,否则不担心把它吓跑啊?往往是这么出去转一圈,就能凑成满满一盘,那些幼虫蠕动着,挨挨挤挤,又是茫茫然的,仿佛呱呱落地的婴儿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一切像在老家,老乡也给它们洗了个“盐水澡”,过了道沸腾的油便迅速捞起,一时香气四溢。我却不敢吃,看着都有些害怕,想象着那些肥软的躯体被牙齿一压,噗地喷出一股凉凉的东西,就好像吃生蚝那样,我就不由得打起寒战。他们却一个个吃得嘴角冒油,好享受的样子。
小时候我曾读过《昆虫记》,法布尔谈到过蝉的生活,“四年黑暗的苦工,一月日光中的享乐,”他觉得大家不该嫌恶它的“歌声中的烦吵浮夸”,“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忽然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与飞鸟可以匹敌的翅膀,在温暖的日光中沐浴着。那种钹的声音能高到足以歌颂它的快乐,如此难得,而又如此短暂。”其实在中国的古代,蝉是很被看重的,它甚至成了复活和永生的象征。从周朝后期到汉代所留下的古墓里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们爱把一只玉蝉放入死者的嘴里,以求得庇护和永生。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也认为蝉以露水为生,将它视作纯洁的象征。不少画家喜欢画蝉,其中尤以白石老人画得最好。据说张大千也曾画蝉赠送友人,友人拿去请白石老人题词,白石老人展开一看,摇首叹曰此画谬矣,蝉附于柳枝,其头焉有朝下之理。因为柳枝柔软飘动,蝉头朝下就会重心不稳。其时张大千声名远盛于白石,得知后很不服气,后经仔细观察发现确实如此,对白石老人的生活根基和观察力叹服不已。有人以为,画蝉之难在于蝉翼,在于画出它的轻薄透光,我却以为蝉最难画的其实是它的神韵,蝉的眼睛漆黑一团,蝉的姿态也多是一动不动,画得不好就成了死蝉。也有不少的诗人吟咏过蝉,骆宾王在狱中借蝉喻己:“无人信高洁。”李商隐也在《蝉》中抒发情怀:“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但我更喜唐虞世南的《蝉》:“垂緌(穗)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蝉是害虫早已成为定论,可还是有那么多的拥趸。它若能知道,会作何感想?
(今晚报2013年8月25日副刊头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