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昆明的茶馆风情
2014-01-02何松
何松
(作者系 中国作协会员 云南《天下茶仓》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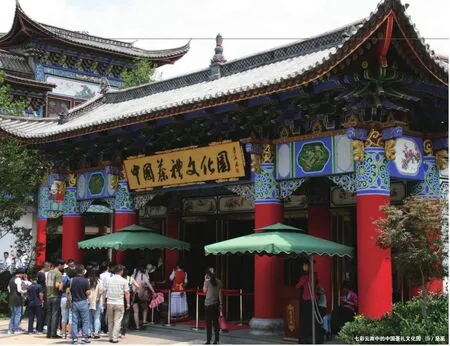
中国的文字里有一种尤如文人大写意画的传统,上下五千年,云里雾里,几句概括下来,“微言大意”——用微小的材料作一番大道理,记述是为了作,过去的说法是“立主脑”,现今大学中文系的写作教材里更是发展到了极致,确立主题,组织材料,“作而不述”。他们全忘了“看法会过时,事实是永远存在”的真理。
一部文学史几乎是由这类天马行空的“作而不述”的大写意文字构成,他们强调的是有“思想”。但这之中也有那些坚实地贴着大地的形而下的写作。他们是“现象即本质”、“存在即本质”的忠实实践者,他们是“述而不作”。我以为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文艺理论,他们的文字具有着诚实的品质,所写都是“如是我闻,如是我见”,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枚的《梦梁录》,洪迈的《夷坚志》,余怀的《板桥杂记》……他们所提供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化信息量,远要大于与他们同一时期产生的那些进入了文学史的名篇。
云南罗养儒先生的《云南掌故》正是这种让人尊敬的“述而不作”的写作。他里面记述了很多清末、民国年间昆明日常生活的琐事。这之中,自然是少不得茶的。昆明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城市,这种悠缓的节奏最宜与茶相伴。
昆明人喜欢泡茶馆,罗养儒写到“昆明人喜往茶社内消遣时日,凡是铺户内之掌柜,窗下读书之士子及一般无事业做之闲散人,都喜于两餐后结伴入茶馆坐谈。本来花钱不多,茶水又便宜,既足以畅叙情怀,又足以听各行人口传播之新闻。一碗茶由浓而喝到淡,由淡而变成白水,只一味的斜坐凳上,由日中而坐至日西,经数小时之久,卖茶人仍是笑脸相承”。旧时的茶馆,它的功能不仅是喝茶,它还是信息中心、娱乐中心、鸟会、书场、戏院……这些,昆明的茶馆也是一样的。罗养儒先生写光绪年间的昆明茶馆,有说评书的,有念小说的茶馆,更有打围鼓的乱弹茶铺——也就是滇剧清唱的茶馆。还有雀茶铺:“逐日俱有十数个卖雀人坐在茶铺内,各携有二三个大笼及三五小笼,俱关着若干雀子在内待售。”还有芦茶铺,芦茶铺除了卖茶,还卖槟榔、芦子。
“惟是在云南边地上,今尚有几种夷族人,仍是离不开槟榔、芦子,一样的和着熟石灰来嚼。”其实,芦茶铺就是除了喝茶还可嚼槟榔的茶馆,这种茶馆外面好像没听说过。
罗养儒先生笔下的老昆明茶馆是很有特点的。罗养儒先生记述道:昆明的茶铺,最早要数昆明县衙门隔壁的那一家,无字号,开设的年代不详……来喝茶的,多是来打官司的人,他们坐在茶馆里等待传讯,衙门里差役出来,就对着茶铺高呼“传某某人”。这家茶馆很有意思,开在衙门门口,专为打官司的人准备茶水。
“四合园营业时间最长,早晨七八时开铺,晚上十一二时打烊,带讲评书。”这是一家说书的茶馆。“晚上打烊后,还有一姓金一姓姚的文人至四合园喝茶,已成习惯,铺家还特地为他们煨一壶水在炉上,直到天亮,伙计起来拨火备水迎早市才离开,因此人称“金半夜”、“姚天亮”,其真实姓名反失传了。”这家茶馆是人性化管理,关门了也不把客人赶走,这姓金和姓姚的老哥俩也够可以的,不回家睡觉,能一夜一夜地呆在茶馆里,他们对茶馆是有感情了,把茶馆当成家了。郁达夫先生就写过,苏州的一家老茶馆里,就有一老哥,天天到茶馆去泡,五十年就坐一个位子。昆明茶馆里的怪人在汪曾祺先生的笔下也有一个:一个姓陆的联大学生居然把洗漱用具都放到了茶馆,每天早晨便跑到茶馆里洗脸漱口,一整天都泡在茶馆里,到很晚才夹着一本厚厚的书回到宿舍。
昆明的茶馆最与众不同的是烧水的壶。罗养儒先生写到,有一家茶铺,极为简陋,火炉上支一把无比之大的铜茶壶,内能容水四五大桶,壶把粗若孩童臂,把以铁链套住,扣在一比较粗实之屋柱上。旁为砖砌蓄水塘,塘近于墙,墙上则绘一乌龙吐水。而另一家烧水的铜壶也是重达三四十斤,高近四尺,能容水两担,壶柄以铁链双系而套于梁柱上,取开水只去其壶嘴上木塞,水自喷射而出。这种大器,大约也只有边地民族才玩得出来。罗养儒先生说:“此偌大水壶实为他省所无,即昆明地方事物上之一种特色。”
昆明也是产茶的,现已属昆明的宜良宝洪寺山上就有宝洪茶,十里铺有十里香茶。宝洪茶在明代以来就是云南的名茶,而十里香茶也是昆明稀罕之物,在乾隆年间作为贡茶,进过皇宫。吴井水泡十里香茶,正如虎跑泉之于龙井、惠泉之于碧螺春,在当时的昆明,是一种生活的品味。昆明产茶,但奇怪的是在中国茶区划分里,昆明那边和澜沧江中下游的临沧、普洱、西双版纳这边并不属于一个茶区,昆明是西南茶区,而临沧、版纳这边是属华南茶区。
罗养儒先生忠实地记述了很多老昆明的茶事,他的文字现在读着依然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汪曾祺也写过昆明的老茶馆。

1983年,我到昆明读书的时候,当年汪曾祺笔下所写到的学校附近的格局大都没变。出校门过凤翥街、书林街、青云街、西仓坡,然后到翠湖。汪曾祺先生写到:“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书林街都不长。两条街上至少有10多家茶馆,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经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翥街。街夹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汪老的文字让人感到亲切。四十年后,大至的方位都还没变,只是“小牌楼式的街门”和茶馆没有了。我们读书的时候,茶馆这种休闲、娱乐的带有旧时代特征的事物已被30多年的革命给洗涮干净了。翠湖附近重新出现茶馆是新世纪普洱浪潮到来以后的事了。我们读书那阵,没茶馆可泡,最侈奢的事是晚上在凤翥街、书林街、环城西路的烧豆腐摊边喝喝啤酒。
汪曾祺先生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1946年离开昆明,在昆明上了四年的大学,泡了八年的茶馆。翠湖、观音寺、白马庙、青莲街、强民巷、钱局街、正义路,都留下过他老人家和那个动荡年代流亡学生们的足迹。汪曾祺先生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昆明茶馆很有意思。有一家绍兴人开的茶馆,主人乡音未改,独在异乡,把联大学生当成了亲人,穷学生们不仅可以喝茶赊账,还可以和老板借钱去看电影。一家很时髦的茶馆,墙上挂着美国电影明星照,除了卖茶还卖咖啡、可可,周末便关了门举行舞会。一家仅有三张桌子的茶馆,除了卖茶,檐下还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出售。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聊天、看书、写文章、做作业。汪曾祺先生最初的几篇小说就是在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我觉得汪曾祺这位茶馆里泡出来的作家,文字里也带着一种隽永的茶味。
汪曾祺先生说:“茶馆出人才”。我相信这是真的,泡茶馆可以广泛地接触社会,且不同学科的人,泡在一起是可以改变一下知识结构和促进彼此间思想交流的。西南联大出了那么多优秀的诗人、作家,应该和泡茶馆是有关系的,茶馆就是一个社会,而作家是社会这所更大的学校所培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