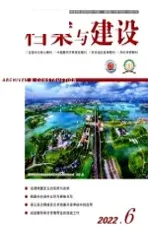开展量化研究获得档案学规律性认识
2013-08-15霍振礼张瑞梅袁向阳乔永芝西北核技术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24
霍振礼 张瑞梅 袁向阳 李 艳 乔永芝(西北核技术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24)
1 引言
我国档案学的量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后期,取得阶段性成果。在这20年间,沈阳市档案局、国家档案局三司等单位部门和杨少田、李晨生、方水清等同志都开展了有价值的研究。量化研究是档案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利用量化研究方法可以获得一些档案学规律性认识。
2 量化研究是获得档案学规律性认识的重要手段
1993年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发表的《科技档案现行作用衰减规律的研究及其应用》一文,使用数学方法研究了科技档案的利用价值[1]。数据来源为该所科技档案工作中积累的数万条利用数据,内容包括借用时间、单位、姓名、档案编号、密级、名称、页数、借用时间、批准人、借用人签字、还回时间和签收人等,数据完整准确。借用登记表按年份装订成册,共32册,时间连贯、系统性强。研究发现,科技档案衰减规律与文献衰减规律基本相同,但也稍有差异:科技档案衰减曲线的尾部较长而平滑,反映出科技档案具有历史价值的特点[2]。科技档案衰减规律说明,档案学应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不能完全照搬图书馆学的有关定律。
衰减规律是档案学中一个基本而实际的问题。科技档案现行价值衰减规律能够从理论上说明科技档案形成后25年间,现行价值从100%衰减至1.3%,显示其历史价值的过程。中间过程为:档案形成当年的现行价值为100%,1年后为 83.9%,2年后为70.5%,3年后为 59.2%,4年后为49.7%,10年后为 17.4%,15年后为7.2%,20年后为3%,25年后为1.3%。因此,科技档案形成后21-25年间为最佳上交档案馆时间,上交时间过早会影响形成单位的利用,过晚会影响更广泛的社会性利用。这符合我国科技档案实际上交时间,也为确定最佳上交时间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衰减规律还可以看出,科技档案提供利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科技档案如果在归档后不能被使用,只是存放在档案室,它的现行价值将不断快速消失,造成科研成果的浪费。这就要求档案管理人员必须重视档案利用工作,并应特别注意在归档后的早期档案利用[3]。
科技档案现行作用衰减规律,还可以定量说明科技文件的生命周期。即:形成当年至形成后5年期间的成果应用阶段,是现行作用发挥最充分的黄金时期,应用方式主要是投资回报和转让等;形成后的6-25年间为半现行阶段,既有现行作用,也有历史作用;25年后为历史应用阶段,基本上只具备历史作用。少量科技专业档案,如地质、水文、气象、天文档案等的历史参考价值历来被看重,其历史作用是无限期的。而一般的技术档案,特别是设备、器材、基建等档案,随着技术的发展、时间的推移、设备设施的淘汰,除少量具有文物、历史价值外,多数都要经鉴定后被销毁。科技档案在形成之前,还存在一个形成阶段,即投资阶段,一般项目是3至5年,有些大项目可能达十几年或更长时间。国内外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都很重视,阶段划分也有所不同,但研究中很少能说明阶段划分的具体时间周期,也没有相应的数据支持。笔者对衰减规律的定量研究,可以作为划分科技文件生命周期的重要参考依据。
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兴起之时,也是档案工作和档案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到90年代中期,档案界量化研究达到高潮。当时,档案界公布了很多相关数据,如全国从事档案事业人员数量,全国档案局、馆数量、经费,馆藏量、利用量,甚至档案馆的建筑面积等。这些数据既有档案工作的宏观数据,也有一线档案工作的有关具体数据。就笔者而言,不但可以使用本单位的数据,而且能参考国内的有关数据,给工作带来很大便利。笔者把32年间积累的5万多条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多方面的分析研究。研究的范围包括:档案利用成本、档案利用的产出投入比、档案社会功能与效益、档案利用指标等。伴随这一工作,笔者还收集到国内外不少有关统计数据,借鉴科学研究方法,开始尝试撰写专著,终于在1998年出版专著《科技档案效益学概论》。书中出现的科技档案现行作用衰减规律的数学公式和曲线,是与科研人员合作的产物,但档案人员起了主导作用。该书出版后,从各种评论和反应来看,在内容和量化研究方法上,应该说取得了成功。该书曾获中国档案学会第四次档案学优秀成果档案学著作一等奖,也被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有关博士生导师指定为博士生阅读书目之一。
3 开展量化研究的决定因素
“科技档案现行作用衰减规律”已经发表20年,但在CNKI检索中发现,除笔者自引外,尚未看到有关解读或评论,也未看到使用档案相关数据进行证实或者发表不同意见的论文。总之,似乎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衰减规律”来源于几十年积累的大量档案利用数据,研究成果又能解释档案学中不少实际而重要的问题,证明它是有科学根据和价值的。未能引起关注的原因可能有三方面:一是基层档案部门,很少能够积累几十年完善、准确、系统化的利用数据,没有数据,就无法进行统计分析;二是量化研究工作量大、耗时多,建立统计模型、抽取样本也需要专业知识,统计分析比撰写一般论文难得多,因此很少有人涉足;三是权威专家对量化研究的意义、价值及其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没有足够的重视。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不外乎两个因素,即条件因素和意识因素。量化研究的开展和深化,有时条件因素起决定作用,有时意识因素起决定作用。
3.1 条件因素
量化研究必须要有全面、准确、完整、规范的统计数据作为基础。在有些情况下,条件因素是决定性的。过去在档案管理学书籍中都有“统计”一章,现在不多见了。实际上“统计”在档案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没有统计工作,档案管理的开展就缺乏数据支持,既没有对以往工作的总结,也难以形成准确的指导性意见,代之而起的就是主观经验。主观经验受人为因素的干扰太多,往往因人而异,使人无所适从。例如,档案馆没有馆藏量、利用量、利用率、动用率、拒绝率、利用人次、进馆量、销毁量以及工作人员量、投入资金等数据,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档案工作的效益和价值,只能被动收集和服务,自然就没有明确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就整体而言,国家或档案综合管理机构每年都应有完善、全面的统计公报,公报的内容应该包括高校档案专业情况、人才培养状况,全国档案机构数量,专职人员数量,兼职人员数量,人员的学历、专业、职称,馆藏总量,资金投入等等。有了这些数据,档案工作者才能了解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才能从大局出发了解工作的意义。公报既是向社会宣传的需要,公布的档案工作成果数据,又是档案界量化研究的下锅之米。
3.2 意识因素
档案学量化研究,在条件因素满足的情况下,意识因素就起决定作用。
量化研究的意识因素之一是态度。必须重视量化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档案工作人员,还有主管领导和权威专家都要足够重视,才能掀起量化研究的高潮。既要有一般性的课题研究,又要有基金支持的高级别的课题研究。有了这种气氛,才会形成良性循环,形成广泛的接力、合力研究。这样,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通过量化研究总结出一些档案学的有关规律,用这些规律来解释、规范目前所遵循的经验性的工作方法、要求、规定、规范、法律。只有具备实践基础和实践数据,才能使这些方法、要求、规定、规范、法律更有说服力,更能体现档案学是科学的、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经验的。
量化研究的意识因素之二是合作。复杂的量化研究必须通过合作的方式才能完成。量化研究不仅需要精通档案学,还要懂得数学、经济学、统计学、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需要多人合作。量化研究从科技档案管理入手比较方便,科技档案主要产生经济效益,也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研究的原始数据比较明确,如某个研究项目的档案工作投资、档案工作的产出效益量等,都有具体数据,宜于量化。社会效益虽难以量化,但通过间接的方法,也是可以量化的。普通档案主要产生社会效益,也产生经济效益,但目前只能用“很高、较高、有限”等模糊语言进行定性方式的表达,难以量化,这是档案研究人员需要攻克的难关。
量化研究的意识因素之三是持久。档案学定量研究,是要花大力气的,也是一场持久战,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见效的。显然,数据积累的时间越长,积累的数据量越大,统计分析才越能体现出规律性,研究得出的成果也必然对档案学的发展具有更深远和广泛的意义。
4 开展深层次量化研究
概括地说,档案学量化研究,就是用数据说话。量化研究有两个层次。一是简单而广泛的统计层次,主要是对原始统计数据的累加、比较或简单运算。例如对馆藏量、利用率、动用率、拒绝率、转让率、引用率、对外交流率、产出投入比等的统计和研究。二是深层次,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进行数据归纳推理,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科技档案现行作用衰减规律数学曲线就属于后者,这项研究使档案学由统计定量研究发展到用数学公式表达的规律性研究。
笔者在1999年发表《三十二年中五万条科研试验档案利用数据的综合统计和分析》[4]。该文内容之一即是对西北核技术研究所上万卷科研试验档案利用频次进行统计分析,最后把统计结果绘制为曲线,发现与拉维昌德拉·劳的《图书情报学定量方法》一书第35页的文献利用频次分布规律基本相似,笔者确信这也是科技档案利用的一条规律。虽然从文献的量化规律看,这不是笔者的原创,但在档案学的量化研究方面,具有原创意义,毕竟档案学不相同于一般图书情报学。该文的统计分析还揭示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实际数据实例和图表,例如:从院士利用档案情况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科学研究领军人物对科技档案的需求状况和需求量。更重要的是,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一些档案利用的规律性认识,例如:科技档案原件利用呈内部性,说明档案主要供内部人员使用,用于连续性研究;主体任务档案利用率最高,说明需要首先保证中心任务的利用;科研人员利用档案呈现不平衡性,同一时期不同专业的科技人员利用量相差7倍以上;科研人员档案利用属深层次需要,每利用一次成果性档案平均借用时间一个月左右,这与普通档案的利用大有不同,等等。笔者还利用该所研究报告的引文,统计分析出该所档案对连续性研究工作的引用率为19.1%。值得说明的是,中外文文献资料引用是参考性引用,而档案引用属科技成果利用,不但具有连续研究价值,还具有直接应用价值,其效益远大于文献资料引用。这些都是依靠数据得出的结论,显然比经验性结论更有说服力。
5 结语
最近笔者拜读了河北大学档案学专业刘红莎的硕士毕业论文《企业档案信息利用效益研究》。论文共5章,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观点明确、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使笔者受益匪浅。当前档案界的人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博士、硕士研究生比例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广,研究能力强,如果能利用量化研究方法,开展深层次分析研究,相信一定能发现档案学研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而推动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量化研究在现代档案学研究中,既是一个薄弱环节,又具备很大的发展空间。笔者在此呼吁档案工作主管领导、权威专家以及广大档案人员,重视开展量化研究以获得档案学规律性认识。笔者相信,量化研究在档案界一定会是大有人在和大有所为的。
[1]中国档案学会科学技术档案学术委员会(荷文执笔).科学技术档案管理学发展综述[J].档案学研究,1994(3):18-21.
[2]霍振礼,上官萍,王青丽.科技档案现行作用衰减规律的研究及其应用[J].档案学研究,1993(3):16-21.
[3]霍振礼,徐定权,刘铁林,尹建.科技档案效益学概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9:136-139.
[4]霍振礼,袁向阳,杜继荣等.三十二年中五万条科研试验档案利用数据的综合统计分析[J].档案学研究,1999(1):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