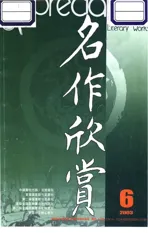论《诗学》的建构方式与意义——对《诗学》的一种细读
2013-08-15范萍萍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杭州310062
⊙范萍萍[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杭州 310062]
作 者:范萍萍,硕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被认为开创了西方诗学理论形而上学的传统,这部最早为诗立法的著作,虽然只有短短的26章,却成为西方诗学研究最为明晰的源流,但在《诗学》里,诗并不是凭借它自身来完成它的命运解放的,亚里士多德的策略是建立起哲学理性精神在文学领域内的有效延伸,从而试图终结“文学与哲学”的对抗。这就使他必然走上了诗学的形而上学之路。本文从对《诗学》的文本细读出发,试图寻绎和梳理亚里士多德对诗学研究的把握方式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作为原创性的诗学
亚氏的《诗学》是西方文论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研究诗的专著,他采用了科学的定义方法,批判了柏拉图对于诗的排斥,确立了诗合法和独立的地位,使之成为完整明晰的研究对象,《诗学》也成为对诗进行独创性研究的典范。而《诗学》的产生,有两个必要和潜在的前提:
第一,亚氏是第一个将知识系统化和学科化的人,他分割了在此以前知识的模糊界限,将人类知识划分为不同范畴加以区分并进行分类研究,这是诗学得以产生的首要步骤。罗素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像教授一样著书立说的人:他的论著是有系统的,他的讨论也分门别类。”①正是这种系统的学科划分才能将其研究对象独立出来,并将其形成要素各自加以确认使之能够被完整明晰地加以把握。这也就是说,诗学的产生有赖于其他不同学科知识类型的存在。这种系统的学科划分是亚里士多德的伟大贡献,正是这种知识类型的“划区而治”为“诗学”成为其自身提供了可能;亚氏在这里虽然将《诗学》作为一门迥异的学科,区别于《形而上学》《伦理学》《物理学》等,但他却都是将它们作为科学认识的对象来加以把握的,是以不同的逻辑范畴来加以限定,这正是《诗学》建立的出发点。
第二,《诗学》产生在当时丰富的文学实践的基础之上,没有丰富繁多的可供描述的文学作品,便不可能有文学理论的产生。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历过了它最为巅盛的时代,充分具备了可做总结的条件,那时已有了丰富系统的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三大悲剧诗人创作出了流颂千古的辉煌剧作,还有其它很多文学类型也已发展成熟和完备,文学自身的实践行程也已昭示了文学自觉独立的努力,比如从索福克勒斯到欧里庇德斯,就已经显示出了文学实践活动中理性原则的逐渐渗入,从中反映出了模糊混沌的神话世界观向清醒自觉的理性世界观的过渡,体现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含蓄的诗学原则的规范化,而《诗学》则将这含蓄的诗学原则进一步明晰了,《诗学》的研究是从文类“悲剧”出发的,它立足于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方面:在对一些文学作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又以先在的理性原则(这个理性原则是和谐于亚氏整个哲学世界图景的)对它们加以规范,这种规范是必然和合理的,它是文学实践以及诗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学实践的发展已不可更改地挣脱了神话世界观,对于理性的呼唤,已成为文学延续的宿命。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性主义精神又使他对于诗的规范完全对象化和形式化了,他以定义法来框定它,由此造成的谬误对其后诗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相当负面的影响。
在以上两个前提的催生之下,亚氏建立了自己原创性的诗学理论,之所以称《诗学》是原创性的,就在于它第一次赋予了诗独立和完整的地位,指出了它本源性的存在,并对于诗的存在诸要素加以了确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亚里士多德赋予了诗作为自律主体的权力,他对诗的自主地位,是从两个层面加以确认的:首先他认为对诗的评价只能以它自身为依据,而不是其它任何外在的标准,比如政治的、道德的、或其它技艺的标准(第25章),他说,“对某些批评的回答应从对诗艺本身的考虑出发”②,这就确立了诗自身存在的自足性(虽然亚氏并没有将诗的这一自足精神贯彻到底);再者就文艺作品所涉及的现实而言,它可能是不准确的、变形的,然而,就作品本身而言,却是无可非议地正确的,比如他说写马的两条腿同时举步,或者对于某种技艺(比如医术或其它任何一种技艺)的不精当的描述,其错误就并不在于诗艺本身。
柏拉图对诗的批判是站在诗的本体立场以外展开的,比如在《理想国》卷十中,他列举诗人的罪状时认为,诗人们虽然会摹仿一切,但却不具备所摹仿现实中的真正的知识,他们摹仿医学的话语,却从未医好过一些病人,留传下一派医学,也从未对其它各种技艺或事业有过发明和贡献。柏拉图是站在以他的最高理念为支撑的哲学认识论的立场上来对诗横加指责的,而亚氏则回击了柏拉图对诗的这一谴责,他认为诗自身就是独立的完满的存在,以医术和其它技艺的标准奴役诗,这是粗暴和无理的要求。
第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是在科学定义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对诗的存在形式和要素加以了确认。在对艺术下定义时,他就采用了属与种差相结合的定义方法。他将艺术规定为摹仿的属,于是摹仿就成为对诗进行确认和区分的依据,比如诗与散文,他们虽然同是韵文,但以摹仿为要素而区分开来。他说:“除了格律以外,荷马和恩培多克勒的作品并无其它相似之处。因此,称前者为诗人的合适的,至于后者,与其称他为诗人,倒不如称他为自然哲学家。”③在摹仿的内部,又以“媒介”“方式”“对象”来作为进一步区分的种差,从艺术到诗再到悲剧有一个逐步定义的过程,单就悲剧而言,他又抽绎出了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等六大要素,这种定义法一方面可以使诗学的理论要素以更为明晰的方式确认,更一方面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些理论要素以苛严的逻辑范畴加以界定,这就使我们对诗的存在的把握陷入了完全地“对象化”之中。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对作品的考察是将描述性和规范性混同起来,这是努力对文学做出合理解释以及使之获得有效延续的必由之路,但其后果就是将文学推进到了逻辑范畴与形式结构的深渊里。这种对诗的形式主义的严苛规定抹杀了文学作品的情感内蕴和独特价值,对文学的本真体验会被纳入到某种结构概念的控制之下,诗之中最为蓬勃的生命力量反而被扼杀了,亚里士多德因此被称为“最没有诗人气质”的诗学理论家。这也是他为诗辩护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危险的代价。
二、为诗辩护
如果说在前文我主要是探讨亚氏何以使诗独立,那么在这里,我是想进一步理解他何以使诗合法。亚氏之为诗辩护是顺着两条线索展开的:1.诗的摹仿是与哲学理性精神相一致,而不是相背叛的;2.诗所引起的怜悯与恐惧能够使我们的情感得以净化,而不是如柏拉图所说的,带来恶性的滋养。但我们注意到亚氏的这两条理由其实是彼此断裂而无法沟通的,尤其是对于后者,亚氏显然无法以他自身的理论对“净化”(Katharsis)这一概念做出清晰有力的解释,他回避了对这一问题的更为深入的探讨。
亚氏为诗辩护的理论背景当然首先是他对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反拨,亚氏认识到了柏拉图以永恒理式构筑起来的哲学王国里两重世界的分裂状态:一个是理性及与理性相对应的理念世界,它只考虑抽象的逻辑自明性和完整性,其自身是永恒完美的;另一个是感性及与感性相对应的可感世界,它是具体个别,充满缺憾而又变动不居的。这两重世界,割裂冲突而又彼此无能为力,柏拉图对此也无法作出满意的答复,柏拉图经验性地认识到了文学中所内含的自然生命的生动流变性是他那个高高在上的永恒理念所无力控制的,所以,他建议把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尽管这也许并不是他衷心所愿的,如亚氏所说的:“不过看来这是较好的选择,特别是作为一个爱智慧的人,为了拯救真理就得牺牲个人的东西。”④然而,文学却并不因此就能够被取消,它自有不可扼杀的常青的生命活力,换句话说,是柏拉图的理念哲学在文学的领域内遭到了失败。
亚氏则试图来挽救这一失败,他将柏拉图对真理寻求的途径从天上拉回到地面,以他的“形式质料”说来取代柏拉图的最高理念。形式质料说解决了本质与现实的存在关系,强调了形式不能离开质料而取得现实的存在,说明了认识对象的构成问题。但形式与质料在亚氏那里依然是各自区别的,他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形式是作为事物的本质构成,它是一种先在的规定性,是特定身体的何以是,而作为质料的部分则是在后的。但形式何以能够在先呢?这就如同柏拉图的理念论一样了,是一种哲学理论的前提预设。罗素在他的哲学史里引用策勒尔的话说:“他从柏拉图想把理念加以实体化的倾向之下,只曾把自己解放出来了一半,‘形式’之于他,正如‘理念’之于柏拉图一样,其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在规定着一切个别的事物。”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亚里士多德并未背叛和远离他的老师,而是在共同的理性主义旗帜的高扬之下,对柏拉图的思想加以继承和修正,使之能够更好地和更有效地服务于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亚里士多德正是以此为立足点来为诗展开辩护的,可以从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继承了诗即摹仿的观点,但因为亚氏将诗所摹仿的现实世界从柏拉图那里拯救了下来,因而这个现实世界就是真实的和可知的。作为摹仿的诗,对于欣赏者来说,他经过推论,能够认出“它就是那个事物,从而有所认识”,这就获得了求知的快感⑥,求知是哲学的目的,而诗亦能使人求知;而作为创作者来说,亚氏则并不认为诗人都是无知的,他认为“知识和理解属于艺术较多,属于经验较少,诗人对于事物是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⑦。那么创作过程也就成为表述知识的过程,诗人凭理性进行创作,那么诗与哲学就是一回事了。
第二,亚氏对于诗的形式构成以及诗人的职责等都做出了种种先在的规定,这些规定是与他理性主义的哲学精神相呼应的,他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在这里,诗成为一种哲学的手段,表现“必然”“可然”或“普遍性”的事,这成为诗与哲学进一步沟通的理由。《诗学》也从此成为理性主义文学的发端。
第三,在谈到悲剧时,他列举了悲剧的四种构成,但又规定只有一种安排是可取的,是能够引起怜悯和恐惧的:悲剧的主人不是因为本身的罪过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过失而遭遇不幸的。但亚氏的这种安排明显不能让我们满意,朱光潜先生在他的《悲剧心理学》里也提到,表现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在经验的层面上也会引发怜悯与恐惧,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将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混为一谈,企图赢得哲学在诗的领域内的有效延伸,那么其艺术观就必然是道德主义的。
第四,在谈论“净化”这个问题时亚氏很显然是语焉不详的,他给后世人留下了一个可引起无数争议的谜团。柏拉图认为诗会迎合诗者灵魂中卑劣的无理性的部分,它滋养人的哀怜癖和感伤癖,作为诗的辩护者,亚里士多德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应答,然而这又必然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它涉及接受者最为隐秘的内心体验,是不可能被清晰把握的,这就和亚氏极力为文学所灌注的理性精神相脱节,因而很多研究者将“净化”解释为道德主义的,试图将它和谐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理性精神之下,然而,在亚氏的著作文本中这一解释却无法找到清晰的强有力的理由。“净化”一词曾出现在他的《政治学》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每每被祭颂音节所激动,当他们倾听兴奋神魂的歌咏时,就如醉似狂,不能自已,几而苏醒,回复安静,好像服了一帖药剂,顿然消除了他的病患……所有的人们全都由音乐激发情感,各各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沉郁而继以普遍的怡悦。”⑧
在这里,我们实在无法为“净化”一词找到任何道德主义含义的痕迹,相反它似乎带有了一种宗教性的神秘气质,这大概是亚氏受尚未消退的神话世界观的影响。在这里“净化”仍尚是一种经验性的感受,而不是一个科学化的概念,这一点造成了亚氏整个科学理论的断裂,而他对于“净化”这个问题也只好一笔带过,按下不表。
通过以上这几点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亚氏的为诗辩护,其实是在柏拉图早已框定的哲学的理性使命的前提下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亚氏不是从根本上来颠覆柏拉图的诗学观,他至少肯定了柏拉图对诗做出种种裁决的这些准则和依据本身是正确的,因为他也是拿同样的标准来框复它们的,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迎合了这种种标准的,而柏拉图则认为恰恰相反。
亚氏确立了诗的独立地位,但又没有将这一独立性贯彻到底,《诗学》这部最早和最完备的诗学理论,它让我们感到诗既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我们通过对《诗学》文本自身的回顾与梳理,可以发现诗学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它自确立之日起,就怎样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形而上学的代价。它为我们对诗学传统地重新审视开拓了全新的视角,然而彻底的反形而上学又势必要将诗学一起反掉,诗学作为一门理论的科学,它对形而上学有着先天的依赖性,在经验与理性的边缘里生存,这是诗学的宿命,如何在两者之间协调并把握这门科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也是我们对开创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亚氏诗学理论进行回顾的意义所在。
①⑤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1页,第217页。
②③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7页,第28页。
④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⑥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3页。
⑦⑧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页,第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