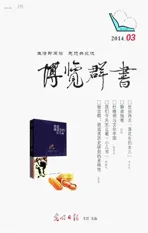武官世袭:明朝另外“那些事”
2013-08-04陈宝良
○陈宝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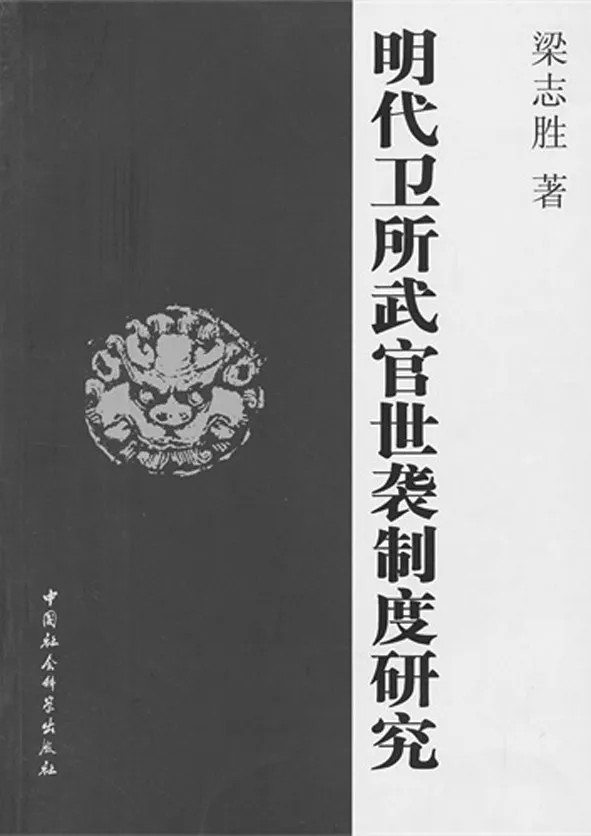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梁志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75.00元。
自《明朝那些事》流行书林,再加之多位名家先后在“百家讲坛”开讲明史之后,在民间的历史爱好者中,显已形成一股“明史热”。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凡是立志研治明史的学者,无不乐观其成。不过话又说回来,明朝的历史既纷繁复杂,又丰富多彩,并非仅仅限于“那些事”,而是还有很多另外“那些事”。明朝卫所的武官世袭制度,无疑称得上另外“那些事”的典型例子。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选修先师顾诚教授开设的明史课时,先师不时会提到吴晗所写的《明代的军与兵》一文,且三致意焉,其用意就是让学生从动态变迁的角度理解明朝的军事制度。先师长期关注明朝的卫所制度及其相关问题,先后著有《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谈明代的卫籍》《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等系列论文,其富有创造性的研究,足以证明卫所以及所涉问题的重要性。师弟梁志胜秉承先师遗志,在攻读博士期间,就选定卫所武官世袭制度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并于2000年6月完成论文。志胜有先师遗风,论文完成之后,并未为谋求一己功利而匆匆出版,而是继续沉潜其中,穷矻长达十余年之后,才最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以下简称《卫所武官》)一书付梓。
一
《卫所武官》主旨在于探究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发展演变情况,由这种制度的实施而对卫所制度本身以及明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制度的历史作用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所有这些,既便于读者对这种制度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且对于全面认识明朝的军事制度大有裨益。
综观全书,大抵有两大突出的特点,值得予以介绍。一是史料相当翔实,尤其是对明代档案中选簿的发掘与利用,更使该书的诸多考订、辨证、论析,无不显得于史有征。从书中读者不难发现,作者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整天泡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而后又花费将近四年的时间,完整地梳理了已经影印出版的明代档案。正是有了如此辛勤的付出,方使该书内容丰厚,有血有肉。二是该书在明史研究领域中,有“填空”、“补白”之功。书中内容所及,诸如卫所世袭武官集团的形成、世袭武官的基本构成、武官世袭的基本法则、犯罪与武官袭替、武官优恤制度、借职制度、比试制度等,作者可以借鉴的前人成果虽不可说付之阙如,但确实相当薄弱。经过作者多方钩稽史料,并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与档案中加以全面梳理,已使武官世袭的具体内容更为深入,大抵厘定了明朝武官世袭制度建立乃至演变的基本脉络。
《卫所武官》一书,称之为老实治学的典范,并不为过。在目下“模式史学”大行其道的时势下,有很多聪颖之士因为不甘寂寞而对这种研究范式大加追捧,且不乏身体力行者。这种随风波流转的治史之法,固然可以吸引一时的眼球,但转瞬就会沦为“明日黄花”。反观老实治学之法虽不敢说字字皆有出处,但无不秉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且有自己一以贯之的精神命脉存于其中,尽管一时可能受到冷落,但因替后来的研究者做了添砖加瓦的工作,终究会受到后世治史者应有的尊重。
当然,所谓的老实治学,仅仅是治史的原则,并不影响研究领域的拓展。就明朝卫所武官世袭制度尤其是卫所制度而言,因其所涉问题相当广泛,举凡明清地方社会史、地方文化史、移民史、家族史之类,无不与卫所制度相关。若是作者在这本论著的基础上,选定一个区域,就卫所武官世袭与家族及明清移民等问题加以开拓性的研究,无疑会将相关问题的研究引向更为深层的一面。我对作者有此期待,也相信作者有此能力。
二
明朝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的建立,确乎可以称之为有利有弊。从有利的一面来看,正如作者所言,武官世袭既可收充实武官队伍及开发边疆之效,又对明代人口的迁移、分布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从其有弊的一面来看,武官世袭导致的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这些世袭的武官,仅仅凭借祖上的门荫,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整天浑浑噩噩,不求上进,过着一种安乐骄奢的生活。
永乐六年(1408)三月二十日,明成祖在所下的圣旨中,对世袭武官的变化,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这个圣旨相当口语化,尚未经过史臣的笔削,读来生动活泼,不妨选取其中的几段,以为范例。如说这些世袭武官“每日惟务安乐骄奢,互相勾引,吹箫、弹琵琶、唱曲儿、赌博财物、看勾栏、说平话,去那歌楼酒馆挟妓买笑,恣肆粗狂,鼓弄唇舌”;说他们“本等弓马全不肯用心操练,其余的武艺又全然不去习学,又不肯读书学道理,看古时名将所为垂名万世不磨的功绩,又不学抚绥军士的好勾当”;又说这些武官平时不好好练习武艺,等到“赴京来告袭替,比试时弓也不曾(会)射,枪也不会拿,马也不会骑,只拼着钱物买求监比官取中”。这些人靠钱买通袭替,又要过一种骄奢淫逸的生活,那么一旦做了官,“便百般苦害军士;遇有征调,惟务假粧事故,使钱买免;便有调到军前的,百般畏避退缩,只是躲藏在人后,得走时便先走了”。宋代名将岳飞曾说过,“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才能成得一个世界。我们知道,永乐三年离明太祖开国仅仅不到40年,卫所武官就如此不堪,不但怕死,而且还贪财,怎能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责!
卫所武官素质下降之速,确实令人咋舌。正因为此,才有了明代中期以后募兵制的兴起。那么,那些招募来的武将,他们的整体素质又是如何?其实,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妨引一个冯梦龙编纂的笑话作为佐证。这个笑话故事的主人公叫汤胤勣,明朝历史上实有其人,原本有“汤一面”之号。这个绰号是有出典的,说汤胤勣博学英发,在成化初年,言官将他当作将才推荐给朝廷,而且在推荐奏疏中,称他“才兼文武,可当一面”,为此才有了这样一个外号。其实,盛名之下,不副其实。随后汤胤勣镇守陕西孤山,有一位故旧前来拜见,留在家中一同饮酒。当时正好军士来报,称蒙古人兵临城下,他就大言炎炎地对故人说:“先生姑且自酌,待我前去迎敌,将胡雏生擒给您看一看。”刚出城,正好有一个蒙古兵埋伏在沟渠中,射出一箭,汤氏中喉而死。为此,人们又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汤一箭”。
这些例子说明,尽管在明朝的武官中,固然不乏俞大猷、戚继光、陈第这样文武双全之人,但大多数已经沦为“汤一箭”一流的人物。到了甲申、乙酉(1644—1645)之际,那些亲身经历了“天崩地陷”一幕的士大夫,无不把自己的目光集聚到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上。在清初士大夫反思明朝灭亡的过程中,有很多学者将矛头直指明朝文武关系的失衡。黄宗羲堪称其中的典型。
当北京陷落以后,悠悠之口,无不认为这是因为明朝廷不任武力所致。其实,这怪不得崇祯皇帝。就崇祯一朝的实际情况来说,崇祯帝为了改变重文轻武的习气,确实特意重用武将。但是,正如黄宗羲所言,崇祯帝所重用的武将,全都是一些粗暴之徒,最终导致“君死社稷”。这不但不得专任武力之用,反成专任武力之过。究其原因,黄宗羲认为,上古以来,真正的将才,无不出自儒术。只有这样,才能当国家多难之时,他们能为国家尽忠尽节,而国家无事之时,他们又能靠儒术闻名。如此典范,王阳明一类的人物才堪称其例,既有将帅之能,又别具文才。换句话说,若是仅仅将“武夫”视为“武”的典范,这就好像将只会参加场屋科举考试的猥琐之士称为“文”一样,是一种“名实之乱”。这是黄宗羲为浙江宁波万氏家族中人万邦孚所作神道碑文中所发的一段议论。万邦孚,虽为武将,但又精通儒术,尤其精于阴阳家言,著有《筮吉指南》《通书纂要》《日家指掌》等书。宁波万氏家族自万表以后,多出文武双全之士,但在明代,如此典型的例子实在太少了。
三
这就牵涉到明代文武关系的演变问题。武以定国,文以治国;乱世思将,治世思相。这显然已经成为传统中国历史的一条定律。可见,文、武二途,不可偏废考察明代文武关系的演变,大抵体现了以下的演变趋势:明初重武轻文,中期以后转而变为重文轻武。
先来看明初的重武倾向。正如该书所引用的明末陆人龙所著小说《型世言第8回所说,明初洪武年间,是一个“尚武不尚文”的时代,武官的地位明显高于文官,进而导致文官有弃文从武的想法。如《逆臣录》卷1记载吏部尚书詹徽曾对手下说:“如今做文官的不曾有个熬得出去”,凉国公蓝玉准备谋反,“莫若随顺他做一场,日后事成时讨个军官做,到得从容快活”。这同样可以从明初文武官员交往的礼仪、体貌得到印证。如明初总兵官的体貌极受尊重,地方各级有司官员前来拜见,均必须行“伏谒”之礼,也就是下属见上司的礼仪。我们知道,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北方各个边镇,先是设立了总兵,随后才陆续添设属于文职的巡抚。这就是说,总兵掌管一切军务,巡抚不得干预,只能辅佐赞襄,所以巡抚的署衔仅仅是“参赞军务”。只有边镇没有总兵官,或者总兵官的设立晚于巡抚,巡抚才能署衔“提督军务”。总兵体貌如此之重,地方都司管辖下的卫所,大致也是如此。如在永乐年间,每次知府一类的官员路过卫所官员的衙门,或者二者在路途相遇,假若知府不下马,那么卫所官员就会鞭打知府的仆隶,可见二者之间并未行平行之礼。
明代中期以后,重文轻武的风气开始盛行,武官的社会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即使像大将、副将一类的高级武官,都必须服从兵部尚书的差遣。这些武官从袭荫初任开始,每次上达给兵部与兵科的手本,其中人格卑污者,动辄自称“门下走狗”,即使稍为自尊一点,也是自称“门下小的”。为了袭荫甚或升迁,他们不得不向文官行贿,守备、把总以下的武官,给兵部的办事员书办送礼,在名帖上更是不得不自称“沐恩晚生”,而且名字还得用蝇头小字,不敢用大字,以免书办误认为倨傲无礼。万历年间,即使已经有了公孤爵位的名将戚继光、李成梁,在拜见首辅张居正时,也是甘愿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至于地方上的卫所官员,更是士气不振,卫指挥在见知府时,甚至称知府为“恩堂”,不再敢与知府分庭抗礼。
到了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为了洗涤重文轻武的风习,矫枉过正,刻意重用武官,最终导致南明弘光朝廷时出现左良玉、刘泽清等江北四镇的武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王铎,在为刘泽清作序时,直称刘母为“老伯母”,这或许可以说王铎为人谦逊,但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体貌应有的自尊。即使如此,看似改变了文强武弱的局面,其实并不尽然。在明末时期,应该说是武强而文不肯弱,相持起衅,互不相下。
在明朝文武关系的演变历程中,中间还出现了武将尚文或文人尚武的风气。武将尚文,是不务正业之举,说明他们受到了重文轻武风气的威慑而不得已为之,藉此提高自己的声望。至于文人尚武,好谈兵,究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唇吻韬略,流于口说而已,并无多大实效。两者相合,终成一个文恬武嬉的结局,明朝最终难以逃脱覆亡的命运。
读罢《卫所武官》的后记,最后我还想就学风问题赘言几句。作者的博士论文曾经多次为他人剽窃发表,甚至出现剽窃者理直气壮、被窃者徒付奈何的尴尬局面。其实,这种穿窬宵小之徒,他们的行为不过是为学林“外史”增加一些范例而已。先师顾诚门下之风,宽于待人,严于律己。志胜隐去剽窃者之名,这是他为人的忠厚之处。至于在后记中刻意提出,其目的还是为了以正视听,以免鱼目混珠、是非混淆。立此存照,当代与后世的明眼人自能判别真伪,加以鞭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