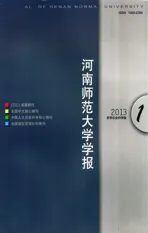卢卡奇自然观的发展轨迹及其成因
2013-04-12郝红军
郝红军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450015)
卢卡奇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一生以研究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著称,被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由于受当时历史环境和其自身理论发展水平的制约,从其早期思想形成时期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到晚年的理论巨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解读,前后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青年时期重求异,晚年又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这一特点在他的自然观思想形成方面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一、青年卢卡奇自然观思想形成的背景及失误
卢卡奇青年时代,国际风云动荡,政局变化莫测,思想界更是极其混乱,旧价值观沦丧殆尽,新的价值观尚在痛苦求索之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第三国际也随之成立,一系列的革命事件不仅在政治上引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杂多变,而且也促使了人们对第二国际理论的进一步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论问题的反思。卢卡奇针对当时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在着重强调和阐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实践观点时,对马克思在自然领域推广辩证法提出了异议,与恩格斯、列宁的哲学发生了某些分歧。这些思想都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得到了体现,显示了该书的过渡性和两重性,也说明了卢卡奇当时还没有彻底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正处于“转型期”,用卢卡奇自己的话说,正处于“马克思的学徒期”。因此,在他那里,并存着两种不同分析问题的思路,即一方面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另一方面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这样,就使其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时,不由自主地戴着黑格尔的“三棱镜”来了解马克思。需要指出的是,卢卡奇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探索过程中,尤其是在其自然观的形成发展理论上出现一些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与其公开背离马克思主义终究不是一回事。
《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第一篇论文是《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写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47-48这里的方法,他认为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而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及意义所在是改变世界,而不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世界。对此,卢卡奇认为改变世界的关节点,就在于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其所谓的“主体-客体辩证法”,也是他认为的马克思辩证法,当然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之中,其中心内容就是论述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人与人所创造的社会世界的相互作用,对于自然界,仅仅是作为被人的活动所改变的,包含在社会关系范围内的产物才具有意义,所以,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能在纯自然的领域发生,也就是说,在纯自然领域内不存在什么辩证法。
这样,卢卡奇就把辩证法限制在了社会历史领域的范围之内,并同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脚注中对恩格斯关于自然领域的辩证法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这里把这种方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1]51不但如此,在正文中卢卡奇还批评恩格斯忽视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恩格斯虽然认识到“辩证法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但是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1]50。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是不能离开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只有主体或者只有客体,都不能构成辩证法。所以,一方面,他把人看成“实体-主体”,即把人看成是存在的本源,把主体构成并且“包摄”客体作为主体和客体同一性的前提,这就势必把自然排除在外。自然界很明显不是人所创造的,而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因而卢卡奇断言,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人内在于社会历史之中,而在自然界及其客观规律制约之外。因此,辩证法“只能限制在社会历史的领域,这是头等重要的”。另一方面,他还把自然看成一个社会范畴,具有社会性,但是他认为,不管人与自然的联结采取什么形式,“自然的内容、自然的范围和客观性总是被社会所决定”。
可见,早期卢卡奇认为,辩证法只能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在自然领域不存在什么单纯的自然辩证法,一切辩证法只有在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中才有意义。这显然是与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相冲突的,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发展轨道。
二、晚年卢卡奇对其早期自然观的补正
作为一名卓越的思想家,卢卡奇本身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理论上的完善,愈到后期其理论愈日臻完善,可以说,其晚年时期是他进行理论上的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时期。针对其青年时期所著《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在自然观的探索方面出现的失误与不足,在其晚年时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且有了很大的改进与完善。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晚年巨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在该书中,卢卡奇对其早期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补正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的。
首先,针对其青年时期把人看作“实体-主体”,即把人看作存在的本源,提出了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卢卡奇认为,早期习惯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本体论作为出发点,按照这种理解方式,马克思主义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主观辩证法的理论,同时总是以现实中的客观辩证法理论,即本体论作为先决条件的”[2]78。基于此,卢卡奇已经认识到早期坚持的“实体-主体”思想,把人看作存在的本源,把辩证法排除在自然界之外,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辩证法的客观性,否定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对此,他通过确立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来论证“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他指出,真实的存在分为三种:无机界、有机界和人类社会,无机界和有机界合起来构成自然存在,人类社会即社会存在。这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同样具有历史主义原则及其在时间上本体论的不可逆性的特点”,其中,人类社会具有本体性存在的意义,但它又离不开自然界,并以自然存在作为前提和基础:“社会存在一般来说并在所有特殊的过程中,都是以无机和有机的自然界为先决条件的”,“社会的客观形式来自自然存在并更加明显地表现为社会的”[3]。因此,他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提出了“返回到存在去”的口号,提出了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从而也标志着他从主观角度去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到依据客观角度去肯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既然自然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前提,那么,“自然本体论”即“自然辩证法”也必然是“社会存在本体论”即“社会辩证法”的基础。那么,卢卡奇是怎样完成两者之间的过渡的呢?对此,卢卡奇也认识到,自然存在虽然是社会存在的一般前提,但这两大类存在各自服从不同的法则,不能简单地把自然法则搬用到社会存在领域中去,也即他所说的“无论如何,社会存在本体论不能直接从自然概念中推演出来”[2]6。这里,卢卡奇引出了劳动的观点,他以对劳动概念唯物的把握和阐释为切入点,通过劳动的中介把两者逻辑地连接了起来,这也就是我们下面所说的第二个角度,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飞跃是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
卢卡奇认为“决不能因为这一过程(指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飞跃)实际上涉及一个漫长的过程,涉及无数的转变形式,就忽视了这一本体论上的飞跃”。这里他所说的“本体论上的飞跃”就是通过人的劳动,使自然存在变成了社会存在,通过劳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之间才搭起了物质交换的桥梁。而作为主体的人也通过劳动的影响和对自然的改造,促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与此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本身的自然,在不断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类本性,成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这样,就最终通过劳动实现了“人的人性化和自然的社会化”的同步进行。所以说,卢卡奇通过“劳动”概念,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承认了自然的优先地位,承认了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存在,并且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里也作出了自我反省,他强调指出:“可以证明,正是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造成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世界观之间真正彻底的区别。回避这一点,就会模糊哲学上的争论,例如,就会妨碍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做出清晰的阐述。”[1]11
三、卢卡奇前后期自然观发展变化的原因分析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读(即卢卡奇自然观的形成)前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历程,即早期偏离了马克思,而晚期又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轨道上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可以说,这是由卢卡奇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上的不成熟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首先,卢卡奇在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去批判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宿命论观点时,忽视了马克思提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基础和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前提,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在坚持唯物主义客观本体论的基础上重视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卢卡奇恰恰忽视了这种本体论基础,却坚持了“实体-主体”的存在思想,以人为存在的本源,把主体构成并且“包摄”客体作为主客体同一性的基础,从而把自然界给排除在外,否认了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否认了自然规律对人类的制约作用,否认了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最终否定了物质自然的辩证性,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类的出现与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也无法得到证明。
其次,卢卡奇没有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关系,忽视和割裂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批驳第二国际一些思想家轻视辩证法的思想倾向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当成了一种纯粹的方法来运用,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等同于辩证法,而且这种辩证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种具有唯心论色彩的“主体-客体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仅仅限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范围之内,强调在纯粹的自然界不存在什么辩证法,否认自然辩证法是对自然规律的概括和反映,并且指责恩格斯把辩证法扩大运用到自然界,是追随黑格尔错误的先导,全面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进而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完整性,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理论轨道。
最后,卢卡奇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自然观与恩格斯的自然观之间的关系,并且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立了起来,没有看到它们在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马克思在致力于社会历史辩证法研究的同时,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也一直和恩格斯进行着密切的交流和合作,并且十分关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明确地肯定了自然存在的优先地位,肯定了辩证法在自然界中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可见,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时,也没有完全停留在自然领域,而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连接起来,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研究的,而卢卡奇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这也可能是由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造成的,因为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还没有出版,它是在1925年才正式出版的,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早在1923年就已经由柏林马立克出版社出版。由此,卢卡奇不可能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对《自然辩证法》中的“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更是不甚了解,再加上当时思想界正处于新旧价值观交替时期,卢卡奇本人的思想也处于转型期(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学徒期),难免会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思想产生误解和偏离。
总之,结合卢卡奇早期和晚期自然观发展的理论轨迹及其成因来看,卢卡奇晚期的自然观思想是对其早期思想的修正和扬弃,是一种自我清理和更新,对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曾指出:“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与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反,它在客观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所有各种表现形式,不论它们的哲学根源和政治影响是如何极不相同,也不论它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的根基的。我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的哲学,因而忽视或者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倾向。”[1]10卢卡奇这种富有“哲学良心”的自我批判,不仅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日臻成熟的反映,而且体现出了一代理论家、哲学家治学严谨、勇于负责的崇高精神境界,这种崇高的精神至今仍是值得我们学术界去学习的。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卢卡奇.黑格尔的虚假的和真正的本体论(英文版)[M].伦敦:伦敦出版社,1982.
[3]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M].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7.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