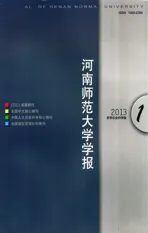旧题李攀龙《唐诗选》真伪问题再考辨
2013-04-12殷祝胜
殷祝胜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541004)
一、引言
旧题李攀龙《唐诗选》一书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唐诗选本之一。关于此书的真伪问题,古今共有三说。明末凌濛初《唐诗广选序》曰:
粤自历下《删》成,元美携其本归吴中。馆客某者潜录之,颇有轶落。他日客复馆先君子所,出其本相示。家仲叔欣然授诸梓,而《选》始传。后元美观察吾郡,见而语先君子曰:“此尚有漏。其完者子与行且校之。”先君子更从子与所请得其原抄本,则子与时自有丹铅评骘之草犁然,秘之书麓。已而《古今诗删》出,《删》止载子与名,不存其笔。此《选》与《删》各行之始末也。嗣后晋陵蒋仲舒取所为《选》笺释之,诠载既详,扬榷咸备,博雅欣赏,海内家传户习之。[1]
在这段对《唐诗选》的来历与早期传播情况的叙述中,凌氏否定了李攀龙对此书的编著权,而以此书为王世贞家“馆客某者”从王氏携归的李攀龙《古今诗删》原稿中的唐诗部分摘抄而成的伪书。此其一。
其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古今诗删〉提要》曰:“流俗所行,别有攀龙《唐诗选》。攀龙实无是书,乃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唐诗,加以评注,别立斯名。”[2]同书卷一九二《〈唐诗选〉提要》、卷一九三《〈唐诗广选〉提要》也有类似说法,此可称为馆臣说。此说也以《唐诗选》为伪书,但具体内容与凌说不同:一是它认为此书成于明末坊贾之手,成书时已被“加以评注”,明显异于凌氏的此书成于王世贞家馆客之手,“嗣后”始被“笺释”的说法;二是它认为此书是“割取《诗删》中唐诗”而成,也不可与凌氏的《唐诗选》摘抄自《古今诗删》原稿的说法混为一谈,因为馆臣距李攀龙生活年代相隔已二百余年之久,见到的不可能是《古今诗删》原稿,其所谓“《诗删》中唐诗”自当指《古今诗删》刊本中唐诗。
其三,蒋寅在介绍日本学者关于《唐诗选》真伪的讨论时有曰:
平野彦次郎先生《唐诗选研究》将《唐诗选》与《品汇》各类作品逐一对比,由其编次肯定《唐诗选》是由《品汇》摘出……而《古今诗删》则是在《唐诗选》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调整了一些不合理的编次。……近年森濑寿三先生在平野氏研究的基础上,从书志学入手……得出《唐诗选》确出于李攀能手之的结论。[3]
此可简称为森濑寿三说。与前两说完全不同,是说认为《唐诗选》确出李氏之手,不是伪书,它摘抄自高棅《唐诗品汇》,《古今诗删》中唐诗是后来在此基础上增补而成的。
以上三说,馆臣说为国内学者普遍接受,森濑寿三说“代表了当代(日本)学者的看法”[3],分别为中日学界的主流意见;凌说则除个别学者将之与馆臣说混为一谈而予以认可之外[4]144,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不足凭信。然而笔者在进一步研究各种相关资料后发现,馆臣说和森濑寿三说均存在较大疑点,凌说则较能经得起推敲,当更为接近事实的真相。下面就不揣谫陋,拟对此作具体的论述。
二、馆臣说最为可疑
在《唐诗选》真伪三说中,国内学界高度认可的馆臣说其实最为可疑。
首先,馆臣说认为《唐诗选》成书时即被“加以评注”是有违史实的。近年国内有学者在对是书的版本进行调查之后,得出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蒋一葵笺释本是所有各本中最早的一个”[5]110的结论,似乎可证其成书时确已被“加以评注”,馆臣所言有据。然而这一调查做得并不完善,从现存书志著录情况看,《唐诗选》最早的本子是万历乙亥即万历三年(1575)吴兴凌氏盟鸥馆校刻本。罗振常原著、周子美编《天一阁藏书经见录》卷下著录此本并介绍说:
《唐诗选》七卷。明李攀龙选,万历刊,行楷小字似赵体,极精。前有正(应作王)世懋序,次王樨登序,次李攀龙序,目录末有牌子三行:万历乙亥秋七月既望吴兴凌氏校刻于盟鸥馆。第一页书口下方署吴门高洪写张璈刊小字一行,余亦有刊工名,卷中各体俱备而所选甚少,惟李杜各有二十余首,余均数首,且有一二首者。王序:“唐诗选至于鳞,卷仅七而终,又加精焉。”白绵纸印,二册。[6]
此本的出版者盟鸥馆,据凌濛初的仲叔凌述知有文集名《盟鸥馆集》[7]17来看,其主人即凌濛初的仲叔,则此本当由凌濛初的仲叔主持出版。按本文开头所引凌濛初《唐诗广选序》中有《唐诗选》最早由其“家仲叔欣然授诸梓”的叙述,与上述书志著录情况契合,可知万历三年凌氏盟鸥馆本《唐诗选》即为此书最早刻本。那么这个最早的本子是不是已经带评注了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如果这是一个带评注的本子,上面所引的那段连刻工姓名都涉及到了的介绍中不至于提都不提一下评注者的姓名。可见馆臣“加以评注”云云未得其实,因之其“乃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唐诗”说有多少根据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
其次更令人怀疑的是,如果《唐诗选》像馆臣所认为的那样“乃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唐诗”而成,那么其编次将非常难以理解。《唐诗选》共收作品461首,虽较《古今诗删》中所选唐诗(739首)在数量上缩减了近五分之二,但基本上保留了《古今诗删》中唐诗的大貌[4]143,这是国内学者认可馆臣说的主要理由。然而这种粗略的观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唐诗选》的编次与《古今诗删》中唐诗编次存在一定差异而与高棅《唐诗品汇》的编次几乎完全一致。这一事实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由日本学者平野彦次郎揭示出来,平野氏由此得出“《唐诗选》是由《品汇》摘出”的结论[3],当然还需要商榷,下文再论;但《唐诗选》“乃割取《诗删》中唐诗”而成的观点的不合理则因此充分暴露出来。
本来,如果孤立地看《唐诗选》与《古今诗删》中唐诗的编次差异,还可以用“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唐诗”时态度随意所致来为馆臣说辩解,可由于这些差异在《唐诗选》与《唐诗品汇》之间并不存在,那么这些差异就只能解释为是明末坊贾在“割取《诗删》中唐诗”以编《唐诗选》时又认真依据《唐诗品汇》改动了部分作品编次的结果,才能保证馆臣说的成立,但明末坊贾这样做的可能性实在太微乎其微了。因为第一,这需要设想明末坊贾已看出《古今诗删》中唐诗完全出自《唐诗品汇》[8]211,否则其依据《唐诗品汇》来改动编次就太过巧合。可要发现《古今诗删》中唐诗与《唐诗品汇》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对这两本书下一番仔细对比的功夫是办不到的,而下这样的功夫对于急于营利的明末坊贾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第二,明末坊贾这样做的动机无法获得合理解释。《唐诗品汇》中的作品或由于编在附录如骆宾王《帝京篇》,或由于列入“旁流”如无名氏《水调歌》等,或由于收在“拾遗”如崔敏童《宴城东庄》等,因而其编次未尽合乎作者的时代先后;《古今诗删》收录这些作品时多已据其作者的时代先后调整了编次。按常理来说,明末坊贾在“割取《诗删》中唐诗”以编《唐诗选》时,只需依照这些作品在《古今诗删》中的编次抄出即可,完全没有必要将其编次再依照《唐诗品汇》改回去。这样做无论从营利的角度还是从学术的角度看都是不可思议的:就前者言,它增加了人力成本;而就后者说,它降低了书籍的质量。二者都是有弊而无益的。
三、森濑寿三说也有疑点
与馆臣说相比,森濑寿三说的立论基础坚实很多。然细加考察,也有可疑处。
森濑寿三吸收平野彦次郎的观点,由《唐诗选》的编次与《古今诗删》中唐诗编次存在差异而与《唐诗品汇》的编次基本一致的情况“肯定《唐诗选》是由《品汇》摘出”,又根据《古今诗删》中唐诗编次比《唐诗选》编次更合理的情况推断《古今诗删》中唐诗是在《唐诗选》基础上增订而成[3]。乍一看,似乎比较稳妥,可再一考察《唐诗选》卷七中出现的一处失误的由来,便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唐诗选》卷七中录有《水调歌第一叠》、《凉州歌第二叠》、《水鼓子第一曲》三诗,此三诗在《唐诗选》问世以前的历代文献中皆作无名氏作品,未见有言其作者具体为谁的,而《唐诗选》则将此三诗的作者署为张子容,显为缺乏依据的误署。这一失误是怎么造成的呢?先来看此三诗和张子容诗在《唐诗品汇》中的编录情况:此三诗收于卷五五,未署作者姓名;张子容诗分别见卷一七、卷六十、卷六三、卷七六及拾遗卷四、卷八,与此三诗皆至少相隔数百首之遥。再来看它们在《古今诗删》中的编录情况:此三诗收于卷二二,未署作者姓名,其前即为张子容《巫山》诗。然后来看《唐诗选》:此书未收张子容《巫山》诗,而《水调歌第一叠》等三诗的作者变成了张子容。很显然,这一失误与其说是因摘抄《唐诗品汇》而来,毋宁说是因摘抄《古今诗删》时的疏忽所致,摘抄者未细审《古今诗删》原文,误将紧接张子容《巫山》诗后的无名氏作品也当作张子容作品了,这正属于校雠学上所谓“因上文而讹”[9]的情况。即此而言,《唐诗选》似乎又应该如上文所否定的馆臣说主张的那样是“割取《诗删》中唐诗”而成,森濑寿三说主张它“是由《品汇》摘出”以及《古今诗删》中唐诗是以它为基础增订而成都要打上问号了。
森濑寿三根据书志上的材料得出《唐诗选》确出李攀龙之手的结论,也同样存有疑点。就现存书志看,能为森濑寿三这一观点提供支持的是上文引录的《天一阁藏书经见录》中那段材料里提到的万历三年凌氏盟鸥馆本《唐诗选》卷首的王世懋序。此序与同样载于此本卷首的王穉登序和李攀龙序不同:王穉登与李攀龙无直接交往①关于王穉登的交游情况,详参台湾学者萧敏材《晚明吴中布衣文人王百穀新探》第4章,国立中央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对于其所序之书是否确为李攀龙所编未必清楚,不能排除他是误信坊贾之言而作序的可能;李攀龙的序从其题目原为《选唐诗序》以及见于《古今诗删》中唐诗卷首等情况来看,应该是为《古今诗删》中唐诗而非为《唐诗选》而作,故此二序皆不能证明《唐诗选》究竟是否李攀龙所编。而王世懋序中有“选至于鳞卷仅七而终”之语,表明其所序者为七卷,这与《唐诗选》卷数同而与《古今诗删》中唐诗为13卷异,可证其非如李攀龙序那样是为《古今诗删》中唐诗而作,而是为《唐诗选》而作;王世懋是李攀龙挚友王世贞之弟,自己也与李攀龙交往密切②参王世贞《亡弟中顺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状》,《弇州四部稿·续稿》卷14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检李攀龙《沧溟先生集》和王世懋《王奉常集》,可见二人诗文交往颇多,关系相当密切。,他应该清楚李氏有没有编过《唐诗选》一书,不会像王穉登那样可能由于误信坊贾之言而为一假托李氏之名的伪书作序;又,此序收于万历十九年(1591)吴郡王氏家刻本《王奉常集》即王世懋别集之文部卷八,题曰《唐诗选后序》,其为王世懋所作绝无问题,故由王氏此序得出《唐诗选》成于李氏之手的结论确实是显得颇为有力的。
那么我们说此论也同样存有疑点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此论只有王世懋序一条孤证让人不免觉得奇怪。从王序中“右于鳞者,以谓宋玉东家之子,宗其心匠;博艺之士,口其编而心内不然者,不佞能家置喙乎”以及“览者从于鳞所入求之,庶几乎苦心哉。必曰较长挈短,摘瑕指瑜,则于鳞之不必尽唐诗,与此编之不必尽于鳞等也,无所容吾言矣”[10]291等语来看,李氏编《唐诗选》在万历三年凌氏盟鸥馆本刻印之前就已经不是什么秘籍,而是知者颇众,并引发许多批评意见,影响相当大了。按说李氏好友中见过此书、了解此事的不可能只有王世懋一人,可流传下来的这些人的作品中除王氏此序之外,再无只言片语提及此书此事,连与李氏关系最为密切、最爱谈论李氏选唐诗之事的王世贞也没有留下任何这方面的文字,这种集体失语难道不是奇怪的事吗?二是此论存在相当有力的反证。前文说过,凌濛初《唐诗广选序》中说《唐诗选》最早由其仲叔“授诸梓”是可以信赖的,此刻本即《天一阁藏书经见录》著录的万历三年凌氏盟鸥馆校刻本,而《唐诗广选序》中说《唐诗选》的编者其实不是李攀龙,从情理上看,这一说法是不宜轻易定为诬妄之词的。试想如果《唐诗选》确出自氏之手,对于首印此书的凌氏书坊而言实为值得夸耀的事情,凌氏应不会歪曲事实,将其先人所刻的一部著名的“真”书诬为伪书;即使是为了抬高新刻的所谓李攀龙编《唐诗广选》的身价以畅销路而需对《唐诗选》进行贬损,他也只要指出其仲叔当年所刻是李氏的初稿,现在刻的是李氏后来的增补本即可,同样没有必要厚诬尊长,以“真”为伪。梁启超归纳乾嘉考据学有“孤证不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的原则[11],持此以衡森濑寿三关于《唐诗选》出自李攀龙之手的推断,其难以为“定说”是显而易见的。
四、凌濛初说的可靠性
凌说在《唐诗选》真伪三说中最不受重视。这当然与此说所自出之凌氏《唐诗广选序》流传不广、知者甚少有关③凌濛初此序见于明末凌氏初印本《唐诗广选》前,其后凌氏再印此书时即删去之,而代以凌宏宪序。参王重民《中国古籍善本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60—461页。,而更主要的还是与学界多认为此说不足凭信有关。
凌说真的不足凭信吗?我以为不然。首先,如前所论,凌序关于《唐诗选》最早由其“家仲叔欣然授诸梓”的叙述可由万历三年凌氏盟鸥馆校刻本《唐诗选》的存在而得到证实,这一点在判断凌说的可靠性时有重要意义,因为从史料来源看,作为此书首刻者的侄辈,凌氏(1580—1644)虽然在万历三年此书初刻时尚未出生,但他关于此书来历的叙述应是得自其家中长辈,这些人为首印此书的参予者或见证人,对于此书的来历当较他人有更亲切的了解,其所言自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其次,在《唐诗选》摘自何书问题上,如上所述,森濑寿三等人提出的《唐诗选》摘抄自《唐诗品汇》的主张虽能对《唐诗选》的编次作出合理解释,却难以解释《唐诗选》卷七中那处失误的由来;馆臣提出的《唐诗选》摘抄自《古今诗删》刊本中唐诗的主张虽能对该处失误的由来作出合理解释,却难以解释《唐诗选》的编次;而凌说以《唐诗选》摘抄自《古今诗删》原稿中的唐诗,就可以没有前二说中所存在的那种左支右绌、进退失据的尴尬。何以言之?第一,既然《古今诗删》刊本中无名氏《水调歌第一叠》等三诗是紧接在张子容《巫山》诗后的,那么其原稿中这几首诗也是如此编排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而在摘抄《古今诗删》原稿时当然也可能会出现“因上文而讹”,误将紧接张子容《巫山》诗后的无名氏作品也当作张子容作品的情况,这就可以解释森濑寿三说所难以解释的《唐诗选》卷七中出现的那处失误的由来。第二,根据《古今诗删》刊刻时已经由徐中行、汪时元作了校订,同时的吴国伦曾抱怨此书刻印不精[12]等情况看,此书原稿与刊本之间应该存在一定差异,那么《古今诗删》刊本中唐诗编次与《唐诗选》有出入,并不表示其原稿也一定如此;相反,根据《古今诗删》刊本中唐诗均出于《唐诗品汇》[8]211来看,其原稿中唐诗摘抄自《唐诗品汇》应该可以无疑,则其编次与《唐诗品汇》保持一致自属可能,因而在摘抄《古今诗删》原稿时当然也可能会出现作品编次与《古今诗删》刊本存在差异而与《唐诗品汇》基本一致的情况,这就可以解释馆臣说所难以解释的《唐诗选》编次问题。由此可见,凌氏对于《唐诗选》来历的了解确有他人不可及之处,其有关叙述的可靠性绝不可等闲视之。
再次,学界关于凌说不足信的论述本身都存在明显的盲点,不能动摇凌说的可靠性。比如陈国球认为凌序所述“着实也没有其他旁证”[8]209,然如上所论,凌序关于《唐诗选》最早由其“家仲叔欣然授诸梓”以及此书摘抄自《古今诗删》原稿的叙述均非虚语,都有旁证,则这种质疑显然不能成立。又如金奎生以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蒋一葵笺释本为《唐诗选》的最早刊本来质疑凌序所述《唐诗选》在《古今诗删》之前刊印不合史实[5]110,这也明显是未知《唐诗选》实有万历三年凌氏盟鸥馆校刻本。今既知《唐诗选》刊印于万历三年,则凌序所述就并不见有何与史实抵牾之处。《古今诗删》的刊印时间,就现存材料看,一是可以肯定是在隆庆四年(1570)八月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古今诗删序》中“(李攀龙)殁而新都汪时元谋梓之”[13]可证;二是应当不晚于万历五年,据万历五年世经堂刊《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7中已收有《古今诗删序》可知,王世贞作此序在万历五年前。而此序是王氏特为汪时元刊印《古今诗删》而作,则此书的刊印自不会与此序的写作时间相隔太久。至于其具体年份可以王氏作此序的地点为线索作一推测。序中“走数千里以序属世贞”之语表明,当时王氏身在距新都(今安徽休宁)数千里之遥的某地。考王氏自李攀龙去世至万历五年,有多次在距离新都数千里之遥的地方任职的经历,其中万历三年正月至四年六月间以都察院右佥都御使督抚郧阳(今湖北十堰)[14]241—253,颇疑《古今诗删序》即作于督抚郧阳之次年,此时《唐诗选》已刊印,则凌序所述《唐诗选》在《古今诗删》之前刊印完全可能。再如查屏球指出,凌序既然把《唐诗选》说成是非出李攀龙之手的伪书,又叙其仲叔将此书“授诸梓”之事于“元美观察吾郡”即王世贞为浙江参政之前,而王氏为浙江参政在隆庆三年(1569),李攀龙尚在世,此时“即有署名为李攀龙《唐诗选》印行,这是很难想象的事”[15]。应该承认,这里提到的凌序关于“元美观察吾郡”见到凌濛初仲叔刊印的《唐诗选》的叙述确实是有违史实的。如上所论,《唐诗选》由凌氏盟鸥馆刊印于万历三年,隆庆三年“元美观察吾郡”时自不可能见到。但查氏由凌序此误而以为凌序所述之《唐诗选》由其仲叔“授诸梓”之事应在李攀龙生前,则显然也是未知《唐诗选》确由凌氏盟鸥馆刊印于万历三年的事实。由今观之,凌序关于“元美观察吾郡”时见到凌氏所刊《唐诗选》的叙述当为凌濛初的一时误记,其真实时间可能在万历四年十月王世贞由南京大理寺卿罢归原籍太仓里居[14]254之初,此时《唐诗选》刚由凌氏盟鸥馆刊印一年,太仓与凌氏所居的吴兴不远,王世贞与凌濛初父辈又颇有交往[7]16-17,其行经吴兴见到此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最后需要讨论的王世懋序的问题。此序无疑是凌说可靠性的最大威胁,如果它确实是王氏为《唐诗选》而作,则《唐诗选》为李攀龙所编当可定谳,凌说自无成立之可能。不过若据凌氏《唐诗广选序》中关于《唐诗选》来历的叙述,则王序只可能是为《古今诗删》中唐诗而作,因为李攀龙所编唐诗选本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唐诗选》根本不是李氏所编,那么王序的威胁就完全不存在了。王序有没有可能是为《古今诗删》中的唐诗而作的呢?我以为可能,理由如下:一、王世贞《古今诗删序》中有“令于鳞而轻退古之作者,间有之;于鳞舍格而轻进古之作者,则无是也。以于鳞之毋轻进,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后之操觚者,亦庶乎可矣”等为《古今诗删》“解纷”[16]之语,表明《古今诗删》在付梓之前已在社会上引起不少议论,这与前论森濑寿三说时所引王世懋序中“博艺之士,口其编而心内不然者,不佞能家置喙乎”等语所谈的情况相近,可见二序所序应为同一对象。二、王序中“选至于鳞卷仅七而终”之语表明其所序之书只有7卷,而《古今诗删》中唐诗有13卷,这该如何解释呢?我以为这可以用上文讨论过的《古今诗删》原稿与刊本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来进行解释。据凌说,《古今诗删》的刊印时间在盟鸥馆刊印《唐诗选》之后,而王序见于盟鸥馆本《唐诗选》卷首,显然只能是为《古今诗删》原稿中唐诗而作,《古今诗删》原稿中唐诗本来是7卷,13卷为后来徐中行校订时所分是可能的,凌序中称其所刻《唐诗广选》为其“先君子”从徐中行处“请得其(指《古今诗删》)原抄本”抄出,而《唐诗广选》就只分7卷,可为佐证。三、王序既然是为《古今诗删》中唐诗而作,又如何会被印在盟鸥馆本《唐诗选》前呢?我以为这与同样是为《古今诗删》中唐诗而作的李攀龙序也被印在此本之前的缘故应该类似,凌说可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据凌说,盟鸥馆本《唐诗选》书稿乃“馆客某者”从王世贞携归的李攀龙《古今诗删》原稿中唐诗摘出,则李攀龙序之所以被印在盟鸥馆本《唐诗选》前,应该是因为它见于王世贞家的那份《古今诗删》原稿中唐诗卷首(据其见于《古今诗删》刊本中唐诗卷首推断)而为“馆客某者”抄入了《唐诗选》书稿。王世懋序被印在盟鸥馆本《唐诗选》前的缘故呢?则应该是因为它见于王世贞家的那份《古今诗删》原稿中唐诗卷末而为“馆客某者”抄入了《唐诗选》书稿。怎见得呢?凌序曰:“粤自历下《删》成,元美携其本归吴中。”此为何年之事不易确定,但当李攀龙去世后的隆庆四年(1570)末王世贞回吴中为母守孝[14]202时,此稿必定已在王世贞家了。王世懋为王世贞之弟,自然也要回家守孝,其序当是他在此期间于其兄长家见到此稿中所选唐诗而作。又,此序在《王奉常集》中题为《唐诗选后序》[10]291,可见原是一篇后序,即“刊于卷末的序文”[17],而在盟鸥馆本《唐诗选》上,据前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之此书提要中“前有王世懋序”之语,可知其不仅被刊于卷首,而且题中的“后”字也应被删掉了,颇有违于一般古籍处理后序的惯例(后序若刊于卷首,一般保留这些序题中“后序”之“后”字,使之与卷首之序不相淆乱,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刊《范香溪先生文集》卷首有吴师道《香溪先生文集后序》、三编影印明刊《密庵稿》卷首有谢谠《密庵稿后序》等,皆其例)。何以如此?设想此序原是王世懋随手题于王世贞家那份《古今诗删》原稿中唐诗卷末,并无题目,《唐诗选后序》之题是后来收入《王奉常集》时所拟是合理的,因为依此设想,“馆客某者”在摘抄《古今诗删》原稿中唐诗时见到此序,自然可能会将之当做一般的序言抄录下来,盟鸥馆刻印“馆客某者”抄出的《唐诗选》书稿时不明就里,就会把此序当作前序印在卷首了。
五、结论
综上所论,目前分别为中日学界主流意见的馆臣说和森濑寿三说均非有可靠的史实作为依据,均难以对《唐诗选》的内容作出圆满解释;而学界认为不足信的凌濛初说却史源最为直接,为圆满解释《唐诗选》的内容提供了可能,其所自出之《唐诗广选序》中所述虽有个别细节失实,但大体可信。故在《唐诗选》真伪三说中,应以凌说最近真相:此书应非李攀龙所编,而是王世贞家“馆客某者”从王氏携归的李攀龙《古今诗删》原稿中唐诗摘抄而成的伪书。
[1]李攀龙.唐诗广选[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34册.济南:齐鲁书社,2002:卷首.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蒋寅.旧题李攀龙《唐诗选》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日本接受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J].国学研究辑刊,2003(12).
[4]蒋鹏举.复古与求真:李攀龙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金奎生.明代唐诗选本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6]周子美.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96.
[7]冯保善.凌濛初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8]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80.
[10]王世懋.王奉常集[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7.
[12]许建昆.李攀龙文学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291.
[13]李攀龙.古今诗删[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卷首之语.
[14]郑利华.王世贞年谱[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15]查屏球.李攀龙《唐诗选》评点本考索[G]//章培恒,王靖宇.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9.
[16]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M].罗仲鼎,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345.
[17]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3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