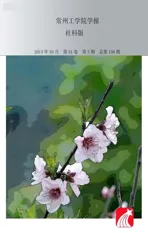精神生态视阈下的《伊甸之东》
2013-04-02张树娟张莹波
张树娟,张莹波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2)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是20世纪美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伊甸之东》是其后期最重要的小说。作者史诗般地描写了两个移民家族从美国南北战争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长达半个世纪三代人的命运交织,展开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对精神的不断探索。作品自问世以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过去的60年中,国内外学者多从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叙事方式、新历史主义等视角研究该作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推动了斯坦贝克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生态学的兴起又为研究这部巨著开辟了新的视角。中国生态学家鲁枢元先生“精神生态学”的提出为解决人类精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是一门研究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1]148然而,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却危机重重。詹姆斯·乔伊斯认为:“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大地、疾病、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却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泪水。”[1]149海德格尔尖锐地指出:新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失所决定的,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2]195。《伊甸之东》揭露了美国社会物欲横流、人的精神出现异化和拜物化的生活现实。文章从精神生态学的审美角度出发,解析《伊甸之东》中特拉斯克家族主要人物的精神生态困境,探究其根源所在,并分析自然人塞缪尔夫妇如何帮助人类找到走出精神困境、重建精神家园的出路。
一、“文明病的受害者”
随着人类对大自然的不断攫取和掠夺,自然被瓜分,土地被掠夺,心灵在分裂,和谐被打破。鲁枢元先生明确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3]20。然而,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却时刻威胁着人的精神性存在,人的精神生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成为了“文明病的受害者”[4]333。在斯坦贝克时代,美国历经了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以及大萧条时期,整个国家经历着深刻而迅速的变化,传统价值观及制度受到挑战,社会的极速发展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人感到困惑。经济危机同时引发了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生态恶化、信仰丢失、道德沦丧、精神空虚和政治的痼疾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疏离。《伊甸之东》中的主要人物如凯西、亚当、赛勒斯等都是“文明病”的直接“受害者”。
《伊甸之东》中,凯西有着天使般的面孔,却是魔鬼的化身。在学生时代,凯西就凭借自己的美色勾引拉丁文教师詹姆斯·格鲁并导致其自杀身亡。她还曾活活烧死亲生父母,新婚之夜与查尔斯通奸,试图枪杀丈夫亚当,抛弃尚在襁褓中的双胞胎幼子,毒死妓院老鸨费叶并霸占其生意。在成功当上妓院老板后,她向妓女们提供毒品,敲诈她们的顾客。她犯下一系列滔天罪行,臭名昭著。“在斯坦贝克的笔下,她是最恶毒和具有毁灭性的女性;在世界文学史上,她大概也是鲜有的魔鬼形象。”[5]152凯西就是一个危害社会、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然而,斯坦贝克没有简单地将凯西归结为善恶二元对立之人,而是通过凯西身边众多的其他人物进一步为读者揭开她邪恶的根源:虚伪无能的父母不关心女儿身心的健康发展,只希望凯西按照他们的愿望维护所谓的淑女形象,当上教师过上体面的生活。凯西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他们以教训代替教育,手段粗暴、残忍;冷酷自私的妓院老板爱德华兹以爱的名义企图用金钱和武力将凯西据为己有,在发现凯西的秘密之后凶相毕露,将其打得奄奄一息,简直就是一个杀人狂;软弱而自欺的亚当无视凯西的真实感受,用想象编织着一个女神;凯西当上妓院老板后,她的主顾有许多政界要员、学术名流,如表面受人尊敬的议员、市政会成员、大学哲学教授,还有传教士。凯西一路走来,深谙人性的虚伪、邪恶并以独特的方式反叛这丑恶的社会,“宁肯做一条狗,也不愿做人”[6]367。她采用极端的形式——性的放肆来反抗社会,颠覆传统的伦理和道德。凯西既不在乎社会对她的态度,也不理会社会的各种规章制度,而是彻底与社会背离。凯西这种自轻自贬的极端言行,只能害人害己,最终自取灭亡。
工业革命的发展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了技术保障和支持,人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于是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无孔不入,征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限膨胀的欲望使人变得无比贪婪。物质发展愈来愈丰富,精神世界则愈来愈空虚。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利益至上的观点盛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人逐渐失去了本真,不再关注内在的自我,在对财富和物质的极度追求中,人的精神世界被污染了。赛勒斯为达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他通过编造历史而从一名列兵混进美国国防部,成功地欺骗了他人并最终得到地位与金钱。当亚当受命到华盛顿国防部部长办公室报到的时候,赛勒斯已俨然是个重权在握的“大人物”,“我可以把你弄进西点军校。我有办法。我可以让你退役,然后进西点军校”[6]57。他玩弄权术,无所不能。“我能操纵联邦退伍军人协会来支持或反对任何候选人。甚至总统都希望知道我对公共事务的看法。我可以击败议员。替人谋差使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可以使人飞黄腾达,也可以把他们整垮。”[6]57赛勒斯平步青云,拥有权力与地位,政治上举足轻重。在当今社会,一旦拥有金钱和权力,人就可以操控一切,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一切。赛勒斯最终靠贪污退伍军人协会的公款非法获得一笔数目非同小可的退休金。美国社会一直强调人人平等,但事实上所谓的平等是缥缈之物。拜金主义腐蚀着人的灵魂,军队、政府充满不正当的勾当,滋生贪污腐败,人成了金钱的奴隶。“万物之灵沦为万物的蛀虫,这不仅是地球的不幸,也是人类的不幸。”[7]203人类的精神家园已轰然倒塌。拜金的赛勒斯就是金钱、物欲的奴隶。流着满身铜臭的冷血赛勒斯虐待两任妻子,视她们为劳作的机器、泄欲的工具,最终逼死了她们年轻的生命。
在金钱面前,原本善良而老实的人也会迷失方向。由于赛勒斯偏爱亚当,他专横地送生性柔弱的亚当去当兵,参加美国开拓疆界、屠杀印第安人的战争。完全出乎赛勒斯意料的是,军队生涯没有给亚当带来成功,却给他带来无尽的痛苦。战争扭曲了亚当的灵魂,改变了他的命运。退役后亚当不能适应社会,徘徊在精神世界之外。参军之前,亚当心灵纯洁,充满理想,但退役之后他变得现实、自私。“爸爸刚死不久,觉得高兴也许是不对的,可是你知道,查尔斯,我一辈子从没有觉得这么高兴过。我从没有这么痛快过。”[6]70尽管亚当憎恨自己的父亲,但当他面对父亲留下的大笔来路不明的遗产时,却十分坦然,欣然接受。当寝食难安的查尔斯揭穿父亲的谎言,拒绝动用那笔遗产时,亚当却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坚定固执地享用这笔非法所得的巨款。为了逃避现实和社会的谴责,亚当离开农场远走加利福尼亚,期望用这笔财富来创建理想的“伊甸园”。也就是说,亚当这个“世上少见的一丝不苟的诚实人”[6]661居然靠父亲贪污的钱过了一辈子。这就是亚当,他不怀疑赛勒斯的贪赃枉法,不揭露凯西的真实面目,盲目追求所谓的“伊甸园”,沉迷于物质享受,浑浑噩噩一辈子。对金钱持现实态度的亚当却始终不能面对凯西这个现实,导致悲剧反复重演。凯西冷酷的一枪不仅打碎了亚当的肩胛,同时把他的精神世界击得粉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伤痛中而不能自拔的亚当,对双胞胎儿子的忽视竟长达十多年之久。亚当对物质享受的盲目追求摧毁了他的精神,改变了他的性格。他不能保持心灵的平衡,以致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尽管在塞缪尔和老李的帮助下,他重新回到现实,却直接造成该隐与亚伯的悲剧在人间再次上演。他对长得像凯西的阿伦偏爱有加,但却无视迦尔对自己的爱。亚当对阿伦的偏爱终使迦尔在善与恶的较量中惨败,导致迦尔人性的毁灭和阿伦的自戕。
二、精神家园的创建
当亚当一家陷于重重困境,生活在阴霾之中不能自拔时,斯坦贝克引进了汉密尔顿家族——自然人塞缪尔·汉密尔顿。塞缪尔尊重自然,用勤劳的双手改造自然,顺从内心的召唤,追求真我,创建美好精神家园。因此,他能够一直保持高贵的品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拒绝异化,不受物质的利诱。和睦幸福的家庭无疑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发展。汉密尔顿一家所发出的正义和谐之光同时也照亮了特拉斯克一家失衡的精神世界,最终帮助特拉斯克家族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生活轨道。
塞缪尔·汉密尔顿和他的妻子来自北爱尔兰,在萨利纳斯河谷寻找新生活,但他们的移民生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艰辛。“塞缪尔和莉莎来到萨利纳斯河谷时……还剩有一些边缘的土地可以耕种,塞缪尔·汉密尔顿便在如今叫做金城的小镇东面贫瘠的丘陵地安家落了户。”[6]11尽管土地贫瘠干燥,没有水源,塞缪尔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坦然接受事实,艰难困苦中依然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聪明且有效地改造自然。凭着一双巧手,他发明钻井机、脱粒机,建起铁工房,修理和改善工具,打井取水,收割庄稼。他性格开朗、幽默风趣、乐善好施,从不抱怨生活中的不幸,而是通过自己的勤劳与智慧把贫瘠的土地变成可耕地,靠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好生活,好口碑。他是农民、铁匠、木匠、机械师、发明家、哲学家和自学成才的医生,接生、看病样样在行。
塞缪尔和妻子莉莎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相濡以沫。莉莎拥有令人佩服的智慧,开拓者的勤劳勇敢,战胜邪恶的正义力量,是家庭的守护神。美国学者桑德拉·比蒂(Sandra Beatty)指出:“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妻子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她们具有坚不可摧的性格力量,这种力量一经展现,就凝聚住身边所有人的力量。她们的丈夫很快认可她们的这种力量,特别当他们在犹豫和懦弱的时候。《伊甸之东》中的莉莎·汉密尔顿就是典型的代表。”[8]2相比之下,莉莎更能洞察人性的复杂和深奥。当塞缪尔帮卡西接生时,他感觉到一种不祥之兆,坚持要求莉莎来到他身边:“我要我的妻子来……如果莉莎说是有鬼,那就真的有鬼,不是幻觉。如果莉莎觉得有问题,咱们赶紧把门闩上。”[6]222莉莎平凡而又伟大,她使全家充满了力量,她能够使全家在贫瘠的土地上得以幸存,“真像是个奇迹”[6]47。她有坚定的精神追求。她信仰上帝,期待天国,每天晚上必读《圣经》,她认为所做的每件事只不过是为通向天国而铺路。她一辈子含辛茹苦,从不怨天尤人。她一共生了四男五女九个孩子,抚养教育,孩子们个个规矩正派。她品德高尚,育儿有方,受到左邻右舍的尊敬。她脚踏实地,坚若磐石,铁一般的意志使她从不向任何困难妥协。即使对待死亡莉莎也十分泰然,在塞缪尔去世后,她坚强地撑起整个家庭。提起母亲,儿子威尔颇为自豪:“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像岩石一般坚强。我想起我们以前艰苦的日子,真是一言难尽……我认为全靠我母亲才撑起我们汉密尔顿这个家,没有落到去济贫院的地步。”[6]373
塞缪尔和莉莎一生追求真我,抵制物欲的利诱,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真实的自我,凭借智慧、勤劳和实干的精神在西部开拓进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他们的物质生活极其简朴但精神世界极其丰富。在塞缪尔和莉莎面前人类中心主义不攻自破,物质膨胀和人性异化自然消失,人处在其本真状态。
塞缪尔崇尚自然,尊重自然,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他驱恶扬善,邪恶的凯西害怕他,“他看透了我——看透了我的心思”[6]364。他身上的正义之光点燃了亚当的阴暗世界,老李承认塞缪尔的不朽。亚当一度沉浸在被凯西抛弃的伤痛中不能自拔,对刚出生就被凯西抛弃的双胞胎儿子不闻不问,十五个月后仍未给他们起名字。塞缪尔愤怒了,主动担当亚当的精神向导,当头棒喝亚当的责任所在,一拳打醒如同行尸走肉的亚当。在给孩子起名字之时,塞缪尔、亚当和老李第一次坐在一起解读《圣经》中亚伯和该隐的故事:罪恶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爱的缺失是引起罪恶的根源,即使是上帝,也有所偏爱。亚当开始正视凯西的恶,逐渐走出伤痛。塞缪尔准备离开农场去萨利纳斯之前,最后拜访了亚当和老李,三人再一次郑重解读《圣经》,赋予了“timshel”新的内涵。“timshel”的意思不是“thou shalt”而是“thou mayest”,即“你可以”之义。“是希伯来文中的‘提姆谢尔’——也就是‘你可以’——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人之所以能成为人,就在于他有选择的权利。”[6]345人被赋予选择善而非恶、选择爱而非恨的能力并且能够不断自我完善。“你可以”给了亚当父子选择的权利,为迷失的心灵指明了方向。当得知凯西(后更名为凯特)重操妓女旧业,他作出选择,拒绝凯西的诱惑,彻底摆脱其精神的枷锁,最终重获心灵的自由。迦尔寻找生母,正面接触了凯西之后,轻而易举地看穿了凯西恶的本质,解开了自己的心结。“本来我担心我有你的种气……不,我没有。我是我自己。我不会像你的。”[6]526迦尔作出了选择,不做凯西,做回自我。可是,因为妒忌父亲对阿伦的偏爱,迦尔向弟弟阿伦泄漏凯西经营妓院的秘密,导致阿伦谎报军龄入伍而战死沙场。迦尔把父亲的中风和阿伦的死归咎于自己的恶,终日惶惶不安。在临终前,亚当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蒂姆舍尔”,爱战胜了恶,帮助迦尔获得重生,人性得以回归。
三、结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何重建一种新型的和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现代文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许多有识之士苦苦思索的命题。人类如何走出生态困境,实现理性的回归也是众多哲学家、文学家们关注的焦点。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9]579斯坦贝克通过对自然人汉密尔顿家族正面、光明形象的塑造及其自我本真的精神追求的赞美,表达了作者为人类走出精神困境所做的尝试。这一尝试无疑也为人类创建精神家园指明了一条出路。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2](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M].李耶波,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5]陈俊松.论约翰·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女性世界[J].世界文学评论,2010(1):150-154.
[6](美)约翰·斯坦贝克.伊甸之东[M].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鲁枢元.精神守望[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8]Beatty Sandra.A Study of Female Characterization in Steinbeck′s Fiction[M]//Hayashi Tetsumaro.Steinbeck′s Women:Essays in Criticism.Muncie,Indiana:Ball State University,197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