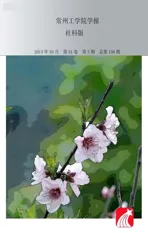论梁元帝的政治悲剧
2013-04-02陈蒲清
陈蒲清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梁元帝(508—555),姓萧,名绎,字世诚,小字七符。他是南北朝萧梁王朝的第三个皇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个儿子。“元”是他的谥号,“世祖”是他的庙号。
梁元帝萧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为特殊的皇帝。他是皇帝兼学者、文艺家。作为学者、文艺家,萧绎是成功的。他热衷学术,著作等身,有颇高的学术造诣。他富有才华,倾心于文学、艺术,无论诗、赋、骈文、寓言,还是绘画,都颇有成就。但是,作为皇帝,萧绎是悲剧人物。他虽然平定了侯景叛乱,中兴梁朝,但是只坐了两年皇帝位,梁朝就被西魏灭亡。如何评价梁元帝萧绎的政治悲剧呢?
一、千秋功罪,评说纷纭
古代历史学家对于萧绎的政治评价可以分为三派:南派,北派,中派。
南派是生活在南朝的史学家,他们倾向于褒扬与同情。何之元在陈朝编撰《梁典》,评价萧绎说:“至于帏筹将略,朝野所推。遂乃拨乱反正,夷凶殄逆。纽地维之已绝,扶天柱之将倾。黔首蒙拯溺之恩,苍生荷仁寿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引)《梁典》肯定了萧绎复兴梁朝、拨乱反正的功绩,甚至用孔子赞扬管仲的话来赞扬萧绎。当然,《梁典》对萧绎的高度评价,跟陈朝开国之君陈霸先的评价有关。陈霸先评价萧绎说:“武皇帝虽磐石之宗,远布四海,至于克雪仇耻,宁济艰难,唯孝元而已。功业茂盛,前代未闻。”梁武帝虽然儿孙众多,而且各自拥有地盘与军事力量,但是,最后平定侯景之乱而恢复梁朝政权的人就是萧绎。陈霸先对萧绎的评价这么高,虽然不排除政治目的,但主要还是根据事实。
北派是出生在北方的史学家。南北朝时代以北方政权征服南方而终结,隋朝、唐朝都是北方政权的继承者,故北方史学家对南朝政治往往贬斥。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令史臣补修前朝五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北周)书》《隋书》。唐太宗任命魏征担任修史的总监,各史官分工编写。贞观十年,这五本史书修成。贞观十五年,又命令李延寿等撰写这五个朝代的史志,历时15年完成。后来,李延寿为了更系统地记述南朝与北朝的历史,避免支离破碎与矛盾,就私自撰写《南史》与《北史》,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
唐太宗本来就否定梁朝的君主,魏征、李延寿又都是出生在北方的史学家,所以他们对萧绎取否定态度。李延寿贬斥萧绎说:“元帝居势胜之地,启中兴之业,既雪仇耻,且应天人。而内积猜忍,外崇矫饰。攀号之节,忍酷于逾年;定省之制,申情于木偶。竟而雍州引寇,衅起河东之戮;益部亲寻,事习邵陵之窘。悖辞屈于僧辩,残虐极于圆正,不义不昵,若斯之盛。而复谋无经远,心劳志大,近舍宗国,远迫强邻,外弛藩篱,内崇讲肆。卒于溘至戕陨,方追始皇之迹;虽复文籍满腹,何救社庙之墟?”(《南史·梁本纪下》)他接着引用了魏征对萧绎的非常激烈的批评:“昔国步初屯,兵缠魏阙,群后释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盘石之宗,受分陕之任,属君亲之难,居连率之长,不能抚剑尝胆,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驱;遂乃拥众逡巡,内怀觖望,坐观时变,以为身幸。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又沉猜忌酷,多行无礼。骋智辩以饰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将,心腹谋臣,或顾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菹醢,朝之君子,相顾凛然。自谓安若泰山,举无遗策,怵于邪说,即安荆楚。虽元恶克翦,社稷未宁,而西邻责言,祸败旋及。上天降鉴,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诬乎!其笃志艺文,采浮淫而弃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后寇仇。虽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李延寿撰写《南史》与《北史》,本来就跟魏征有瓜葛,他又赞成魏征对萧绎的批评,那么,自然要引用魏征对元帝的评论了。
中派是能够折中南北的史学家。贞观五史中的《梁书》与《陈书》,是由姚思廉撰写的。姚思廉的父亲姚察,本来是梁、陈两朝的旧臣,在隋朝继续担任史官,他完成了《梁书》与《陈书》大多数篇章的撰写。姚思廉子承父业,完成了《梁书》与《陈书》。《梁书·元帝纪》评论萧绎说:“史臣曰:梁季之祸,巨寇凭垒。世祖时位长连率,有全楚之资,应身率群后,枕戈先路。虚张外援,事异勤王;在于行师,曾非百舍。后方歼夷大憝,用宁宗社,握图南面,光启中兴,亦世祖雄才英略、绍兹宝运者也。而禀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无术,履冰弗惧,故凤阙伺晨之功,火无内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达,留情政道,不怵邪说,徙跸金陵,左邻强寇将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祸,荡覆斯生,悲夫!”姚思廉撰写《梁书》与《陈书》时,魏征担任修史的总监,所以,姚思廉虽然观点跟魏征有差异,但是不能忽略唐太宗的意见与魏征的评论。姚思廉只好在《梁书·敬帝纪》中跟李延寿一样引用了魏征对萧绎的评论。但是,姚思廉不在《梁书·元帝纪》中引用魏征对萧绎的评论,正是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
三派的评论,各有道理。南派的《梁典》,对萧绎只有赞扬,当然不全面。北派的《南史》与魏征的批评,为了突出历史的鉴戒作用,连萧绎平定侯景、复兴梁朝的功劳也抹杀了,更是偏颇的。代表中派的《梁书》对萧绎有褒有贬,既能肯定他平定侯景、复兴梁朝的功劳,又能批评他导致亡国的错误举措,是比较公正、公允的。以上三派的批评,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过于看重萧绎的个人素质,而没有看到造成萧绎悲剧的终极因素是封建体制的弊端。
二、平定叛乱,功不可没
《梁典》与《梁书》都肯定萧绎平定侯景、复兴梁朝的功劳。这是实事求是的。
萧绎年幼时就被封为湘东王。太清元年(547年),担任荆州刺史,驻守江陵,并且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还有“使持节”“镇西将军”的官衔。荆州刺史的地位非常重要。东晋和南朝的疆域,主要在长江中下流。长江下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长江中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江陵。所以,担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实际上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命脉,几乎可跟朝廷分庭抗礼。
萧绎身处重位,不贪图声色,而是喜欢读书、藏书、著书。他聚集到江陵城的图书达到15万卷以上;自己写了接近700卷著作。南北朝时代的藩王,大多数骄奢淫逸,无法无天。萧绎作为当时的一个藩王,是超脱时俗的。但是,他的作为,仅能适应不由自己担当国家安危的太平时代,不能适应需要自己担当国家安危的战乱时代。不幸的是,战乱降临了,而且必须他自己担当国家的安危。这是萧绎文弱的肩膀所不堪负担的。
萧绎担任荆州刺史的第二年,即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发生了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那就是侯景之乱。原来,梁武帝萧衍晚年沉溺佛教而荒废政事,又法纪松弛而政治混乱。太清元年(547年),东魏叛将侯景致信梁武帝,说他愿意依附梁朝,献上黄河以南十三州的全部土地。萧衍贪图土地,不惜破坏跟东魏的关系,接受侯景,封他为大将军、“河南王”,并运送大批粮食接应他。侯景却暗中跟萧衍的侄儿萧正德勾结,准备叛乱。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起兵叛乱。当年十月,侯景兵临长江,萧正德秘密派遣几十艘大船接应侯景的军队从采石渡(今安徽马鞍山)渡过长江,侯景攻入首都建康。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攻陷内城——台城,幽禁梁武帝。五月,梁武帝忧愤而死。梁武帝虽然子孙众多,但是,或死,或败,或另有野心,于是,平定侯景、中兴梁朝的重任落到了梁元帝身上。
据《南史·元帝诸子》记载,萧绎派长子萧方等去朝见梁武帝,正碰上侯景攻入建康,萧方等不肯退缩,萧绎就调集一万军队,要萧方等率领支援台城。萧方等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直到台城沦陷,才回荆州。又,《梁书·王僧辩传》记载,萧绎派遣他的主要将领王僧辩率领一万军队乘船东下,准备驱逐侯景。可惜,王僧辩率领军队到达京城,梁武帝已经跟侯景议和,并被侯景所控制。王僧辩只能先见侯景,再见梁武帝,然后脱身返回江陵。此后,因为侯景控制了梁武帝、简文帝,萧绎也不便采取行动。这时,梁朝的王侯官吏,纷纷到江陵依靠萧绎。如:江夏王萧大款,山阳王萧大成,宜都王萧大封,他们都是简文帝的儿子;还有郢州刺史南平王萧恪,等等。
太清三年(549年)四月,梁武帝秘密派太子舍人、上甲侯萧韶到达江陵,萧韶宣布梁武帝于三月十五日写的密诏,任命萧绎为侍中、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假黄钺”,就是可以代表皇帝的权力。“承制”,就是秉承皇帝的权力而代理皇帝行事。于是,萧绎准备东征,“令所督诸州并发兵赴都”(《北史·僭伪附庸·萧詧》)。
大宝二年(551年)十月,侯景杀死简文帝萧纲,萧绎也清除了后顾之忧。于是,萧绎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侯景,也可以集中兵力讨伐侯景。大宝三年(552年)二月,萧绎亲自写了《讨侯景檄》。这篇檄文,篇幅宏大,气势充沛,颇多警句。如历数侯景罪恶之后,总括说:“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书其罪。”他命令王僧辩率领大军从浔阳出发东下,陈霸先率领三万甲士担任先锋。不久,王僧辩、陈霸先会师白茅湾(今江西九江北)。三月,攻下军事重镇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再合围建康城。王僧辩击溃守军,侯景逃跑到吴郡(今苏州)。萧绎命王僧辩率领百官祭奠萧纲,追谥萧纲为简文帝,庙号太宗。四月,侯景在松江战败,只剩下三只兵船,想下海逃跑。羊鹍(名将羊侃之子)乘机杀死侯景,把尸首送到建康。王僧辩曝侯景之尸示众,又传首江陵。萧绎封羊鹍为明威将军、昌国县公。
侯景叛乱,到处杀戮掠夺,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严重破坏了江南经济。平定侯景之乱,萧绎起了中坚作用,这是他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劳。
三、身死国灭,因素复杂
在平定侯景叛乱,并战胜萧纪、陆纳以后,萧绎于太清六年十一月,在江陵即皇帝位,改元“承圣”元年。但是,他即皇帝位还不到两周年,灾难就降临了。
承圣三年(554年)九月,西魏派遣大将于谨、宇文护、杨忠(他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等率领五万大军南下。十一月初,包围江陵。西魏军队先占据东方的渡口,拦阻梁朝的各路援军,然后用精锐部队攻城。萧绎命令胡僧佑等分工守卫,自己也巡行都栅。二十九日,魏军猛烈攻城,萧绎出枇杷门,亲自临阵督战。战斗中,主将胡僧佑中流矢牺牲,梁军溃败。反叛者杀死西门的守卒,引西魏军队进入城内,江陵城被西魏攻陷。萧绎派太子萧元良与王褒做人质,向西魏求降。然后,自己乘白马、穿白衣走出东门。他抽剑击城门说:“我萧世诚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啊!”这场战争,总共持续了28天。
萧绎投降后,被萧詧押往军营。萧詧对他进行数落、侮辱。当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公元555年1月27日,萧绎被押向刑场。行刑者用土囊压死萧绎。萧绎的太子萧元良、小儿子萧方略,同时被萧詧杀害。
造成萧绎悲剧的主要因素是当时的客观形势。西魏、北齐、梁三国鼎立,西魏最强大,梁最弱。萧绎即位时,梁朝已经非常衰败,版图大大缩小。河南、苏北、淮南都被北齐占据,汉中、蜀地、鄂西北被西魏占据,岭南地区又被萧勃(梁武帝的堂侄)所割据。萧绎能够管辖的范围只限于长江沿岸,西起江陵,东至建康。江陵处在西魏的威胁之下,危如累卵。正如《南史·梁本纪下》所说的:“自侯景之乱,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缘以长江为界。荆州北界武宁,西拒峡口,自岭以南复为萧勃所据。文轨所同,千里而近,人户著籍,不盈三万。中兴之盛,尽于是矣。”萧绎,没有能力改变北强南弱的客观形势,无力阻挡西魏宇文集团统一中国的步伐。
然而,北强南弱的客观形势是如何造成的呢?主要原因是南方政权比北方政权背负着更加沉重的封建体制的包袱,皇族争权夺利,自相残杀。
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深刻分析了封建君主制度的危害,他说:“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每个封建帝王取得天下后,都把天下当成自己的私人产业,大封亲族为王侯。梁武帝也不例外。《南史》的《梁宗室上》《梁宗室下》《梁武帝诸子》《梁简文帝诸子》等记载,梁朝有近四十个王,侯就更多了。这些王侯包括梁武帝的兄弟、堂兄弟、儿子,以及他们的后代。
众多的封建侯王往往是酿造祸乱的根源。这是因为:第一,他们不劳而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第二,他们占据高位,机构臃肿,使真正的人才不能脱颖而出,在危难时刻国家无人可用;而他们自己则养尊处优,完全丧失能力,“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战乱中只好任人宰割。第三,王侯多,既享受特权,又不受法律的制约,往往胡作非为,而且培养了各自的攫取更大权力的欲望,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失控,他们就会起来争夺帝位,酿造祸乱,互相屠杀,这是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即使是统一而强大的秦王朝、汉王朝、唐王朝、明王朝,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在中央政权不稳定的两晋南北朝时代,这种现象更加突出。西晋灭亡的内因,就是“八王之乱”;东晋走向衰败,内因是晋孝武帝兄弟间的勾心斗角;刘宋王朝,宋明帝残杀皇族,屠杀他的兄弟辈与侄儿辈,宋武帝刘裕的儿孙们几乎被杀尽;萧齐王朝,齐明帝与东昏侯,疯狂杀戮皇族与大臣,终于走向灭亡。梁武帝想吸取前代的教训,为了防止骨肉互相残杀,对皇族采取宽容的政策。例如:他封六弟萧宏为临川王,后来发现萧宏贪污,反而更加信任;萧宏的儿子萧正德叛国逃奔东魏,不得志而回来后,萧衍竟然原谅他的过错,还重用他。梁武帝的这种政策,不仅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反而诱发了诸王侯争夺国家大权的野心。儿子萧综、侄儿萧正德的叛国,儿子萧纶、萧纪、萧誉、萧詧、萧绎因为争夺帝位而相互残杀,终于导致梁朝灭亡。所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分析侯景之乱说:“这次大祸乱归根是士族制度自然的结果。”钱穆《国史大纲》说:“宗室强藩,亦不能忠心翊戴,转促骨肉屠裂之祸。”
萧绎亡国,当然有主观因素,包括政治失误与个人素质。
萧绎作为一个君主,他个人的主要政治失误是:不识时务。这突出表现在重文轻武、定都江陵与缺乏外交经验上。
萧绎即皇帝位之后,就以为天下太平,对严峻的形势完全没有警惕。他偃武修文,沉溺于学术与文艺,亲近宗懔、黄罗汉、王褒、庾信、徐陵等文士,而疏远军事将领。王僧辩是他必须倚仗的军事大臣,却曾经受到他的侮辱,又不留在京城。谢答仁是一员战将,却被他怀疑。《南史》记载,当西魏大举进攻江陵快要沦陷时,武将朱买臣、谢答仁建议萧绎乘夜晚突围,投奔任约的军营,当时任约率领的援军就驻扎在临近江陵的马头岸。萧绎却拒绝了这个唯一可行的建议。一是因为他自己很文弱,不会骑马奔驰;二是因为轻信王褒的话。王褒说:“谢答仁、任约,原来都是侯景的部下,难道可信吗?不如投降。”萧绎轻信王褒而投降,终于遭受可悲的结局,谢答仁也壮烈殉国。萧绎在投降前,反思自己读书万卷,仍然免不了亡国,烧毁聚集到江陵城中的图书,这大概是悔恨自己重文轻武吧。可惜,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图书,反而造成一场文化浩劫;也可惜,他觉悟自己重文轻武太晚了。
《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当萧绎称帝时,曾经发生定都的争议。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定都建康,宗懔、黄罗汉、王褒等却反对从江陵迁都建康,认为建康已经残破,而且“王气已尽”。宗懔、黄罗汉、王褒等都是楚地人,所以反对迁都到吴地。萧绎自己则缺乏对西魏的警惕,又贪恋江陵的繁华,不愿意迁到已经残破的建康,决定定都于江陵。等到西魏包围江陵,萧绎才省悟。朱买臣等请求说:“只有斩宗懔、黄罗汉,才可以谢天下。”萧绎说:“当时是我的意见,不能怪宗懔、黄罗汉。”宗懔、王褒等都是萧绎信任的文士,他们在萧绎被害后都被西魏俘虏,后来做了北周的臣子。如果萧绎不定都江陵,不把首都直接暴露在西魏的威胁之下,而是迁都到建康,就不会迅速被西魏灭亡。
萧绎对待西魏,最缺乏外交经验,既轻信,又没有谋略。萧绎对西魏屈服,却幻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西魏灭萧绎的导火线,是萧绎得罪了西魏的当权者。他对西魏的使臣不卑躬屈膝,还希望西魏归还部分领土。柏杨《中国历史年表》说:“孝元帝萧绎致书西魏太师宇文泰,请依旧图定疆界,词颇不逊。宇文泰笑曰:‘天之所废,谁能兴之?’遣柱国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军击南梁,径围江陵,百道攻城。”萧绎不加强国家的力量,对西魏抱有幻想,缺乏外交谋略,也是亡国的重要因素。
萧绎的个人素质,也是有明显缺陷的。例如,他过于自信,性格暴躁,多疑猜忌。正如魏征所批评的那样:“沉猜忌酷,多行无礼。骋智辩以饰非,肆忿戾以害物。”《南史·梁本纪下》还举了两件例证:“悖辞屈于僧辩,残虐极于圆正。”
《梁书·王僧辩传》记载,王僧辩是萧绎最主要的将领。当河东王萧誉不服从征调军队的命令时,萧绎的长子萧方等讨伐失败而牺牲,萧绎急于派王僧辩领兵讨伐萧誉,王僧辩却反对马上出兵。因为,他认为必须等待自己先从竟陵调集一万精兵,否则不足以取胜。萧绎疑心王僧辩是故意拖延,召见王僧辩说:“卿何日当发?”王僧辩说出自己的意见,萧绎大怒,马上逮捕王僧辩。萧绎对王僧辩说:“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贼,今唯有死耳。”王僧辩说:“僧辩食禄既深,攸责实重,今日就戮,岂敢怀恨?但恨不见老母。”萧绎竟然拔剑砍伤王僧辩的左大腿,王僧辩大量出血而晕死,连王僧辩的儿子、侄子也被逮捕入狱。这时,萧誉的军队前来攻打江陵,萧绎不知所措,只好派人到狱中向王僧辩询问计谋,释放出王僧辩,任命他担任城内都督。对待王僧辩的态度,充分反映出萧绎的确性格暴躁,多疑猜忌。
又,《南史·梁武帝诸子传》记载,萧圆正是萧纪的第二个儿子,他在江陵任职(江安侯、散骑常侍),并不赞成萧纪发动对萧绎的战争。萧纪在长子萧圆照的怂恿下,率领巴蜀大军东下,企图占领江陵,于是萧圆正被萧绎逮捕入狱。他在狱中看到萧绎写的《回首望荆门》诗,就写诗说:“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萧绎看了圆正的诗,也感动流泪,却没有从轻处理圆正,而是希望圆正自杀。萧纪大军失败后,萧圆照也被捕入狱,萧圆正见到哥哥圆照,感叹说:“阿兄!何乃乱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圆照悔恨自己的失误。萧圆正是无罪的,但是,萧绎始终不放过萧圆正,而是命令萧圆正与萧圆照在狱中绝食,过了十三天,活活饿死。萧绎不放过萧圆正,虽然根源于株连无辜者的封建法律,但是也反映出萧绎的残虐,不能宽容。
四、具体批评,值得商榷
史学家们的某些具体批评,是值得商榷的。
魏征批评萧绎说:“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后寇仇”。这种批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值得商榷。第一,据《梁书》《南史》的元帝诸子传的记载,在侯景攻入建康后,萧绎就调集一万军队,要长子萧方等率领守卫台城;又据《梁书·王僧辩传》记载,萧绎为了驱逐侯景,接着又派遣他的主要将领王僧辩率领一万军队乘船东下。可惜,王僧辩率领军队到达京城,梁武帝已经跟侯景议和,并被侯景所控制,萧绎也不便采取行动。等到梁武帝一死、简文帝被杀,萧绎就大举进军,似乎不能说“不急莽、卓之诛”。第二,因为争夺帝位而相互残杀,主要责任还不在萧绎这一方,而在他哥哥萧纶、弟弟萧纪及侄儿萧誉、萧詧的一方。我们已经在前文叙述了这些事件。我们再看一段具体情节。《南史·梁武帝诸子传》记载,当萧纪率领巴蜀大军东下企图占领江陵时,萧绎还写信规劝萧纪,让他平安返回蜀地,永远镇守。萧纪不听劝告,被打败以后,萧绎又写信说:“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平难之功。膺此乐推,事归当璧。倘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上林静拱,闻四鸟之哀鸣;宣室披图,嗟万始之长逝。心乎爱矣,书不尽言。”并且写诗抒情:“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我们还可以把萧绎跟萧詧对比。萧绎没有主动进攻萧詧,而是萧詧配合西魏进攻江陵,侮辱、处死萧绎以及萧绎的子孙。对比一下,就可看出萧绎对待皇族中的对手,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个人还猜测,魏征的批评还有可能是有感于唐太宗兄弟间的相互残杀而发。
萧绎跟萧纶、萧纪相比,也不是急于做皇帝的人。《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占建康后,就有手下大臣请求萧绎“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主盟”,萧绎坚决拒绝说:“议者可斩。”四月,萧韶到江陵宣布梁武帝于三月十五日写的密诏后,萧绎才担任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主盟。《梁书·元帝纪》反复记载了萧绎推辞的过程。太清四年(大宝元年)十一月梁武帝逝世后,南平王萧恪及萧大款、萧大成、萧大封、萧圆正等亲王们就上表劝萧绎即皇帝位,被萧绎拒绝。太清五年(大宝二年)侯景杀死简文帝以后,亲王、大臣们又在十月与十一月两次上表劝萧绎即皇帝位,萧绎回答说:“大耻未雪,何以应龙图?”四方官吏纷纷上表,萧绎干脆下了一道晓谕四方的命令:“四岳频遣劝进,九棘比者表闻。谯沛未复,茔陵永远。于居于处,寤寐疚怀;何心何颜,抚兹归运?自今表奏,所由并断。若有启疏,可写此令施行。”可见他是坚决拒绝的。太清六年平定侯景叛乱后,王公、大臣们于三月上表劝萧绎马上即皇帝位,仍然被萧绎拒绝。四月,萧纪已经在成都宣布即皇帝位,王公、大臣们于五月上表劝进,还是被萧绎拒绝。八月,萧纪率领军队东下,徐陵上表规劝,言辞特别恳切,其中有句云:“伏愿陛下因百姓之心,拯万邦之命。岂可逡巡固让,方求石户之农;髙谢君临,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见圣人之不仁。率土翘翘,苍生何望!”接着,王公、大臣们又三次上表劝进,萧绎才在十一月即皇帝位。而且,他仍然坚持“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但是,如果全面考察萧绎的言行,他似乎不是一个腐化的君主,也不是一个残暴的君主。萧绎不腐化,是史学家们一致肯定而没有异议的,《梁书》《南史》都说他“不好声色”。萧绎是否是残暴的君主呢?否。且举几个实例。(1)侯景控制梁武帝、简文帝以后,梁朝的王侯官吏,包括简文帝的儿子萧大款、萧大成、萧大封等,他们纷纷到江陵依靠萧绎。萧绎都接纳安排,甚至委以重任。(2)除了在战争中消灭对手,除了王僧辩、萧圆正事件,萧绎似乎并没有迫害其他大臣,而且,他认识到自己对待王僧辩的错误后,一直重用王僧辩。(3)他关心农业。大宝三年正月发表《课耕令》;十一月即位后,次年三月又马上发布《蠲免力田诏》,关怀下层民众。(4)大宝三年五月,侯景传首江陵,萧绎下令斩侯景之左仆射王伟、少卿周石珍等四人于江陵,接着就发表《赦余党令》,赦免其他被侯景裹胁的人。这一切,说明他不是暴君。所以,魏征批评萧绎“爪牙重将,心腹谋臣,或顾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菹醢,朝之君子,相顾凛然”,似乎太过分了。
我们还要看到,萧绎对于自己曾经有所反省。他在《金楼子·自序篇》中说:“余不闲什一,憎人治生,性乃隘急。刑狱决罪,多从厚降;大辟之时,必有不忍之色。多所捶朴,左右之间耳。刘之亨尝语余曰:‘君王明断不凡,此皆大宽小急也。’”他还在《金楼子·立言篇上》中说:“性颇尚仁,每宏解网,重囚将死,或许伉俪自看,城楼夜寒,必绨袍之赐。……但性颇狷急,或有不堪,不欲蕴蓄胸襟,须令豁然无滞。”这种个性,是不适宜担任封建君主的,特别不适宜在乱世担任封建君主。他还说,自己特别憎恨叛变者、不服从命令者、违法者,规定“叛者死”“不附者死”“违令者抵罪”。这也大概是发生王僧辩、圆正事件的原因。
魏征又批说:“虽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萧绎热衷甚至沉溺于学术与文艺,作为一个帝王,特别是作为一个身处乱世的帝王,当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造成亡国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赞成因此而否定他的艺术成就,更不能因此否定他的人格。
李延寿贬斥萧绎:“外崇矫饰”,“攀号之节,忍酷于逾年;定省之制,申情于木偶”。萧绎的确有矫饰的毛病。其实,许多封建君主,包括有作为的君主,都有矫饰的毛病。因此,我们对萧绎不能责备求全,更不能深文罗织。梁武帝去世后,侯景把持政权,又立萧纲为帝,所以,萧绎既不能马上兴兵,又不能跑到建康吊祭。这是客观形势使然,不能说是忍酷于逾年。他母亲去世时,政治局势安定,他为什么不能刻木像而虔诚侍奉呢?如果连他为去世的母亲刻木像而虔诚侍奉,也认为是矫饰,那就太过分了。
总之,我们认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成败定人品,因此应该全面评价萧绎,既要批评他导致亡国的错误,也要肯定他平定侯景之乱的功劳。造成萧绎悲剧的客观形势是“北强南弱”,而终极因素是封建体制的根本弊端。在南朝的君主中,梁元帝萧绎,是不可以跟宋孝武帝、宋明帝、苍梧王、齐明帝、东昏侯、陈后主之流受到同样谴责的。他的亡国,主要是侯景之乱以后“北强南弱”的客观形势造成的,是封建体制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