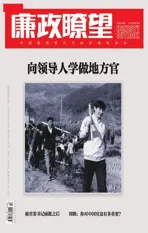苏共亡党与既得利益群体
2013-03-17李永忠董瑛
文_李永忠 董瑛
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和从上到下层层任免干部的等级授职制的强力控制之下,前苏联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群体。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在苏共亡党中扮演着各种角色。
既得利益群体出现与固化
前苏联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于斯大林时代,到赫鲁晓夫时代有短暂的改革和遏制,勃列日涅夫时代则继续集成和固化。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时,苏共已到了“极度萧条衰退时期”,党和国家开始显露出“苏联之灾厄”。
斯大林是苏共既得利益群体的肇始者,打造了既得利益阶层。
斯大林借助“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的“高效”,一方面进行残酷的大清洗,排除不同政见者;另一方面建立高度等级化、稳定化、优厚化的特权制,拉拢和集聚现有体制的“守夜人”和崇拜者,形成“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
勃列日涅夫是苏共既得利益群体的集成者,固化了各种既得利益群体。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党内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滋生蔓延,成为苏共走向衰亡的起点和执政红利盈亏的临界点。为了消除“他将被更有才华、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代替”的担忧,他果断停止了赫鲁晓夫推行的改革,恢复、延续斯大林模式,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第聂伯罗帮”,以及党政、军警、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各种利益集团。
此时,前苏联党政机关急剧膨胀,全联盟和联盟共和国部门从1965 年的29个增加到80 年代前期的160 个,前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64 个部和20 多个国家委员会及直属机构的正副部长级领导干部达到800 多人。
戈尔巴乔夫是苏共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者,又是新的既得利益群体的肇始者。
戈尔巴乔夫曾担任过“疗养院书记”,在国家处于深重的危机时,临危受命。他先着手经济体制改革,但立马遭到了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此时,他意识到以陈旧腐败的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为核心标志的政治体制及其衍生和庇护的既得利益群体是制约苏联改革发展的“阻碍机制”。1986 年1 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作了《关于改革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表示“如果不改变现行干部政策,我将辞职”。他转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仍遭到了旧体制旧模式所累积的强大阻碍。
戈尔巴乔夫终于明白了: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是他面临的现实难题。与其等死,不如九死中觅得一生。于是,他在二难悖理中选择了改革。但是,维稳抑变长达18 年的勃列日涅夫,既未给他提供经改特区,也未给他留下政改特区,更要命迫在眉睫的改革,既没有可资借鉴的试点空间,更没有起码的回旋时间!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只好转向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但是,由于没有通过党内的改革,先把党建设好;没有通过党内的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领导苏联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日益衰竭并穷途末路,新的最高权力中心因孤家寡人、势单力薄,加上合法性的先天不足很快被苏联的保守派、改革派和广大群众所抛弃。
既得利益群体扮演的角色
既得利益群体是旧体制的最多受益者和最大守成者。
“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各部门在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就有100 多处,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 万人。同时,他们还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为自己及其亲属子女和身边人员谋取非制度化的特权和利益。如斯大林在两年内将其小儿子瓦西里指定提拔为少将到中将,还指定授予其厨师、食品采购员等不同的勋章与军衔。
据此,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旧体制旧模式最坚定的支持力量和守夜人,它们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主政者达成默契和共识:保持“稳定”,停止改革,阻碍改革,禁止改革。从上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取消了改革,甚至禁止使用“改革”一词。
既得利益群体是旧模式的最大改革阻碍和最先背叛者。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内困外忧,还面临着改革发展的“阻碍机制”,即“在斯大林体制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觉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顽固的、一时难以克服的机制。”
叶利钦敏锐地看到了整个体制的严重弊端,感到了苏联党和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下降,于是选择苏共的“特权”作为突破口,凭借反特权、反专制、反腐败的大旗,迅速形成反对派,最终利用“8.19事件”,导致戈尔巴乔夫不战而降,改革破产,亡党亡国。
但是,可悲的是,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旧模式的最先背叛者,其部分成员迅速成为新体制的主要成员。前苏联权贵阶层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占最高领导层的75%,占政党首领的57%,占议会领导的60%,占政府部门的74%,占地方领导的82%,占商界精英的61%。
对中国的镜鉴与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告诫全党:“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苏共亡党为我党推进权力结构改革、建设廉洁政治、实现美好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镜鉴。
加快推进权力结构改革。
“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构是形成既得利益群体的“总病根”,也是苏共亡党的“总病根”。以苏共亡党为历史鉴镜,着眼于“总病根”切实推进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加快以权力结构改革为核心的民主法治和制度反腐进程。
全面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等级授职制的组织制度是“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加速器,导致苏共执政能力层层矮化以至无能替天下负责。列宁建党之初就敏锐地认知到,党的执政队伍“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因此,建议树立执政党质量建设意识,建立严格的执政队伍“准入标准”,改革党员纳新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宁缺勿滥。
同时,改革组织人事制度,建议实行“三三制”初始提名权改革,候选人1/3 由党组织提名,1/3 由党员群众提名,1/3 由民主党派提名;并在县乡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试点。
切实保障人民和党员的国家主人和党内主体地位。
苏共执政过程中,权力来源的变异性和畸形化,造成只对上负责难向下负责,只对个人利益负责难对天下和民生负责。因而,脱离了人民群众既无力解决自身腐败问题,更无法经受长期执政和改革世情的考验。为此,建议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权为民所赋”原则,建立群众参政议政、推行民主政治和反腐败的机制和平台,落实党员、群众在党和国家建设上的主体地位。
当前尤其要动员并组织群众支持和参与反腐败,鼓励举报包括匿名举报,引导实名举报,最高可奖励举报者50%的追缴赃款。同时,发挥网络反腐的平台作用,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改革监督体制、人员结构和方式方法。
苏共亡党的深重教训告诫我们,同体监督机关既无法对“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执行机关特别是“一把手”进行监督制衡,更无法组织打赢反腐败这场战争。建议加快改革监督体制和反腐败体制,尽快完成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加强对权力主要是执行权力的监督制衡。
同时,加强反腐部队的职业化建设,建议各级反腐败领导班子和队伍启用和充实一批反腐败专家、学者、律师,逐步实现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职务、职责、关系分离,不交叉、不隶属、不兼任;建立监督者必须接受监督的机制,把反腐败机关建设成为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良心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