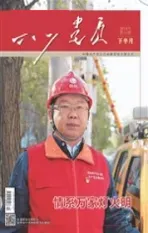乡镇干部的“假记者之困”
2013-01-17
一些假记者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对乡镇机关进行敲诈勒索,严重干扰了部分地区乡镇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河北省邯郸市某镇党委书记李俊山(化名)的办公桌上,有一本厚厚的名片夹,里面存放的都是和他打过交道的“记者”名片。从名称上看,既有传统报纸,也有新兴网络,既有公开媒体,也有内部刊物;从地域上看,有河北省内的,也有北京的。李俊山说:“这么多名片,只有一张是真的。”
“绕来绕去最后都离不开钱”
在多年的乡镇工作经历中,李俊山见惯了形形色色的假记者,可谓饱受困扰:“熟识点的,来了直接摊牌搞发行;关系不熟的,一般都打着批评报道的旗号,绕来绕去最后都离不开钱。”
“通常几千块钱就能‘搞定’,从这些年的情况看,没有低于1000元的,也很少有高于1万元的。”李俊山说。只有一次例外:当时因为修路引发群众上访,某报社“记者”采访完后,直接把附有现场照片的稿子寄给了县长,声称“3日内没有回信,直接登报”。县长批示下来后,李俊山找到该“记者”沟通,最终花了2.5万元订阅该报社的刊物。“花了钱以后,稿子是没登,但是刊物一直也没见到。他们说那刊物都是给省里领导看的,你说可笑不可笑?”
一张放羊照片“吃”遍三个乡镇
在陕西省安塞县,一位有过乡镇工作经历的干部告诉记者,实行退耕还林以来,陕西省制订了封山禁牧条例,但在有放羊传统的陕北,仍时有农民偷牧。“一些‘记者’开车进山找羊、拍照后,拿着照片到乡镇谈价钱。由于陕北地形地貌比较相似,有时在安塞找不到素材的,就跑到邻近的靖边县找羊群拍照,再跑到安塞的乡镇要钱。更有甚者,一张照片从镰刀湾、化子坪、谭家营一路敲诈,走哪‘吃’哪。”
多地乡镇干部反映,这种以采访为名行敲诈之实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基层乡镇的负担。每年仅此一项开支,少则数万元,多则10多万元。“每月都有两三拨,一拨一到两人。”
近年来,在山西忻州,“当记者”已渐渐成为城乡无业青年的一种“职业”。这里已经出现了忻府区合索、曹张乡令狐庄和原平市神山村等当地闻名的“记者村”。这些“记者”,有的曾以卖花圈为生,有的做过牛贩子,他们“当记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当地黑煤矿诈钱。基层政府为不被曝光,常常会严令被“逮住”的矿不惜一切代价摆平事件,否则整个地区都有被集体停产的“连坐”之忧。这时,一种“合作互保”的方式就出现了:被逮住的矿出大部分,周围所有黑矿都给它赞助“摆平费”。
“假记者也不得不包容”
谈到面对假记者时的心态,乡镇干部们普遍五味杂陈,一方面既不堪忍受乃至反感他们的骚扰,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敢得罪。之所以会如此,河南省兰考县某乡党委书记表示,一是乡镇工作的确存在问题,担心曝光;二是工作中打“擦边球”,怕经不起深究;三是本来问题不大,担心媒体炒作,舆论压力大,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前任党委书记翟伟栋认为,在一些地方,乡镇干部明知是敲诈,但又不敢得罪假记者,一定程度上还跟“害怕给领导添麻烦”的心理有关。“有些地方领导对媒体报道过于敏感,一旦出现负面消息,往往是先处理人再说事。这样一来,乡镇即使没事也担心假记者找事。”
一个基层宣传部长的“记者经”在将近20年的宣传工作生涯中,某县宣传部副部长老丁(化名) 接触过上千名记者。老丁琢磨出了一套鉴别真假记者的经验:和对方寒暄时,他会跟这些人聊国家最近的方针政策。假记者这时候一般只会打哈哈,而真记者则会和老丁有一个对等的交流。
对于假记者,老丁从不揭穿他们,但对他们的“舆论监督”也不买账。而仅仅在几年前,老丁的底气还没这么足:“那时媒体刚放开,小报不断地办,你得重视它,毕竟我们是基层。我并不是怕小报曝光,而是担心,这种只印十份八份的小报,可能直接寄给市里的领导,或者省里的领导。领导可能对报纸不大了解,一看我们这里有这么大的污染事件,会过问,领导就会有压力。”
随着对假记者的鉴别力与日俱增,老丁也更加应对自如:“几年前,一些小报要给哪个单位曝光,我们会给个两三千元。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最近3年内,一分钱都没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