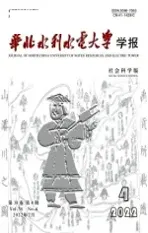从考古发现看先秦中原地区的内河航运
2012-08-15衡云花
衡云花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0)
从考古发现看先秦中原地区的内河航运
衡云花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0)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河、湖水系较为发达。考古发现证明,先秦水利技术的进步不仅促进了人工运河的发展,而且舟船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古人航运活动的范围。内河航运的拓展使得中原和沿江临海地区的文化交流日益紧密。
先秦;中原;内河航运;舟船技术
先秦时代,中原地区的气候环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温暖湿润。根据相关研究,我国全新世大暖期出现于距今8 500~3 000年之间,这一时段对应于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夏商王朝时代,它反映的是我国古代社会长达约5 500年的漫长时期内生态环境状况的综合系统[1](P42)。这种温暖的气候直至殷商时期,大部分年平均温度仍高于现在2℃左右[2]。这一历史时期的气候环境也是我国古史传说中洪水时代发生的历时背景。根据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盨”开篇即言的铭文“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3](P15),说明大禹治水的历史记载事实存在。多水的气候环境使得当时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有名的古湖泊就达数十个,如大陆泽、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孟渚泽、圃田泽、荥泽、海隅泽、弦蒲薮、阳华薮、焦获、昭余祁等[4](P106~112)。河湖交织的水系网络成为内河航运极为便利的基础条件,加强了中原地区与各地的文化交流。
一
中原地区地势平坦,河流水势落差较小,水陆交通的连接相当便利。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册》先秦文化遗迹分布看,古人临河滨水而居,以便于用水又不遭水患,水陆通行比较便利。所谓“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板,以为舟航”(《淮南子·氾论训》)。如南召县庙坡村新石器遗址就在黄鸭河与白河汇流处,陕县、灵宝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多在黄河三门峡水库地区附近,贾湖遗址滨湖发展,裴李岗文化分布于溱洧水流域,夏商都城均临水而建等。在黄淮流域傍水而居,以舟涉水捕鱼,聚众围猎采集,是中原地区先秦人类社会生活的大致情景。夏禹治理洪水时,“陆行载车,水行载舟”(《史记·河渠书》),导山导水,水陆并行,率领子民奔波于黄河中下游治理洪水。通过对河道的疏浚治理,沟通了各河流之间的水上运输,初步形成了以黄河为骨干的水运网络。利用舟楫可“浮于济、洛,达于河”;“浮于汶,达于济”;“浮于淮、泗,达于河”;“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及“浮于洛,达于河”(《尚书·禹贡》),基本上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间的水上运输。当时夏族对异族的数次征伐均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展开,数次渡河行军作战已经显示了中原地区水上航运的初步发展。
商朝前期,迁都频繁,商人数次举族涉河迁民,围绕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迁徙定居。如殷汤都亳(今商丘);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尚书·盘庚》),商族频繁地在黄河两岸迁都,而每次迁都都是一次重大的军事渡河行动。古黄河风急浪险,每次渡河时商王都要占卜问天,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留有许多这类卜辞,足见当时水上航运已有一定的规模。至武王伐纣时,会合八百诸侯,两次从孟津渡黄河北伐。据《艺文类聚》引《太公六韬》:“武王伐纣,先出于河,吕尚(姜太公)为后将,以四十七艘船济于河。”《史记·周本纪》载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孟)津”,此次抢渡孟津的虎贲甲士有四万八千人。数万大军的渡河军事行动,说明当时不仅具有大规模的船队,而且已经有了较大型的船只。周穆王时从洛邑渡黄河西征,遇大沼“乘龙舟”,经漳水西行。另据《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云:“魏襄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越人从东南沿海经历海路、山东半岛至黄河流域再入渭水,跨流域长距离航运说明当时中原与周边地区水上交流,不仅有一定的航运路线,可能交流还相当频繁。越人献舟的内容极其丰富,大量辎重经历长途水上运输亦显示当时水上航运不仅流域广、航程远,而且规模确实不小。
春秋时,中原地区水上航运著名的事件是秦国赈济晋国粮食的“泛舟之役”。是说公元前647年秦国利用渭水、黄河、汾水的近700里河道,经由今陕西凤翔沿渭水而下至黄河,溯黄河而上再溯汾水至绛县大规模运粮的故事。即《左传·僖公十三年》所云:“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说明黄河流域水上航运已颇具规模和成熟,而人们一般也把此次“泛舟之役”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漕运之始。
二
随着水利技术的进步,人工运河的发展大大拓展了人类内河航运的能力和范围。
夏时禹治洪水“开九州,通九道”,用“准绳、规矩”等简单测量工具对内河航运线路的开辟,根据地势、流水高下的动态形式,控制与调节各水系的径流量,沟通了晋、豫、陕间的各个水系,与江汉相连,可东达于海。至春秋战国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及铁器工具的应用,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出现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发展高潮,主要有灌溉工程、航运工程、堤防工程等。这些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地貌特点,合理地储水、引水、导水,并设置水门和闸坝以调节和控制水的流量,所谓“陂有五门,吐纳川流”(《水经注·肥水注》)即指此。从《考工记》“匠人为沟洫”条的记载来看,显然,古人在沟渠工程的建设中已经对水体的各种运动形式,以及水体重力对堤坝的作用力关系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并初步总结了堤坝建设中一些经验性的比例规律。如其对堤坝修建的比例尺寸总结为:“凡为防,广与崇方,其閷叁分一,大防外閷。”水利专家认为,“广”应指堤顶之宽,“叁分去一”为堤两面坡度的总和,即每边边坡均为 1∶1.5[5](P110)。
铁器工具的发展及工程技术手段的提高,推进了这一时期运河开凿事业的快速发展。此时,魏在黄河以南的荥阳,楚在汉水、云梦;吴在江、淮、太湖;齐在山东临淄、济等地都开凿了运河,即“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与齐则通淄、济之间……百姓享其利”(《史记·河渠书》),其中以吴国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和魏国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最为著名。邗沟于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年)始挖,据《左传·哀公九年》载:是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企图通过连接长江、淮河水系,进而通过淮河水运进入黄河水运网络,北上与齐、晋争霸。邗沟利用长江、淮河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以人工渠道相沟通,北过高邮,折东北入射阳湖,经邗沟北上入淮,逆淮河水而上入泗水、沂水达齐国等地。但邗沟此时只能通往东方的齐、鲁,不能通中原的晋、宋等国,而夫差为了要争霸中原“盟主”,不久又于商鲁之间挖深了菏水,沟通了泗水和济水之间的航运,由此,黄、淮之间的东段水域网得以沟通。
据历史记载,中原最早的运河是春秋时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开凿的。《水经·济水注》引《徐州地理志》云:“……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陈都于今淮阳,蔡都于今上蔡,二者分别紧邻淮水的两条支流:沙水和汝水,此条运河在何位置,于史已渺不可稽,当是规模较小,不久以后被湮废而不为人所提及。
鸿沟是中原河、淮相通的重要水道。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今开封),为控制中原,加强与宋(商丘)、郑(新郑)、陈(淮阳)、蔡(安徽凤台)等的联系,于迁都次年便开凿鸿沟。引河水,循汴水,东至圃田泽(中牟县西),又从圃田泽东至大梁城北,在大梁通黄河,向东折而南,与淮河北面的支流丹水、睢水、沙水、颖水等河相通。由于有丰盛的黄河水源供给,又有圃田泽做了它适当的水柜,因此鸿沟航运畅通无阻,把当时中原地区黄、淮之间的重要水道济、濮、汴、睢、颖、涡、汝、沙、泗、菏等水都连接了起来,不仅可行舟,水量丰余时还可供灌溉,形成了以黄、淮为骨干的水运交通网络,鸿沟则成为这一水运交通网络的核心水道。其外围自淮以南,直达长江、太湖、东海;沿济水下航,又可达齐临淄等地。
鸿沟的开凿促进了淮河流域工商业的发展,一些沿河的重要城镇应运而生,除大梁外,位于济水、菏水交汇处的陶(今山东定陶)、濮水边上的卫都濮阳(今濮阳南)、颖水边上的韩都阳翟(今禹县)、丹水与泗水之交的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鸿沟入颖处的楚都陈(今淮阳)、濒临濉水的濉阳(今商丘)、颖水入淮口的寿春(今安徽寿春市)等地逐渐成为当时繁华的工商业中心城市。秦时在鸿沟通往黄河的广武镇修建了大型转运粮草的仓库——敖仓。敖仓积粟,是鸿沟水路转运的终结。《史记·高祖本纪》敖仓下《正义》解引《太康地理志》云“秦建敖仓于成皋”,以充分利用鸿沟和济水水运之便利,鸿沟地位日益重要。秦汉以来,东南地区大量粮食通过内河航运进入中原,由鸿沟至汴梁,沿黄河入关中,敖仓成为漕粮转运的重要枢纽。汉以后,由于黄河屡次决溢,鸿沟系统多次被淤浅,其航运不如以前畅通,航运的地位也逐渐被东面的汴渠所代替。东汉时人们曾经修濬鸿沟(时称汴渠),结果发现“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后汉书·王景传》),可见鸿沟当时是设有水闸的。运河的开凿,不仅需要进行闸坝等工程的设计,还要求掌握沿途地形、土质、水源、流量等情况,是一项复杂的水利工程,所以运河的开凿是水利工程技术进步的标志。
三
航运的发展离不开舟船技术的进步与航运管理。
先秦时期的水运及船舶管理在周时已有一定规制,当时制定了按官阶及身份等级乘船的规章制度。《尔雅·释水》云:“(周)天子造舟(用船搭浮桥),诸侯维舟(并联四舟),大夫方舟(并二舟),士特舟(单舟),庶人乘桴(筏)。”为此专设主管舟船的官员“舟牧”,管理周王室出乘的船舶安全等事宜。《礼记·月令》云:“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其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有关舟船建造的质量安检制度。当时水上航运管理的情况在鄂君启节铭文中有部分反映。其中水节铭文规定了对水运船队数量(3艘船为一批,每年50批为限)、船队外出经商的时间、水运所过关卡以及免税物质范围等的限制。其航行线路有一段自汉水转入唐白河至芑阳,即汉之淯阳[6](今南阳南,张衡《南都赋》“汤谷涌其后,淯水荡其胸”即描写此水)。鄂君启节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楚国江、汉、淮水系水运交通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向我们展示了分裂割据的政治形势对水上航运交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甚至在各诸侯国内的各封君之间,也是关卡林立,设限繁多。
据文献记载,我国先秦时期的水运工具是从独木舟逐渐发展起来的。传说“古人见窾木浮而作舟”,《易·系辞下》亦云:“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这大概是伏羲作舟的最早传说,它截取粗大树干的核心部分,挖空一部分干体形成槽状,因其不仅具有一定的干舷,具备一定的浮力,承载适当的重物,能够承受一定强度的风浪,且还提供了水上航运过程中的密闭空间,使人、财、物与水彻底隔绝开来。因此独木舟的出现开辟了人类水上航运中真正意义上的舟船,是渡水工具在结构形制和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考古发现证明,继独木舟之后,至迟在据今三千多年以前,我国就出现了木板船[7](P29),这在造船技术史上是一次突破性的飞跃。用木板造船,摆脱了受天然木材原始形状和大小的束缚,为船舶的继续发展开创了广阔的天地。由于独木舟长、宽、深受单根木材制约性大,在水中的稳定性较差,且材料浪费严重,载货量有限,加之筏的干舷低,易遭水湿,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上运输需要更大更稳的工具。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表示船的舟字从其形状上看为平底、方头、方尾,首尾略翘,是小型木板船的雏形。甲骨文中的“舟”字形状不一,亦说明当时用船十分普遍,出现了多种形制的木板船。
夏时,已经出现了一种制作精娴猛锐的船舶——“荡舟”,可能已经是多木结构的船舶了。据《史记·周本纪》所载,此次抢渡孟津的甲士共有四万八千人,因此姜太公调用的这47艘船可能已是有众多桨手操驾的大型船舶了。西周时,随着金属工具的广泛应用,造船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载重量较大的船舶。当时,周人的造船技术还得益于隅居东南沿海一带的越人相助。《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引《周书》云“周成王时,于越献舟”。其献舟路程经海上、山东半岛、中原黄河流域才能达渭水周地王室。越地水沼遍处,人们习以水生,自古就造船技艺高超,“献舟”之事反映了东南沿海与中原内地技术传播与经济交流的社会生活事实,它推动了中原内地舟船技术水平的发展和进步。《诗·大雅》云:“淠彼轻舟,丞徒辑之”说明当时船体较大,需多人划船。
后来为了增加载重量,人们又发明了“舫舟”,即以两船相并,上铺以木板,不仅浮力增大,且稳定性得到加强。内河舟船技术已有明显进步。舫,并舟也,是一种将两船并列相连成为一体的“双体船”,古籍中称其为“方”或“方舟”。如《国语·齐语》云“方舟设泭,乘桴济河”。两舟相并,并加木板于上,使得宽度增加,稳定性增强,增加了排水量,能装载较多货物,逐渐成为一种新型船只。在西周金文中不仅有“舟”字,而且开始出现了“船”字。古时舟与船有不同含义,舟是用于江河两岸的过渡工具,而船则是沿岸上下的航行工具。汉字的发展变化客观反映了我国古代舟船的演变历程,亦说明商周时期的造船技术已脱离了“刳木为舟”的原始方式,进入了接板为船的新阶段,而且还能较好地处理板间的缝隙,粘合船板使其密不透水。接板为船的技术方式在文献中亦有间接的反映,《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昭王溺于汉水的事实真相就充分反映了当时楚汉大地木板船发展的技术水平。其云:“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正义》引《帝王世家》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具没于水中而崩。其右(卒)[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舟人讳之。”可见当时人们已掌握了木板制船过程中的密闭与防水渗漏问题,对胶的物理性质处理得当并有一定经验认识,以至能够成功溺毙昭王于水中。这些造船技术的发明与进步为以后船舶的多样化、大型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工具的出现推动了工业生产领域内的专业化分工及木器加工的精密化。以鲁国建筑工匠鲁班为代表的专业匠人,及斧、锯、凿、锛等铁制木工工具的出现为舟船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中葬船坑中的木船,经复原总长达13.1米,宽2.3米,吃水深度0.76米,排水量达13吨多。配有木浆等航行属具,船体以木板拼接,铁箍锁固,流线形船体美观大方[8]。在河南汲县(今卫辉市)山彪镇一号墓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铜鉴上的纹饰绘有带甲板的战船[9](P18-20),纹饰描绘了左右相向行使的两艘战船,船身修长,首尾高翘,战船上置有甲板,甲板下面的船舱内有桨手多人在用力划桨,甲板上有战士多人正在作战,或击鼓,或射箭,或舞枪,或奏乐,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水上攻战的场面。这种船没有风帆,亦无尾舵,完全以人力划桨作动力。山彪镇出土铜鉴上的水陆攻战船纹是目前中国古船最早有甲板船的例证,这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出现了有甲板的船。船舶与航运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古人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促进了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1]王星光.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
[3]保利艺术博物馆.遂公盨——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M].北京:线装书局,2002.
[4]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5]《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
[6]姚汉源.鄂君启节释文[J].安徽省考古学会刊,1983(7).
[7]席龙飞.中国造船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8]王志毅.战国游艇遗迹[J].中国造船,1981,(2).
[9]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责任编辑:刘 明)
Abstract:River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relatively well in the central plain area during Pre-Qin period.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show that progress in hydrotechnics has accel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can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hip making techniques has noticeably widened the range of ancient shipping activities.The development of inland water transport has led to closer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area and areas along rivers and coast.
Key words:pre-Qin period;central plains;inland water transport;ship making techniques
Research on Inland Water Transport in Central Plain Area during Pre-Qin Period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ENG Yun-hua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Zhengzhou 450000,China)
G112
A
1008—4444(2012)04—0020—04
2012-04-09
衡云花(1973—),女,河南遂平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