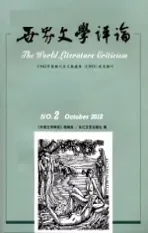《喧哗与骚动》的多视角叙述
2011-08-15杨如月
杨如月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kner)以其家乡偏僻的南方小镇为背景,创作了令人惊叹的约克纳帕塌法(Yokna patawpha)系列小说,1949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一、南方文学的杰出代表
福克纳的创作极为丰富,题材广,规模大,有史诗般的气魄,其中较为重要的作品有:《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去吧,摩西》(Go Down,Moses)等,其中《喧哗与骚动》是最成功,也最为作者钟爱的一部小说。“除了《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为艺术而创作的小说,是他的第—部大量使用新手法的成功之作和在写作过程中他体会到创作欲的极大满足这些原因之外,他之所以特别喜欢它,还因为康普生家的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童年”①。小说的书名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中的一段精彩独白:“……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②小说共分四个部分,截取了南方破落庄园主康普生一家生活中的四天作标题,由四个不同的叙述者班吉、昆丁、杰生和迪尔西分别讲述主要人物凯蒂的故事,展示了南方豪门大户康普生家族的衰亡史。
《喧哗与骚动》是一部美国评论家一致认为难懂的书。它是福克纳以全新的艺术手法创新的成果。它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的故事叙述主要是以一种叙述视角来完成的,并且叙述者的位子也相对固定,创作《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这一传统,采用了全知视角和内视角相结合的叙事视角来叙述故事,而且叙述者的位置也经常变动,这种多重复合的叙述视角使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具有了更多的意味和增强了故事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福克纳在介绍其作品的创作过程时说:“我先从一个白痴孩子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由一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可以更加动人。可是写完以后,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把故事讲清楚。我于是又写了一遍,从另外一个兄弟的角度来讲,讲的还是同一个故事。还是不能满意,我就再写了第三遍,从第三个兄弟的角度来写。还是不理想。我就把这三个部分串在一起,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就索性用我自己的口吻来加以补充。”③在这里福克纳正是通过小说叙述视角的不断调整、转换来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渐趋完美的。当福克纳感受到仅仅使用一种叙述视角和一个固定的叙述故事的模式所带来的局限时,他勇敢地打破了它,代之以多叙述视角的转换和叙述者位置的灵活多变。
多种叙述视角的运用,是长期以来福克纳创作实践的结果,它不仅有助于内容的表达,而且还被当作一种创作实践经验的成果保存下来,并随着创作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充实,有力地推动着小说的本能性能的更大发挥和发展。
《喧哗和骚动》小说的四章分别采用了四个叙述视角。前三章分别用的是内视角,叙述的内容、感情、智力水平都与叙述者的性格完全相符。它使读者更容易进入小说特定的情境之中,调动读者的情绪和创造性。前三部分的内视角的转换,又可以使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体验同一事件,对人物有—种审美的整体把握。第四章采用了全知视角,叙述者能全知全能地叙述事件中每一个人的活动,能解释每一个人的思想,让读者与事件拉开一定的距离。内视角和全知视角交替使用,并且不断变换叙述者的位置,小说中既有叙述的交叉重合,又有许多空白和疑点,叙述者们既是小说的主角,又是小说的配角,即是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和目击者,却又不能全知事件的整个过程。由于小说的悬念与预示的取消,作者的意图越来越隐晦,小说客观化的意味越来越强烈,读者面对小说进行某种审美价值判断时就因此失去了对于作者提供大量暗示的依附,在阅读小说时所拥有的审美期望就会变得不明确起来,读者不得不对小说的故事展开做出独立的预想,用自己的想象去连缀,补充、开发,再创造一部立足于原作而又超过原作的属于自己的小说。这就是叙述视角的求新创造带来的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也显然是作者企求同读者一起进行审美过程体验,一起进行审美创造的叙述观念的表现。
在《喧哗与骚动》中,叙述者由一个增至四个,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围绕同一个中心讲述故事。它是福克纳对于全新的创作手法的成功尝试。小说的第一部分通过白痴班吉的视点展开,写的是1928年4月7日班吉33岁生日那天他的意识活动。班吉虽然是33岁的成人,但其智力仅相当于一个3岁的幼儿。他既缺乏思维能力又无时序观念,完全凭直觉、印象和本能去对待周围世界,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其大脑中相互交织,但我们还是可以在班吉的意识流动中,获得一些关于凯蒂和康普生家族的信息。比如,他喜爱的那块林中草地被卖掉了;关心他、照顾他的姐姐凯蒂离家出走了;1913年的某天,他因追赶女生被打昏进了医院,杰生让医生给他做了阉割手术等等。班吉没有思维能力,但嗅觉特别灵敏.当凯蒂是纯洁的少女时,他能闻到姐姐身上有“树的香味”④,而凯蒂失身堕落后,班吉逐渐闻不到姐姐身上树的香味了。由于班吉的母亲将自己做母亲的职责推给了女儿凯蒂,在班吉的心目中,姐姐便是母爱的化身,是他生活中唯一精神支柱。凯蒂为班吉的生活带来了幸福和光明并使其有意义。凯蒂是福克纳所深爱的形象,她是人性美好的体现。
小说的第二部分是以昆丁的视点展开的,写的是1910年6月2日班吉的大哥昆丁自杀这一天的意识活动。昆丁是康普生的长子,是没落的南方贵族的末代子孙。他从父亲那儿得到的只是悲观和绝望,他迷恋家族的过去,又无能为力于家庭的急剧败落,对妹妹凯蒂爱到不正常的地步。凯蒂被诱骗失身以至于堕落,使昆丁受到严重打击而精神错乱,行为失常。他要报复妹妹的情人却难以付诸行动。他与妹妹的情人决斗更显得过时可笑.在思想极度混乱之中,他竟准备向父亲说明他是妹妹私生女儿的父亲(其实不是)。他这一天里,满脑子是凯蒂的失身堕落、乱伦和自杀:
“因为如果仅仅是下地狱,如果事情仅仅如此,事情就到此为止。如果事情到这里就自行结束,地狱里除了她和我,就再也没有别人。如果我们真的干出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能让人们逃之夭夭,光剩下我们俩在地狱里。我犯了乱伦罪,我说父亲啊,是我干的,不是达尔顿·艾密司……于是我就会低头去看我那副淙淙作响的骨骼,深深的河水像风儿一样吹拂着,像是一层用风构成的屋顶,很久以后人们甚至都无法在荒凉、无瑕的沙地上把骨头分辨出来。”⑤
凯蒂的行为是旧贵族庄园主家族的奇耻大辱,标志着康普生家族的体面与荣耀已不复存在。昆丁是南方贵族阶级的最后一位代表,作为在贵族传统观念与价值标准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继承并遵循着旧传统,所以接受不了凯蒂堕落的现实,他想杀死凯蒂的情人为家族挽回荣誉,可他并未动手杀死仇人。他离不开旧生活,却又无力捍卫之,他就只能选择自杀了。昆丁在已经改变了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坚持旧的意识与旧的生活模式,他不承认时代在前进,竞然砸碎了钟表,其实时代照样前进,被砸碎的其实是他自己的生命。
小说第三部分以杰生的视点展开,通过1928年4月6日杰生的内心独白,把这个贪婪无情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杰生与昆丁正好相反,他嘲弄自己家庭过去的一切,对亲人毫无感情.他反感哥哥半夜游泳自杀,还一心想把班吉送进疯人院,并借机阉割了弟弟。他怨恨姐姐凯蒂影响了他的前程,竟侵吞凯蒂每月给女儿小昆丁的生活费用,还欺凌这个远离母亲孤苦无依的外甥女。他对凯蒂母女既无亲情,又无怜悯之心。在杰生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他在父亲的坟前碰到久未见面的凯蒂,竟然斥责姐姐。他要凯蒂的丈夫为自己安排一个职位,可凯蒂被丈夫抛弃了,杰生的希望成了泡影,他因而对凯蒂耿耿于怀。杰生不讲什么道德廉耻,他只看重世俗生活,迷恋金钱,为赚钱投机取巧不择手段。他整日忙于赚钱,却一事无成。他不爱别人,没有一个女人爱他,所以爱情、家庭也就与他无缘。杰生一味摈弃过去,割绝传统,在背弃旧的传统的同时,也扭曲了自己的人性而受到现代社会的鄙弃。
小说的第四部分不同于前三部分的意识流内视角叙事手法而改用了传统的全知视角的叙事手法。1928年4月8日,由康普生家的忠实黑人女仆迪尔西来补叙康家的有关情况,作者通过讲述迪尔西这一天的活动,透过迪尔西的眼光,将康普生家族三十年间的变故和人世沧桑一览无遗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个不断走向没落的南方世家:小昆丁的私奔出走,杰生的狂怒与追寻,女儿凯蒂的沉沦堕落,大儿子昆丁的精神崩溃,投河自尽……小说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没落南方世家的各家庭成员的遭遇和精神状态来描摹南方社会的浮沉变迁,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对南方乡村人性的吞灭与腐蚀,从而使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批判主题。
总之,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的这种多视角叙述手法为读者树立起了一面面生活的镜子,它们相互映照,互相反衬,形成一个万花筒式繁复杂乱的立体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正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作者通过多种叙述视角的变换,实现了语言诗学功能对言语行为的最大限度的凸现,使叙事能够有效地获得符号意义。通过处于不同视角和意义层次的叙述者的个性化的眼光,获得了不同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实现了多视角叙述在小说中的美学价值。
注解【Notes】
①②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杜,1999 年)236,233。
③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262。
④⑤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5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