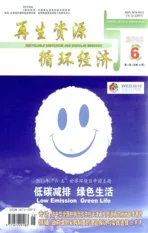循环经济的政府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
——基于政府与企业的动态博弈分析
2010-09-01朱雪梅
朱雪梅
(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安徽合肥230009)
循环经济的政府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
——基于政府与企业的动态博弈分析
朱雪梅
(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安徽合肥230009)
循环经济条件下,政府制度安排与政策制定需要考虑更多利益主体。引入动态博弈理论的有关成果,通过建立政府与企业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的博弈模型,对两者的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对循环经济背景下政府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提出建议。
循环经济;动态博弈模型;政府制度与政策
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物质运动是周而复始的物质循环,而非物质的单向线性流动。生态系统的特征是系统内部以及外部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1]。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将经济系统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其核心是以物质闭环流动为特征,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重构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和“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环利用模式,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到尽可能小的程度[2]。
1 背景分析
1.1 现实分析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GDP的增长反映了人类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人们通常视其为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然而,在GDP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类通过各种生产活动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使环境污染,或滥用资源使生态破坏;二是人类无休止地向生态环境索取资源,使自然资源的绝对量上逐年减少。传统工业经济是由“资源—产品—废物和污染排放”所构成的单向物质流动。在这种经济中,人们强制把自然资源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弃物大量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一次性的。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过程,使得在整个经济系统以及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只产生很少的废物[3]。循环经济发展中,政府和企业的目标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决定了二者行为方式的不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来自政府的行政指令,对于政府公布的各种政策性措施,企业在行动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由行政隶属关系向契约式和交易性方向发展。
1.2 经济学分析
1.2.1 公共资源
如果其物品不具有排他性,则每个人出于自己利益考虑,就会尽可能多地去利用它。如果不加限制公共资源,可能很快就会被过度地使用,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2.2 外部经济
假定某个企业采取某项行动的私人利益为Vp,该行动所产生的社会利益为Vs。由于存在外部经济,故私人利益小于社会利益:Vp<Vs。如果该公司采取该行动所遭受的私人成本Cp大于私人利益而小于社会利益,即Vp
1.2.3 外部不经济
假定某个人采取某项活动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分别为Cp和Cs。由于存在外部不经济,故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Cp
2 博弈分析
循环经济的主体是政府与企业,所以循环经济自发机制设计的重点是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的投资需要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而企业的行为则必须在政府的法律与制度框架内。为此,政府必须考虑在政策制定和政策设计中,如何使得企业遵循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2.1 参与者分析
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
政府:扮演公益者、管制者和仲裁者的角色,其目标是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企业:企业利润最大化。
冲突原因:由于资源环境影响的外部性,如果没有外在约束,市场机制是不能直接引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自发地发展循环经济的。
总结:发展循环经济意味着减少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往往会使企业增加即时生产成本,在短期内降低利润。也就是说,企业推行循环经济,实现绿色转变,并不是企业的自觉行动,而是企业在外部环境和社会制度约束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2.2 博弈过程分析
博弈的过程实质上是在循环经济中政府将自身的价值标准传递或强加给企业的过程,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理性与政府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集体理性存在一定的冲突,必然会在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产生博弈。因此,在博弈局中,企业是作为拥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一方(对于资源环境信息而言,企业往往对其生产过程、生产技术、排污状况、污染物的危害等方面了解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向政府隐瞒真实信息,甚至不严格按照环保要求生产,不披露废弃物信息,假报产品性能等。而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就是博弈局中的“委托人”,虽然不能直接获得污染企业的真实状况,但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促使企业的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化。政府如何设计出一种有效率的“机制”成为博弈的关键,其“机制”目标是为企业提供足够的选择空间,创造最有利的制度安排,从而使“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达成一致,达到最佳博弈均衡[5]。
2.3 动态博弈模型
根据博弈方是否相互了解得益情况,动态博弈有“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之分,根据是否所有博弈方都对自己选择前的博弈过程完全了解,有“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和“不完美信息动态动态博弈”之分[6]。
2.3.1 双方博弈模型的假设
(1)博弈方:企业(E)和政府(G),各博弈方均为理性经济人:企业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目标是社会效益最大化。
(2)博弈规则:针对企业的污染违规行为,政府可以选择对污染企业征收排污费或对其处以罚款,或对治污企业予以奖励如减少税收或给予补贴,但同时政府为获取信息以执行政策则必须付出检查成本。企业可以选择缴纳排污费、接受排污罚款或治理污染,除经济利益外,企业的行为可能影响其社会形象和声誉。
(3)合作过程中不存在道德风险。
(4)假定成本与治理污染的努力成正比,即治理越努力,成本越大,反之越小。
(5)各方都清楚对方的支付情况,也能观察到对方的选择。
企业、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被认为构成一区域母体的函数,即 Y=F(E,G),这里把企业(E)和政府(G)当作自变量,把某一单纯区域母体看作因变量(Y)。
2.3.2 博弈模型的构建
为这类合作治理设计一个具有2个参与人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其扩展性如图1所示,括号中的数据依次是企业的收益状况和政府的收益状况。

图1 政府先行动时的企业治理策略选择图
假设Ce为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Cg为政府检查的成本,Re为治理污染给企业带来的直接收益(政府的补贴),F是政府对不治理企业的处罚。Ri为企业达到环保要求带来的间接收益(好的社会形象或声誉),Ci为企业污染带给企业的形象损失;因Ri和Ci是间接收益和损失,不易量化,故在本博弈模型中忽略。只考虑R0与R1。R0为企业治理前或者不治理时净利润。R1为企业治理后达到环保要求所带来的间接收益后形成的不考虑治理成本的净利润(之所以R1不考虑治理成本,是为了与上面R0的可比性),Rg为企业独立治理污染时,政府取得的社会收益。该博弈中,政府首先行动,在博弈的第一个阶段,政府有两种战略:第一,实施积极治理政策;第二,实施消极治理政策。政府实施积极治理政策时,对采取治理的企业征收的税率为t*,未治理的为 t,一般有t*<t;政府实施消极治理政策时,对企业实施统一税率t。另外政府实施积极治理政策时,先对企业发放治污补贴。而政府实施消极治理政策时,仅在检查后,对治污企业发放治污补贴。
当政府实施积极治理政策时,企业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可以选择治理和不治理。当企业选择不治理时其期望收益为Re-F,政府为F-Cg-Re,支付向量为(F-Cg-Re,Re-F)。
在第三阶段,企业有两种战略:第一,企业自主完成污染治理,{t*×R1-Re-Cg+Rg,Re-Ce+R1(t-t*)+(R1-R0)};第二,通过技术交易从高校与研发机构获得关键技术或者要求高校与研发机构参与到企业污染治理过程中,共同完成污染治理。当企业获得了所需的关键技术后,它的治污能力将得到提高,同时需要支付给高校或科研机构较高的报酬W,且政府获得较大的社会效益M,此时会对企业及相关高校或科研机构根据其努力程度进行奖励P。由此在第五阶段,当高校与研发机构接受企业进行合作的战略组合的支付向量为{t*×R1-Re-Cg+M-P,Re-Ce+R1(t-t*)-W+P}。
当政府在第一阶段实施消极政策时,企业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可以选择治理或不治理。当企业选择不治理时,其期望收益为-F,政府为F-Cg,支付向量为(FCg,-F)。在第三阶段,当企业选择独立治理时,此时的支付向量为{t×R1-Re-Cg+Rg,Re-Ce+(R1-R0)};当企业选择合作治理,则支付向量为{t×R1-Re-Cg+M,Re-Ce-W+(R1-R0)}。
3 博弈模型的一般性均衡解分析
依据所作的假设,各方都清楚自己和对方的支付情况,也能观察到对方的选择,所以本博弈是一个完全且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适合用逆推归纳法进行分析。
3.1 政府先行动时企业的治理策略选择
3.1.1 政府在第一阶段选择积极治理政策
先看第三阶段企业的选择。从图1中可看出,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合作治理的条件是:

不满足此条件,企业将选择独立治理。
然后看第二阶段企业是否选择治理的策略。显然,从动态博弈模型图1中可以看出,企业若选择治理的条件应分别满足:

综上讨论,可以得到本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如下。
(1)如果Re-Ce+R1(t-t*)-W+P+(R1-R0)<Re-F,并且Re-Ce+R1(t-t*)+(R1-R0)<Re-F,企业在第二阶段不选择治理,博弈结束。处于主导地位的治理主体是否有意愿进行治理,最基本的条件是它从治理中获得的利益(支付)不能低于它的保留效用(这里保留效用相当于不治理时企业能够获得的支付Re-F)。而治理主导方企业根据治理的模式不同,获得利益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文中,主导方企业独立治理时的收益是Re-Ce+R1(t-t*)+(R1-R0),采取合作时获得的利益(支付)是合作成果与其付给高校的报酬之差。
(2)如果Re-Ce+R1(t-t*)-W+P+(R1-R0)<Re-Ce+R1(t-t*)+(R1-R0),企业在第三阶段将选择独立治理,博弈终止。大多数情况下,合作治理中总有一方处于主导地位。处于主导地位的企业是否有意愿与另一方合作,最基本的条件仍然是它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支付)不能低于它的保留效用(这里保留效用相当于独立治理时企业能够获得的支付)。
(3)如果Re-Ce+R1(t-t*)-W+P+(R1-R0)>Re-Ce+R1(t-t*)+(R1-R0),企业在第三阶段选择合作治理。在双方都有意愿合作的情况下,理性的治理主体都希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很难保证双方利益最大化的一致性,而只能找到某一个最佳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双方利益存在相互制约的情况下,双方为了得到最好利益所采取的行动。本博弈模型中,满足企业合作所得大于独立治理,满足高校与研发机构合作时取得正向收益,企业将选择合作,高校与研发机构将接受。双方将从合作治理中得到各自最好的收益。
3.1.2 政府在第一阶段选择消极治理政策
见图1的右侧,由于本博弈仍然是一个完全且完美信息博弈,在这里仍是用逆推归纳法进行分析。
企业在第三阶段选择与高校等进行合作的条件是:

式(4)表示企业选择合作治理的条件是,合作治理企业的期望收益大于它在独立治理时所保留效用,否则企业将选择独立治理。满足以上条件的前提下,企业选择治理的条件是:

式(5)表示企业选择治理的条件是治理收益大于免除的处罚,否则企业亏本,将选择不治理。
以上分析就是政府实施消极治理政策时企业的策略选择过程。如果以上条件同时成立,那么本博弈模型的子博弈的完美均衡是:第一阶段政府采取消极策略,第二阶段企业选择治理,第三阶段企业选择合作治理。
3.2 企业先行动时政府的策略选择
由于在双方博弈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引导性治理,通过制定政策来调控企业进行治理或合作性治理中的行为选择。换句话说就是政府的策略选择问题渗透在企业的每一次决策之中,当企业先行动时,双方博弈的具体策略选择见表1和图2。

表1 企业先行动时的政府策略选择表
如果企业选择不治理,则博弈结束。此时政府采取积极政策与消极政策的收益分别为F-Cg-Re和F-Cg,显然F-Cg-Re<F-Cg-,因此,此时政府的最优策略选择为消极政策,即不理会企业的行为。
当企业在第二阶段选择独立治理时,政府采取积极政策与消极政策的收益分别为t*×R1-Re-Cg+Rg和t×R1-Re-Cg+Rg,(t*<t),显然 t*×R1-Re-Cg+Rg<t×R1-Re-Cg+Rg。
当第三阶段企业进行合作治理时,政府采取积极政策与消极政策的收益分别为t*×R1-Re-Cg+M-P和t×R1-Re-Cg+M,显然 t*×R1-Re-Cg+M-P<t×R1-Re-Cg+M。
在这里注意到,从总体上来说,政府不愿也不应该过多干涉市场的正常秩序,只有在企业面临困难时,政府才更愿意通过积极政策导向来促进其成长。
3.3 博弈分析总结

图2 企业先行动时的政府策略选择图
通过以上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在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局中,最优的博弈均衡点为,不需政府检查,企业主动治理污染,实现绿色转变。显然,这在目前状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正是这种不对称,使得政府和企业的行动都可能偏离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
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回归到最优均衡状态的关键取决于博弈均衡的激励相容条件。从政府层面上讲,其自身获取信息的能力决定了对企业奖励或处罚力度的合理性和在执行监督中检查成本的大小;从企业角度讲,实现节能高效的绿色转变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理念和行为标准是息息相关的,是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或激励和企业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可见,要实现政府与企业在循环经济发展博弈中的最优或次优均衡,就必须设计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增强政府获取信息能力的同时,又对企业外在行为产生激励或约束,让循环经济发展由外部压力转化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1] 志 斌.自然辩证法概论[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70-90.
[2] 曹风中,周国梅.生态全息论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启示[J].环境污染与防治,2002(6):321-323.
[3] 保罗·霍肯.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M].夏善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52-175.
[4]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6版)[M].费方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91-505.
[5] 刘志荣,陈雪梅.论政府与企业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博弈均衡——兼论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设计[J].经济研究参考,2007(07):28-31.
[6] 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05-164.
Circular economy oriented institution design and policy making—Dynamic game analysis o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ZHU Xuem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Economics,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Under the goal of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more stakeholders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institution design and policy making.Based on the dynamic game theory,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game model on the selection of government or enterprises under the circular economy goal,and raise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circular economy oriented institution design and policy making.
circular economy;dynamic game model;institutions and policy
F049
A
1674-0912(2010)06-0017-05
2010-04-02)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于循环经济的投资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2008AJRW0453)
朱雪梅(1982-),女,安徽蚌埠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金融业发展与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