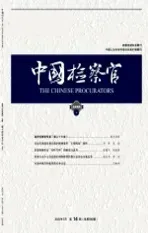案名:郑民生“校园凶杀案” 主题:故意杀人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适用思考
2010-08-15焦武峰
文◎焦武峰
案名:郑民生“校园凶杀案” 主题:故意杀人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适用思考
文◎焦武峰*
一、案件回放
[基本案情]2010年3月23日,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一起凶杀案。犯罪嫌疑人郑民生携带一把尖刀,从家里窜至该校门口,7时25分许,郑民生见校门口聚集了数十名等候入校的学生,便先后抓住12个小学生,持刀朝他们的胸、腹等要害部位猛刺,其中8名小学生因血管、脏器被锐器切断、刺破,造成大出血死亡,另有5名重伤。
凶案发生后,郑民生被当场抓获。3月24日,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3月27日,郑民生被提起公诉。4月8日,经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郑民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郑民生提出上诉。4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确认原判决认定郑民生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被告人郑民生因恋爱多次受挫,图谋报复泄愤,竟迁怒无辜,选择在学校门口行凶,持刀连续捅刺,致8名小学生死亡,5名小学生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并且犯罪后果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裁定核准被告人郑民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之后,郑民生被执行死刑。
郑民生被依法处以极刑是罪有应得,然而,郑案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没有因郑民生被执行死刑而消失,类似于郑案的“校园凶杀案”屡见报端,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而,针对此类“校园凶杀案”,以刑法学为视角,进行重新认识和再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法理思考与解析
思考一:是故意杀人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为视角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采取“四要件说”,即对于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罪,依据的是犯罪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等四个要件的相符性。郑民生主观方面是故意,客观方面持刀杀害小学生,并造成8死5重伤的严重后果,违反了我国刑法的规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罚的处罚,因而构成犯罪,这一点比较明确。然而,是否以杀人为目的而故意实施的行为都是故意杀人罪呢?回答是否定的。
从表面上看,郑民生出于杀人的故意,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结果也造成了他人的死亡,虽然死亡的人不是“特定的人”,而按照“概括的故意”[1]和犯罪对象“具体符合说”[2]的观点,只要造成了人的死亡,郑民生的杀人行为就已经完成,从而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既遂状态,因而,判处郑民生故意杀人罪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深入分析郑民生的犯罪行为和动机,及其社会危害性和造成的影响,加之法院的判决理由,从规范刑法学及犯罪构成理论来分析,定故意杀人罪似乎也存在一定的疑问。
(一)犯罪客体分析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共同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具体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针对的是个人最为珍贵的“生命”。从郑民生所实施的持刀杀人的行为来看,直接针对的是小学生的生命,非法剥夺的是人的生命权,似乎郑民生的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并无疑义。然而,透过郑民生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行为的现象,看到的却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深深刺痛的是广大社会公众的心理安全防线,郑对手无寸铁小学生举起的屠刀,砍伐的是社会公共安全的机体,挑战的是社会公共安全的体系。郑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激起广大群众的公愤,不仅仅是因为郑的凶残和冷酷,更在于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担忧。可见,郑的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与其说是人的“生命权”,不如说是“公共的安全”,其所犯的罪行与其说是“故意杀人罪”不如说是“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犯罪客观方面分析
从本案看,郑民生的犯罪地点是在“小学门口”这个公共场所,犯罪手段是“冲进校园,持刀砍杀”的方式,犯罪对象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犯罪结果是8死5伤的严重后果,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并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和混乱,由以上犯罪客观方面分析,郑民生以危险的方法,针对不特定的人所实施的砍杀行为,应当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故意杀人行为。郑案之所以被看作是故意杀人罪,是由于郑民生所采取的砍杀无辜的行为方式,以及造成多人死亡严重后果的“表象”,对人们视觉的强烈冲击和精神刺激从而影响了人们深入的分析判断,假如说郑民生所采取的不是持刀砍杀而是其它方式,诸如扔炸弹、开车冲撞、放火焚烧、投放有毒物质等方式,在这种特定的场所并针对不特定人群的行为,则鲜有人会认为是故意杀人而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
此外,从法院判决理由来看,进一步印证了郑民生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事实。最高院在对郑民生死刑判决的复核中确认:“郑民生因恋爱多次受挫,图谋报复泄愤,竟迁怒无辜”,因而,郑民生杀人的原因是“恋爱多次受挫”,杀人动机是“图谋报复泄愤”(是报复社会而不是报复特定的“个人”),从而“迁怒无辜”造成小学生的重大伤亡,可见,郑民生实质上是通过杀人的手段进而达到报复社会、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目的,说明郑民生的犯罪性质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而不是单纯的“故意杀人”。
(三)刑法价值位阶及选择分析
人的生命权和社会的公共安全作为法的两种价值,既存在位阶先后也存在主体选择的问题。在刑事司法领域,二者作为犯罪客体,其价值位阶的先后及主体的不同选择,决定着刑事司法的最终样态,这一点往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生命的价值优先于公共安全的价值时,刑事司法中对非法剥夺生命的犯罪会表现出不宽容,进而影响定罪和处刑,反之亦然。如在郑民生案件中,若以生命权作为优先价值的话,那么就定故意杀人罪;如以公共安全为优先价值的话,则定危害公共安全罪。当然这种价值位阶是相对的,很多情况下互有交叉,因而,根据特定的条件如何进行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在“义务本位”的社会中,往往公共安全的价值优先于个人的生命权,而在“权利本位”的社会中则与之相反,因而,选择的结果体现了社会主流法思想、法观念和法文化,同时也对社会起着导向和规制等作用。郑案定故意杀人罪,体现了我国在刑事司法领域中“以人为本”“人命关天”等法律思想,也起着引导民意及儆诫、威慑、教育等作用,但同时也可能掩盖了“公共安全防卫”不足的弊病。郑案若定危害公共安全罪,则能体现了防卫社会、国家责任、矫正犯罪等法律思想,有利于提高人们对建立和完善社会防卫体系的重视,进而促进社会法治的整体进步。
思考二:死刑的适用及其执行——以死刑存废为视角
郑民生被判处并被执行了死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议,死刑似乎理所当然。一直被激烈争论的死刑存废问题,在郑案中却没有再起波澜,反对死刑者集体保持了沉默,在平静的表面下似乎是对死刑适用的容忍和认可,此种迹象表明,对于死刑的存废,人们处于一种相对“纠结”和“矛盾”的心态。以郑案为契机,重新认识和反思死刑存废问题,并对死刑“中国话题”进行再检讨。
(一)从实然角度分析,郑民生被判处并被执行死刑,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
我国是一个保留死刑并执行死刑的国家,无论对郑民生定“故意杀人罪”还是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都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情节,应被判处并被执行死刑,从而在规范意义上实现了法律正义,刑法的权威得到了维护。从对郑民生的审判实践来看,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郑就被依法逮捕、起诉、判处死刑并执行,反映了我国对恶性刑事案件“从重从快”的理念,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务中的体现,也表明了我国刑事司法对该类案件的基本态度。
(二)从应然角度分析,郑民生被判处并被执行死刑,是现实社会条件下的最佳选择
1.郑案适用死刑的合理性问题。唯物辩证主义认为,符合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是合理的,事物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只有达到质变,旧事物才会消亡,新事物才会产生。在我国,死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死刑的适用范围及方式虽历经变化,但在我国刑罚体系中仍然是一种主要刑种而大量适用,广大民众和刑事司法机关对死刑仍然有着广泛的信赖和深深的依赖。可见,死刑虽是旧事物,但尚有强大的生命力,尚无新事物可取而代之,足见在现阶段其存在是合理的。
2.郑案适用死刑的道义性疑问。反对死刑者认为“人的生命生而具有并不得剥夺”,因而认为适用死刑是非道义的,是残酷和野蛮的,是同态复仇的体现,是对人的不尊重,确实如此吗?刑罚作为一种“人为”施加的痛苦,增加了社会“痛苦的总量”,对任何被处刑者都是残酷的,可见,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刑罚本身就存在着道义性的疑问,因而,一味地突出和夸大“死刑”的非道义性并不公平。剥夺生命真的残酷吗?自杀是对“自我”生命的剥夺,并不认为是残酷的。死刑是对“他人”生命的剥夺,肇始于严重的刑事犯罪,黑格尔甚至认为,“刑罚是罪犯自由意志的选择结果,适用死刑是对罪犯理性存在的尊敬,并且罪犯已经通过自己的行为给予了死刑适用的同意”,[3]死刑形同自杀,并不能认为是残酷的。现实中有的罪犯,但求一死,以获得自身的救赎和精神的安慰,死刑实为一种解脱而非残酷,不适用死刑似乎却成为不正义了。
3.郑案适用死刑的目的性辩解。郑案发生后,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并激起很大的民愤,对郑民生适用死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民意”,即为广大群众所认可的,并在司法实践中所遵奉的底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本质上却是刑罚“报应主义”的体现,实现的是刑罚报应目的。郑案的恶劣影响远不于此,校园凶杀案的“示范效应”及其“传染性”,膨大了其社会危害性,必须予以扼制,因此通过对郑民生处以极刑从而预防犯罪,是郑案死刑适用的另一目的——预防目的。报应体现了情感,预防体现了理性;报应着眼于现在,预防面向着未来;报应呈现冷漠的面孔,预防带着默默的关怀。对郑民生适用死刑,能够实践并实现刑罚报应、预防目的“二元论”的主张,尤其是在我国“无期徒刑的最短执行期限只有10年,死刑缓期执行的最短执行期限只有12年”,在没有完善的死刑替代刑罚并且现行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不能起到足够报应与预防犯罪的情况下,对郑案适用且只能适用死刑。
4.死刑的误判不构成废除死刑的正当理由。审判活动实质上是对已发案件的证成过程,是对案件事实的还原与推定过程,是特定司法程序及其规定中法官所认定的事实,“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也不等于客观真实”,[4]在此意义上误判不可避免,对于一般刑事案件如此,对于死刑案件亦如此,因而减少误判而不是消灭误判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剥夺生命和自由的误判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不可逆转的,生命只有一次,自由亦不可回复,在特定语境及条件下,生命并不必然重于自由,不可过分夸大死刑误判的严重后果而视其为“洪水猛兽”,死刑误判只是客观存在的刑事误判之一种而矣。此外,刑事审判是法律程序,是实现实体正义的保障,不能因司法程序上可能存在的误判而废除实体上的规定,否则即为“本末倒置”,因而,“死刑可能存在的误判不能证明死刑存在的非正当性”,因而也不是废除死刑的正当理由。
总之,死刑是存是废要综合考虑,在我国,由于没有长期监禁刑作为死刑的替代,报应刑主义根深蒂固,民意广泛支持,司法成本投入不足,恶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等社会条件下,死刑宜存不宜废,但应从实体和程序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思考三:对被害人赔偿亦或补偿——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郑案中,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处郑民生赔偿每个死亡孩子家庭40万元至41万元不等,伤者家庭1万元至3万元不等,共计330多万元。然而,根据郑民生的经济状况及其被执行死刑的事实来看,民事赔偿判决只能成为“空判”,被害人的经济赔偿、补偿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也就难以最大限度的籍慰被害人的伤害,从而很难通过“尊重被害人,保护被害人”,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或补偿等方式,进而实现恢复性司法的最终目标。
(一)尊重被害人,保护被害人,满足被害人的合理诉求是恢复性司法的应然之义
受到侵害的被害人,有着急切需要国家司法权尊重与支持的诉求,被害人境遇的改善,离不开国家司法权的积极行使。如果说犯罪是由社会因素引起的,犯罪是社会中存在的必然现象的话,那么,社会就应对犯罪人和被害人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和国家责任,一方面是对犯罪人的矫正,使之早日回归社会;另一方面是对对被害人的补偿,使之境遇得到改善。在国家司法权接管“私力救济”的法治社会,被害人个体寻求权利保护的力量较小,“在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在人格的发展过程中,个体消除挫折、冲突和焦虑的主要机制是自我防御。当自己所能采取的正常和理性方法对降低和解除焦虑不能奏效时,个体就会转向自我防御机制的非理性方法。”[5]而当被害人不能够有效地借助国家权力寻求保护,平复其所受的伤害时,被害人对社会的不满可能转化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而,国家应当承担起对被害人更大的责任,通过国家补偿等方式,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改善被害人的境遇,最终不仅在矫正犯罪人方面实现恢复性司法,同时也在“关注与尊重被害人,保护被害人”的另一面实现恢复性司法。
(二)亟需探讨并制定有关被害人补偿的法律机制
郑案中,由于客观上的原因,被害人家庭无法从犯罪人那里得到应得的经济赔偿,同时,由于国家补偿机制的欠缺从而使被害人无法得到国家的经济补偿,被害人在犯罪行为的侵害下陷入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困境,因而,对被害人的补偿不仅是道义责任,更应是法律责任,不仅是善举,更应是义务。郑案不是个案,“根据广东省高院的统计显示,全省受害当事人无法获得经济赔偿的比例高达75%,截至2006年年底,全省无法执行的刑事被害人赔偿金额达数亿元之巨”。[6]可见,对被害人补偿是一个亟需面对的社会和法律问题。环视世界,国外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已经建立且比较完善,早在1963年新西兰就制定了世界首部《犯罪被害人补偿法》,1965年美国制定了《暴力犯罪被害人补偿法》,1976年德国制定了《暴力犯罪被害人补偿法》,在亚洲,日本、韩国、泰国、我国的香港与台湾地区也通过了对被害人补偿的立法。在我国,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制度还是一片空白,因而亟需借鉴国外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做法,尽快建立被害人救助及补偿的相关制度。
在我国,关于被害人待遇及救助的问题也正在逐步从理论热点走向司法实践,在全国人大第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在回顾2009年工作中指出,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共救助生活确有困难的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285人”。最高法也在 《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中提出,要按期完成刑事被害人救助、司法公开制度等5项改革任务的实施方案。”因而,探讨和制定有关被害人补偿的法律机制,减轻或消除由郑案等严重刑事犯罪引发的悲剧,从而才能最终实现恢复性司法所要达至的理想目标。
注释:
[1]张永红:《概括故意研究》,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
[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页。
[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3-104页。
[4]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基本范畴》,载《北方法学》2009年第1期。
[5]乐国安:《社会心理学理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6]曹晶晶、李惠媛:《广东试点国家救助刑事被害人》,载《新快报》2007年9月6日。
*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27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