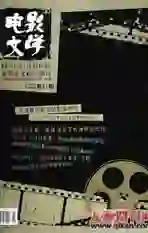《邦尼和克莱德》:反叛、宿命和执著
2009-07-14王晓丽
王晓丽
[摘要]对正统文化的反叛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冲动,黑社会和温柔乡成为人们反抗主流正统文化的两条道路。类型片《邦尼和克莱德》借助现实和形式交织的电影语言,叙述了主人公持枪暴力抢劫的生命历程,以一个“黑社会”的故事表现了人们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以及反叛的限度,展示了人类反叛正统文化的执著以及难逃失败的宿命。
[关键词]反叛;限度;宿命;执著
逃避正统文化的压迫,历来有两条路:一条是黑社会,一条是温柔乡。一本《水浒》,一本《红楼梦》,一红一黑,中国人以简明的方式提供了反文化的两种基本形式。武夫多会铤而走险,如林冲被逼上梁山,挑起造反大旗,而诗人、哲学家则容易怜香惜玉,从而堕入后者,如贾宝玉穿梭于大观园。
一、反叛和限度
强盗片《邦尼和克莱德》是一部典型的美国类型片,主人公是备受人们同情的两位小人物,从州立监狱假释的年轻人克莱德和咖啡厅女招待邦尼。影片通过二人的暴力抢劫故事,对美国当时的社会秩序进行了批判。
影片故事发生在一个经济萧条、价值观念混乱的年代,上层虚伪堕落,就如同那一对互相欺骗伪饰的男女,下层受侮辱受损害,好比那一家搬迁流浪的农民。在这样的世界,克莱德选择以持枪抢劫的形式作为自己活着的方式,这既是他的生产方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抢劫既是手段,本身也是目的。他自由选择并承担责任,走上了暴力的道路,一条注定无法回头的道路。克莱德也许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沉溺于温柔乡中,就像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抑或是像关汉卿不满元朝统治,自堕于勾栏瓦舍中谱曲唱词。但他选择了暴力的道路,他的性无能暗示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无法堕入温柔乡。主观和客观的因素都促使他走上与国家暴力机器相对抗的道路,命运决定了要么他屈从于他所进攻的世界,要么做一个孤独而注定失败的斗士,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年轻漂亮的邦尼出生于古板的大家庭,穿着令人痛恨的粉红色制服,敷衍粗鲁的卡车司机的打情骂俏。无聊、黯淡、单调的咖啡厅女招待生活令她厌倦,她畅想另外一种优雅、闲适的生活:穿越德克萨斯、密西里、奥克拉荷马,走进达拉斯的爱达佛饭店,穿着美丽的丝裙,住进高雅的套房,旁边是垂手而立的侍者。这种梦想使得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加入暴力抢劫的道路变得那么合情合理,那么自然。
持枪抢劫的道路上有新鲜、兴奋、蒯激,在亲眼看到克莱德持枪抢劫一家店铺后,邦尼欣喜若狂地狂吻克莱德。这种超越日常生活之外的情感正是邦尼想要的东西,她一直梦想却在现实中迟迟不能出现的东西。这时候邦尼的心情犹如那明快的音乐和清新的大自然景色,以乐景写乐情,此刻的影片给人以轻松、心旷神怡的感觉。影片的前半部分将二人的反叛故事浪漫化,但随后发生的一切并不像最初想象得那么惬意,最初的抢劫只不过是非暴力的武装行为,但当后来为了脱身无奈实施暴力后,抢劫开始变得不那么美好。
邦尼和克莱德离经叛道的反叛是有限度的,他们并不是彻底否定这个社会,他们反对的只是社会的不公和上层的堕落、虚伪,电影中他们对那对中产阶级恋人的讽刺表明了他们的姿态。邦尼和克莱德反叛的基点和内核是纯朴诚实,真诚怜悯,他们是想涤清损害这个社会真情圣洁的功利、平庸与虚伪。这种反叛姿态就如同中国古代的竹林七贤,他们反抗的只是虚伪、欺世盗名的礼教。但邦尼和克莱德暴力的反抗形式往往会超出他们的控制,超出他们的限度。他们在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伤及无辜,这让他们为之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当他们打死一个反抗的银行经理时,他们发现反叛的外部行动已经与理想内核相抵触,这让他们感到一种深不可测的莫名恐惧。因为这时他们的反叛从开始的人与世界之间,走向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双重纠葛,而人与自我不可见的搏斗激烈程度更甚于可见的与外在敌人的对抗。邦尼和克莱德的反叛已经超出了他们最初的边界,超出了生命的限度。
随着跨越限度和边界后的暴力升级,流亡痛苦逐渐加剧。他们开始面临随时可能被捕或死亡的危险,与年迈母亲离别的伤感和无奈,与警察短兵相接的残酷,不可避免的肉体的伤痛,而更可怕的是那种逐渐加强的不稳定的感觉。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能摆脱对稳定的长相厮守的渴望,克莱德性功能的恢复则使得这种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这是人类共同的特性,就像《水浒》最终不免招安,江湖豪杰在闯荡江湖后总是向往退出江湖,归隐田园。完整和谐的生活情趣总是吸引着人们,小说《红旗谱》中春兰憧憬革命胜利后这样的乡村生活,“黎明的时候,两人早早起床,趁着凉爽,听着树上鸟叫,弯下腰割麦子……在小门前点上瓜,搭个小窝铺,看瓜园……她也想过,当他们生下第一个娃子的时候,两位老母亲和两位老父亲,一定很高兴……”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抗争生活之后,人们都会向往万家灯火的小巷人家。但这种愿望注定无法实现,只不过是一种梦想,就像《水浒》中英雄的凄凉下场。影片以血腥残酷的场面作为结局,死神在一片风平浪静中骤然出现,令人猝不及防。
二、宿命和执著
邦尼和克莱德的身上具有现代人的气质,他们超越边界,超越道德,却无法超越悲剧。当他们以日常生活中散见的暴力来对抗背后隐藏的、庞大的国家机器,以非主流文化对抗主流文化时,悲剧结局就已经为他们预设好了。
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对抗,总是以非主流的失败作为结局。如同中国古代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不管是主动招安还是被动求佛,梁山、花果山的非主流反抗最终被主流文化所整合,难逃失败的宿命。梁山上这个庙堂外自由的聚义厅从它改为忠义堂的那一刻起,它的悲剧结局就渐行渐近。花果山的自由生活使得它在制度森严的天宫外别有洞天,只可惜从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那瞬间开始,这种非主流的生活空间也就被压缩得所剩无几,孙悟空也只能在主动或被动的返乡中享受片刻的欢愉。从克莱德和邦尼持枪抢劫第一个目标起,他们就走上了一条永远无法回头的不归路。主流统治不允许异端的存在,它为它的每一个反抗者都准备了同样的归宿——断头台。
对于失败的结局,克莱德和邦尼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他们从一开始就料到自己的结局,只是没有料到自己的结局以何种方式,何时何地到来。他们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具有悲壮的气息,让观众在为他们扼腕的同时,也为他们的勇敢感到豪情万丈。二人在受伤躲避时仍愤怒地表示要去抢劫草原银行,以此来使警察的污蔑变为现实。在这种先有罪名后有犯罪事实的情节中,恰好透露出当时官方的无赖和社会的荒诞,烘托出二人的勇敢和光明磊落。正是在反抗宿命中,克莱德和邦尼的身上体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尽管在抢劫中建构自己的非主流生活方式最终是一个失败,尽管总是以悲剧或破碎的形式呈现,但建构的过程却洋溢着一种动人的执著,虽然这执著伴随着难以言表的沮丧和悲哀。
在克莱德和邦尼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包法利夫人的影子,那种渴望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生活,并为之奋斗的
精神信念。包法利夫人不断尝试生活中未知的新鲜的部分,设想成为另一个更好的样子。在她从乡村迁到永镇的新居时,作品这样描写她的感受,“这是第四次她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每次都像在她生命中间开始一个新局面。她不相信事物在同一个地方,老是一个面目,活过的一部分既然坏,没有活过的一部分当然好多了”。爱玛不断追求新局面的打开,把自己憧憬为另一个更好的样子,只不过残酷的生活进程不断扼制了她的梦想和神话。德·戈吉耶由小说而发明“包法利主义”这个名词,定义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邦尼便是这样,渴望改变生活的她加入了抢劫的道路,尽管注定不会有好的结局,个人的力量最终无法对抗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但她却为之付出了不懈努力。
这种执著的精神穿越文化和时代,成为人类共同的集体无意识的冲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水浒》《红楼梦》《西游记》无不体现这种反抗主流文化的意识,展示了反规范的社会结构,反规范的生活方式。毛泽东特别欣赏这种精神,《贺新郎·读史》下阙写道:“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矫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竞,东方白。”一部二十四史竟要从盗跖庄踽写起,足见毛泽东对这种反抗文化的重视。
一个时代和国家的社会忧虑和精神焦虑会在它的艺术中表现出来,作为“一种寻找内容的形式”的类型片,“反映广大观众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忧虑,可以被看做是当代的神话,是日常生活的种种事实具有哲学的意义。”强盗片在不断重复同样的故事和仪式中,让人们宣泄内心深处的对主流文化的不满和反抗,也正是这种艺术功能的存在,才使得强盗片这样的类型片以及其他的类型片长久受到人们的欢迎和欣赏。
三、现实和形式的交织
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电影中有时是很难区分的,现实主义也好,形式主义也好,作为一部影片,它必须从杂乱无章的现实中选择其中的细节来作为自己要表现的对象,不同的是这种选择在现实主义的影片中表现的不及在形式主义影片中那样明显。
整体上看,影片《邦尼和克莱德》是一种写实的风格,没有什么特殊的样式翻新的技巧以及独特的蒙太奇剪辑,而更多是隐藏在摄影机后的对现实的忠实记录和客观表现,较多的全景镜头和长镜头,很少主观评价和炫耀,但却不失一些表现主人公心理和精神真实的细节,使得影片更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
电影一开始就用一系列近景和特写镜头表现邦尼在家无所事事的活动,女主人公锤打床头的动作以及抑郁的眼神都显示了她此刻的烦躁、无聊,为其以后走向抢劫的道路作了铺垫。影片在表现邦尼与母亲相见、离别的场面时,对邦尼和母亲都用了特写镜头,将邦尼渴望安慰母亲,和母亲对现实的清醒以及对女儿担心之间的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母亲说出“你最好继续逃亡”时,邦尼的脸上是震惊、凄凉、无奈,有连续两次轻微的抖动。当未来生活的前景由母亲说出来时,无疑更有震撼力,这里面既包括了邦尼对以后生活的忧虑,还有不仅无法陪伴母亲反而还让母亲也为自己担心的不忍。这些特写镜头都让观众对邦尼充满了同情,而这也正是影片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所需要的艺术效果。一般来说,摄影机离拍摄对象越远,我们的情感投入就越中立,更容易采取超脱的情感来对待。反之,我们和影片中的人物越近,就觉得在感情上和他越亲近,那时,我们就会投入更多感情。“拍喜剧片用全景,拍悲剧片用特写”,卓别林的话无疑是有道理的。
在他们被包围,克莱德胳膊中枪倒下邦尼去扶他的时候,影片曾用俯拍角度来营造出困窘、绝望、孤立无援的气氛。而影片最为震撼的则是结尾的屠杀,我们已经习惯地认为危险潜伏在黑暗中,而影片却将屠杀放置在景色明媚的乡间小路上,这场在光天化日下的致命袭击带来了更加强烈的恐怖效果和震撼力。之前两人的卿卿我我瞬间变成了一场对手无寸铁恋人的残害,在暴风骤雨般的枪弹声中,邦尼和克莱德犹如无助的兔子死在猎人的枪下,令观众为之震惊、扼腕。“以乐景写衷情,一倍其哀”,观众的同情心在这一刻被最强烈和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那种惯常的警察最终抓获罪犯的正义感和喜悦感,在这部影片中被完全屏蔽在外,警察的胜利与其说是政府的正义武装镇压,还不说是一次卑鄙和阴险的个人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