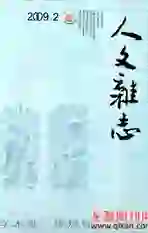论元曲奇崛的文化特质
2009-05-11高益荣
高益荣
内容提要
我国传统文学观念由于受儒家诗学精神影响,强调“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即使对时政的批评也是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到了元代由于蒙古人入主中原,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文人地位的下降使之于传统文学精神产生了背离,从而使元曲表现出新的文化特质,即:突破传统的“中和”观念,大胆歌颂人性爱和本能欲望;看破红尘,陶醉山水,皈依佛老;揭露社会的黑暗,带有明显的草原文化的“蒜酪”风味。
关键词 元曲 传统文学精神 文化特质
〔中图分类号〕I20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2-0110-07
作为元代文学主体的元曲,在其所表现出的时代精神、张扬个性、揭露黑暗、赞美人性等诸方面,都表现出同传统文学观念不同的奇崛的文化特质,显现出新兴文学样式的博大生命力。
一、热情歌颂人对情爱的追求,突破理学对人的合理情感扼杀的樊笼
不管是杂剧,还是散曲都表现出对爱情、乃至情欲的肯定,作者有意突破传统观念对人的束缚,闪现出人性解放新思想的火花。
追求爱情虽说是人的本能欲望,但传统的观念认为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的所有感情,都要受到理(礼)的制约,不能违理而行。表现爱情虽然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之一,但传统的文学观念却认为对爱情的表现应该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和“乐而不淫”等原则,不能毫不掩饰地表现。宋儒更是把包括爱情在内的所有“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朱熹就说:“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注: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4页。)他完全把人欲和天理对立,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因此,在元以前的正统文学里即使描写爱情的作品,也往往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如元稹的《莺莺传》只能为男主人公开脱罪责,表现为“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结局,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也只能发出“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的劝戒之词,很难表现出爱情的轰轰烈烈之美。元曲则不同,它往往能突破封建理学牢笼,毫不掩饰地表现爱情(包括情爱、情欲和性爱),显示出全新的思想特征,大胆热烈地赞颂男女对爱情追求的精神,谱写出一曲曲以情反理的赞歌。
《西厢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王实甫不但提出了男女婚姻要以真挚爱情为基础、两情相依,而且大胆地肯定人欲,细腻地展示了崔张二人追求情爱的心理历程,具有现代情爱的意味。正如瓦西列夫所说:“研究和观察表明,爱情的动力和内在的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属的本能。”(注: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他用生动的语言表现出崔莺莺和张生这对妙龄青年对彼此的爱慕正是本能欲望推动的作用。作为相府千金的莺莺在佛寺邂逅相遇一男子,按照封建礼教她应回避,但她不但不回避反而“尽人调戏軃着香肩,只将花笑拈”,临走时居然还敢“回顾觑末下”。崔莺莺的这些举动,表明在她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被压抑的青春本能欲望需要释放。张生更是如此,他功名未遂、本欲到京城应试,当他见到莺莺就把原来准备博取的功名忘得一干而净,完全被莺莺的美貌所打动:“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是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到半天。”张生之所以对崔莺莺一见钟情,首先是因为被她的美丽容貌所吸引。戏曲通过一系列的感情纠葛,这对有情人终于挣脱礼教牢笼的束缚,大胆合欢。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的首次结合进行了毫无掩饰的、淋漓尽致的描写:“我将这纽扣儿松,把搂带儿解。兰麝散幽斋,不良会把人禁害,怎不肯回过脸儿来?”“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这种描写,完全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传统观念。作者的反传统精神可谓惊世骇俗。《西厢记》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被列为禁书,这便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作者的心目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欲和性爱是符合人性的,因而也是美好的,幸福的
,合理的,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歌颂。这正如奚海先生所说,人欲和性爱是“人类蓬勃奔放、创造生命的永恒活力,是每一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因而是美,是善。人们不应被‘天理、‘礼的伪善说教所欺骗而对‘人欲、‘性遮遮掩掩,噤若寒蝉,而是要勇敢地去拥抱‘人欲,理直气壮地去享受性爱的美和幸福”。(注:奚海:《元杂剧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如果说崔莺莺是经历了一番思想的斗争最终才“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般艰难地走上追求幸福的大道的话,那么白朴的《墙头马上》里的李千金却是毫无羞涩忸怩之态,她完全把追求爱情幸福放在第一位。作为一位大家闺秀她在三月上巳佳节因见屏围所画才子佳人,便春心荡漾,大胆狂想:“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宁可教银缸高照,锦帐低垂;菡萏花深鸳并宿,梧桐枝隐凤双栖。这千金良夜,一刻春宵,谁管我衾单枕独数更长,则这半床锦褥枉呼作鸳鸯被。流落的男游别郡,耽搁的女怨深闺。”当她在墙头上看见裴少俊就迸发出火辣辣的爱慕之情,并想象着两人暗中结合后的性爱生活:“休道是转星眸上下窥,恨不的倚香腮左右偎;便锦被翻红浪,罗裙作地席。既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爱别人可舍了自己。”对于裴少俊的主动求爱,她大胆应允,当晚便与裴少俊在自家花园幽会,后又离家私奔,随裴少俊来到裴家,秘密在后花园同居生子。白朴笔下的李千金,为了追求情爱和性爱,视封建礼教如草芥粪土。充分表现出女子在追求爱情中的主动性,大有现代女作家王安忆笔下的那种“颠覆了女性性屈辱的文化传统,女性终于焕发了原有的光彩,女性的生命欲望得以淋漓尽致的宣泄与张扬”,“让女主人公在性行为中掌握主动,使情爱表现为性爱,透露了女性意识的真切觉醒”的味道。(注:李小玲:《中国文学女性形象中的洛神原型及其现代重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在送别赴京应试的意中人王文举后,相思难耐,一病不起,灵魂离体,背着母亲,月夜紧追王文举并向他表示说:“我本真情”,即使母亲知道了,自己也“做的不怕”,于是灵魂跟随王文举一块赴京,充分表现出她为了爱情敢作敢当的豪侠气概。最能说明“人欲”战胜“天理”的是《竹坞听琴》中的老道姑。她谆谆告诫初入庵的郑彩鸾:“须要坚心办道,休要半路里还了俗。”当她得知郑彩鸾离庵还俗与心上人喜结良缘时,她便怒气冲冲地找上门指责郑彩鸾,巧逢前来造访的梁公弼却是她离散多年的丈夫,于是她马上改变态度说:“我丢了冠子,脱了布衫,解了环绦,我认了老相公,不强如出家!”作者借郑彩鸾之口揭示出人们追求性爱的不可抗拒性:“多应是欲火三焦,一时焰起,遍身焚烧。似这等难控难持,便待要相偎相傍,也顾不得人笑人嘲。”因而她让师父和自己“总不如两家儿各自团圆,落得个尽世里同享欢乐”。戏剧通过师徒二人还俗的故事热情讴歌了追求性爱是人所具有的本能属性。《留鞋记》里的卖胭脂女王月英见到秀才郭华便情不自禁地感叹:“好个聪俊的秀才也。”而郭华更是为情而痴,“日日来买胭脂,若能勾打动他,做得一日夫妻,也是我平生愿也。”于是二人密约元霄夜在相国寺观音殿中相会,王月英到时,郭华因酒醉而卧,王月英推唤不醒便以帕裹鞋放在郭华怀中而去。郭华醒来后发现绣鞋,悔恨吞帕而“死”,后包公断他们二人为夫妻。《萧淑兰》里的萧淑兰更是一位为了追求爱情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子。她看上了她家的坐馆先生张世英便不顾一切主动向张世英示爱,遭到张世英的拒绝,她仍不泄气,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婚姻理想。人世间是如此,即就是神仙世界也是如此。《误入桃源》、《柳毅传书》、《张生煮海》等剧作“通过一个个不惜违逆‘天理,跨越人神、仙凡鸿沟而勇敢追求爱情幸福的令人迷醉的浪漫故事,进一步歌颂了人类爱欲的合理性”。(注:奚海:《元杂剧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在散曲里这些剧作家更是高扬人性美的大旗,大胆突破传统观念,热情赞颂性爱情欲,撕去传统文人的羞羞答答的伪善面孔,歌真性情,抒本能欲,表现出与传统决裂的“铜豌豆”精神。作为元代的“梨园领袖”的关汉卿直言不讳自己对性爱的追求“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并永不回头:“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痛快淋漓,嬉笑怒骂,表现出他风流倜傥的奇特个性。如他的《双调•新水令》套曲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的幽会,从等待、见面、接吻,直到“地权为床榻”的交媾,风格大胆、自然,毫无忸怩之态。再看他的《一半儿•题情》:“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头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诗里完全是真情的流露,火辣辣的欲望的喷泄,让苍白无力的“天理”见鬼去吧!再如白朴的《阳春曲•题情》:“笑将红袖遮红烛,不放才郎夜看书,相偎相抱取欢娱。止不过迭应举,及第待如何?”作者把男女的欢娱置功名之上,认为及第还不如两情相偎更富有人生的乐趣。贯云石的《中吕•红绣鞋》:“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把一对“偷情”人的热烈相爱,既怕分离,但又不得不离的心态描绘得细腻逼真,洋溢着人性美的气息。
所有这些都说明,元曲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传统观念,毫无掩饰地表现爱情,显示出全新的思想特征。
二、在人格理想上同传统精神的背离
中国文人的传统审美观是在儒学的“中庸”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以强调“温柔敦厚”为特征的审美人格,从而形成文人做事持平和的态度,不偏不离的为人准则。压抑个性,以适应社会的规范,文人的最高人生理想便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儒家的这套人格理想已成为后来文人自觉追求的为人规范和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种人生理想,人们必须积极入世,不断进取,即使明知理想难以实现,也要有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执着精神。
可元曲的作者们则不同,他们突破了“治国平天下”等传统观念,表现出看破功名利禄、陶醉隐逸生活的人生理想,显示出全新的思想特征。因为他们出身低下,社会将他们抛入娼丐之列,从而使他们突破传统人格理想,表现出放纵自我,怡情山水,看破红尘,陶醉仙境的人生追求。
这集中体现在占元杂剧八分之一的“神仙道化剧”中。这类戏曲和一味宣扬成仙思想的作品不大相同,它只是借用“神仙道化”的外壳,实际所表现的却是作者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和对新的人生理想的追求。
在元代由于文人的社会地位很低,经济上的极度贫穷击碎了他们美丽的人生梦,长达81年的停止科举,又使他们的仕途之路被堵塞,从而使他们对封建政权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松散,于是促使他们用不同传统的目光重新审视社会,调整自己的人生理想,蔑视传统观念,迸发出异样的火花。这些“神仙道化剧”中的所谓的“神仙”,实际上都是穿着道服的文人,在他们身上,寄寓着元曲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些文人原本也想建功立业,希望能够“治国平天下”,如《陈抟高卧》中的陈抟就说:“我往常读书求进身,学剑随时混,文能匡社稷,武可定乾坤,豪气凌云。”《庄周梦》里的庄子“窗前十载用殷勤,多少虚名枉误人。只为时乖心不遂,至今无路跳龙门”。《猿听经》中的樵夫“想俺这读书的空有经纶济世之才艺”,“空学得五典皆通,九经背诵,成何用!铲得将儒业参政,受了十载寒窗冷”。《黄粱梦》中的吕洞宾“自幼攻习儒业,今欲上朝进取功名”。他们尽管“胸中豪气三千丈,笔下文才七步章”,但在“不论文章只论财”的元代,他们却怀才不遇,仕进无门,只能发出声声愤怨:“将凤凰池拦了前路,麒麟阁顶杀后门。便有那汉相如献赋难求进,贾长沙痛苦谁偢问,董仲舒对策也无公论。便有那公孙弘撞不开昭文馆的虎牢关,司马迁打不破编修院里长蛇阵”。(《范张鸡黍》)
在怀才不遇、仕进无门的情况下,他们转而看破仕途,轻视功名,另换一种活法,像《误入桃源》中的刘晨所说:“幼攻诗书,长同志趣,因见奸佞当朝,天下将乱,以此潜形林壑之间”。既然在社会现实中无法实现“治国平天下”和建立功业的人生理想,他们索性优游林泉,怡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寄托他们的人生情趣,从而消解了传统观念中社会政治功利因素,表现出传统文人少有的旷达,吟诵出一曲赞美隐居的乐章:“卧一榻清风,看一轮明月,盖一片白云,枕一块顽石,直睡的陵迁谷变,石烂松枯,斗转星移。”(《陈抟高卧》)
此曲词,无不表现了文人陶醉隐逸生活、看破滚滚红尘的人生情趣,但它决不是醉生梦死的混世,也更不是完全忘却人世的消极遁世,而是在现实的无奈之时对人生、历史的一种理性的思考所做出的理性抉择。正如刘彦君所说:“当他们在政治归属运动中成为失败者之后,就把目光转向自然,转向倾斜的人生。他们在红尘里放浪,在山林里隐逸,企图寻求一种心灵的归宿。”(注:
刘彦君:《元杂剧作家心理现实中的二难情结》,《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于是他们有意突破传统文人的理想人格,对功名利禄重新评判,想到人生短暂岂能被虚幻的名利牵。他们便对功名利禄进行了重新评价:“古人英雄,今安在哉!华容路这壁是曹操遗迹,乌江岸那壁是霸王故址。曹操奸雄,夜眠圆枕,日饮鸩酒;三分霸王,有喑哑叱咤之勇,举鼎拔山之力,今安在哉?(《岳阳楼》)“岁月如流水,消磨尽自古豪杰,盖世功名总是空。”(白朴《乔木查•对景》)在他们看来,曹操、项羽这些功名盖世的英雄豪杰,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灰飞烟灭,而其所谓的“盖世功名”,到头来亦如一场空梦。功名利禄既被看破,则唯有短暂的人生值得珍惜:“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的斜阳又晚,想这百年人则在这捻指之间。”(《岳阳楼》)于是他们从传统观念中跳出,大声宣告“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马致远《夜行船•秋思》)人生是有限的,红尘是险恶的,何必苦留此处。而应该“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波。槐阴午梦惊破。离了名利场,钻入安乐窝,闲快乐”。(关汉卿《四块玉•闲适》)在他们看来,社会黑暗,尘世险恶,醉心名利,必惹是非,只有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才可在隐逸生活中安享人生乐趣。由于看破功名利禄,陶醉隐逸生活,因此他们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判价值也与传统观念大不相同,受传统文人尊崇的屈原、贾谊受到否定,范蠡、张良、陶渊明等功成身退的人物成了他们人生理想的榜样,“怎学他屈原湘水,怎学他贾谊长沙?情愿做归湖范蠡,情愿做噀酒的栾巴”,(《误入桃源》)“学列子乘风,子房归道,陶令休官,范蠡归湖”(《任风子》)“休想楚三闾肯跳汨罗江”(《贬夜郎》)。张养浩甚至说屈原跳入汨罗江是“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先生畅好是胡来”。(《中吕•普天乐》)这里共涉及到对七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屈原和贾谊都积极追求功业,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而奋斗终生,被传统观念视为文人效法的榜样,但元曲作者却认为他们不值得效法,这种看法当然是反传统的。范蠡和张良是“功名身退”的代表人物,虽然传统观念和元曲作者都对这二人予以肯定,但侧重点不同。传统观念看重的是他们在“身退”之前的“功成”,即他们都曾建立了盖世功业;而元曲作者看重的是二人在“功成”之后的“身退”,即他们最终都走向隐逸。陶潜是典型的弃官归隐者,元曲作者效法他,自可见其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至于列子和栾巴,原本都是道家人物。列子后被道教奉为神仙。栾巴是东汉顺帝至灵帝间人,少而好学,不务俗事,虽曾做官,非其所好,《后汉书》有其传记,道教《神仙传》又载他有“噀(即‘喷)酒为雨以灭火”的法术。无论是道家人物还是道教神仙,都与隐逸生活相联系,而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观念毫不相涉。元曲作者效法这两个人物,其人生理想不言自明。
所以这些都说明,元曲突破了“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观念,表现了看破功名利禄、陶醉隐逸生活的人生理想,显示出全新的思想特征。
三、元曲的批判精神突破了传统的“美刺”观
我国传统诗学强调“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正所谓《毛诗序》所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文学作品虽然可以揭露批判社会,甚至可以批评最高统治者,但不能毫无忌讳地揭露批判,也只能“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遵循“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等原则,即不能直言其过,只能和颜悦色地微言讽刺,情绪可怨而不可怒。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给统治者留些面子,不要使其过于难堪。
元曲则有意背离这一传统,它突破了“主文而谲谏”等传统观念,毫无忌讳地揭露批判社会现实,嬉笑怒骂,无拘无束,酣畅淋漓,自由狂放,表现出奇峭的艺术风格,朱权将其称之为“不讳体”(注: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将“乐府”分为15体,其中讲“盛元体”时说:“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无忌惮,又曰‘不讳体。”见《录鬼簿》(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2页。),沈德符称之为“蒜酪”风味(注:沈德符《顾曲杂言•弦索入曲》:“嘉、隆间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僮习唱,一时优人俱避舍,以所唱俱北词,尚得金、元蒜酪遗风。”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204页。),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奔放与辛辣风格。
身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的剧作,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对黑暗的社会有深刻的认识,对广大人民的苦难有着全面的体会,于是他通过杂剧揭露社会的黑暗,表达人民的心声。正如王季思先生所说:“关汉卿的戏曲作品有不少是直接从当时社会现实汲取题材的。当元朝贵族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黑暗势力跟他们勾结起来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内部有的屈服、逃避,有的起来反抗,更多的是暂时忍耐下来等待时机。关汉卿在作品里反映这些现象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无动于衷地把这些不同人物的生活面貌摄影下来,而是热烈歌颂那些敢于对敌斗争的英雄,批判那些对黑暗势力屈服的软虫,大胆揭露当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各种丑恶的嘴脸。”(注:王季思:《玉轮轩曲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1页。)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对贪官当道、好人受欺的黑暗社会予以有力鞭挞,尤其是窦娥临刑前所唱的“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矛头直指封建“天道”思想,彻底揭露批判了其欺骗人民群众的反动本质。《蝴蝶梦》、《鲁斋郎》以及无名氏的《陈州粜米》都对社会的黑暗势力“权豪势要”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追韩信》、《气英布》和《赚蒯通》毫无忌讳地对最高封建统治者杀害功臣良将的反动本质进行了揭露批判:“兀的不是狡兔死走狗僵,高鸟尽良弓藏?”(《赚蒯通》)《赵氏孤儿》塑造了以程婴为首的一大批舍身成义的悲剧英雄,洋溢着悲剧酣畅淋漓的崇高美;《豫让吞炭》展示了豫让重义轻生的豪侠气概,具有摄人心魂的悲壮美;《介子推》既赞颂了介子推的忠义精神,又揭露了晋文公伪善凶残的本性:“不争你个晋文公烈火把功臣尽,枉惹得万万载朝廷议论;常想赵盾捧车轮,也不似你个当今帝主狠”。另外,《冻苏秦》、《谇范叔》、《王粲登楼》、《贬夜郎》和《赤壁赋》等都是以古讽今,无论是苏秦、范雎,还是王粲、苏轼,实际上在他们身上表现的都是元代文人怀才不遇的现实遭际,戏曲通过他们对元代黑暗的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在散曲中更具有这种“蒜酪”风味。大量作品直抒性情,揭露黑暗,怀疑权威,张扬个性。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的最高统治者,如薛昂夫的《中吕•朝天子》:“沛公,大风,也得文章用。却教猛士叹良弓,多了云游梦。驾驭英雄,能擒能纵,无人出彀中。后宫,外宗,险把炎刘并。”这是专门揭露批判汉高祖刘邦的:刘邦虽然在《大风歌》诗中说“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但他却将真正的猛士(功臣良将)杀戮殆尽,使其发出“高鸟尽,良弓藏”的慨叹,可见他言行不一;刘邦对功臣良将设置圈套,时擒时纵,使其常怀畏惧,俯首听命,可见他善于玩弄权术;刘邦担心功臣良将造反,将其杀戮殆尽,但后来险些篡夺刘汉政权的却是他的妻子吕后家族,可见他聪明险被聪明误。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从一个深知刘邦底细的迎驾乡民的视角,把做了皇帝的刘邦荣归故里的“盛典”写成一出滑稽可笑的讽刺喜剧,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的汉高祖刘邦,在乡民眼中只不过是个流氓无赖而已,从而撕下了封建帝王神圣的虚伪面纱,对至高无上的皇权进行了大胆的揶揄和恣意嘲弄,淋漓痛快,生动泼辣,幽默风趣,具有“蒜酪”风味。再如传遍大江南北的无名氏《正宫•醉太平》:“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揭露和控诉“大元”朝政的腐败和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和官逼民反的社会因素,情辞激越,痛快淋漓,犹如一篇义正辞严的战斗檄文。张养浩《潼关怀古》中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一具有历史规律性的呐喊,更突破历代文人怀古诗抒发个人情怀的传统主题,揭示了在封建制度不加改变的大前提下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封建王朝如何兴亡更替,百姓始终摆脱不了受苦受难的悲惨命运。该曲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实际就是对封建制度本身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揭露批判。
四、元曲奇崛文化特质的成因
元曲为什么会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精神的背离?我们应该从元代的社会、文化和审美风尚等方面因素来考察。
首先,蒙古人入主中原,带来了游牧文化和中原的农业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有利于人们的思想从传统的思想文化中解放出来,接受新的文化特质,背离传统的文化精神,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由于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诚然如此,蒙古人建立元朝后,确实给中原的传统文化带来很大的破坏,但同时也给已接近僵化的中原传统文化输入了新生命的因子。“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蹄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进取的性格席卷南下,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封建帝国被输入率意进取的精神因子。随着原社会僵硬躯壳的破坏,长期被严格束缚的种种和封建社会主体理论离心的思想情绪也乘隙得以暂时抒放。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失去原有重心和平衡的混沌状态。虽然元统治者对汉文化体系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正统意识形态也十分重视并加以提倡,但是,对传统理性和政治现实怀疑、漠视、厌恶乃至反对的心理与情绪,仍然执着地弥漫于社会各阶层中,尤其是下层社会。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具象化,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杂剧。”(注: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7页。)元代社会蒙古人成为统治的中心,他们作出和中原统治者所不同的审美选择,更重视文化的愉悦性。《蒙古秘史》就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跃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加之,他们汉化的程度很低,不了解中原文化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重要作用,更多的是从娱乐的需要来选择,因而传统的诗文受到冷落,代之而兴的元曲受到欢迎。蒙古民族的能歌善舞,草牧文化的豪迈奔放,给原来的中原文化输入“异质”,“为积淀深厚的儒家礼法撕裂了一条缝,使得各种被压抑、深隐的思想能够放纵,脱笼而出,”(注:刘祯:《元代审美风尚特征论》,《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第78页。)从而使元曲可以突破传统文学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审美风尚,表现出草牧文化所影响的豪迈奔放、敢爱敢恨,不受约束的文化特质。
其次,由于元代统治者尚武轻文,看不到儒学对稳定统治的作用,因此,入主中原以后停止科考长达八十年,从而使文人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他们原有的理想信仰、人格追求和恶劣的现实存在之间产生了极度的不协调,从而使他们的理想人格发生变异,形成多面的人生追求:外在的放浪形骸,乐山好水,而内心深处却拂拭不去的现实的不得志的愤懑。
元代文人的人格结构,普遍呈现出儒、道、释融合的特征,如元代著名画家倪瓒在《良常张先生像赞》所说:“诵诗读书,佩先师之格言。登山临水,得旷士之乐全。非仕非隐,其几其天。云不雨而常润,玉虽工而匪镌。其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者欤?”元代的文人自幼就受到儒学的熏陶,笃信儒学的信条,形成其济世报国的人格理想。但元代是蒙古人的天下,汉族失去其中心位置,沦为边缘民族,受到歧视,文人像往朝通过科举一朝天下闻的理想化为泡影,于是只好在道教与禅宗中寻找精神的避难所,但又时时流露出对儒学理想的怀恋。因此,元曲的作家们的人格结构便表现为斗士、隐士和浪子的三位一体。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使他们具有极强的参政欲望,但现实的黑暗、科举的废止,堵塞了他们的进身之途,这便使他们中有些人“绝意仕进”,同统治阶级产生离心,如关汉卿等,从而大胆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成为勇敢的斗士。但他们“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面对着强大的黑暗现实也只能“读书人一声长叹”,于是迫不得已他们只能换一种活法,或者逃入山林,皈依全真,这便是以马致远为代表的“神仙道化剧”产生的社会根源;或者混迹勾栏,与优伶娼妓为伴,放纵人欲,以此表现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便是元曲中歌颂人欲思想形成的根源。
总而言之,由于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游牧文化给几千年已近乎衰微的中原农业文化输入“异质”,使传统的儒家诗学精神被撕破,新思想的灵光闪现。再加之元代科举长期被废止,文人沦落为娼丐之列,贫穷的生活吞噬了他们的传统人格理想,从而使他们与传统的观念不得不产生一种背离情绪,以新的生活方式消解自己内心的愤懑,这就是元曲所表现出的对传统文学精神背离的文化因素,也是元曲繁荣的主要原因。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