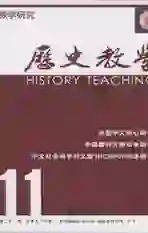有关公车上书的学术研究与争论
2009-03-11杜维鹏
杜维鹏
[关键词]康有为,公车上书,史实真相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21-0063-04
很长一段时间内,“公车上书”的若干史实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已有“定论”,而且被学者们赋予了多重意义。近些年来,随着档案史料的发掘利用,许多学者对“定论”提出了挑战。本文拟对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公车上书”的研究作一简要回顾,归纳学界所取得的新成果。
以往研究者对公车上书这一事件的认识,大都沿袭《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的说法,基本过程是这样的:康有为在3月21日得知李鸿章求和的消息后,即令梁启超等人率先鼓动广东举人80余人,上折吁请拒绝合约,之后湖南、奉天、江苏、山东、湖北等16省举人约31300多人加入到上书的队伍之中。康认为“士气可用”,决定联合十八省举人集会于松筠庵谏草堂,共上“万言书”。至四月初八日投递都察院,而都察院则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收。康认为当时的军机大臣孙毓汶是阻挠此次上书的罪魁祸首。
最早对《年谱》的说法提出质疑的是台湾的黄彰健先生。黄先生采信《公车上书记》《四上书记》的说法,认为《年谱》中所说公车上书于四月初八日投递都察院,与二书均抵触,很可能并未呈递给都察院。黄先生还对《公车上书记》后附的六百零三人签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公车上书记》之刊行,系为了宣传民权,吸收党羽,故序文需说出该书由康草拟。其附《公车题名》,应系故意牵涉多人,使官府不便追究。
继黄先生之后,汪叔子、王凡两位先生也对《年谱》中的说法进行了辨伪。他们于1987年发表了《“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一》一文。两位先生分析了康党叙述公车上书的三种主要史料(即《公车上书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年谱》),指出了其中所记上书人数的三个阶段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为康党的政治宣传服务的。在他们看来,康有为及其门人对上书过程多处作伪,其记录并不可信,康也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袖。孔祥吉先生参酌清官档案作为旁证,间接证明康有为未曾向都察院呈递《公车上书》。
中国近代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公车上书”一事?1999年7月23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姜鸣先生《真有一次“公车上书”吗》的文章。姜先生认为《年谱》的说法大为可疑,且指出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各级官员,他们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当时并不是都察院拒收了康有为的“万言书”,而是康根本就没有去递。因而,作为历史事件的“公车上书”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者“公车拟上书”而已。“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
同年12月17日,汤志钧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公车上书”答客问》,反驳姜鸣先生的观点。汤先生利用《汪康年师友札记》《直报》等史料,证明历史上确曾发生过康有为领衔18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一事。
2002年,欧阳跃峰先生发表《“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一文,再次否定了“公车上书”事件。据他研究,康有为虽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至都察院上书。康梁等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目。
对公车上书事件作出系统考证的是茅海建先生。茅先生对“公车上书”的研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运用了大量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并将档案文献与相关史料互证使用;二是研究视角转向了当时的政治高层,探讨了政治高层与公车上书之间的关系。经过考证,茅先生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其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组织、由梁启超、陈景华等公车直接参与的上书,共计31次,参加的人数达到1555人次;这一概念的“公车上书”,对当时的政治决策起到了微弱的作用。其二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号称18行省举人联衔的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并无作用。第二,公车上书是由翁同稣等政治高层发动的,康梁本人是被策动的对象而非运动的领袖。第三,康将上书的失败归罪于都察院,但并非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茅先生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07年,《近代史研究》连载了房德邻先生《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的文章,一场新的学术论辩由此展开。这场论辩主要围绕以下内容:
首先,公车上书是否由翁同稣等政治高层发动。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公车上书是由康有为组织发动的。而茅先生认为是清廷政治高层中的主战派于三月二十一日有意向康有为泄露了马关条约的内容,幕后的主事者乃是翁同稣。目的是策动公车们上书,“要利用下层的压力,让光绪帝自我否决三月二十日的电旨”。房先生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翁同稣等政治高层在三月二十一日有意向外泄露消息,以鼓动京官和举人们上书反对议和”。余外,房先生还分析了《随手登记档》中所记上书的起因、经过、数量、内容和时间,认为“反对议和的大规模的上书浪潮是从三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而不是茅先生所谓翁同稣等透露《马关条约》内容的三月二十一日开始的,上书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上书人知道了《马关条约》的内容,而是因为知道了李鸿章画押归来的消息”。所以此次上书不是被人策动而是自发进行的。
其次,康有为是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袖。茅先生运用档案中上书举人的名录与《公车上书记》所附的《公车上书题名》比较后指出,康有为对当时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并没有号召力。与茅先生不同,房先生更多取信康有为《年谱》中的说法;认为康有为不仅是乙未年公车上书的鼓动者而且还是18省举人联合上书的倡议者、主持者、上书起草人。以康有为当时的名望领导公车上书是足以胜任的。康是公车上书当之无愧的领袖。
再次,孙毓汶、黄曾源是否阻挠了公车上书。在《年谱》和康有为的学生徐勤所写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中均提到孙毓汶指使黄曾源破坏上书之事。茅先生认为黄曾源在主张拒约这个问题上与康有为是一致的,而孙毓汶当时已经失势“此时他若派人公开阻挠上书,必遭弹章无数。就其政治经验而言,似未必出此下策。”所以两人都没有阻挠康有为上书的动机。此外,茅先生还论证了康有为《年谱》中所说孙毓汶“迫皇上用宝,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诬奏海啸”之事并不可靠。房先生质疑了茅先生的结,论,他认为黄虽然对拒约表示认同,但并不像康有为一样主战,而是“主张贿赂列强、通过列强的干涉来改约”,而且黄、康二人在迁都问题上有很大分歧,这很可能就是黄阻挠上书的动机所在。
最后,康有为上书的失败是都察院拒收还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呈递。这一问题历来是学者最为关注的。据茅先生考证,在四月初六、初八
日两天,都察院的带奏有了两次明显的变化,举人上书的阻力已大为减少。从档案记载来看,自四月初四日开始,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五日都察院均有带奏的记录。由此可以断定,康有为称四月初八都察院拒收上书之事并不可靠。房先生则指出,都察院曾有拒收上书的记录,而拒绝康有为的理由很可能是上书言辞过于激烈。房文还援引天津《直报》、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胡思敬《戊戌履霜记》以证明康有为可能曾赴都察院上书。
针对房先生的辩难,茅先生于2007年发表了《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一文,作出回应。他引用了《退想斋日记》《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等材料,并对《直报》的报道做了新的解读,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这次论争双方所用史料更为丰实,考证更为细腻,讨论的问题也更为广泛,基本上涉及到公车上书的方方面面。最为可贵的是茅先生摆脱了前期研究中就“公车上书”论“公车上书”的思维框架,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当时的政治高层,探讨京官与公车上书的关联。这一研究毫无疑问地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在上述学术争论中,虽然各位先生所引证的材料大同小异,但研究结论却各有不同。原因在于学者们在研究视角与史料解读方面存在差异。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了解,康有为是惯于作伪的,为了政治局势的需要时常制造有利于自己的“事实”与材料,这本身就给历史研究造成了困难;加之学者们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和价值取向,很难对同一史料有完全一致的认识。以茅海建、房德邻两位先生的争论为例,两人的最大分歧在于,茅先生认为从《公车上书记》到徐勤的《杂记》,再到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已经有了多重的“放大”与“层累”。尤其是康有为《我史》中关于公车上书的记录多处有误,不甚可靠,相比之下,较为可信的史料是《公车上书记》中的记载。而房先生则恰与之相反,认为“《序》(即《公车上书记序》)的说法可信度低,而康的说法比较可信”。史家对史料解读的差异之大由此可窥见一斑。诚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历史学家主观的价值观念,自然会影响到其对史料的研读,这是历史学生来具有的先天性缺陷。”正是由于这样的“缺陷”,才使学界对诸如京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举人们上书?孙毓汶是否真的指使黄曾源破坏上书?康党对公车上书一事的叙述究竟有多少可信的成分等问题至今仍未有一确切的答案。
但回避问题毕竟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只有积极面对才能趋近历史的真相。从以上诸位先生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们大都遵循从史料到史料的研究路径,将不同类型的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互证和辨伪,确认其中合乎逻辑的成分,重建史实,却忽略了史料形成的过程与历史语境。茅先生在分析康有为《我史》时,已经运用了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的方法,‘但这种方法至今还未得到国内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不过在笔者看来,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有所突破这不失为一个可资参考的方法。
关于“公车上书”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综观诸位先生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较为成熟的结论。
第一,“公车上书”不能等同于康有为组织的号称18省举人联衔的上书。“公车”即入京应试的举人,“公车上书”就是举人上书。汤志钧先生指出:“甲午战后的‘公车上书有两类:一是赴京应试举人经都察院的少数上书,一是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传统观点只强调康有为“发动”的18省举人联衔的上书,而忽略汤先生所言的第一类“公车上书”。茅先生的两个概念的“公车上书”与汤先生的划分基本一致,茅先生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在他看来:“后一概念的‘公车上书原本只是前一概念的‘公车上书的组成部分;然而,康有为已将后一概念的‘公车上书放大,致使今人将该词汇作为其专用名词。”但二者仍有细微差别,茅先生认为第一类的“公车上书”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不过这一点尚未得到学界认同。故此,从学界对“公车上书”所下定义来看,“公车上书”确有其事。
第二,在关注各省举人上书反对议和的同时不应忽视各级官员上书的作用。茅海建先生对军机处各类档册统计分析后,指出在诸多反对议和的声音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他的研究可谓“证据确凿”,而房先生也未对此提出疑义。
第三,康有为组织各省举人集会的地点——松筠庵地方狭小,似不能一次性容纳一千余人。所以康有为组织上书的方式很可能是茅先生所说“先将上书撰就,然后在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各省举人也是陆续而来,并非为一次千人大聚会”,而且是否所有举人都知晓上书的内容也是问题。
第四,康有为并没有向都察院呈递上书。笔者在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时发现,承认康有为曾向都察院投递“万言书”的学者,主要依据的是康有为《年谱》中的说法,其中只有汤志钧、房德邻两位先生对这一“成说”做了具体的考辨。两位先生虽然例举了几条旁证,但其结论却不具有唯一性特征,可以与他说并存。连房先生自己也承认:“现在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康有为究竟是投书还是没有投书,只能通过相关的周边史料来推测。”而对汤、房两位先生最为看重的佐证材料——天津《直报》,茅海建先生进行了批驳,认为《直报》对当时都察院上书细节的描述不太可靠,可能是因为作者“不完全了解当时的全部情形”。用以证明康有为没有向都察院呈递“万言书”种种的证据,归纳有以下几点:1.根据文廷式《闻尘偶记》所载,文廷式、戴鸿慈曾于四月初三日出奏,弹劾都察院“带奏公呈迟延请教责”,之后都察院就改变了态度,将各省举人上书悉数呈上;2.《公车上书记》所附603名公车的题名是值得怀疑的,名单可能来自松筠庵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反映的只是参加会议的人数,而不是上书的人数;3.松筠庵容不下一千余人;4.依据清官档案所记,在四月初八日,即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之日,都察院带奏条陈有15件之多,唯独不收康的上书似不合情理;5.康有为上书期间都察院对于举人上书的态度已相当宽容。6.《公车上书》内容激进,各省举人是否敢签名值得商榷;7.以康有为当时的身份、威望似乎并不能组织起各省举人共同上书;8.当时众举人的政治觉悟能否到达“变法救国”的高度值得怀疑。由此可见,康有为没有向都察院呈递上书这一论断是可靠的。
寥寥数千言要想囊括80年代以来关于公车上书研究的所有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但笔者所做的学术史回顾,基本可以反映出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向。当然,许多问题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只有随着越来越多新史料的发现与更多史林高手的加入,才能达到茅海建先生所期望“重建一个难存二说的事实”的目标吧!
[责任编辑:任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