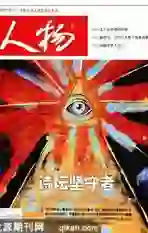奥巴马:让听众为整个故事而鼓掌
2008-05-14毛希
毛 希

2006年夏季的某天,伊利诺伊州南端、沃巴什河沿岸一个名叫卡米的小镇。在一张用几张台子临时拼凑的长桌旁,十来个白人农夫正和资浅的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围桌而谈。此时的奥巴马还没有宣布竞选总统,有着充裕的时间。他坐在长桌的一头,脱去了外套,打着领带,卷起了袖子,倚着凳子的靠背,膝盖轻轻抵着桌沿。这时,一个农夫提出了一个关于生物燃料的问题:
我们一向从玉米中提炼酒精,并且有了一套完备的系统,但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倡从软枝草中提炼纤维类酒精,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为什么政府如此重视纤维类酒精?
奥巴马不紧不慢地回答:
虽然我不是科学家,但按照我的理解,纤维类酒精释放的能量是玉米酒精的8倍,因为它节省了中间糖分转化的环节。目前,巴西生产的酒精要比我们廉价得多,布什正打算让它们进入本国市场。我和资深参议员理查德·宾投票反对,我们支持维持现有税率,让本国的酒精市场能够继续发展,充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和最好的农民,但不希望我们的农民不思求变,原地踏步,只会说‘我们只种玉米和豌豆,对这个没兴趣……
背不起十字架,就戴不起皇冠
了解美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民主党候选人向选民拉票时,通常有3个步骤:首先,他们夸大对方哪怕是鸡毛蒜皮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接下来,他们责备有钱人是如何靠剥削老百姓发家致富,激起对方的愤慨;最后,他们便推销自己未来的施政方针是如何地行之有效,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奥巴马很少这么做,他从不卖弄学问,也不非议他人,而是让对方不知不觉地接受:问题既然已经摆在那里了,我就要动手解决它。他提出的建议往往细致、切实,而非艰深、空泛。比如他曾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健康论坛上做过这样的发言:
我们应该把更多开支用作预防。目前,20%的慢性病患者花费了80%的开支,我们当务之急是控制诸如糖尿病之类的慢性病。只要确保他们当前得到适当治疗,就能省下日后为他们截肢的3万美元。……我们要针对特定人群制订计划,尤其是少数族裔社区里的孩子,确保他们摄取足够的营养,能够吃到水果和蔬菜而不只是炸鸡,给他们足够的空间玩耍,而不是整天把他们困在屋子里。
站在讲台上的奥巴马平静而松弛,言语间既未对患者表现出同情,也没有对政府机构进行嘲讽,又或对社会不公表示愤怒。他只是娓娓道来,告诉他的听众,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出了问题,需要修复。这种理智且克制的作风常被人说成是学者做派,连奥巴马自己也曾把这样的演讲比作他在芝加哥大学里教授的宪法课程。当然“学者做派”还表示另一重含义——炫耀和说教,但奥巴马对此不屑一顾。早在他在哈佛念书的时候,尽管法学院的传统就是推崇博学和辩才,他却对这种炫耀性的学术争论嗤之以鼻。
奥巴马的超然和冷静,使他更接近一名医生——倾听病人诉说病情,自己却从不表现出惊讶,一切都只是习以为常。一些慕名前来听奥巴马演讲、辩论的人或许会感到失望,他深知,情绪上的宣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正如在南亚普遍出现的女性执政,并不代表当地重男轻女的传统已经消失;在美国这样一个白人占多数的主流社会,尚未能接受一个过于激进和具颠覆性的黑人政治家,即便他奥巴马有朝一日当选总统也并非意味着一场“种族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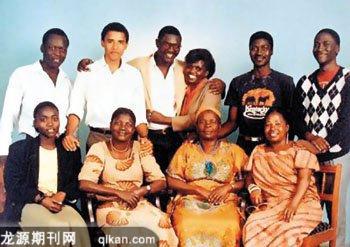
认识奥巴马的人都知道,他具有高度自制能力,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他不追求面面俱到,待人亲切有礼却不过分亲近。他外表整洁,动作流畅,声调平稳,让人不由怀疑他是一名正在饰演政治家的出色演员,因为他的言行举止完美得不像是真的。奥巴马喜欢穿开领衬衫,领带之于他,正如帽子于肯尼迪,但无论何种场合,他从不给人留下戏谑的印象。“人们会拿戈尔和布什开玩笑,但不会拿奥巴马开玩笑。”哈佛的政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说,“不是说他开不得玩笑,但布什可以是傻瓜,戈尔可以是傻瓜,奥巴马却不可以。”
耐人寻味的是,朋友口中的奥巴马和他笔下的自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回忆录《父亲的梦想》一书中,年少时的奥巴马迷茫、愤怒,在白人和黑人的身份中间摇摆不定,不断质问自己“我是谁?”他在现实中苦苦挣扎,只能在毒品制造的幻象中寻求解脱。然而,这不过是奥巴马精心设计的桥段——一个老掉牙的“发现自我”的故事,结局无非是主人公浪子回头。故事中的奥巴马和现实中的奥巴马之间的巨大反差,为他赢得了不少关注的目光。“他很满意自己的肤色,他清楚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奥巴马哈佛时代的同学、现任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马克说,“我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觉得非常惊讶,里面描述的困惑和愤怒,我从不曾在他身上看到。”对此,奥巴马的解释是:“那段日子从15岁持续到21岁,复杂的成长背景加上青春期的躁动,导致了我的所作所为。这并非我的本性,这本书描述的也并非我的全部。我还可以写一本关于打篮球的书,告诉读者我充满阳光的一面。”
为什么奥巴马不选择写一本打篮球的书?为什么要翻出那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在法学院学习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要当芝加哥市长。人们乐于看到政治人物早年的污点,也乐于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他深知,主动承认远比日后被别人挖出来好。同时他是讲故事的高手,他深谙候选人宣传的老套——在校时品学兼优,毕业后工作出色,人生一帆风顺——已不能打动人民。
在芝加哥当社工的时候,奥巴马曾经与很多黑人领袖深入交谈,说服他们加入社区组织。其间,奥巴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有的过去是赌徒,有的是成功的企业主管,然而,他们都曾对所信奉的宗教产生怀疑,在社会底层挣扎,自尊尽失,但最后都重获新生。因而他们对人生充满信心,他们坚信: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正是过去的经历,让他们更具说服力。”奥巴马的在法学院的朋友卡珊德拉·巴特还记得,“巴拉克说过,他最喜欢的一句关于民权运动的话就是‘背不起十字架,就戴不起皇冠。”
回顾往来径,美国梦的开始
奥巴马在政坛上初露峥嵘,要回溯到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他在演说中,把自己的人生刻画为一个“美国梦”:非洲青年和堪萨斯少女建立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爱情,并生下孩子。这个瘦小的孩子有一个古怪的名字,他艰难地成长并考上了哈佛的法学院,成为自内战后的第三名黑人参议员。他摒弃了父辈和祖父辈所追求的人生理想,触及了这个国度某些更深层、更古老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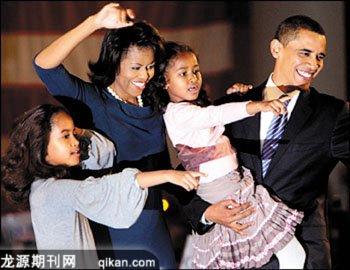
奥巴马的外祖父斯坦利·杜汉在堪萨斯州旗鱼市长大,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无业游民。他对人生毫无规划,只知道自己要离开堪萨斯,离开父母的束缚,离开那个闭塞落后的中西部小镇。《父亲的梦想》里曾这样写道:如果让恐惧和缺乏想象力扼杀了你的梦想,你就只能在这个地方出生,然后在这个地方死去。在外面磕磕碰碰几年后,杜汉结识了一个同样不安于现状的女孩子,两人一路向西,先是搬到加利福尼亚,然后是西雅图,最后停留在国土最西边的夏威夷。
远在8000公里以外的肯尼亚,奥巴马的祖父侯赛因·安扬高为了同一个理由,朝着同一个方向踏出了家门。附近村落的白人移民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使他不再安于现状,他开始穿上欧式的服装,接受欧洲的观念,对一切欧洲的文化心向往之。二战期间,他来到了欧洲,成了英国军队中的一名厨子。
他们的下一代——奥巴马的父母比父辈的思想更为开放。奥巴马的母亲安先后嫁给了肯尼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当两段婚姻均告失败后,她回到家乡夏威夷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然后去了印度尼西亚,花了几年时间在当地务农。她让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自行决定,是跟她离开还是留在夏威夷上学。奥巴马选择了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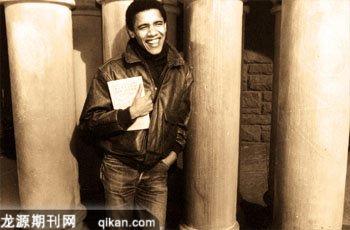
奥巴马的父亲上中学时就被学校开除,父子交恶,断绝了往来,但他顺利考取了留美奖学金,于是抛下怀孕的妻子和儿子,只身来到夏威夷大学攻读经济学。在大学里,他邂逅了安·杜汉,和她结婚并生下儿子巴拉克。没多久,他又抛弃了他的第二个家庭,回到家乡肯尼亚,在政府部门工作,并且和另一个美国女人结婚,生下了两个孩子。几年以后,他的第三个家庭也宣告破裂。由于不满政府的僵化腐朽,他始终郁郁不得志,最后穷困潦倒,只能借酒消愁。
“我的家族的经历,是一连串极度无知的行为。”奥巴马这样描述自己的父辈,然而“无知”对他而言却是不可原谅的。奥巴马很爱自己的外祖父,同时也瞧不起他,“他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美国人,盲目追求个性和自由,却不懂得两者真正的含义。……无知意味着无畏,也意味着无成。骨子里的无知,最终只会让他们陷于失望。”斯坦利·杜汉作为一名失败的保险经纪人,奔波半生,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和那些不曾离开堪萨斯半步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从父亲的经历中,奥巴马的母亲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父亲的问题,不在于他选择了出走这一方式,而在于他走得不够远。因此,她决心走得更远。“他想抹煞过去,凭空地创造一个将来,”奥巴马写道,“母亲不幸也继承了这一想法。”
在奥巴马的记忆中,母亲天真得就像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人物:她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因为她以为世界和她想象中一般单纯,她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不知道离开夏威夷是为了什么——她甚至不知道,在她出发去印度尼西亚前的几个星期,当地刚发生过一场造成数万人丧生的流血政变。即使后来有人告诉了她,也未能改变她的初衷,“在一个以宿命论解释贫穷的国度里,她孤独地捍卫着人道主义、罗斯福新政、美国和平队和所谓的自由主义。”凭着从父亲身上继承来的信念,她固执地相信,“有理性、有思想的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许她该庆幸,她仅仅离了两次婚而不是更多。“情况可以坏得多。”儿子为母亲的一生写下注脚。
天真、率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这几个名词概括了“美国梦”的西迁史:从古老的国家来到新大陆,然后从拥挤的东岸,经过广阔的中部平原,抵达太平洋沿岸。然而对奥巴马来说,这个梦过于浅薄和浮泛,失去了它应有的深沉。当奥巴马第一次踏上肯尼亚,才真正了解父亲的一生——他为了抵抗古老的体制,甘愿赔上自己的前程,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凭信念改变社会。肯尼亚的阿姨告诉奥巴马,父亲一直不明白,“如果把所有人都看作你的家人,你就根本没有家人可言。”追求世界大同和绝对的人身自由并不切实际,因为那意味着你要放弃你的信仰、父母、家乡、朋友和原有的生活方式。
轮到奥巴马离家的时候了,他刻意沿着与父辈相反的方向前行:先是回到美国本土,在加利福尼亚上了两年大学,继而到了纽约,最后是芝加哥,回到了外祖父母当年离开的中西部,重拾他们错过的一切——厚重的历史、悠久的传统、局促但融洽的社区,并学会用一生去经营与一群人的关系。他同时包容了暴力、污秽、褊狭,因为这构成了当地文化的一部分。他开始着迷于一个世纪以前,从南方迁移到芝加哥的黑人移民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文化。“借由他们的记忆,我和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发生了联系。”奥巴马坦言。
离开出生、成长的故乡,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奥巴马似乎在重蹈覆辙。但与父辈不同的是,他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家庭和出身,努力在既定的事实上作出最佳的抉择。他希望在芝加哥扎下根来。奥巴马选择米歇尔·罗宾逊作为终身伴侣。米歇尔出生于一个血统纯正的、来自南方的黑人家庭。在芝加哥,奥巴马放弃了原有的工作,扮演起社工的角色,并成为一名基督徒。“我为了解而来,”在自己的第二本书《无畏的希望》中奥巴马写道,“只有让工作成为我的信仰,才不至于失去生活的重心,我向往母亲的自由,却不愿继承她的孤单。”
困在民主党内的共和党灵魂?
27岁进入哈佛法学院,此时的奥巴马早已脱胎换骨。他不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你绝不会想到他是黑人和白人混血的后代,”肯尼斯·马克说,“也绝不会想到他在夏威夷长大。他就是一个在芝加哥长大的黑人,一个来自中西部的黑人。”
美国人坚信,自由可以凌驾于历史之上,奥巴马却拒绝相信,哪怕它以“民权运动”的形式出现。他认为,这场运动改变了从肯尼迪当选总统到《投票权法案》获得通过这段时期历史的走向,它看似是一场大同主义对抗狭隘种族观念的胜利,但实质上只是个人魅力和群众狂热造成的错觉。

正是这种错觉,促使美国妄图靠军事侵略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治。打从战争一开始,奥巴马就知道这是个错误,是引火上身的无知,是自我欺骗的自由主义,是幼稚可笑的救世理想。“如果你认为,我们将会以自由战士的身份受人景仰,或是在沙漠上建立杰弗逊式的民主,那你就太天真了。”奥巴马说,“大美国式的理想主义总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出现,正如二战后的联合国和马歇尔计划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国力上和精神上都优于别人,我们不能独善其身,要凭一己之力改变世界。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促使我们妄图改变他国的文化和历史进程,结果给自己带来麻烦,越南战争便是最好的例子。”
奥巴马尊重每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认为世界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发生变化。他在骨子里是个保守派,有时候甚至是个伯克式的现实主义者,他不相信一般化的推论和普遍性的概括,认为激进的革命并不可靠,事物只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缓慢而稳定地转变。以医疗保健为例,“如果从零开始规划,”他说,“加拿大所采用的全民参与、不必与雇佣关系挂钩的医疗保健体系,当然是最好的。但我们已有了一套惯用的制度,要执行重大的变革非常困难,我们只能换一种方式使人们逐渐接受,而不能让他们觉得健康和生命突然失去了保障。”
奥巴马在参议院中的投票纪录倾向于自由派,但他往往受到共和党人的欢迎。因为他在阐述政见时,采用了一种保守的方式。比如,在探讨贫穷问题时,他不是对财团和税制展开猛烈批判,而是说:我们是同胞的守护者,保障穷人是我们一贯的传统。有人问过去20年里他的思想有没有发生变化,他说:“现在的我,对依靠政府施政便能解决一切问题有所保留,例如我认为,父母和社会组织对孩子所造成的影响,和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同等重要。”他很少直接批评布什政府。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次演讲上,他对听众说:“虽然我是民主党人,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市场主义者,只要提出了好的建议,我都会欣然采纳。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不可知论者。很多保守主义者会把我视作战友或袍泽,他们说:‘他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民主党人,并非因为他和我们意见一致,而是因为他重视我们的声音。”
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结束后,共和党人在博客上打出了这样的标题“正确的演讲,错误的场合”、“巴拉克·奥巴马:困在民主党内的共和党灵魂”。奥巴马的演讲虽然没有里根的慷慨激昂,却成功取悦了大部分美国人。共和党人与他志趣相投,尤其是那些同样反对伊战的共和党人,一些当年支持布什竞选的财团也开始资助他。在竞选参议员的投票中,奥巴马赢得了40%来自共和党的选票。有一个组织名叫“支持奥巴马的共和党人”,由约翰·马丁始创,并在6个州设有分支。当然并非所有共和党人都支持奥巴马,约翰·马丁不时也会收到恐吓邮件:“我告诉你,支持奥巴马的都不是共和党人。”“你是共和党的渣滓!”
把梦想看得比现实重要的人,
是无法作出妥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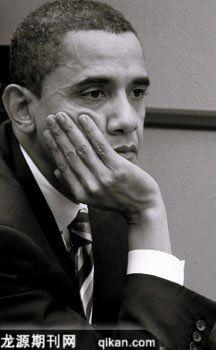
奥巴马被人引用的最多的一段讲辞是:学者喜欢把我们的国家分为红州和蓝州,红州代表共和党,蓝州代表民主党。但我要告诉他们:在蓝州,我们也崇拜万能的上帝;在红州,我们也不会让联邦特工到我们的图书馆四处打探。一位资深的华盛顿观察家对这段讲辞嗤之以鼻,认为是毫无意义的空话。连奥巴马的盟友也担心他的立场不够坚定,“他所说的一切不外乎号召两党团结那一套,但他的话还不如丘吉尔的来得煽动。”然而对奥巴马来说,这并不是空话——是出于真心,并且会拿出行动。
最让支持者失望的是,奥巴马往往过于尊重对手并作出太多让步。“在法学院的时候,我们一起开研讨会,其中有个保守派叫查尔斯·弗里德”,卡珊德拉·巴特说,“是《第二宪法修正案》的坚决支持者。奥巴马倾向于枪支管制,他想听听弗里德的意见,因为他在苏联的盟国长大,那些国家是不允许拥有枪支的。然而,他们之间的争论并不激烈。”奥巴马说过,如果布什政府以包含撤兵时间表为由,否决军费支出法案,那他宁愿删除时间表来换取军费支出法案的通过。自由派对他的妥协深表不满,但奥巴马对外政策智囊、作家萨曼塔·帕瓦说,“认定一个立场,然而却袖手旁观,这不是奥巴马的作风。”
或许是奥巴马的性格使然。“我天生不容易激动。”奥巴马在《无畏的希望》中写道,“每当我看到安·古特(激进的律师兼传媒人)和肖恩·哈尼蒂(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在电视上辩论,我发现很难把他们当回事。”在他看来,对手不是穷凶极恶而是无知可笑。“我不是个阴谋论者,我从来不相信背后有人在操控一切。你花越多的时间与人相处,就会发现对方越人性化。越是那些有财有势、掌握了社会资源分配权的人,自我保护的意识就越强。越是了解金钱和权力的重要性的人,就越希望维持社会的稳定。”
奥巴马的妥协意识并不只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是出于本能,近乎一种条件反射。“巴拉克具备一种消弭分歧的能力,”卡珊德拉·巴特说,“这种能力来自他的成长背景:他在白人家庭长大,但人们把他当作黑人看待。他必须接受并适应这种身份对立,正是这种对立造就了他。”在参议院里,这种能力让他左右逢源,使得一些开始被认定过于自由化的法案获得顺利通过。“在研讨会上,无论我们讨论的是劳工、宗教或政治问题,他总会不动声色坐在一边观察,然后总结我们每个人的发言。”罗伯特·普特南说,“不是说他能化解所有分歧,但他从不以对立的角度看待问题,而是寻求两者的共性。虽说他并非总是对的,但当前美国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作出了很多妥协却不自知,比如在投票中,我们以种族、宗教、社会阶级划分出不同人群,其实我们夸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所以就目前而言,他是对的。”早在奥巴马年轻的时候,已经在文字中表现出对这种夸大情绪的不屑,“把梦想看得比现实重要的人,是无法作出妥协的。”
当某些非黑即白的问题无法作出折中时,奥巴马会坚持己见,但不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如果说大部分美国人对同性恋结婚作道德谴责,认为婚姻只能产生于男女之间,尽管奥巴马未必同意,但却不会当面驳斥。”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的同事凯斯·桑斯坦说。因为奥巴马认为,公民维护道德的普遍自觉性,远比问题的对与错更重要。“宽容和妥协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基础,”桑斯坦说,“奥巴马的阐述更接近于法官汉德:‘自由的精神是永远不确定自己是否正确。奥巴马之所以为保守党所认可,是因为当两者的理念发生冲突时,他知道自己也有可能是错的。而政治人物是从来不会这样思考的。”
即使问题不涉及宗教,奥巴马也会同样尊重他人的想法和其植根的文化背景。“我相信有普世价值观的存在,”他说,“比如,切割生殖器曾在某些地方盛行,但时至今日,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都应该受到禁止。不是说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处处要受到道德制肘,但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谦卑的姿态,去推行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
林肯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林肯是奥巴马心目中的英雄。
奥巴马之所以选择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宣布参选总统,是因为那正是林肯当年宣布参选的地方。亚历山大·毕克尔在《最不危险的部门》一书中写道:林肯坚信,某些原则在法律表述上决不能让步,但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作出调整。虽然林肯说过“自由政府原则上不允许奴隶制度存在”,但由于大多数白人的反对,林肯并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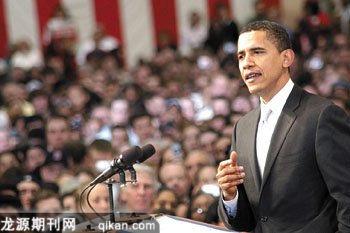
奥巴马把其竞选策略定位为:重新联合分裂的美国社会。他认为,美国的建立正是一次“重大的妥协”,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家的福祉,反之,它是联邦得以存在的基础。正如林肯在致《纽约论坛报》主编的信中写道:“如果不解放一个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一个不放;如果解放全部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全部解放;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不解放其他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也照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林肯可以放弃信仰,”奥巴马认为,“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必须通过磋商达成共识。”
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奥巴马惬意地靠在椅背上,似乎能保持这个姿势坐上一整天。他说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挥着手臂。他谈论着伊拉克战争,坚称只有撤兵,才能避免“越战症候群”的再度出现。“任何国家都存在安全隐患,”他说,“一旦无人监管,它们就会成为恐怖主义、流血冲突滋生的温床,危害我们在邻近地区的利益。然而我们插手他国内战时,必须本着维护地区和平和人道主义的原则,让当地人民明白,只有恢复秩序,他们才能看到希望和分享利益……我会把部分军力从伊拉克转移到阿富汗以支持北约,在那里,我们还有取胜的希望。”
众所周知奥巴马反对伊战,但无论内政或外交,他都并非鸽派。自进入参议院,他已对两项国际性的重大议题——禽流感和核不扩散条约,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是两项极具风险性的议题,成功遥遥无期,一旦失败就会引发全球性的灾难。然而奥巴马在处理全球性事务上还是个新手,当老布什第一次派兵侵入伊拉克时,他还不到30岁,正在考虑是否进入政坛。
“当时州议员的位置出现了空缺,社区组织的人问我是否感兴趣,”回忆当初竞选参议员的情形,奥巴马说,“我作了一个所有黑人男性都会作的决定:问上帝,问老婆(笑)。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做了所有竞选人都会做的事情,和每一个愿意听我说话的人聊天,我去家庭教师协会,去理发店,去垒球场,每个地方的人都会问我同样两个问题:第一,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很多人会把它读作“阿拉巴马”或“友友·马”(笑)。第二个问题是我决定参选的理由,他们问我:你是个好人,你有很高的学历,赚很多的钱,还有一个美好、虔诚的家庭,为什么你要参与政治这个肮脏的行当?”
在2004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乔恩·法夫罗为奥巴马撰写了著名的讲词《无谓的希望》,当时他对奥巴马说:“你要讲一个故事,一个用一生去融入美国的故事,你要让听众为了整个故事,而不是为了其中一两句台词而起立鼓掌。”这与奥巴马的构想不谋而合,也成为他后来的竞选策略:竞选是一个漫长而反复的过程,不要为一张选票、一个选区耗尽所有精力。他在竞选时从不高声呐喊,从不歇斯底里,甚至很少把手举过肩膀,总是保持着其一贯节制而不失激情的节奏。
哈罗德·华盛顿是奥巴马进入政坛的目标,他至今不能忘怀这位非裔芝加哥市长当选时,在黑人社区所掀起的巨大反响:人们把他的照片挂在墙上,纷纷跑到街上庆祝,既为他当选感到骄傲,也为自己感到骄傲。有人说,“华盛顿的当选,完成了对黑人的一次救赎。”假使奥巴马自己当选为总统,他绝不会作这样表述,因为他向这个国家承诺了团结,承诺了停止分裂,承诺了结束战争,这不仅仅是一次对黑人的救赎,也是对白人——他们投票选出了一名黑人总统,对共和党人——他们包容了一名民主党人,对所有美国人——他们终于鼓起勇气向世人承认,这场战争(伊拉克战争)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