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边野餐
2024-04-11章雨恬
雨竹把车子停在双秀湖公园门口,我和母亲先下车。下车时,母亲表现得异常顺从,我朝她伸出手,她立刻就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像从松土中拔一颗萝卜,我很轻易地把她从后座拉出来,尽管她的手一直在颤抖。
车外阳光猛烈,迎面吹来的微风夹杂着淡淡的燥意。我从后备箱中拿出野餐包,拉着母亲,走到附近的树荫中。过了一会儿,雨竹提着装有食物的袋子从停车场回来,我们挨个刷身份证进园。
暮春时节,公园内景象变换的速度惊人。上个月我和雨竹来时,进园大道两旁的泡桐树上结满了铃铛一样饱满的花苞,栅栏内的草地一片绿茵。如今树上的泡桐花大多凋谢了,草地上却盛开了五彩斑斓的郁金香。阳光照耀下,那些郁金香仿佛涂上了一层透明的釉,自内而外地散发出晶亮的光泽,像未干的格雷夫斯油画中的花朵,我情不自禁地多看了兩眼。
“花。”我转过头,看到母亲颤巍巍地伸出一根手指,指着草丛中的郁金香。
“要拍张照吗?”草地里有不少人正在拍照。印象中,母亲也很喜欢和花拍照,那种披着丝巾、蹲在花海中的标准中年妇女拍照姿势,也曾是母亲所钟爱的。
母亲没有回答,自顾自地往前走。我有些尴尬,充满歉意地看了雨竹一眼。雨竹冲我笑了笑,用眼神示意我赶紧跟上母亲。
我们继续沿着主路前行,沿途的景象慢慢发生了变化。郁金香花海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悬铃木,棵棵都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像两队静默的卫兵,尽职尽责地立于道路两旁。风吹过,悬铃木的枝叶摇晃起来,发出了唰唰的声响,地上大大小小的光斑也随之晃动。穿行其间,我产生了一种正处于二十世纪迪斯科舞厅的错觉。道路两旁的草地上,已有不少人在野餐,柠檬黄的、橘粉的、天蓝的帐篷和野餐布,把草地切割成一个个小方块,大人席地而坐,小孩和宠物在草地上跑来跑去。
“要在这里野餐吗?”雨竹问。
我看了一眼略有些拥挤的草地,说:“这里太挤了,去湖边吧。”
“行。”雨竹应了一声。
走出悬铃木树林,有一片湖。在阳光照耀下,湖面反射出粼粼的波光,像无数条碧蓝的丝带同时舞动,晃得我有些睁不开眼。
“水!好大摊水!”母亲突然高声叫起来,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把我和雨竹吓了一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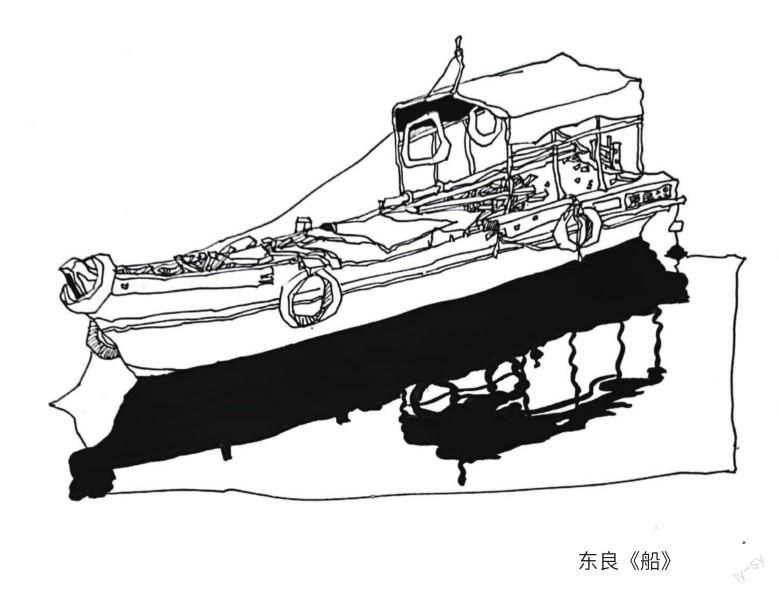
我赶紧蹲下来,扶住她的肩膀,说:“妈,这是湖,你看清楚。”但母亲仍然抱着头,做出一副戒备的姿态,连我的靠近都会引起她巨大的惶恐。过了好一会儿,母亲才从这种紧张的状态中缓和过来,把手慢慢从头上放下。我和雨竹从两边架着她的胳膊,帮助她从地上站起来。
一个月前,我父母在自驾时出了车祸。那天下暴雨,路面过于湿滑,父亲在转弯时没控制住车速,小货车撞破护栏,掉到了山下。那场车祸夺走了父亲的生命,母亲虽然活下来了,却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同时被诊断出抑郁症。前一种病症显然是受车祸影响,后一种就很难说了,究竟是原先就患有,还是被车祸激发,我不清楚。确诊之后,母亲没有特别排斥坐车,但无法面对和雨有关的事物。医生说,可以把雨理解成一个触发她记忆的按钮,按钮被触碰了,母亲的大脑就会拉响一级警报。下雨天母亲会异常惊惧,总是想把自己藏进柜子,甚至听到浴室里的水声,也会受惊心悸。不发病时,她看起来还算正常,只不过受外界刺激时的反应远比正常人麻木。有时候,我看着她,总觉得自己在看一株正在枯萎的植物。母亲从来没有说过她被困在车内时经历的一切,我无从推测那段时间内她的内心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那时起,她的活力、激情、欲望,所有可以称为“生命力”的东西,都同那些讨厌的雨水一样,一点一滴地流逝了。
坦白来讲,对于父亲的离开,我心里没有多少难过,但看到母亲患上如此难缠的精神病,我瞬间觉得天塌了半边。我不可能放任母亲一个人生活,便把母亲从老家接到了我这里,和我同住。
“湖,不是雨……”母亲盯着远处的湖,喃喃自语。我转过头,看到她脸上是白纸一样茫然的表情。
“对,是湖,不是雨。”我重复了一遍,搀着母亲往湖边走。她不像刚开始那样抗拒,但我依然能感觉到她的紧张,步子迈得很小,每走一步都像是试探。为了配合她的速度,我也放慢了脚步。
这片湖是市区内少见的天然湖。从地图上看,湖的轮廓形似葫芦,两边宽,中间窄,就像两个圆形湖泊交叠在一起。但从岸上看过去,只不过是一片稍大一点的湖,完全看不出轮廓的玄机。湖上漂浮着几条动物形状的小船,最中心处有两个小洲,上面覆盖着青绿色的芦苇,没有经过刻意地修剪,自然生长成了柔软的波浪形。远远看去,像是两个赤裸匍匐的女人的身体。湖边没有过分高大、参天蔽日的树林,只有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地、沿湖而栽的柳树和几处凉亭,因而阳光充足,气温明显比树林中要高。或许,也是这个原因,在湖边野餐的人远没有树林中那么多。
我们挑选了一个人少的地方,雨竹把野餐布铺到草地上,我把袋子里的食物拿出来。准备的食物比较家常,雨竹带了三明治、水果和酸奶,我带了自己卤的牛肉,还有一些水煮的红薯、罗汉豆和花生。
摆好食物后,我拍了拍身旁的野餐布,喊母亲坐下。她攥着手,慢吞吞地朝我靠近,定定地站在我旁边,像是个突然被老师点名后不知所措的大孩子。我又对她说了一遍,她才迟疑地蹲下来,用手撑地,再把屁股慢慢放下来,最后手收回到膝盖上,依然攥成拳形。
看到她这副模样,我心里不免又难过几分。在我记忆中,有一段和母亲一起外出野餐的经历。那时候父亲在外打工,我和母亲还住在村子里。放暑假时,有一天家里停电了,实在热得受不了,母亲便把我带到后山乘凉。说是后山,其实就是我老家后面的一座小土丘,很矮,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爬到山顶。村里人怕小孩子在山上乱跑,便吓唬我们说以前有女人吊死在山上,死后化为女鬼,专门抓小孩子吃,所以我们一般不敢上山玩。那天母亲说要带我上山,我既激动又害怕,一颗心咚咚狂跳,几乎忘记了炎热,等我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坐在山里的一块大石头上休息。
头顶有高高的树遮挡太阳,脚下还有奔腾的溪流,母亲把脚放在溪流中浸泡,我也学着母亲,脱了鞋,把脚伸入溪中。滑滑的水流从脚底淌过,我感觉自己好像踩在无数条鱼的背上,全身上下都被凉意包裹了。过了一会儿,我肚子饿了,母亲便从布包里拿出几个红薯,捡了些树枝,用打火机点着,再把红薯放上去烤,用草木叶子紧紧埋住。
记忆中应是烤了很久,半个小时那么长。空气越来越热,烟味熏得我都忘记了我们最初上山的目的只是消暑。烤好时,红薯的表皮已经黑了,很烫很烫,轻轻一撕,就大片大片地掉落下来,露出里头跟金线团一样绵软的薯肉。我边吹气边吃,咬开外头那层酥酥的皮,红薯的甜香软糯荡漾在唇齿间,最里面的部分没有烤得很熟,咬下去脆脆硬硬的,但我还是把红薯吃光了。
后来这段记忆总是被我写进作文当中,我把它同“難忘的经历”“旅游”“母爱”之类的主题相勾连,从小学写到初中,经常在考场上获得高分。当雨竹向我提议带母亲出来野餐散心时,我没有拒绝。或许,在我心中,也一直期盼着能有一个机会再和母亲一起野餐。
“阿姨,小楠,中午了,你们吃点东西吧。”雨竹打开一盒切好的西瓜,递到我和母亲面前。
我用牙签戳了一块西瓜吃,又戳了一块放到母亲嘴边,母亲张开嘴,我把西瓜塞进她嘴里。
“这西瓜好甜。”我说。
“是吧?我早上从菜场买的。”雨竹说。
“那你蛮会挑的嘛,有没有什么秘诀?”我故意这样问雨竹,隐隐期待着母亲能加入我们的谈话。
“秘诀?这有什么秘诀?就是看眼缘呗,挑一个我喜欢的就是了。”雨竹边说边朝我挑了挑眉毛。
“那算你运气好。”我瞪了她一眼,“我妈以前买西瓜可厉害了,买回家的西瓜就没有不甜的,眼睛比瓜农还毒。”
“哦?阿姨这么厉害啊。”雨竹笑着说。
“那可不,我妈挑瓜的秘诀多着呢。”我用手肘顶了顶母亲的手臂,希望她能够给我一点反馈,但她只是垂着头,盯着膝盖发呆,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们在谈论什么。
类似这样没有结果的对白,这个月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虽然母亲以前也称不上健谈,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或是说,无力关心。而我,从最初的不敢置信到现在的被迫习惯,似乎也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拍。”母亲突然开口。
“拍?拍什么?”我疑心是我听错了。
“拍,这样,拍,拍,会震的,就要买。”母亲左手朝上,像是托举着什么东西,右手在空气中不停地拍打。我看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拍西瓜。
“妈,你是说要挑那种拍下去会震的西瓜吧?”我帮她理顺了句子。
母亲很慢地点了一下头。
“那我下次就按阿姨说的挑。”雨竹笑嘻嘻地说。
“吃点红薯吧,垫垫肚子。”我打开塑料袋,把红薯分给母亲和雨竹,“妈,你还记得有一年暑假,你带我去后山烤红薯吗?”
“阿姨还会烤红薯啊?”雨竹附和道。
“那当然,我妈她几乎什么都会。”我说,同时用余光去瞟母亲。
母亲正在剥红薯皮,她剥得很仔细,每一丝粘在薯肉上没剥干净的皮,她都会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剔下来。脸上是少有的专心。
母亲没有说话,雨竹便开始说她小时候烤红薯的经历——她和小伙伴“钻木取火”,木叶烧出来的烟呛得她直咳嗽,烤好后怎么也扑不灭火,差点蔓延成森林大火,最后她们所有人都被家长训斥了一顿。她讲得有趣,说到她的一个同伴为了灭火朝火堆撒尿时,自己咯咯直笑。我听得出来,在她记忆深处,应该也有一段和我一样难以忘怀的经历。
“那时候真有意思啊。”雨竹右手压在膝盖上,支着头,眯着眼,手指将她眼角往上推拉,她的凤眼看上去像是一片弯折的柳叶。她的脸上是完全陷入回忆的迷醉,和她微醺时的状态几乎一模一样。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到了柳树掩映下的双秀湖。湖面宽阔,漂浮着碎金一样闪闪发亮的阳光,大朵大朵的柳絮悬在空中,像将落未落的雪团。
“吃。”我正在发愣,突然感觉手中一沉。我低头,是一个剥了皮的红薯,外面还贴心地套了一个塑料袋。我转过头,看向母亲,她脸上依然是那种麻木的、平静的表情,我期望能够从中窥见什么不同,但什么也没有。不过她能把剥好的红薯递给我,已让我万分欣喜。
“你吃呀,我自己也可以剥的。”我想把红薯塞回母亲手上,但她没有接,反而又从袋子里拿起一个红薯开剥。不管母亲有没有想起那段关于后山、关于红薯的记忆,但此刻的她,应该是沉浸在这种劳动当中的。这样一想,我便打开塑料袋,吃起了母亲为我剥的红薯。红薯是我早上煮的,放到中午已经凉了,外部的薯肉被水泡得稀软,里头是甜的。
母亲剥好了第二个红薯,套上了塑料袋,递给了雨竹。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小孔吃。”母亲说。
雨竹愣了一下,随即看向了我。我吞了吞口水说“你吃呗”,雨竹才接过,说“谢谢阿姨”。
“妈,我们都吃了,你自己也吃呀。”我说。
母亲点了点头,从袋子里拿出最后一个红薯。我把其他袋子一一打开,把卤牛肉、罗汉豆和花生分给雨竹和母亲。
午餐后,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把花生壳和罗汉豆皮装到塑料袋里,把保鲜盒放回野餐包中,只留了一些水果和酸奶,野餐布一下子空旷起来。
“累的话,可以躺下来。”我说,“妈,你起得早,要不要休息一下。”
母亲点了点头,侧身躺在野餐布的边缘,背对着我们,两条腿向外弓着。
我和雨竹坐在一旁,玩起了手机。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母亲发出含混的鼾声(也有可能是很重的呼吸声)。我瞅了一眼母亲,她双目紧闭,嘴唇紧抿,松弛平滑的皮肤上潜伏着大大小小的褐斑。我想母亲大概是睡着了。
这个月来,母亲晚上几乎没有睡过好觉。医生说,像她这样的患者,一个人安静下来,那些创伤性质的记忆会在她脑海里一遍遍地播放,每个可怕的瞬间、窒息的细节,都会像特写镜头一样被放大到极致。把母亲接来与我同住后,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母亲在忍受这些记忆的折磨。有一天凌晨,我被尿意憋醒,起床后看见母亲背对着我,坐在床边。我叫她,她没有反应,我绕到她面前,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那种没有焦距的眼神,虚无而空洞,就像在打量一个陌生人。那天之后的每一天,我入睡前都会再三确认家中的门窗是否全部锁好。
手臂被人顶了顶,我转过头,雨竹指了指母亲,对我做了个“阿姨睡着了”的口型。我用口型回复“干吗”,她贼兮兮地笑起来,打开手机相册给我看。我连续滑了几张,每一张都是她早上偷拍的我的照片——有喝水时被呛到咳嗽的,有牙齿上粘着香菜叶的,还有不知看着什么正在发呆的……每张都搞怪到可以用作网络表情包。我作势要打她,她边偷笑边闪躲。我又往后翻了几张,是她偷拍的母亲和我。大如伞盖的榕树占据了照片的三分之二,重重枝叶下,我和母亲直挺挺地站着,色调和构图倒是蛮有文艺片海报的质感。
我让雨竹把照片发给我。传输成功后,我把照片调大,拉动到母亲和我的位置。放大后的画质有些许模糊,但不怎么影响视觉效果。我穿着黑T恤白裙子,母亲穿着白色棉麻衫和黑色阔腿裤,我们站在一起,像拼合完整的棋盘。我仰着头发呆,母亲看着地面,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眼睛有些酸涩,我便躺在母亲身旁的野餐布上。湛蓝的天空中,漂浮着几朵洁白的云,边缘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像大块大块熬煮好的棉花糖,其中有一小坨云朵特别像是一只奔跑的兔子,耳朵、四足、尾巴几乎都能对应上。我朝母亲的方向翻了个身,眼睛正对的位置是她的后脑勺,她的头发散落着,露出隐藏在发间青白色的头皮。再翻了个身,我继续平视蓝天白云。云朵发生了变化,刚才那只被我标记的兔子,变大了一点,已经化为了一只有点像老虎的动物。困意如浪潮一般上涌,我眯上眼睛,身体慢慢地放松下来,每一寸的皮肤都在逐渐与大地融合。又过了一会儿,迷迷糊糊间,我感觉身旁好像也躺下了一个人。
这一觉睡得很舒服,暖烘烘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整个人就像被浸泡在浓稠的蜂蜜中。不知睡了多久,我再醒来,面前是雨竹的脸。她没醒,仍然在睡觉,头发大部分都落在野餐布上,还有一部分粘在了脸上。我曾经打趣她,别的女生都有海藻般飘柔的长发,她的头发短而硬,就像晒干的紫菜。每次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我都能感受到颈间沙沙的刺痒。我盯着她的睡颜看了一会儿,帮她把脸上的头发撩到耳后,雨竹丝毫没有要醒的迹象,我便不再去逗弄她,独自起身。突然,我的动作顿住了,猛地回头,果不其然——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了,盘腿坐在野餐布的一端,面向我。
不知是因为睡醒时意识昏沉,还是因为母亲的脸处于背光区,四目交接的瞬间,我竟无法看清楚母亲的表情。眼前只有一片混沌的丁香花般的绛紫色阴影,可我却本能地感受到了惶恐。再过了一瞬,我的目光清明了些,母亲的脸上仍是那副麻木的表情,我从中读取不出任何不同寻常的情绪。
“妈,你醒啦?”我揉了揉压得有些麻的右臂,尽量用平常的语调说话。
母亲没有回应。
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开雨竹发给我的那张合影。“喏,妈,你看这张。”我把照片放大,递给母亲看,“认得这是谁不?”
母亲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抬起手,先指了指我,又指了指自己。
“对,就是我们嘛,拍得好不好?”我说。
“谁,谁?”母亲说。
“什么谁?”我皱起了眉头。
“谁,谁拍?”母亲说。
“雨竹,哎,就是小孔啊。”我指了指雨竹,平静下去的心又开始紧张跳动。
“小孔。”母亲说,“小孔拍。”
听到了我们的声音,雨竹含混地应了一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怎么了?”雨竹说。
“没什么,我妈问照片谁拍的。”我淡淡地说。
听完我的回答,雨竹轻声地“嗯”了一下,闭上眼睛,又迅速睁开,一骨碌从野餐布上爬起来,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说:“对了,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去划船?”
我转过头,看向湖面,下午湖的水色要比正午时分更深一些,湖面上漂浮着鸭子船、天鹅船、鲤鱼船和龙头船,热闹得就像是一个水上动物园。之前我和雨竹来湖边玩,本想去划船,但是碰到雨天,游船没有开放。
我看了眼手机,还不到两点半,确实还有很长时间可以消磨。
“妈,我们去划船好不好?”我问。
“划……船……”母亲喃喃地重复道。
“对,去划船。”我扶着母亲起身,示意雨竹把野餐布收起来。
去售票处买完票,我们选了一条天鹅形小船,穿好救生衣,便拿桨登船。小船的核载人数是四人,我们三个人坐,非常宽敞,我和母亲坐在一边,雨竹坐在我们对面。我和雨竹各执一条小桨划船,船在水波的作用下慢慢离岸。刚开始划得很吃力,总感觉是在逆水行舟,有好几次,我们发现各自划的方向是相反的,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母亲自上船后就一直紧攥着手,我感受得到,她还是有点紧张。我想调动气氛,问她好不好玩,知不知道划桨的技巧,想不想也来划一段,但她都不答话,用一张凉薄的脸回应我所有的提问。渐渐地,我不问了,心头有些闷。
船慢慢划向湖心,湖心的水流比岸边的要急一些,只要无所谓方向,完全可以由着水流助推小船前行。我把船桨收起来,放在座椅下方。雨竹也学着我,收起了船桨,只是在船快撞到湖心小洲时,才把桨放入湖中奋力划几下,拨出了“扑棱扑棱”的水声。
一架飞机从天空划过,伴随着一阵轻微的、类似零件崩坏的声音,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白线。
“飞……阿飞……”母亲突然开口,食指颤巍巍地指向天空。
雨竹没有听懂母亲在说什么,向我投来了一个疑惑的眼神,但我非常清楚,她说的是,阿飞,我的父亲。
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我和他的关系就僵到了极点,他死了,我也不觉得悲伤。我小时候,他在东莞打工,一年回家一两次,每次在家待半个来月。回来头两天性情还算温顺,会抱着我,用他粗硬的胡茬贴我的脸颊。之后十几天他就摆起了大爷派头,每天往村头的赌桌上跑。在家他也不安分,让我和母亲忙前忙后伺候,我稍稍忤逆,他就立刻暴跳如雷,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没用”。那时候同村打工人都说他在东莞有了相好,还说那个相好给他生了个小儿子。听了那些话,母亲一下子就老掉了。她本身不是那种粗神经的女人,不会把丈夫對自己的伤害做成谈资,用诉苦的方式博取周围人的同情,动员别人和她一起讨伐那个远在天涯的负心汉。她什么也不说,所有的羽箭落到了她身上,她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
我读高中时,父亲在工地上出了意外,背部被重物砸到,伤到了脊骨。之后,父亲在家休养了近两年,伤好后不能干重活,他便不再外出打工,盘了辆二手小货车,替人跑些短途运输的活。奇怪的是,每年总有那么一两次,父亲会无缘无故地从家里消失,每次至少消失半个月,和他以前在东莞务工时的情形完全颠倒过来。和他一起消失的,是家里的部分钱财。
这个月来,我从来没有和母亲聊过父亲,她自我封闭,我避而不提,父亲像是硬生生地从我们生活中被裁剪掉了。留下的人形疮口,也被我们或有意或无意地绕行了。母亲的这声呼唤,勾连起了我心底的很多记忆。过去我对父亲是有怨言的,总把他视作我们家庭内部不时发作的顽疾,但他的猝然离世抚平了这一切。我对他的怨恨消失了,我跟他之间的联系反而更弱了。对现在的我而言,与父亲相关的记忆都渺远得如同发生在前世。
眼前忽有一道白光闪过,我抬起头看向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阳光消散了,大块大块铅灰色的云朵盘踞在一起,周围的空气沉闷凝滞。天气预报之外的雨,我的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赶紧叫雨竹把船划回去。果不其然,我们刚划到岸边,就听到了轰隆隆的雷声。雨竹说走到停车场最快也要二十分钟。我心知,来不及了,就算刚好赶上,母亲也没办法在那种状态下坐车。
“先找个地方避一避。”我当机立断。
我们就近找了一个凉亭,我扶着母亲坐到凉亭中心的石凳上。不一会儿,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
“雨!雨!下雨了!”母亲发出惊叫,抓着我的手,挣扎着要从石凳上起来,“小楠,快回家!下雨了!”
“妈,你听我说,我们等雨停了再走。”我用另一只手紧紧按住她的肩膀,迫使她看清楚我的脸,“妈,你放心,我们在亭子里很安全。”
“雨,下雨,阿飞……”母亲双手捂着耳朵,身体控制不住地打战发抖。看到她这副模样,我再也忍不住了,伸手拥抱住她,让她的脸靠在我的肩膀上。
雨下得越来越大,斜斜地漏进了亭中,最外圈的那些座椅上汇聚了一小摊雨水。一个多月前,我和雨竹来公园野餐,突然接到了小姑的电话,说我父母出了车祸,父亲当场离世,母亲生死未卜。那瞬间,我觉得整个世界在我眼前旋转起来,雨竹搀着我,带我到一处凉亭中休憩。那天下午,我处于情绪失控的边缘,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现在我也一點都回忆不起来,只记得雨竹说,无论如何,她都会陪我一起面对。半个月前,雨竹搬出了我们合租的一居室,方便我把母亲接进来照顾。
远处,湖面上炸开了水花,像是被千万把机枪同时对准狂轰,噼里啪啦的水花炸裂声让我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草地上,有帐篷的人直接钻进了帐篷,没有帐篷的人忙着打伞,收拾食物,有几个年轻人直接顶着野餐布往树林中跑。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让雨竹把野餐布拿出来,盖到我和母亲身上。黄白格子的牛津布落下来,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令人觉得踏实、安心。母亲在我怀中动了动,渐渐安静下来,我听着那些雨声,觉得它们好像来自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雨竹的声音,雨停了。我摘下了野餐布,沉闷的空气散去了,我闻到了一股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气味。天光摇曳,一绺绺雨水从亭盖的飞檐上滴落,形成一串透明的水形链条。
我拍了拍母亲的背,告诉她雨停了,我们可以回家了。母亲愣愣地看了我一眼,又慢慢扭头去看亭子外面。天空仍是阴沉沉的白,草地被雨水冲刷过,一片湿漉漉的毛茸。我扶着母亲起身,雨竹提着野餐包,默默地走在我们旁边。路面上有不少积水,一小摊一小摊汇聚着,上面飘着被打落的草叶和花朵,像一枚枚小小的、散落的镜子。我看到后尽量绕行,但还是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引来了母亲的一阵惊呼。
快走到停车场时,我明显感觉到母亲走路的速度变慢了。雨竹按下车钥匙,隐藏在车堆里的银灰色雪佛兰车发出了一声轻快的号叫。母亲停在原地,我想拉她,发现她的手心里渗出了汗水。汽车、雨天,两个足以触发记忆洪流的开关同时出现,我瞬间明白了母亲正在经受着一种怎样的煎熬。我转过身,告诉雨竹,我要带母亲坐地铁回家。
地铁站离公园门口很近,我们稍稍走了一段路,就看到了地铁标志。我帮母亲在手机上绑定了地铁卡,刷码进站。母亲从来没有坐过地铁,看到对面一班地铁呼啸而过,一群人进进出出,瞪大了眼睛。我向她解释,地铁就像地下的火车,都有各自的轨道,不可能出现碰撞。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
又等了一会儿,五号线到了,我拉着母亲进去。不是上下班高峰期,地铁里人很少,我们挑了个靠门的两人位坐下。很快,地铁就开动了,发出了一阵“轰轰”的噪声,母亲不安地看了看周围,我握紧了她的手,安抚她说:“没事。”
二十来分钟的车程,坐地铁加上步行要将近四十分钟。母亲起初有些紧张,不敢靠在椅背上,直僵僵地挺着背,坐得板正。随着地铁一站站地停靠,人上人下,母亲渐渐放松下来,靠在椅子上,头偏向车厢内的墙壁。我把头靠向另一边,闭目养神。
半睡半醒之际,我突然听到了一声抽噎。我心中一惊,赶紧睁开眼睛看向母亲。不知何时,母亲的脸上竟已挂满了泪水。在我的注视下,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滑落,留下了一条湿亮的水痕。我惊呆了,过去这一个月,我在她身上看到了麻木,看到了恐惧,看到了茫然,但唯独没有看过她流泪。我怔怔地看着母亲在我面前拭泪,看着她继续无声地哭泣。
“妈。”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的声音也有些哽咽,“妈,怎么突然……”
“小楠……”母亲凑过来,抱住了我。
“妈……”我用力吸了吸鼻子。
“小楠……你和小孔……”母亲伏在我的肩膀上,背部一起一伏,“你们俩……你们俩都这么好……这么好……”
肩头那块衣料被母亲的泪水洇湿了,一种温热的液体正通过那里源源不断地渗入我的身体。我想回抱母亲身体的手停在了半空。许久,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了母亲的背上。
坐在我们对面的也是一对母女,小女孩一直瞪着大眼睛打量着我们,我和她对视,她“啊”地叫了起来,立刻就被她母亲捂住了嘴。我朝她挤出了一丝笑容,她扭过头,钻到她母亲的怀里。
手机响了一下,我腾出手,解开锁屏,是雨竹发来的微信,问我们到了没有。我看了眼地铁上方的行程路线表,目的地闪闪发亮,回了句“快了”。隔了几秒钟,她发了一张刚拍的蓝天白云的照片,说她刚刚开车回家,一路上都没有下雨。
到站广播在这时响起,地铁窗户外跳跃的广告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站台。玻璃门向两边打开,我搀着母亲走出地铁,再刷码出站。我们的双脚安稳地踏上了电梯,让一股坚定的力量托举我们上浮。离那个散发着亮光的出口越来越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我不知道地铁站外的雨是否已完全停止,想着雨竹发来的照片,我和母亲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责任编辑 猫十三
作者简介
章雨恬,1999年生,浙江温州人,北京师范大学2021级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入选浙江省“新荷”计划人才库,曾获逸仙文学奖、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作品见于《小说选刊》《江南》《长江文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