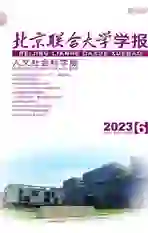有序的非平衡: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系统自组织协同的演化过程
2024-01-12尹德挺赵政史毅
尹德挺 赵政 史毅














[摘 要]基于系统科学的自组织理论,结合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本文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演化过程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应、伺服效应和自组织效应,并表现出可预见的发展趋向。第一,形成了首要主导城市、次主导城市、主协作城市、次协作城市的整体协同格局,层级化协同特征较为突出;第二,形成了四大圈层城市结构,圈层化格局特征较为稳定;第三,存在多极→单极→双极、突变→稳态→成长、无序自组织→有序自组织、弱非平衡关系→强非平衡关系的协同阶段趋向,并且在当前双极协同的状况下,正处于由成长状态向突变状态转变的阶段。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将呈现五个方面的特点:有序、非平衡、有序的扩大、非平衡加剧趋势放缓、双极协同向多极协同的潜在趋向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系统自组织;功能地位;协同圈层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4917(2023)06-0038-13
自2014年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和人口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更为明显,人口转变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性作用更加突出,城市群人口要素分布格局优化更显紧迫。与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群相比,近年来,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增长相对缓慢,2000至2020年期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仅为058%,大湾区和长三角人口增速分别是京津冀的37倍和28倍。与此同时,首都都市圈和河北部分城市人口规模也存在小幅下降趋势,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呈現出整体增长缓慢、局部持续收缩的不均衡特点。在新时期人口协同的新视角下,重新理解城市群发展的新特征对研判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风险、问题和挑战具有重要价值。
当前,从人口视域出发,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城市群人口协同的空间优化。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中,通过人口的空间重组和整合,推动人口在空间上优化布局,其实现途径的探索包括有效引导人口与产业在空间上的适度集中[1],以合理产业布局规划驱动人口空间聚集优化[2-3],以及在协同机制上创新形成“国家—区域—城市”两两间互动的新三角模式[4]。二是城市群人口协同的极化格局。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中,在经济和投资的集聚作用下,人口逐渐呈现以北京和天津为核心的极化格局[5-6]。如果资源进一步集聚,这种极化现象还会加剧[7],使得核心城市与周围城市间的关系呈现出“集聚阴影”,即二者之间存在着虹吸作用带来的极化效应[8]。三是城市群人口协同的圈层效应。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中,圈层效应明显,呈现出总量增长、分布不均、集聚凸显等特征[9]。四是城市群人口协同的博弈关系。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中,主要存在着北京与首都、北京与天津、北京与河北 “三种关系”[10],其在协同理念、发展方向、区域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和利益博弈会使“三地共输”的可能性增强[11]。因此,为实现三地人口协同发展,推动产业与人口在城市之间的合理布局[12],优化城市之间的人口结构与空间布局相关政策[13],应在新发展理念的驱动下打造京津冀三地利益、经济和命运共同体,从而形成更高阶的“区域共同体”,才能真正破解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集体行动困境”[14]。
现有研究表明,在产业集聚驱使下,人口在城市群中也呈现出集聚的态势。然而,这种集聚是否存在着人口空间自组织之力,以促进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系统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呢?这样的问题值得研究。因此,我们需要将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系统来研究其人口协同问题,而系统自组织理论的“协同论”“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对于系统内部结构演化过程的分析可为推进区域人口协同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参考。其中,协同论中对子系统之间的“伺服机制”“自组织机制”“协同机制”的分析为讨论城市群内部子系统之间的作用机制提供新视角;耗散结构论中对于系统形成“耗散结构”即稳定有序结构过程的分析为考察城市群子系统关系的演变特征提供新思路;超循环论中对于系统演化由“低阶协同”到“高阶有序”演化趋向的分析为城市群人口协同模式的未来方向提供新解释。
因此,基于系统自组织理论,本文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的效应机制、演进阶段和发展方向进行研判,拟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探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系统协同效应机制,即“协同的层级性”。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子系统在人口层面的协同中形成的竞合关系、功能地位和圈层结构是怎样的?二是探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系统协同演进阶段,即“协同的阶段性”。京津冀人口系统协同演进过程都包括哪些阶段?当前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自组织协同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具有怎样的阶段性特征?三是探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系统协同演进趋向,即“协同的方向性”。未来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模式将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利用我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近70年的人口协同发展脉络,旨在把握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的趋势及其内在机制,为增强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韧性、助力京津冀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政策参考。
一、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已有研究大多利用单一年份或较短时间段的统计数据研究京津冀城市群人口问题,而本文试图贯通1953—2020年我国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以观察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协同变化。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内部行政区划发生了一系列变动,因此,在统计京津冀各地人口数据时,需要对统计口径进行调整。本文以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空间数据为标准,对各期县级人口数据按照2020年地级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并对历史数据使用空间分析工具进行逐年回溯,最终形成了7期、每期13个地市、共计91个样本的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1.引力矩阵网络分析法
使用系统自组织理论对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协同发展状况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构建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协同程度的分析指标。本文借鉴传统引力模型中对于地区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型的方向性进行改进,构建起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引力有向矩阵网络”,从而对城市群中各城市子系统的人口间的协同程度进行研究。
其中,Rij为城市i、j间的人口空间联系作用强度,G为引力常量(通常取1),Mi和Mj为城市i、j的常住人口规模,βij为城市i、j之间联系强度的衰减因子(取值为2),dij是城市i、j之间的距离(采用城市空间坐标之间的直线距离)。
其中,Pi→j为城市i对城市j的空间人口引力作用强度,Pj→i为城市j对城市i的空间人口引力作用强度。
2.社会网络分析法
在构建起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系统之后,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对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演变机制和自组织结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具体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网络密度分析。网络密度是对整体网络之间的各个节点的联络紧密程度进行衡量。网络密度越大,说明整体网络之中各个节点的联系越紧密,整体网络的变化对于网络中各个节点的影响力就越大(公式如下)。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引力有向矩阵网络进行测算,可推演出京津冀整体人口协同与各城市子系统之间变化的联系。
D=mn(n-1) 。
其中,m为在有向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数,n是有向网络中的节点个数。
第二,中心度分析。根据社会网络分析中对于“出度点度中心度”和“入度点度中心度”的测算,得到城市群子系统对外影响作用的总和与向内受整个城市群人口系统作用的总和,再通过对比两者的强弱关系,确定其在协同中主要是“主导功能”还是“协作功能”。为降低矩阵中数据表达差异对于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以中位数为阈值作为二值化的依据,将有向矩阵的多值关系数据转化为二值关系数据,筛选出具有强协作关系的节点,得出标准化后的点度中心度数据,从而对矩阵网络的核心程度这一关键特性进一步比较观测,具体公式见表1。
第三,凝聚子群分析。基于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人口引力场强矩阵,利用SNA分析中的CONCOR方法,对城市子系统之间通过人口相互协同作用凝聚在一起所形成的子群的演变趋向进行分析。结合系统自组织理论中对于自组织机制的分析,自下而上地对城市群的人口协同系统内部进行研究。其中,对凝聚子群的分析维度包括:子群内部凝聚程度即凝聚力的分析、子群之间有向的作用程度分析以及两者的演化趋势分析。
结合现有研究方法,本文重点从“协同”和“非均衡性”两个维度对城市群人口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在引力模型中,“协同”重点指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规模增长的关联性,引力越强表明城市间人口发展的联动性越强,城市网络相对完善;引力越弱表明城市间人口发展的单体效应越强,尚未形成联系紧密的城市网络。“非均衡”重点指城市群内部存在引力极差较大的情况,即中心城市引力过高、非中心城市引力过低的特征。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测量协同性的重点指标为网络密度,网络密度越高表明城市群整体变化对各城市的影响普遍越高,网络密度越低表明城市群整体变化对各城市的影响相对有限;测量非均衡性的重点指标为网络中心度,网络中心度最高的城市与最低的城市之间的差距大小可反映城市群内部人口均衡性水平的高低。
二、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竞合的“协同效应”
在城市群内部,不同节点人口的引力作用既受到不同城市之间构成的复杂网络关系结构的影响,也受到城市群内其他节点引力大小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城市群间关系结构和引力大小的影响。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可以对各节点的人口引力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有效测度,分析城市群内部人口竞争与合作的协同效应。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人口空间引力作用强度Pi→j和Pj→i进行计算后发现,自1953年以来,城市之间的人口空间作用强度的绝对差值的平均值和绝对差值的标准差都呈现出增大的态势,说明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各城市子系统之间引力作用的差异增大,这意味着从整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子系统之间在协同中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以非平衡关系为主,并且这种非平衡性呈现加剧的态势(见表2)。
基于七次人口普查京津冀城市子系統间人口空间引力作用强度值,将城市子系统之间的人口引力强度转换为坐标点,以散点图(见图1)的形式进行直观呈现,可看出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的关系在初期以“弱非平衡”关系为主,城市群子系统间人口空间引力作用值的绝对差值较小,非平衡的协同关系使得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系统进行自组织,向着有秩序、多功能的方向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关系逐渐向强非平衡的关系扩散,城市群子系统间人口空间引力作用值的绝对差值扩大,使得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格局呈现出“强非平衡”的趋向。
三、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的“伺服效应”
在京津冀城市群内部人口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弱非平衡”走向“强非平衡”的过程中,不同城市的人口演化特征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何种差异?在城市群整体网络之外是否存在子系统?哪些子系统在城市群人口协同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这些问题当前仍然有待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依据系统自组织理论,在评价京津冀人口协同的程度时,可以通过不同子系统的伺服效应机制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子系统的功能和定位,以探寻城市群人口协同的主导力量和协作力量。
(一)人口协同极化程度:由强转弱
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协同系统中,人口引力有向矩阵网络的密度D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见表3),说明城市群整体协同网络对各城市子系统的作用逐渐增强。同时,从1953年开始,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网络的标准差也在不断增多,且标准差较网络密度有更快的增速,进一步说明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整体呈现出极化的格局。然而,通过对比2000年以来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网络标准差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这种极化程度有缩小的趋势。
1953年至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所有节点间有向引力作用强度平均值由201上升至1697,各城市子系统之间的人口引力作用整体呈现加强态势,城市之间整体人口的相互作用程度加深。另一方面,若以平均值作为阈值,筛选高于平均值的引力强度线分析京津冀人口引力强度格局时发现,1953年高于平均值的人口引力强度线有45条,而2020年则减少至33条,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表现出极化格局加剧的趋势(虚线圆圈由大变小,见图2)。值得指出的是,2020年连接北京或天津节点、高于平均值的人口引力强度线有20条,占高强度关系总数的60%以上,形成引力作用的高值区域,在极化趋势中主导着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系统整体协同。同时,保定、廊坊、石家庄等城市节点也连接着部分的高强度关系线,成为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格局中从双极向多极分化的潜在力量。
(二)四类城市群人口协同格局的形成
在整体极化的京津冀人口协同格局中,研究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结构,首先需要对决定主导京津冀城市群协同格局的力量进行界定。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中心度分析,可以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中的城市子系统是“主导力量”还是“协作力量”及其协同力量的强弱程度进行界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外影响力的“出度点度中心度CDi_out”和对内受影响的“入度点度中心度CDi_in”(见表4、表5)。
根据各城市子系统的出度点度中心度和入度点度中心度的强弱对比情况,可以将京津冀城市群的各城市子系统分为两股力量:一是人口协同主导力量。从总体来看,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出度中心度要高于入度中心度,即在京津冀人口协同中整体发挥着主导作用,虽然也受到京津冀人口协同系统的影响,但其中主导作用较为凸显。二是人口协同协作力量。从总体来看,廊坊、沧州、唐山、衡水、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入度中心度要高于出度中心度,即在京津冀人口协同中整体发挥着协作的作用,虽然在京津冀人口协同系统中也具有影响力,但以协作作用为主。在对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子系统从功能力量上进行划分后,可根据其核心程度的不同,对其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中的地位作出进一步的划分。通过计算可得到有向网络矩阵标准化后的点度中心度数据(见表6),对以主导功能为主的城市子系统,以在城市群中标准化后的相对点度中心度的最大值作为区分的阈值,将达到100的城市子系统划分为首要地位,其余居于次级地位。对以协作功能为主的城市子系统,以在城市群中标准化后的相对点度中心度最小值作为区分的阈值,将在城市群中相对点度中心度为最小的城市子系统划分为次级地位,高于此的居于主协作地位。
根据对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子系统的初步划分和核心程度的测算,可以发现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呈现明显的层级分化,形成了首要主导城市、次级主导城市、主协作城市、次级协作城市的协同格局(见表7)。
第一,人口协同的首要主导城市。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中,首要主导城市是协同的核心,其关系的变化对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协同格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要为:北京、天津。北京一直具有极高的核心程度,在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协同作用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能充分影响协同关系。与北京相比,天津的核心程度波动较大,在“一普”和“二普”并不处于较高位置,到“三普”“四普”和“五普”处于仅次于北京的位置,再到“六普”和“七普”达到和北京一样的相对点度中心度,并列位居第一,使得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发展格局呈现出双极的格局。
第二,人口协同的次级主导城市。次级主导城市的主导力弱于首要主导城市,但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中的主要作用以主导而非协作为主,主要包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其中,保定的相对点度中心度从“一普”到“二普”跃居第二后,在“三普”时被天津赶超,位居第三,说明虽然保定在京津冀人口协同中的作用逐渐弱于天津,但保定对京津冀的人口协同发展仍具有强影响力。虽然石家庄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中的出度和入度中心度略低于邢台和邯郸,但石家庄的相对点度中心度整体高于邢台和邯郸,其对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影响作用更为核心。
第三,人口协同的主协作城市。主协作城市的主导力弱于首要主导城市和次级主导城市,但在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协同中主要作用以协作而非主导为主,主要包括:廊坊、沧州、唐山、衡水。这些城市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中主要是协作力量,因其相对点度中心度整体高于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即核心程度高,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中发挥着主协作的作用。其中,廊坊的入度点度中心度高,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协作力强,但其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相对点度中心度较低,即核心程度较低,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的整体协同中的“权力”较低。
第四,人口協同的次级协作城市。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的相对点度中心度较低,说明其在人口发展中的独立性和核心程度较低,扮演着“跟随行动者”的角色,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受到北京、天津和保定等城市在人口协同发展方面的调节与整合。
四、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圈层的“自组织效应”
尽管通过协同效应和伺服效应分析有助于认识京津冀城市群网络各个节点和子系统的人口引力作用及其功能定位,但不同子系统之间良好的协作关系会带动各个节点的发展能力,直接关系到城市群内生循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而也是影响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城市群演化过程中,人口系统内部各城市子系统会按某种规则自发形成一种相对稳定有序的结构,各子系统之间可以通过竞争和合作的自组织作用来形成协同圈层。因此,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凝聚子群”方法对不同子系统之间的自组织效应进行了测度,通过对七次人口普查京津冀城市群“自下而上”形成的协同圈层进行分析(见图3),得出四个凝聚子群(协同圈层):
第一,以北京和天津为主的“京—津协同圈层”。自“二普”以来,北京和天津所在的凝聚子群呈现出不断缩小的态势,从由北京、天津、保定、廊坊、沧州、张家口构成的子群缩小为由北京、天津、保定、廊坊构成的子群,以北京和天津为双核的子群呈现出更加凝练的态势。与此同时,通过对密度矩阵进行分析,其内部密度从3945上升至99227,可见此凝聚子群的内部关联性在进一步加大。
第二,包含唐山、承德、秦皇岛在内的“唐—承—秦协同圈层”。这三个城市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凝聚子群的核心。随着北京和天津所在子群的强聚集,离开京津子群的沧州和张家口逐渐加入该子群。通过对子群的密度进行分析,可见虽然该凝聚子群的构成成员在不断扩大,但其内部联系一直处于协同圈层中的最低水平,即1953年的内部密度为1761,2020年时为3033,均处历史同期若干子群的最低水平。
第三,由石家庄和衡水形成的“石—衡协同圈层”。自“一普”以来,石家庄和衡水形成了稳定的凝聚子群,其内部联系紧密程度不断增加,但与另一稳定子群邢台和邯郸的高内部联系程度相比,其总体的内部联系程度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即1953年时为4856,低于四个子群的内部密度平均值7971,而2020年时为2029,虽然有增长,但仍低于四个子群的内部密度平均值6281。
第四,由邢台和邯郸形成的“邢—邯协同圈层”。这两个城市形成较为稳定的凝聚子群,其内部密度与其他凝聚子群相比处于最高级别,且与“石—衡协同圈层”之间的密度联系处于较高水平,与其存在较强的空间联系。
五、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的阶段性和方向性
基于系统自组织理论中的协同论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的关系、格局和圈层进行分析,可得到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演进中的三种效应机制。因此,在对演进效应机制深入探索的基础上,结合系统自组织理论中的耗散结构理论和超循环理论,进一步研究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向。
(一)阶段性:稳态、成长与突变的人口协同耗散结构变化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比七次人口普查下的凝聚子群内部结构,可以将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根据城市子系统自组织形成的凝聚子群(即协同圈层)的结构稳定性分为:突变状态、稳态状态、成长状态。其中,突变状态是协同圈层内部结构发生较大改变的状态;稳态状态是协同圈层内部结构未发生改变的状态;成长状态是在突变状态之前和稳态状态之后,协同圈层的内部结构未发生改变但积蓄着改变力量的状态。结合之前对于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子系统人口协同功能地位的界定,可将由主导城市、协作城市的力量博弈而形成的空间网络结构划分为:多极网络、单极网络、双极网络。其中,多极网络是京津冀城市群中功能为主导的城市之间的核心程度差异较小的网络;单极网络是在京津冀城市群中首位主导城市与次级主导城市之间的核心程度差异逐渐扩大,首位城市的主导能力更强且在数量上唯一的网络;双极网络是在京津冀城市群中首位主导城市与次级主导城市之间的核心程度差异大,且首位城市的数量为两个的网络(见表8)。将空间网络结构和发展状态统一起来,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演化的过程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多极阶段、单极阶段、双极阶段。而在三个阶段之下又包括成长状态、突变状态、稳态状态。通过对七次人口普查时期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演进阶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预判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的主要特征,并对下一次人口普查可能出现的新趋势作出规律性研判(见图4)。
1.多极阶段—突变
第一阶段为成长Ⅰ状态。“一普”时期,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作用呈现出多极协同的趋向,其中,北京、保定、石家庄具有较强的人口场强引力,人口的极化效应并不明显。北京与保定、廊坊、沧州和张家口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协同作用圈层,天津与承德、秦皇岛、唐山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协同作用圈层,石家庄和衡水、邢台、邯郸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协同作用圈层,而邢台与邯郸的协同作用更为紧密。
发展状态城市子系统形成的协同圈层结构突变状态协同作用之中形成的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圈层的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其强协同作用的群体成员发生改变“二普”“五普”
稳态状态在突变状态发生后,整体的协同圈层仍然保持着突变后的趋向和趋势,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协同圈层结构“三普”“六普”
成长状态成长状态是在稳定状态之后和突变状态之前,是协同圈层处于相对稳定未发生结构上的巨大改变,但是与稳态相比又在内部的子系统的相互协同作用下积蓄着突变的力量“一普”“四普”“七普”
第二阶段为突变Ⅰ状态。“二普”时期,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系统整体孕育着从多极向单极突变的力量,其中,北京的人口场强作用力增强,天津加入以北京为主的协同圈层中,且协同圈层的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进一步加强。但与此同时,北京、天津、保定和石家庄等城市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核心程度区分差异较小,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网络整体仍然处于多极阶段。
2.单极阶段—稳态
第一阶段为稳态Ⅱ状态。“三普”时期,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出由多极正式突变为单极的趋向,其中,以北京为主导的协同圈层对其他人口协同圈层的作用力呈现由相对均衡到不均衡的态势,以北京为主人口场强的协同圈层对其他圈层的作用力和主导力增强,使得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网络呈现单极化的趋向。
第二阶段为成长Ⅱ状态。“四普”时期,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系统处于单极趋向的稳态,以北京为极核,环绕天津、保定、廊坊、张家口、沧州形成了人口协同圈层,且其内部的凝聚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对唐山、承德和秦皇岛的协同圈层和石家庄与衡水的协同圈层形成了较强的控制力。而对于以邢台和邯郸所形成的协同圈层来说,相对的影响力处于均衡态势。
第三阶段为突变Ⅱ状态。“五普”时期,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处于单极趋向双极的成长态势,其中,以北京为主导的天津、保定、廊坊、张家口、沧州的人口协同圈层进一步集聚,沧州加入唐山、承德、秦皇岛所在的人口协同圈层中,而在以北京为主导的协同圈层中内部的联系程度变得更加紧密。同时,天津也孕育发展成为京津冀城市群的双极之一,而天津的成长之路与北京有较大差距,北京具有极强的对外的人口主导作用,且这种首要主导力量不断增强;而天津在拥有较强的对外影响作用的同时,对内受到京津冀城市群中其他城市子系统的人口协同作用也比较强。
3.双极阶段—成长
第一阶段为稳态Ⅲ状态。“六普”时期,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由单极突变为双极,其中,天津对京津冀城市群中其他人口子系统的影响力增强,与北京构成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系统中的双极。而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协同格局逐渐趋于有序,以北京和天津为双极,与保定、廊坊、张家口形成人口协同的共同体,并对其他的人口协同体形成更为强势的引力,使得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网络中的非均衡的状态进一步加剧。
第二阶段为成长Ⅲ状态。“七普”时期,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的整体网络呈现双极下的有序非均衡格局,其中,“有序”体现为各协同圈层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主要包括以北京和天津为双极、保定和廊坊强相关的协同圈层,由唐山、沧州、张家口、秦皇岛、承德构成的弱相关的协同圈层,由石家庄与衡水、邢台与邯郸形成的较强相关的协同圈层。“非均衡”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双极协同网络是非均衡的,即虽然北京和天津构成了人口协同发展的双极网络,但天津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的影响作用力与北京的差距不小,双极协同仍具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系统是非均衡的,即由北京、天津、保定和廊坊构成的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圈层与其他的协同圈层之间是存在主导力差异的,且这种差异呈现扩大态势;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中形成的协同圈层是非均衡的,即以北京和天津為核心的协同圈层中因核心程度的差异而使得形成的协同圈层呈现非均衡态势,石家庄与衡水因其核心程度不同也使得所形成的协同圈层呈现出非均衡态势。
(二)方向性:超循环视域下人口自组织协同集聚走势
在超循环理论中,协同论中的竞争和协作的相互作用在形式上表现为循环。整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系统的超循环是从多极→单极→双极、突变→稳态→成长、无序自组织→有序自组织等趋向螺旋上升的。在城市之间的人口协同模式上,多极协同也是未来阶段中的进一步发展趋向[15]。当前,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协同处于由成长Ⅲ状态向突变Ⅲ状态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特征表现为有序。通过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的自组织的作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协同体,包括北京、天津、保定、廊坊所形成的强相关的双核心协同圈层,唐山、沧州、张家口、秦皇岛、承德构成的弱相关协同圈层,以及石家庄与衡水、邢台和邯郸形成的较强相关的半核心协同圈层。
第二个特征表现为非平衡。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子系统对京津冀城市群其他城市子系统施加的强人口协同作用,以及由北京和天津形成的协同圈层对其他协同圈层的强人口协同作用,使得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呈现出非平衡的倾向。
第三个特征表现为有序的扩大。从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圈层的发展倾向看,当前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结构呈现有序扩大的态势,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圈层中城市群与城市子系统之间协同的紧密程度加大,协同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也处于扩大的态势,整体相对有序的格局呈现扩大的趋向。
第四个特征表现为非平衡加剧趋势放缓。相较于从“五普”到“六普”双极非平衡格局的强化,从“六普”到“七普”以来,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的非平衡虽然处于进一步扩大的态势,北京和天津所组成的双极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作用进一步强化,但在这个过程中,这种非平衡加剧的态势也呈现放缓的倾向。
第五个特征表现为双极协同向多极协同的潜在趋向发展。这种多极协同的趋向和在“一普”和“二普”时的多极协同不同,是在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系统自组织发展后具有有序的、更高级的多极协同趋向,这也充分体现了系统论中超循环理论中螺旋上升的系统自组织规律。通过分析发现,当前我们正处于双极阶段的成长Ⅲ阶段,未来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协同格局可能会向更高组织力的多极协同方向突变。因此,把握好人口协同的趋向,通过经济和政策手段因势利导,对于京津冀城市群研究意义深远。
六、结论与讨论
随着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人口系统的协同性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呈现出明显的伺服效应、自组织效应和协同效应。从作用机制上看,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系统通过伺服、自组织和协同机制作用不断重塑内部结构,对弗里德曼城市群发展的四阶段论以及孙久文等的三阶段协同发展时空演化理论形成了新的回应和阐释。
第一,京津冀城市群四类人口协同格局的形成。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发展过程中层级分化特征明显,形成了首要主导城市、次级主导城市、主协作城市、次级协作城市的协同格局,主导城市对整个城市群的人口变动影响力仍在不断上升。
第二,京津冀城市群四类人口协同凝聚子群的形成。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且有序的结构,形成了以北京和天津为主的第一子群,以唐山、承德、秦皇岛为主的第二子群,以石家庄和衡水为主的第三子群,以邢台和邯郸为主的第四子群,其中,第一子群的集聚优势较为明显且与其他子群的协同程度较高,第三和第四子群与其他子群的协同程度较低。
第三,京津冀城市群五个人口协同阶段性特征的形成。京津冀城市群各圈层或子群间的关系逐渐从弱非平衡向强非平衡扩散,使得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格局呈现强非平衡的趋向。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强非平衡加剧的趋势已开始放缓,城市子系统之间的协同紧密程度加大,协同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也处于扩大态势。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协同的非平衡性特征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区域发展政策不均衡带来的“拉力”与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带来的“推力”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一是区域发展政策的均衡性不足。长期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沿海地区和特定城市的经济发展,大湾区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和资源,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相对有限,人口发展空间也相对有限。同时,在城市群内部,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在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优势地位,集中了区域内主要的人口和资源,存在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和高素质人才。在区域产业政策影响下,河北省内的其他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空间更加有限,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相对较少且吸引力较低,人口流出较多,部分地市人口不增反减,较早进入负增长阶段,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群人口的不均衡流动。二是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均衡性不足。北京、天津作为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地理位置優越且交通便利,拥有更好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对非京津冀地区和京津冀内部人口均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尽管北京在持续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但超大体量的常住人口对基本生活服务业的刚性需求客观存在,优质且“含金量”较高的公共服务资源对城市群内部其他地区人口的吸引力持续存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群内部人口的不均衡流动。为改善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建议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加大对河北省内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加强非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体化视角下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区域均衡,依托雄安新区建设契机增强京津冀中南部地区的网络中心度,以吸引更多的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提升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缩小城市间人口引力的差距,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陆大道:《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定位及协同发展》,《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3期,第265—270页。
[2]吴群刚、杨开忠:《关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思考》,《城市问题》2010年第1期,第11—16页。
[3]孙久文、王邹、蒋治:《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1—10页。
[4]张兵:《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城市规划学刊》2016年第4期,第15—21页。
[5]郑贞、周祝平:《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状况评价及空间分布模式分析》,《人口学刊》2014年第2期,第19—28页。
[6]鲁金萍、杨振武、刘玉:《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网络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5年第5期,第117—122页。
[7]李国平、罗心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1期,第25—33页。
[8]陈玉、孙斌栋:《京津冀存在“集聚阴影”吗——大城市的区域经济影响》,《地理研究》2017年第10期,第1936—1946页。
[9]封志明、杨玲、杨艳昭等:《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疏过程与空间格局分析》,《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1—18页。
[10]张可云、蔡之兵:《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制约因素及未来方向》,《河北学刊》2014年第6期,第101—105页。
[11]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第1期,第110—118页。
[12]王继源、陈璋、胡国良:《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北京人口调控: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0期,第111—117页。
[13]李国平、罗心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的影响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94—102页。
[14]张贵、孙晨晨、刘秉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程、成效与推进策略》,《改革》2023第5期,第90—104页。
[15]尹德挺、于倩、史毅:《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的人口空间聚集与传统产业升级》,《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第89—99页。
Orderly Disequilibrium: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Population System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An Analysis Based on Previous Census Data
YIN Deting1,ZHAO Zheng1,SHI Yi2
(1.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Beijing 100044, China;
2.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of system science and combined with previous population census data,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opulation co-evolution proces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an obvious synergistic effect, servo effect, and self-organization effect, showing a predictable development trend. Firstly, a comprehensive collaborative pattern has been formed with prominent hierarchical collaborativ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primary leading cities, secondary leading cities, primary collaborative cities, and secondary collaborative cities. Secondly, four major circular urban structures have been form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rcular pattern are relatively stable. Thirdly, there are collaborative trends from multipolar to unipolar to bipolar, from mutation to steady state to growth, from disordered self-organization to ordered self-organization, and from weak non-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to strong non-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ipolar coordination, it is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from the growth state to the mutation state. The coordinat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will present five characteristics: order, unbalance, orderly expansion, slowing down trend of unbalanced intensification,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from bipolar coordination to multipolar coordination.
Key words: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population synergy; system self-organization; functional status; synergetic layer
(責任编辑 刘永俊;责任校对 朱香敏)
[收稿日期]2023-07-07
[基金项目]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目标导向下首都人口空间分布优化研究”。
[作者简介]尹德挺(1978—),男,湖南沅陵人,北京市委党校教授;赵政(1997—),女,河南平顶山人,北京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史毅(1990—),男,河南濮阳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