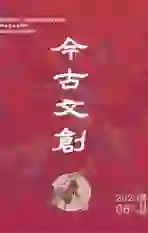简牍所见秦及汉初的免老、 睆老
2023-05-30王威
【摘要】 免老制度是秦汉养老制度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然而传世文献关于该制度的记载少之又少,以至于很少学者提及这个问题。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中的相关记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张家山汉简中关于不同爵位人群免老、睆老年龄的规定,结合当时军功爵在国家制度中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社会背景,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汉旧仪》中关于秦免老年龄的记载是不宜轻易否定的。
【关键词】简牍;免老;军功爵;《汉旧仪》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6-004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6.015
免老制度是秦漢养老制度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然而,因为史料的缺乏,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未有学者谈及这个问题。随着简牍的出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对秦及汉初(高祖、惠帝、吕后时期)免老、睆老的内涵,免老、睆老的年龄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下面,笔者就简牍所载的相关材料提出一些见解。
一、免老、睆老的相关记载
(东汉)卫宏《汉旧仪》:“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1]这是秦汉时期的传世文献中唯一一次出现“免老”两字。
然而,随着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现世,学者们能够看到的有关“免老”的记载也逐渐丰富了起来。《秦律十八种·仓律》:“免隶臣妾、隶臣妾垣及为它事与垣等者。食男子旦半夕参,女子参。”[2]根据学者的说法,“免”是指达到免老年龄。其依据正是上文《汉旧仪》中的记载。
《秦律杂抄·傅律》:“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3]《傅律》中的这条记载是关于百姓谎报年龄应受处罚的规定。整理者将其释为“百姓不应免老,或已应免老而不加申报、敢弄虚作假的,赀二甲。”
上述简文中,整理小组并没有对“免老”的具体内涵做出解释。张鹤泉对“免老”的具体内涵进行了一些探讨。[4]他结合史料对免老的内涵作出了解释:免老免除的是徭役,免老的年龄是56岁。如此,《汉旧仪》的记载便可以这样解释:根据秦二十等爵的规定,男子只要有一级爵位以上的,年56岁就可以免服徭役,没有爵位的,年60岁可以免除徭役。
随后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也有与“免老”相关的记载:《二年律令·傅律》:“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袅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5]其中,学者将“免老”解释为“因年高免服徭役”。“不更年五十八,簪袅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伍六十二,皆为睆老。”[6]整理者将“睆老”解释为“减半服徭役”,其依据则是《徭律》中相关记载:“睆老各半其爵徭,口入独给邑中事。当徭戍而病盈足岁及繁,勿摄。”[7]“半其爵徭”当可解释为减半服徭役。
综上所述,免老、睆老当有免除徭役、减半服徭役的内涵。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然有部分学者提出免老、睆老的内涵不仅于此,如洪淑媚认为徭役一定会先免除,也就是赞同免除徭役的说法,但是她又对免老是指算赋、徭役一并免除,还是只免除其中一部分产生了质疑。[8]李恒全根据天长纪庄木牍《算簿》的相关记载,认为“免老”也有免除算赋的内涵。[9]所以,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二、不同身份人的免老年龄
前引《二年律令·傅律》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免老、睆老的年龄与爵位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这与商鞅变法之后,军功爵制盛行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频繁发生,各国都需要扩大兵源,为了鼓励民众参军,军功爵制度孕育而生,各国相继实行了军功爵制度。军功爵在当时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军功爵提高了军队的积极性和战斗力。
在各国施行的军功爵制中,以秦国的施行的军功爵制最为完备,贯彻得最为透彻。商鞅吸取了各国的经验,又结合了秦国的情况,颁布了“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10]的法令。意思就是,没有军功的旧贵族,要被开除贵族籍,不能得到封爵。同时,又规定拥有爵位可以得到相应当官职。史料记载:“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11]“相称”两字突出表现了秦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与军功之间的关系。
在秦代的治狱文书中,凡提到与案件有关的人员,不论是罪犯、受害者,或是证人,都要写明有无爵位和爵位的级别。仅以《封珍式》为例, 在这一组治狱文书中,共有二十三个案例,涉及的罪犯、受害人和证人共四十一七名。其中有爵者九人,无爵者三十一人,身份不明者七人。
楚汉战争时期,军功爵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垓下之战,项羽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12]为争军功,众将抢夺项羽尸首,自相残杀。
到了西汉开国,军功爵的作用仍在。刘邦为了奖励那些随他打天下的将士们的功劳,多次下诏布告天下,给他的功臣将士晋爵增封。《汉书·任敖传》: “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13]上至公卿,下至一般官吏,都是军功出身。
对于军功爵在秦汉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及作用,朱绍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秦和西汉初期为军功爵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军功爵制度在秦和西汉初,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再分配的一种基本形式。[14]正是在这样一个军功爵盛行的大背景下,简牍中才会出现不同身份、不同爵位的人有着不同的免老、睆老年龄规定的记载。
再来看具体律文。前引《二年律令·傅律》说爵位在大夫(第五级)以上者五十八岁免老;不更(第四级)、簪袅(第三级)、上造(第二级)、公士(第一级),免老的年龄分别为六十二岁、六十三岁、六十四岁、六十五岁,可以发现,免老的年龄随爵位的降低而逐渐提高,无爵的普通人如公卒、士伍等则六十六岁免老。[15]与《汉旧仪》的记载相比较,不难发现,《二年律令》中规定的免老年龄,甚至比我们一致认为律法严格的秦朝的规定还要高出二至六年。
《二年律令·傅律》:“不更年五十八,簪袅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伍六十二,皆为睆老。”也就是说,不更五十八岁,簪袅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伍六十二,都可以减半服徭役。《二年律令·傅律》:“民产子五人以上,男傅,女十二岁,以父为免□者;其父大夫也,以为免老。”[16]这条简文的大意是:百姓有子女五人以上,并且兒子已经傅籍,女儿都已经十二岁,父亲就可以直接免老。如果父亲有大夫爵,那么只需有五个子女就可以免老,无需有子女年龄的限制。结合汉初人丁凋敝,役源不足的社会背景,这条律文的意图也就很明显了:鼓励生育。这条律文同样可以看出对于拥有不同爵位的人,国家的政策规定有所区别。
以上三条简文是关于不同爵位人群的免老、睆老年龄的记载,结合当时军功爵在国家制度中起着重大影响和作用的社会背景,不难发现,这些简文中的规定无疑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汉中期是军功爵制走向轻滥和衰落的时期。这个源头可以追溯到文景时期。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条:1.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财政需要和奖励民众),西汉政府开始卖爵或赐爵,这一做法逐渐破坏了军功爵制的严肃性和用爵位来赏赐功劳的原则。2.景帝、武帝时期国家已经稳定下来,国家需要的“治世的能臣”,所以统治阶级选拔的多是办实事的文人,军功地主则逐渐式微,慢慢地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3.军功地主安逸已久,失去了往日的进取精神,奢靡腐化之风悄悄地在军功地主中蔓延。
三、《汉旧仪》记载质疑
关于秦代的免老年龄,出土的秦简中并无详细记载,学界多依据《汉旧仪》:“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依照《汉旧仪》的记载,秦代的免老年龄根据有无爵位可以分为两种,有爵位的人56岁免老,无爵位的人60岁方可免老。这一明显的区别也正是当时极其重视军功爵的一个表现。
《史记·项羽本纪》载,“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赴荥阳”。对此,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内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疲癃。”[17]如淳根据《汉仪注》的记载解释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史骑驰战阵。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18]
按照如淳的说法,楚汉战争时期,刘邦仍然在施行秦朝有爵者五十六免老的政策。然而根据张家山汉简《傅律》中“大夫以上年五十八……皆为免老”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在楚汉战争结束,汉王朝建立之后免老的年龄竟然比秦朝的统治下以及楚汉战争时期这种人力征发频繁时期的免老年龄还要高。换句话说,就是刘邦在急需劳动力的时候仍然奉行“秦制”,实行五十六岁免老的制度。战争结束之后,却提高了免老的年龄,变成五十八岁才允许老年人“退休”。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可以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推测:1.如淳的说法有误,当时并不是56岁以上即为免老。这一种推测难以证明,故暂且不论。2.如淳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就带来了上文提到的有意思的现象。
朱绍侯认为“睆老”律文中没提大夫级爵,是因为大夫以上爵位已享受五十八免老的待遇。年龄的上升大概和汉初人口锐减、役源不足有关。正因为汉初服役年限较长,故又增加一项“睆老”的律文,即减半服徭役的规定。[19]朱红林认为汉初的免老年龄比秦代高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唯一的解释就是秦制不是五十六岁免老。“《汉旧仪》关于秦代免老年龄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张家山汉律较之于《汉旧仪》更接近于秦代实际。”[20]张荣强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在秦代免役年龄似乎不可能比汉初提前这个前提下,分析认为《汉旧仪》所谓“赐爵一级”即公士以上,“五十六”免老,与汉初的“六十五”,只是“五”“六”数字倒置;无爵者“六十”免老,与汉初的“六十六”也仅是
脱一“六”字,若确实《汉旧仪》版本脱、倒的问题,汉初免老标准则是沿袭秦制。[21]
针对这三种观点,我们需要加以分析。首先,朱绍侯把免老年龄的提高归于人口锐减、役源不足确实说得通,同时他注意到的汉初增加了秦代没有的“睆老”为他这一说法提供了不小的助力。其次,朱红林的说法从逻辑层次否定了《汉旧仪》的记载,他的依据是对汉昭帝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颂扬当时仁政的话,提出了怀疑:如果秦时已经实行了“五十六岁而免”的制度,那么桑弘羊不会不知道,贤良文学也不可能不就此反驳他。
笔者认为这一点很好解释,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秦王朝已经完全沦为“反面教材”,连带着秦朝的任何政策都被打上了“暴政”的烙印,即使有一些不错的“善政”也会被自动屏蔽。另外,贤良文学也都不是傻瓜,想来也不会蠢到“以古非今”:通过夸赞秦朝的政策来贬低本朝的政策。最后,张荣强的观点和朱红林的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怀疑《汉旧仪》的记载存在问题。
笔者更倾向于朱绍侯的观点。其一,既然《汉旧仪》明确说秦制五十六岁免老,又有如淳引用《汉仪注》作为作证,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这一说法的准确性。我们在没有其他充分而有力的证明的基础上仅凭着逻辑推理就去否定史书中的记载似乎有些草率。其二,笔者推测《汉旧仪》的记载不一定有错,因为我们知道秦代的徭役之重,突出表现在临时加派的那部分。这就是所谓规定的内容不一定与实际情况相吻合,所以《汉旧仪》的说法仍有一定的可信度。朱绍侯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考虑楚汉战争之后人口减少、户籍不完整的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新增加的“睆老”条目,认为免老年龄的上升大概和汉初人口锐减、役源不足有关具有比较大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1]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85.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53.
[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43.
[4]张鹤泉.西汉养老制度简论[J].学习与探索,1992,(06):132.
[5]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81.
[6]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81.
[7]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87.
[8]洪淑媚.從《张家山汉简·傅律》看汉代前期免老、睆老[C].弱水简牍研读会,2004-4-25.
[9]李恒全.从天长纪庄木牍看汉代的徭役制度[J].社会科学,2012,(10):159.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230.
[11]赵沛注说.韩非子[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411.
[1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6:336.
[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6:2098.
[14]陈长琦.朱绍侯与军功爵制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10,20(04):16.
[15]袁延胜.荆州松柏木牍及相关问题[J].江汉考古,2009,(03):116.
[16]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81.
[1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4.
[1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6:38.
[19]朱绍侯.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53.
[20]朱红林.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家山汉简《傅律》初探[J].东南文化,2006,(04):61.
[21]张荣强.《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份[J].中国史研究,2005,(02):28.
作者简介:
王威,硕士,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历史教师,研究方向:历史研究,历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