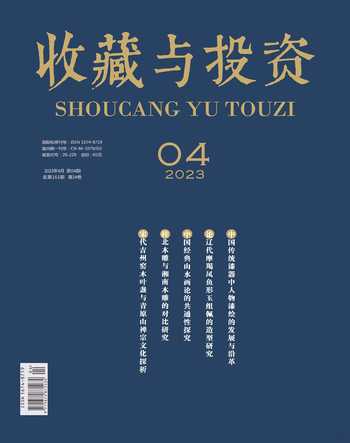浅析张掖大佛寺罗汉造型艺术特征
2023-05-10吴德芳青海师范大学青海西宁810000
吴德芳(青海师范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0)
一、大佛殿概述
张掖大佛寺位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中部,坐东朝西,占地面积三万余平方米。大佛寺几经易名,曾称作“迦叶如来寺”“弘仁寺”“宝觉寺”“宏仁寺”等,民间称作“甘州卧佛寺”“大寺”等,近年来也称“西夏国寺”。寺内建有大佛殿、佛教艺术陈列厅、佛教经籍陈列厅、土塔、山西会馆、金塔殿等,正殿南为感应寺,北为金塔殿,后为藏金阁和土塔。
大佛寺主殿大佛殿平面呈长方形,长48.3米,宽24.5米,高20.2米,占地面积1 370平方米。大佛寺主殿内塑有彩绘泥像31尊,中央是全国最大的室内泥胎卧佛,为西夏所遗,金装彩绘,形态逼真。卧佛全身长34.5米,整尊造像金装彩塑,头枕莲台,侧身而卧,嘴唇微启,两眼半闭,右手掌展放在脸下,左手放在大腿一侧,胸前饰有“卍”字符号,梵文寓意“吉祥海云相”。卧佛两侧塑有天部两大护法大梵天和帝释天立像各一尊,两大护法身高七米,身体略微前倾,表现了对佛祖的尊敬与虔诚。卧佛对面是明清时期所绘的二十四诸天礼佛神像画,卧佛背后是十大弟子像,十大弟子身后的壁画是明清时期所绘的天龙八部,卧佛南北两侧是十八罗汉像,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卧佛后面是著名的《西游取经》图,是大佛寺所有壁画中的经典之作,高约2.9米,长约4.4米,壁画前塑地藏王菩萨像一尊,与壁画并不是同一时期所塑。而《西游取经》图左右两侧是《观世音救难》图,绘有“持花二菩萨”“持花两观音”等。这些壁画也是晚清时期的,画的是供养菩萨,供养菩萨斜对面的三尊塑像是2000年新塑的,但是后面这些壁画是大佛殿历史最为久远的壁画。两边的壁画取自《妙法莲华经》第二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观世音菩萨救八难的故事。
二、十八罗汉造像身份特点分析
(一)大佛殿十八罗汉
张掖大佛寺在佛像的制作工艺上,采用木胎泥塑,从罗汉的破损处可以看出佛像是由木头搭成架子,用草泥贴塑,由内至外,逐步加泥,再彩绘而成,这是将建筑技术与塑像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张掖大佛寺自建寺以来经历多次维修,明代注重对寺庙的重修,对大佛寺前后进行了六次维修,清代维修了四次。其造像布局很显然是遵循前代已形成的造像布局,卧佛前侧首和足底处分别站立帝释天和末罗族首领,身后站立十大弟子,左右壁近墙处为十八罗汉等。因时代不同,造像风格会有所改变,头冠衣饰则取明制。改革开放以后,又维修了一次,但只是简单的维修,整体风格没有改变。目前大佛殿的十八罗汉历经700多年,破损严重,有八尊手臂断落,六尊眼睛、面部破损,大部分造像颜色脱落严重,保存情况较差。我们很难从已有的文献资料中明确地掌握张掖大佛寺十八罗汉每一尊的名号,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和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罗汉造像进行对比,可以通过罗汉动态、神态、造像手法、外在形象等推断出一部分罗汉身份。
(二)十八罗汉身份辨认
大佛寺北侧第六尊罗汉经过对比,应是笑狮罗汉,此罗汉为青年男子形象,面形椭圆、额头饱满、面部圆润、挑眉弯目、慈眉善目。袈裟搭于左肩,身体微向左转,目视左前方,左腿垂放,右腿曲起,左脚下轻踩一小动物,整体造型端庄大方、怡然自得。此尊罗汉与山西崇庆寺的笑狮罗汉(图1左)都脚踩一直昂首翘尾的小狮子,整体造像相似度很高,所以可以认为此尊罗汉是伐阇罗弗多罗尊者,俗称笑狮罗汉(图1)。

图1 笑狮罗汉
大佛寺南侧第一尊罗汉经过对比,应是挖耳罗汉,中年男子模样,眼神惆怅,目视左前方,左手放于膝盖,右手抬起,展放于右脸上,左腿盘回,右腿曲起。手臂衣纹随形下垂,起伏大,变化丰富,节奏感强烈,同身体衣纹形成对比。经过与云林寺挖耳罗汉(图2左)和仙人崖挖耳罗汉(图2右)对比,此三尊罗汉共有的特点是单手做挠耳状,虽然此三尊罗汉在造型上有所不同,但从整体的造型特点分析可以认为此尊罗汉是那迦犀那尊者,俗称挖耳罗汉(图2)。

图2 挖耳罗汉
大佛寺南侧第五尊罗汉经过对比,应是布袋罗汉,老年男子模样,坐姿稳如泰山,眼角与嘴角上翘,方面垂耳,面部布满皱纹,形象憨态可掬,袒露胸腹,僧衣自双肩垂下,左腿拱起时左手置于腿上,右腿盘起,右手握布袋,自然垂放在右腿之上。此尊罗汉与山西阳高云林寺的布袋罗汉(图3右)形态相似,都手握布袋,形象憨态可掬,可以认为此尊罗汉是因揭陀尊者,俗称布袋罗汉(图3)。

图3 布袋罗汉
大佛寺北侧第九尊是降龙罗汉,即“迦叶尊者”,他是张掖大佛寺十八罗汉中最好辨认的一个。大佛寺的降龙罗汉怒目圆睁,目光斜视左上方盘旋的龙,双手上举,似双手持拿兵器,右腿向右上方弓起,左腿自然下垂,衣缘作荷叶边翻卷蜿蜒。这里的降龙罗汉和其他寺庙里的降龙罗汉有所不同,其他地方的降龙罗汉是把龙降于身下的,而张掖大佛寺大佛殿的降龙罗汉只做了一个降龙式,没有把龙彻底地降于身下(图4左)。这是因为大佛寺是一座皇家寺院,而龙在古代的时候代表的是天子、帝王,是皇权的象征,所以不能把龙压于身下,是有意地避讳了皇权、避讳了天子。
大佛寺南侧第九尊是伏虎罗汉,老年模样,头型圆中偏方,瘦骨清像、皱纹满面、面带微笑、慈眉善目。老虎半坐于罗汉右侧,双腿垂放,右手抚摸老虎头部,左臂向上举起,左手从小臂处断落(图4右)。

图4 降龙罗汉(左)伏虎罗汉(右)
除去一部分可以推断出身份的罗汉以外,还有很多无法推断身份的罗汉,如坐鹿罗汉、看门罗汉等。之所以身份难以推断,有以下几点:(1)在传承的时候名目太多,容易混乱;(2)十八罗汉并没有固定的形象,是后来的艺术家凭着自己的想象画出来的;(3)张掖大佛寺的十八罗汉破损严重,大多数罗汉都从手臂处断落,手中法器也不复存在,所以很难辨认。
三、十八罗汉造像的创作手法及艺术特点
(一)佛像衣着造型
大佛寺的罗汉造像的衣纹塑造整体流畅精细,僧衣和袈裟的层次表现丰富而有韵律,衣纹转折厚实明晰,使衣服带有很强的分量感,并且随身体动态变化,裙裳、帔帛的质感较强,尤其在衣褶的处理上,转折起伏自然,洒脱生动,可以说是体现了皇家气派的雍容华贵的佛像样式。此外,罗汉僧衣样式讲究,种类也较为丰富,据统计共有八种僧衣样式之多。衣纹处理工整严谨,线条运用合理细腻。衣褶的节奏变化平顺,衣服质感柔和贴身,衣纹转折对身体结构交代清楚准确。下面将具体展开讨论。
1.衣纹由疏至密的处理
在衣纹的处理上采用由疏至密的处理手法,在贴近塑像肩膀、胸廓、膝盖的部分,采用适当平铺的方法使其紧贴身形,而在形体的重要转折处,如胳膊、腿部则会适当地出现起伏堆积较大的衣纹,这样由疏到密的处理使得衣纹体积的节奏感逐步增强,作者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衣纹“疏”的处理,是为了使衣服能够跟得住形体,而“密”的处理,则是体现衣服的质地以及表现衣服随着动态的变化而出现的下摆或扬起。整个塑像也形成了由上而下、由内而外扩散的张力。如北侧第一尊罗汉像的衣纹处理充分体现了这种处理方式。作者在贴近塑像肩头、胸廓和腿部的高点部分,对罗汉的衣纹采用了平铺的概括处理,使我们能够清晰地分辨罗汉形体的起伏。衣服的边缘下摆部分与衣袖的重要转折处则体现了衣服随形体转动而产生的真实效果。
2.衣纹对身体动态的强化作用
如大佛寺北侧第六尊罗汉,作者在处理搭在左肩上的袈裟时,采用了大量重复密集并且纵向排列的衣褶,强调了袈裟因动态的变化而产生的翻转折叠,致使塑像的大部分起伏线都集中在腹部与抬起的右臂上。这种对衣纹夸张的表现,产生了一种无形的牵引力,进而强化了塑像整体的动势。在膝盖处衣纹的处理上,仅用几条衣纹处理,与袈裟的处理形成繁简不同的节奏。
(二)艺术特点
1.彩塑
中国古代大多数佛造像都采用彩塑,用彩绘的方式表达,可以表现出更多的细节,还使得服饰的装饰更加丰富。大佛寺的十八罗汉在色彩上整体以蓝、红、绿三色为主,色彩搭配简单明了且对比强烈。用简单的色彩来区分,则会展现不同的质感,使罗汉造像更加逼真、生动。在光线幽暗的大佛殿里,运用这种对比强烈的设色手法,可以使罗汉塑像更加绚丽夺目,既兼顾了宗教本身所需要的庄严肃穆的氛围,又突出了佛像造型的彩塑形象,从而加强了艺术感染力。在上色的方式上使用涂、刷、描、染以及沥粉堆金等造型方法,既能真实地描绘出衣服、皮肤的不同质感,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身份、地位设色,同时还与整体的建筑、壁画的色调保持协调统一。
2.装饰
从局部看,大佛寺每尊罗汉造像服饰在细节的处理上极具匠心且富于变化,有部分罗汉僧衣上绘有装饰图案,但由于颜色脱落严重,大部分已经辨认不清。如北侧第一尊罗汉造像,僧衣袖口处有花草纹,偏向写实;南侧第八尊罗汉袈裟下沿绘有类似于菊花的装饰花纹。除了在衣纹上的装饰外,在罗汉所坐的台座上也绘有四瓣花,深色的台座上绘有白色的四瓣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作用。
四、结语
对张掖十八罗汉彩塑造像的研究目前十分欠缺,张掖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河西走廊中段,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把仙人崖张掖大佛寺与周围的石窟寺如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联系起来作比较研究,对于甘州及西北一带的石窟艺术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张掖彩塑造像艺术研究道路还很漫长,相信后期会有更多学者实现进一步的突破,发掘张掖彩塑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其在西北地区宗教造像艺术中的重要性也会得到进一步肯定与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