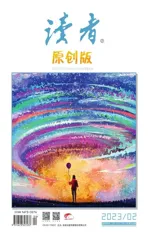振兴街
2023-03-23文|周乐
文|周 乐

一
振兴街是条街。早年人们戏称它为“震醒街”,大概是因为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开过去能把里面的人震醒。而那些坑洼或许就是因为常年有大货车隆隆地驶过,轧出来的。
没人知道为什么这条街会跑那么多大货车,它们带着北方工业城镇特有的沉重喘息,扬起粉尘,日复一日地在我家门口来去。它们拉着什么?拉去哪里?我从没想过,就像我从没在意过家门口那个油饼摊子是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消失的一样,反正我也不是很爱吃他家的油饼。大货车或者油饼摊子,扬长而去或者默默离去,只留下深深浅浅的轧痕或者黑黑黄黄的油渍,而振兴街和属于它的人们始终在这里。
我家住邮政局家属院,但并没有大门、没有门卫、没有物业,也没有牌子。唯一的娱乐设施是两个没有篮筐的篮球架,因此也没有人会在这儿打篮球。和我一起玩的几个小朋友发明了“爬杆游戏”,他们像猴子爬树一样手脚并用地顺着篮球架的杆向上爬,两只胳膊挂在横杠上荡几下再下来。我是所有小朋友中唯一不会爬杆的人,因此我在他们中没有什么话语权。而当我在烈日下苦练,以脚背破皮的代价终于爬上了那根杆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个游戏抛弃了。
上幼儿园和小学,父母为我选了县城最北边的学校,每天上学我都要由南至北跨越整个县城。学校实在是太远了,我妈蹬着自行车接送了我七八年。每当学校有以歌颂母爱为主题的作文比赛时,我的文章里总绕不开“妈妈蹬车子”的情态,绕不开她一起一伏的背。我变换着各种姿势坐在车子后座,斜着坐、叉着腿坐、背靠着妈妈坐。此时,我看的最多的就是倒退的振兴街的水泥路面,路上一截儿一截儿的白线段标识逐渐连成一整条白线,水泥路面布满深深浅浅的条纹。
“像挂面。”我在心里想。
22岁读到帕蒂·史密斯的自传,她书写自己童年的想象,那些天鹅和锡兵、祷文和诗句,万花筒一样瑰丽的想象和美给予她的震颤。而同年龄的我坐在摇摇晃晃的自行车后座,盯着倒退的水泥路,只想到了挂面。“这就是为什么帕蒂日后成了一个艺术家,而我长成了一个越来越无趣的小孩。”我凄楚地想。萨莉·鲁尼在小说里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有想象力的人和不想拥有它的人”,而我是第三种—没有想象力却渴望拥有它的人。
二
初中时,母亲疲于接送我,决定让我读那所离家不到一站路的初中。这个决定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是当时没有人意识得到。
我陶醉于第一天上学被同学指着说“实验小学来的,牛啊”,陶醉于作文被传阅的虚荣。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不爱说话,别人也不知道要和我说什么。等到了稍微会进行自我审视的年纪,同年级女生校服里的灰色高领羊毛衫与我的我妈买的减价玫红色秋衣、别人的大屏HTC手机与我的小灵通,还有在每个上学日的中午检查自己腋下的气味,将磨得开线的校服袖口折到里面。我将这些添油加醋地堆砌在我的周记里。我留了又短又丑的头发。我想用另一种自认为更加明显的不好掩饰自己身上属于振兴街的那一份自卑。
上高中之后我开始坐班车,开始注意同车一个学美术、像丹顶鹤一样清瘦的男孩子,同时也变得更加敏感谨慎。有时候他先于我上车,有时候相反。我总是在离邮政局家属院很远的地方等车,想把自己与那座污黑的老楼撇清关系。
坐在车上时,我有时候会想象跟他走在一起,背景当然是蓊蓊郁郁的榆山路—那里种满榆树,在夏天织起细细密密的绿网;或者是公园,有垂柳。反正不是振兴街。振兴街路两旁种的都是乌青的松柏,蒙着厚厚的灰,一夜过去,树后常常散发令人掩鼻的味道。我允许自己每天在他上车之后想象一会儿,直到他的QQ空间出现了另一个女孩子的照片。
可奇怪的是,即使振兴街这么破落,我却从没产生过想要真正离开那里的念头。
振兴街街道脏,旧房子逼仄,但我觉得我天生就属于这样的环境,我从未觉得自己应该生活在更宽敞的街道和更亮的灯光里。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更愿意站在角落里,灰暗的颜色是那么熟悉,那么令人安心啊。
2020年的某一天,我居家上网课,父亲突然开门,说把邮政局家属院的房子卖了。错愕间,振兴街猝不及防地在我的生命里成了历史。父亲咬咬牙借了些钱,带着我们从最南边搬到最北边,住上了有大门、有门卫、有物业、有牌子,甚至有幼儿园的小区。这个小区每年会举办老年人包粽子大赛,家长跟放学的小孩说着普通话,人们说“我”而不说“俺”,刷卡自动开关的雕花铁门取代了坐在大石头上检视来往行人的妇女,“祝您出入平安”取代了她们的叽叽喳喳和灼人目光……我意识到自己换了剧本,扮演起另一个角色了。
极偶尔的时候,我还会路过振兴街,路过“7+1”小超市,路过十三中,路过凌云小卖店,路过那些早餐摊、五金店、公共厕所,当然,也路过邮政局家属院。这里还有人在卖二手自行车,路边靠着缠着头发的塑料扫帚,人们还在用着雨天反臭的马桶、洗一会儿等一会儿的太阳能热水器和用矿泉水瓶子装的洗发露。
那样局促的、羞赧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我的生活似乎有了一些起色,但它依然没有振兴,有关它的感受和记忆像块狗皮膏药似的扒在我的心里,有时候觉得不堪回首,有时候又莫名心生眷恋。十三中门口开了一家奶茶店和一家汉堡店,里面放着几张油腻腻的桌子椅子,很有路内文章里的感觉。
那些谜一样的人,仿佛是振兴街长出的青涩果实。他们都去了哪里?他们现在过着怎样的人生?这条满是扬尘、尾气和油污的灰蒙蒙的街,我不曾想念它,却时常想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