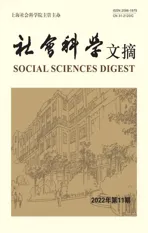论第二人称叙事
2022-12-21张闳
文/张闳
所谓“叙事人称”
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叙事性作品中,人称问题是叙事诗学的基本问题之一。
谁在经历故事,谁在讲故事,谁在编故事,甚至,(假设)谁在听故事,等等,这些是叙事学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经常纠缠着作者和读者。尤其是初学写作者,往往被这些繁复的叙事学问题搞得困惑不已。选择一个怎样的叙事人称以及相关的叙事视角,关乎写作者接下来如何处理故事,如何推进叙事,以及形成一种怎样的叙事语调和风格等一系列诗学难题。
众所周知,叙事性作品通常采用的人称形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他(她)。这也就意味着,叙事人以自己或听众为对象的讲述。毫无疑问,这是叙事(讲故事)的基本言说状态:讲述者与听众的共同在场。必须假定这样一种在场状态,叙事方得以进行,即便是孤独的个人写作,也必须设定一个所谓“潜在读者”。潜在读者扮演了可能的听众,倾听叙事人的讲述。
什么样的叙事人称,部分地决定了叙事场域的基本面貌和叙事语调。谁在讲、向谁讲,这在叙事性作品中是一个重要问题。一般而言,首先是第三人称叙事。第三人称是最基本的叙事人称。第三人称叙事,总是首先假定了讲述者与听众共在状态,这形成了经典的叙事场域。任何故事,总是讲者与听者构成了话语行为。尽管第一人称(叙事人我)也在场,但在古典时代,一般并没有必要以第一人称来讲述。
如果讲述人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奇异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不可确信而又难以证实的事情,就是一种“神话”。如果讲述人并不同时又是亲历者,不能同时成为故事的主人公的话,那即便他要以第一人称来讲述,也不过是一个旁观者、转述者而已。他的第一人称叙事的效能有限,是以我的见闻和口吻,来讲述他人的故事,以“第一人称”来讲述“第三人称”的故事。讲史即是如此。所谓History,不过是His story而已。
那些史诗的讲述者,开创了人类伟大的叙事范式。讲述者将族群古老的记忆得以彰显。讲述人成为族群神话记忆的承载者。他本人的身份无关紧要。他甚至需要消弭自己个人的身份特征,清除个体的记忆痕迹,以及个人的情感、观点、意见和判断,才有可能成为神话的代言人。史诗讲述中即便有第一人称,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主体话语,一种无人称句。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叙事的出现,必须以叙事人的独立人格和身份的确立为前提,而且,它不以集体记忆中的神话、传说为讲述内容,而是讲述关于某个个体化的事件,是作为当事人或旁观者而存在的。这样,只有近代以来故事成为普通人的事务的情况下,第一人称叙事的重要地位才得以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人称叙事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所谓“小说”诞生的重要标志。这实际上是文艺复兴以来所逐步形成的传统。将个人经验作为事件的核心部分,以取代族群集体记忆。因此,近代小说产生之初,往往也带有浓重的自传体色彩。如果我们将这种所谓“自叙传”体的小说视作现代个体意识的觉醒的话,这种觉醒在小说中,首先即是通过叙事人称的变化而呈现出来。独立的叙事人以及叙事人的主体意识,通过叙事话语的自觉,成为现代人对自身在事件中的位置的自觉。
叙事人“我”的出场,宣告了一种独立的叙事文体的诞生。“我”首先是作为一定程度上的当事人、可能的亲历者,在向人们讲述他所经历的或知道的故事。人物同时作为叙事人的主人公,不只是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其生命状态和心理状态,还决定了叙事人的叙事语态、句法,以及叙事结构。
第二人称叙事问题
第二人称是叙事诗学的一大难题,也是一个诱惑。作家们在这个事情上,总是跃跃欲试,希望通过在叙事人称等方面的尝试性的改变,来取得在叙事上的突破。然而,毫无疑问,第二人称叙事是困难的。
米歇尔·布托尔的《变》是一篇著名的使用“第二人称”叙事的小说,也是使用得最彻底的一篇。(他的小说《度》也是如此。)尽管整个故事是讲给所有读者听的,但第二人称叙事将事件亲历者和叙事人都转移给“你”,而作者却设定了一个只有两个人在场的语境,似乎是你我之间的一场对话。或者,他试图让读者成为亲历者,置身于事件现场,并亲历人物动作。如果将所有的“你”都改成第三人称“他”,仅就事件描述本身而言,也能够得以成立,但叙事效果则完全不同。读者很难完全置身局外,很难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受述人”来面对事件。第二人称叙事乃是一种召唤、一次吁请,迎接读者进入事件的现场,成为与人物同在的角色,甚至,他就是作品中的人物本身。这样,读者真正建立起与作者、人物和叙事人之间真切的和现场式的关联。
布托尔在《对小说技巧的探讨》中谈到“第二人称叙事”时,解释道:
这种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尤其是第二人称不再是我们在现实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那种简单的人称代词。“我”包含着“他”;“您”或“你”包含着其他两个人称,并在这两种人称之间建立联系。
很显然,布托尔认为,“你”作为叙事人称出现,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人称变换范畴,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叙事学问题。“你”的存在,同时意味着“我”和“他”的存在,“你”成为一种人际纽带,将任何一种人称联结在一起。“你”将叙事人视作一位当下在场的言说者或倾听者,他们共同构成一种对话关系。并且,“我”像是“你”的一个镜像,反射着“你”的存在和言说。
第二人称叙事人的出现,彻底扭转了叙事路径和叙事语境。“我”与“你”之间的对话,隐藏着一种即时交谈和回应的可能性,而不是第一人称叙事或第三人称叙事的那种单向度的信息传送。更重要的是,它将故事视为现在进行时态的事件。在事件的意义上,第二人称叙事重构了事件的语境和叙事关系,重新定义了事件的时态和空间状态。这是对存在本身的一种重新设定。“你”的在场和可能的回应,随时可能阻滞和打断叙事的路径,使得事件变得看上去不那么稳定、不那么确切,似乎充满了偶然性(尽管实际上叙事话语的路径仍控制在作者手中)。这种人称关系的变化与交往伦理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进而,这种语言行为的多视野性和可理解性,即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伦理”的语言学基础。
在叙事中,我们能够充分自信地讲述“我”的故事,同样,也能够自信地讲述那个被叙事人所设定的“他”的故事。唯有在讲“你”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并无把握确定自己是话语主体。这种主体的不确定性,使得言说变得不确定。其语义也开始变得飘忽不定。事实上,我们无法确定自己在说什么、对谁言说、言说的意义何在。第二人称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话语困境。而正是这种对言说的质疑态度,更加指向了言说深处的真相。第二人称叙事的存在论意义及其难度,也正在于此。
第二人称叙事中的“你问题”
然而,你是谁?这是一个问题。我将它称之为“你问题”。文学是自我认知和自我表达的手段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认知性的精神活动,都关涉人的自我认知,都在回应“谁问题”,即“我是谁?”
我们通常并不关心“你”是谁。一般而言,人类文明总是从关心“我是谁”开始的。“认识你自己”,意思是精神活动的根本问题是“我问题”。大多数哲学家普遍同意,“我问题”才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在哲学家看来,倘若连“我是谁”都无法解答,对“我”自身都无法认清,又如何认识“你”呢?
当人们问出“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发问者知道有“我”的存在,而且,这个“我”在认识论上首先乃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我问题”在根本上意味着人之“我”的自我分裂,作为认知主体的我和作为认知对象的“我”之分裂,“我”成为一个不认识或者说亟须加以认识自己的人,或者说,一个“他者”,一个陌异化的“他者”。如此一来,“认识自己”的命题也就成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单纯的自我反思,未必能够真正发现、认识和理解“我”。“我”在我之中,就像眼睛在眼眶里一样,它是我们视觉的盲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眼睛,“我思”同样也没法真正认知自身,如果不能引进某个参照系的话。
任何“谁问题”实际上有一个被忽略的在场者,一个迎向问题的同在者。以第一人称提问,只有在设定一个第二人称的前提下,方得以成立。现代哲学将“我问题”转化为“他问题”,亦即所谓“他者”问题。必须将自我“他者化”,“我问题”方得以成立。如此一来,“我问题”实际上就变成了“他问题”。当我问出“我是谁”的时候,“我”是一不在场之“他者”。“我”之不在场,则不可能真切地回应“我问题”。可是,被“他者化”了的主体,不可避免地再一次陷入“自我认知”的困境。一个孤立的和静止的“他”,实际上与“我”一样,是无法被认知到的对象。“他”无非是一个外化了的和对象化的“我”。“他者”问题乃是因为现代世界首先搁置了“我—你”关系,“我—他”世界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架构。这乃是对于“我”问题的偏离。因此,他不能真正解答“我”问题。
“你是谁?”这个问题却不是这样。对“你”发问,表明“你”是一个在场之事物。因为某一次瞬间的和偶然的相遇,“你问题”必将摊在“我”面前。并且,这很可能也是你的问题,你同样也需要向我发问——你是谁?在“我—你”关系中,“我是谁”问题首先是“你是谁”问题。我们是在“你—我”关系中确定主体的身份和位置。第二人称“你”的出现,使得这一切都开始产生变化。只有在第二人称叙事中,“你问题”才真正成为问题。
“你问题”是对另一存在物的盘查、质询和追问,是对存在物之实质的当面考察。“你问题”凸显了主体认知问题的无可规避的现场性。“你是谁?”这个问题需要回答,而且其迫切性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我—你”关系就无法被建立,我—你旋即分离,形同陌路,转而充其量成为“他是谁”问题。你若能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意味着你能够回答“你是谁?”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你能够回答“我是谁?”这个终极性的问题。“你是谁?”——这个问题一旦被发出,有可能废除了那个以变动不居的“自我”为中心的标准,引入一个恒定不变的“你”。
抒情性作品中的第二人称
在抒情性作品中,更普遍地存在人称问题。诗歌更愿意选择以第二人称来表达。这也就意味着诗歌更加努力地寻求即时的交流。诗的言说,更多地是一种“你—我”关系的表达。诗的语言总是一种倾诉的语言,它总是指向某个在场的或不在场的对象。
在诗歌中,“你”的位置显得至关重要。抒情主体需要在与抒情话语的倾听当中得以建立。抒情诗中需要“你”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唯有因为“你”,“我”方得以存在。“你”是一个更为恒久的存在,是“我”的精神存在得以超越“我”有限肉身而存在的依据和条件。与其说是“我”对“你”对倾诉,不如说是“你”呼召“我”,唤醒“我”。“我”吁求和礼赞,才构成诗的本质。我们可以在古老的祷词和赞美诗中,看到这种诗歌话语形态的始源。
吁求和礼赞之言一经发出,抒情者“我”即有所期盼,期盼作为倾听者的“你”有所回应。一种来自“你”的应答和回馈,始终在呼求的间歇的静默当中回荡。或者说,这种吁求和礼赞之言,就是为这个“你”的回应而准备的。“我”自己不能回应,“他”也不能回应,唯有这个当下在场的“你”,方有可能做出回应。而且,如果没有这种对“你”的回应的期待,诗歌的抒情就沦为空洞的呼喊,没有意义。因为这种期待,抒情主体“我”由发话者变成了倾听者,或者说,他揭示了任何真正意义上言说者身上都存在的另一重本质——倾听。同时作为倾听者,言说的意义方有了依据。
现代诗人更多地使用“我”直接作为抒情主体,他们不停地说着“我如何”“我怎样”,同时并不具备倾听自身之外的声音的能力。诗人们在无限制的自我倾诉中,耗尽了语词的意义甚至抒情性,以致不得不求助于叙事性和戏剧性,求助于日常生活事件的介入,来遏止抒情的泛滥;进而让诗歌抒情像现代的小说和戏剧一样,陷入破碎、琐屑和冷漠。无情乃是滥情的结果。无限膨胀的“我”,同时也是不断被消耗一空的主体,这也可以视作一个孤立无援的主体对言说的空洞化的内在焦虑症候。从根本上说,诗人总是一个孤独的存在。诗人的存在状态看上去像是对人类存在的根本状态的一种提示。然而,因为“你”的存在,这种孤独反而成为必要。诗歌中的“你—我”共同体,构成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一道屏障,阻挡来自世界的搅扰,哪怕他仍面临内在分裂的危险。
总之,第二人称在文学话语中是一个难题,这一难题既是叙事学上的,也是伦理学上的。它关涉交往和商谈的伦理关系。应该说,第二人称叙事(如果得以成立的话)虽然首先是作为一种叙事学上的技术因素而存在,但它同时还包含着对于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和交往伦理的期待和想象。尽管并不能保证叙事中的这种交往状态一定是友善和睦的,但显然揭示了在叙事中,人对一种直接面对面交流关系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