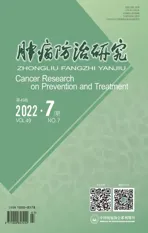产甲胎蛋白胃癌治疗及预后相关基因的研究进展
2022-12-11卢顺利于建平陈为凯李安东何清远陈超韩晓鹏
卢顺利,于建平,陈为凯,李安东,何清远,陈超,韩晓鹏,
0 引言
胃癌已经成为全球最常诊断的五大肿瘤之一和第四大肿瘤死亡的原因[1]。其中普通型胃癌包括乳头状腺癌、管状腺癌、低分化腺癌、黏液腺癌等。除此以外,还有些特殊类型,如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癌、产甲胎蛋白胃癌(alpha-fetoprotein producing gastric cancer,AFPGC)、淋巴上皮瘤样癌等。由于AFPGC具有高侵袭性、预后差等特点,传统的手术与放化疗已无法满足患者对长期生存的期待,且目前AFPGC相关基因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国内外一些学者发现有多个基因与AFPGC治疗以及预后存在着密切关系,本文将对近些年国内外产甲胎蛋白胃癌治疗及预后的相关基因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AFPGC的相关基因
外国学者最先报道了1例胃腺癌伴肝转移的病例,并在患者血清和病理标本中发现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呈阳性,由此诞生了一个新概念“AFPGC”。主要将其分为卵黄囊型、肝样型(HAC)和肠母细胞型(GCED)。最初对于AFPGC的诊断是基于血清AFP水平的升高,至于升高多少却没有明确的标准。后来学者发现,并非所有的AFPGC都伴随着血清AFP水平的升高,这表明血清AFP水平并非是AFPGC的诊断依据。随着AFPGC的研究不断深入以及病理学的不断发展,目前AFPGC的诊断是基于血清AFP升高并结合免疫组织化学AFP阳性的结果。在所有胃癌中AFPGC发病率为1.5%~7.1%[2],它是一种少见的恶性肿瘤,具有侵袭性高、生存期短、预后差等临床特点。目前对AFPGC机制的研究尚无定论,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胃癌中AFP的表达来自于转移的肝细胞癌,使胃癌患者血清以及病理组织中出现AFP高表达;另一种认为肝和胃都从胚胎期的前肠演变而来,胃的原始细胞可产生AFP,但随着胃的进化过程受到抑制,当胃发生肿瘤时,这些被抑制的基因被激活,导致AFP的重新表达。本文将介绍几种与AFPGC相关的热门基因。
1.1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是上皮生长因子受体家族成员之一,属于原癌基因,其编码基因位于染色体17q21,是肿瘤发生的关键驱动因子,主要机制是通过激活下游的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 (Akt)等信号通路,促进肿瘤血管和淋巴管新生、抑制肿瘤凋亡、增强肿瘤的侵袭能力[3]。HER2是人类在乳腺癌中认识最为透彻的基因之一,另外发现其在胃癌中也广泛表达,尤其是在AFPGC中。Fujimoto等[4]通过免疫组织化学对35例AFPGC与334例普通型胃癌研究发现,HER2阳性率在AFPGC中高达37.1%,且HER2阳性的普通型胃癌更容易进展为AFPGC。这很有可能是AFPGC高侵袭性、极易发生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1.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一种高度特异性的促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包括VEGF-A、VEGF-B、VEGF-C、VEGF-D、VEGF-E和胎盘生长因子(PIGF),能够诱导旧血管的再生或新血管的生长。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是能与VEGF特异性结合的受体,主要分为3类:VEGFR-1、VEGFR-2、VEGFR-3。其中VEGFR-1和VEGFR-2主要分布在肿瘤血管内皮表面,调节肿瘤血管的生成。目前除了在胃癌、结肠癌、乳腺癌等肿瘤中发现VEGF表达异常,还在AFPGC中发现其高表达。它们主要通过VEGF与VEGFR结合,激活下游Ras/ΜAPK、FAK/Paxillin、PI3K/AKT(RASRAF-ΜAPK-ERK)等信号通路,进而诱导内皮细胞生长、增殖。国外发现VEGF-C在AFPGC中比在AFP阴性的胃癌中表达更频繁,且AFP具有上调VEGF-C表达的能力,导致AFPGC预后不良。后续在国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5]。
1.3 甲胎蛋白
AFP是一种糖蛋白,编码基因位于染色体4q11~4q22区域,主要存在于胎儿体内,随着胎儿出生后AFP含量迅速减少。在临床中,血清AFP升高主要用于筛查或监测肝细胞癌。AFP基因通过与肝癌细胞膜上的受体结合,激活Ca2+和PI3/AKT等信号通路,上调癌基因的表达,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分化。在AFPGC中,AFP过表达可增加AFPGC的侵袭性以及恶性潜能,并与VEGF具有相关性[6]。进一步研究发现,AFP过表达主要通过激活的Wnt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的增殖和侵袭[7]。
1.4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 3,GPC3)是一种细胞表面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可以参与多种信号通路,如GPC3过表达可上调c-Μyc的表达,可激活wnt信号通路;GPC3过表达可与Hedgehog信号通路结合,抑制下游通路,从而在肿瘤细胞生长中发挥重要生物学功能。除发现GPC3与肝癌存在密切关系外,还与多种癌症相关,如AFPGC。多项研究表明,在AFPGC中GPC3存在高表达,甚至均表达GPC3,并且GPC3表达程度可能与肿瘤T分期有关[8-9]。
1.5 人类婆罗双树样基因4
人类婆罗双树样基因4(Spalt-like transcription factor 4,SALL4)是一种锌指蛋白转录因子,对胚胎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和多能性至关重要。目前其对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机制尚未明确,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1)SALL4可通过激活TGF-β/SΜAD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2)SALL4通过上调分化拮抗非编码RNA,激活β-catenin通路发挥促肿瘤的作用;(3)近期研究发现,SALL4的过表达可激活多个信号通路,如Wnt/β-catenin、上皮-间充质转化、KRAS和TGF-β信号通路,影响胃癌的预后[10]。通过对338例胃癌患者研究发现,其中51例(15.1%)胃癌患者SALL4阳性,包括全部的31例AFPGC[11]。随后Ikeda等[12]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且发现SALL4与AFPGC的分期呈正相关。另一项对1 815例胃癌患者的研究发现,SALL4阳性与肿瘤晚期、淋巴转移、血管侵犯以及甲胎蛋白升高等因素相关,并且发现这是由Wnt信号通路激活所致[10]。以上研究说明了SALL4高表达加剧了AFPGC的恶性程度,两者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2 相关基因在AFPGC治疗中的应用
尽管人们对肿瘤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治疗手段不断丰富,但对于AFPGC仍未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案,目前治疗手段主要采取以手术为主,放化疗为辅的联合治疗模式,王雅坤等[13]研究表明早期发现以及早期手术是治疗AFPGC患者的有效手段,可大大提高患者生存期。但因AFPGC具有高侵袭性、极易转移等特点,当确诊时大多数患者已处于肿瘤晚期,失去手术机会。现有的化疗方案对AFPGC的治疗易产生耐药性,以至于AFPGC的治疗往往差于普通型胃癌。面对着传统治疗模式的乏力,许多研究者和临床医师都在寻求新的治疗方式——基因治疗。
2.1 HER2
HER2在胃癌中的阳性率为12%~20%[14],针对HER2在胃癌中的高表达现象,以曲妥珠单抗为首的抗HER2靶向药物已应用于胃癌的临床治疗。曲妥珠单抗通过与HER2细胞膜外Ⅳ区结合,阻断下游信号通路而发挥抗肿瘤作用。TOGA Ⅲ期临床试验[15]显示,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HER2胃癌相比单纯化疗延长mOS(13.8月vs.11.1月),从此奠定了曲妥珠单抗在一线治疗HER2阳性胃癌中的地位。基于Fujimoto团队的研究[4],1例HER2阳性的AFPGC患者在常规化疗的基础上加入曲妥珠单抗,患者存活3年以上且无复发[16]。Lu等[17]通过建立合适的人源性组织异种移植(PDX)模型,进一步证实了曲妥珠单抗在HER2阳性AFPGC中具有抗肿瘤作用。根据以上研究,建议所有AFPGC患者行HER2检测,其准确性和标准化的检测对于确定HER2靶向药物治疗的目标人群至关重要,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案,缺少临床大数据的支持。此外在治疗过程中曲妥珠单抗出现了耐药性。除曲妥珠单抗外,还有抗HER2的帕妥珠单抗[18]、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拉帕替尼以及药物偶联抗HER2单克隆抗体TDΜ-1[19]等,针对转移性胃癌的Ⅲ期临床研究结果均为阴性,未能获批,但抗偶联药物一直备受关注。DESTINY-Gastric01试验[20]显示,接受过至少二线治疗的HER2阳性胃/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DS-8201(抗体偶联药物)相比于化疗组PFS(5.6vs.3.5月)和mOS(12.5vs.8.9月)均延长,鉴于以上研究,今年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适应证的批准。HER2的双特异性抗体靶向药物Zanidatamab在Ⅰ期[21]HER2阳性胃癌的临床实验中也获得了可喜的疗效,目前正在Ⅱ期研究中。这些新药将弥补曲妥珠单抗的不足,应用于AFPGC的治疗。
2.2 VEGF
针对VEGF与肿瘤之间的关系,研制出了作用于VEGF/VEGFR的大分子单克隆抗体和下游通路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前者有雷莫芦单抗、贝伐单抗;后者包括阿帕替尼、瑞戈非尼等口服药物。下面主要介绍两种在AFPGC应用的抗血管生成药物,而其他类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尚无应用。
雷莫芦单抗是针对VEGFR-2的大分子肿瘤血管生成抑制剂,早在201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其应用于晚期胃癌二线治疗。Arakawa等[22]报道了1例化疗耐药复发的AFPGC患者在接受雷莫芦单抗治疗后,生存长达16个月。同样,1例老年AFPGC患者伴远处转移,给予全身化疗后病情仍快速进展,随后给予雷莫芦单药治疗,用药后患者症状得到缓解,疾病进展受到抑制,最终患者生存了18个月[23]。另1例肝转移的AFPGC患者在接受胃癌根治术后,给予紫杉醇/雷莫芦单抗全身化疗,并以雷莫芦单抗维持治疗,患者生存30个月未复发[24]。雷莫芦单抗在治疗AFPGC中取得可喜的治疗效果,但尚无不良反应的数据,同时缺乏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研究。
阿帕替尼是新一代小分子VEGFR-2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主要机制是高度选择性地抑制VEGFR-2酪氨酸激酶活性,阻断VEGF结合后的信号转导,从而有效抑制肿瘤血管生成。阿帕替尼已被批准用于晚期胃癌三线及其以上的治疗,且制定了甲磺酸阿帕替尼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匡菁等[25]对阿帕替尼单抗联合多西他赛或伊立替康二线治疗78例晚期胃癌患者的研究显示,AFP阳性组2、4周期疾病控制率(DCR)优于AFP阴性组(85.7%vs.54.5%;81.8%vs.45.7%),AFP阳性组mOS与AFP阴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5月vs.6.0月),AFP阳性组近期疗效明显优于AFP阴性组,但远期疗效并无明显差异。唐仕敏等[26]回顾性分析41例AFPGC患者研究显示,阿帕替尼联合多西他赛三线及以上治疗相比单纯化疗可延长OS(6月vs.4月,P=0.017)。最新研究显示,阿帕替尼不仅可以用于二三线AFPGC的治疗,而且在一线治疗AFPGC也取得显著的疗效[27]。随后在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阿帕替尼单抗作为一线或二线治疗相比三线或更多线治疗延长了PFS(10.0月vs.3.2月)和OS(14.0月vs.6.4月),而且阿帕替尼在AFPGC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疗效和可接受的安全性[28]。以上研究将为阿帕替尼在AFPGC的应用提供临床依据,但仍需得到循证医学的验证。
2.3 AFP
AFP不仅是AFPGC的产物,而且在肿瘤的侵袭、肿瘤新血管的形成和肿瘤的发生中起调控作用,同时AFP作为一种分泌蛋白,大量表达后可干扰免疫细胞的监测,导致肿瘤细胞逃逸,因此AFP可能成为AFPGC潜在的治疗靶点[7,29]。研究发现,AFP基因被敲除后,细胞增殖被抑制,早期凋亡细胞数量显著增加,此外Bax/Bcl-2表达上调,降低突变型p53蛋白的表达,诱导肿瘤细胞凋亡[30]。目前针对AFP相关靶点药物的研究已成为热点,主要集中在肝癌。近期,针对AFP靶点的TCR-T细胞疗法的ADP-A2AFP靶向药物Ⅰ期临床试验显示,11例肝癌晚期患者中,1例获得完全缓解,疾病控制率为64%(7/11),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31]。虽然该研究存在着样本量少、研究周期短等问题,但却给AFP靶向药物研究带来了希望。目前已研制出多种AFP疫苗,如多肽疫苗、DNA疫苗以及树突状疫苗,尤其是多肽疫苗在试验中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将为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提供依据。AFP是一种载体/转运蛋白,可将各种营养物质运送到细胞(包括肿瘤细胞)内,所以可通过AFP携带抗癌药物进入癌细胞中,杀灭癌细胞[32]。Pak等[33]研究发现,只有在AFP高表达的肿瘤中,AFP携带药物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同时,AFP携带抗癌药物能够解决困扰已久的化疗多重耐药的问题[34]。综上,AFPGC作为AFP高表达的肿瘤,AFP靶向药物、AFP疫苗以及AFP携带药物将会扩展AFPGC的治疗模式,给AFPGC患者带来希望。
2.4 GPC3
GPC3在AFPGC组织中特异性高表达,且与预后相关[8]。同时GPC3存在于肿瘤组织中,而健康成人中几乎不表达,因此GPC3有望成为AFPGC的治疗靶点,为肿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以GPC3为治疗靶点,研究出了多种治疗肿瘤的方法。Codrituzumab是首个GPC3靶点的抗体,但Ⅱ期临床试验显示,经Codrituzumab治疗后肝癌患者未能在临床治疗中获益[35]。此外,GPC3疫苗在治疗晚期肝癌的临床试验中表现出了较好的抗肿瘤效果,并为肿瘤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近些年,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因其具有高特异性、持续杀瘤等特征而成为了肿瘤治疗的热点[36]。以GPC3为靶点的GPC3特异性嵌合抗原受体(GPC3-CAR)目前主要应用于肝癌细胞。Shi等[37]对CARGPC3 T细胞治疗晚期肝细胞癌Ⅰ期试验显示,患者获得了较好临床疗效,且安全可控。近期,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公布了首个靶点4代GPC3-CAR T细胞疗法治疗肝癌,Ⅰ期临床研究显示,4代GPC3-CAR T细胞单独或与TKIs联合治疗肿瘤显现出了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且对于接受多种治疗的晚期患者显示了潜在的抗肿瘤活性,将为后续临床试验奠定基础[38]。目前对于GPC3靶点的应用大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而且GPC3在AFPGC的分子生物机制尚未被阐明,但作为一种癌基因,GPC3在AFPGC的诊断、预后和靶向治疗中的价值已经逐步显现,通过深入研究GPC3靶点以及借鉴在其他肿瘤中的应用,有望为AFPGC的治疗提供新方向。
2.5 SALL4
作为一种癌基因,SALL4在胃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DNA损伤修复和耐药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且SALL4有潜力作为肿瘤标志物和治疗靶点[39]。早期研究显示,SALL4属于不可成药的靶点,而随后的研究发现[40],SALL4蛋白与核小体重塑去乙酰化酶(NuRD)相互结合后,共同促进肿瘤的进展,因此研究者改变了以往的思路,设计出一种可与SALL4竞争结合NuRD特异性结合位点的多肽,通过SALL4多肽(FFW)阻断SALL4-NuRD的结合可使肿瘤细胞死亡并减少肿瘤细胞的进展,多肽药物-FFW与索拉非尼联合治疗肝癌时,可以减少索拉非尼耐药性,同时对多种伴有SALL4激活的实体性癌症和白血病产生疗效[41]。由此可见,将SALL4-NuRD复合物作为癌细胞特异性靶点的新方法,为肿瘤药物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目前对于SALL4-NuRD药物研究方面仍然处于试验阶段。相信不久的将来,SALL4靶向药物将应用于AFPGC患者。
3 相关基因在AFPGC预后的应用
在预后方面,面对进展迅速且复杂化的AFPGC,普通型胃癌的标志物(如CEA、CA-199、CA74-2等)和单一的预后指标已无法适应AFPGC的预后监测,需要新的预后标志物,由多种标志物进行预后的监测。
HER2在AFPGC中具有高表达性,且HER2阳性比HER2阴性胃癌更容易进展为AFPGC[4]。此外,Lu等[17]发现,HER2阳性与AFPGC淋巴结转移、淋巴血管浸润以及肝转移相关,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HER2阳性状态在AFPGC中是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且17q12位点有HER2扩增的AFPGC存活率较低,侵袭性更强。面对着HER2在AFPGC的作用,应将HER2监测作为评估AFPGC的预后常规监测指标。
早期国外研究发现[42],VEGF导致AFPGC易发生淋巴转移,且与AFP水平呈正相关,是AFPGC预后差的原因之一。随后在国内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5]。VEGF与AFP存在着相关性,可将两者共同作为AFPGC的预后指标,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预后。另有研究显示[43],肿瘤VEGF的表达水平与抗血管药物的疗效密切相关,血清VEGF水平可以作为抗血管药物疗效的预测指标,预测晚期肿瘤患者疗效和预后。血清学检测具有方便、可重复、定量、客观等特点,是组织学检测的一种重要补充。
监测AFPGC患者血清AFP水平也非常重要。高水平的血清AFP是AFPGC的独立预后因素,并且可预测AFPGC早期治疗效果[28,44]。在AFPGC患者中,血清AFP水平与TNΜ分期、化疗以及手术治疗存在相关,尤其是术后患者血清AFP会显著降低,甚至恢复正常,如若再次升高多考虑为肿瘤复发或转移[45]。但该研究未能表明血清AFP升高多少对AFPGC的治疗与预后有意义。另有研究表明[46],AFP≤20 ng/ml、20 ng/ml<AFP≤300 ng/ml和AFP>300 ng/ml的AFPGC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45.8%、17.8%和0。虽然此研究将血清AFP水平与AFPGC的关系量化,有利于临床医师对血清AFP的应用,但迄今为止仍未有确切的规范。
Ushiku等[47]研究发现,AFPGC均表达GPC3,且GPC3的免疫反应比AFP更敏感,此外GPC3的表达程度与肿瘤的T分期密切相关,表明GPC3是AFPGC预后标志物。另有研究发现[8-9],GPC3阳性区域几乎总是与AFP阳性区域重叠,且发现GPC3是AFPGC的敏感标志物。GPC3和AFP在AFPGC的表达调控机制可能有共同之处,而且两者在评估AFPGC预后中也可能存在关联。GPC3细胞外的结构域可脱落进入循环系统[9],因此血清GPC3的监测为AFPGC的复发和转移提供了依据。SALL4不仅在AFPGC中几乎均有表达,而且其高表达加剧了AFPGC的侵袭性[12],所以SALL4可作为AFPGC的预后指标。
综上,AFP、GPC3和SALL4在AFPGC中几乎均有表达,HER2与VEGF在AFPGC中高表达,但对于血清GPC3、SALL4的监测可能存在着困难,一方面是部分医院设施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价格昂贵。在AFPGC治疗和预后的随访过程中,临床医师应多监测血清AFP、GPC3、SALL4、HER2、VEGF等指标。
4 讨论
综上所述,AFPGC不同于普通胃癌,其发病率低,生物学行为差,预后不佳,是一种特殊型的胃癌。目前,基于胃癌的治疗模式以及预后因子已无法适应AFPGC,而多靶点治疗和多因子预后监测将成为一种趋势。AFP、HER2、GPC3和SALL4作为AFPGC的靶点治疗和预后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大多数研究者是通过单一分子标志物对AFPGC的靶点治疗与预后因子进行研究,但单一标志物对肿瘤治疗与预后的预测不如多种标志物,未来需要进一步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