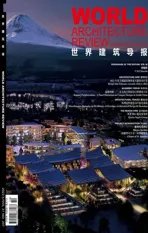红岭七辨
——重织校园和城市经验
2022-11-16作者何健翔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作者:何健翔(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图1.施工中的校园

图2.地景公园之上的山谷庭院

图3.再粗糙化的多义地景 ©吴嗣铭

图4.成对的鼓形学习单元

图5.校园“微都市”之构成

图6.E 形“微校园”楼层
源计划的校园设计经验由深圳而起,一直以来也在这个大陆最南方的超级城市中持续进行校园设计实践,面对高速成长和变化中的高密度城市,笔者对重构过往城市记忆和经验的诉求与未来校园空间的成长愿景之间的两难冲突、以及当中的机遇甚感兴趣。红岭实验小学是“8+1新校园行动”计划的前奏,在此之前深圳早已沿用纯粹的空间生产方式开展“高密度校园”的建造;但在这种生产型建造中,城市和其中的学校建筑被视为快速生产线上的标准化产品,几乎无需被思考和斟酌。发起安托山小学(红岭实验小学的立项名称)概念设计竞赛的部门负责人周红玫女士希望借此项目来探索和创建“高密度校园”新范式1,探索过程充满各种观念、管理程序以及实际建造方面的挑战(图1)。因此,与其把红岭实验小学项目总结为专业上所指望的、按部就班式的设计加建造的过程,不如将其视为一次对现有造城和校园建设既有模式的抗辩和反思。这是本文书写的大背景,笔者尝试将这种辩思和行动归纳于以下的“红岭七辩”之中。
城之辩
第一个辩思的议题必定是“城市”。高速发展的城市在普遍擦除地理和在地人文信息,以便快速拼装出以车行交通为主导的、“电路板模块”式的现代城市系统,城市的不同机能被分区布置于平整而规矩的规划网格之中,每个自上而下式被细化的网格将在特定机构协调下展开同样管理模式的空间划分和建造规划,最终由“建筑师”整装成琳琅的商品性功能空间集合体。于设计者而言,城市扩张是“新校园”行动和范式所亟需面对和解答的背景议题:如何在几乎平滑无阻(同时也极尽无趣)人工网格布上展开营造和重建场所,在急于求“城”的时空话语中呈现具有“意义”的空间行动,而过去的记忆和消失的历史能否与城市公共机能进行连结、成为逆向化城市进程的空间锚点?
为此,设计对红岭实验小学场地实施一种(再)粗糙化操作,情感的冲动让我们将设计过程视作某种地理重塑的行动(图2)。笔者认为,即便在被规定的网格红线范围内,校园仍有机会恢复珠三角原有的丰富而生猛的自由原发状态。赋予设计以行动性的另外一个现实条件是极端紧迫的项目周期。除去竞赛之前被耗费的时间,设计团队仅有大概不到一年十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完成设计和施工。被实现的方案概念是在极短时间内脑力和设计生产的成果,基本上今日所见的实施结果与最初十天设计所生产的概念高度一致:进入校园所见是一个被重新开垦的全架空的粗糙地景,它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密度关系;项目红线以内的场地重塑构成了记忆中孩童可以随处玩耍和交往的公园场景。施工过程的记录或许能更准确地表达被人工改造后场地的蚀刻状态,我们刻意让其“再粗糙化”,通过建立地形的高低起伏以使得校园产生复合多义的活动空间和场所(图3)。
校之辩

图7.高密度校园剖面

图8.密度化城市中的“生态城堡”
个人经验中二十个班的小学已不算个小型学校,而现在新建学校动辄三五十个班,甚至更大。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如何建立符合6-12岁年龄段小朋友交往与体验的空间场所是大容量城市校园的设计要旨。高密度已是深圳建校的常规要求,而红岭实验小学项目由原规划的二十四班增加到三十六班,再加上深圳标准的生均面积指标比国家标准要高出50%以上,导致建设强度接近3.0的容积率。面对高密度,我们在竞赛阶段对建筑的高度控制持坚定立场:小学校园建筑需要维持24米以下的多层状态,此举能使校园内部空间获得最大化的水平向度且无需采用封闭楼梯,如此可灵活自由地联通楼层以获得整体连续的校园体验。
通过上述初始设计条件的输入,设计认为如此规模的校园至少需要三个空间尺度层次以适应孩童们的身体和心理感知需求。最基本的可感知尺度为课室、或称教学单元,一个让孩童们感觉为“家”的单元空间(图4)。第二层次围绕该年龄段的孩子所能熟悉的社群空间尺度,笔者把这个适合孩子们交往的中间尺度限定为两个年级12个班。教学单元被布置在同一水平楼层,走廊宽度的错动变化使每个楼层都获得不同阳光、风景和外界信息。第三个空间尺度是校园整体,结合了日常教学、集体尺度的体育运动和演艺集会空间、以及地面、半地下层的地景公园,三者构筑出全新的校园“微都市”(图5)。
标准的教学楼层基本上容纳了各种教学、游戏、配套和花园绿化,形成了一个笔者称之为“微校园”的日常活动状态(图6)。设计利用原有规划中北高南低的地形,在不同排教室之间,各水平楼层实际上产生了大概一米高差;在两排教室之间有一个非常缓的坡,这个轻微的动作在楼层内形成独特的庭院和空间体验。最终这些单元的楼层叠合在复合地景花园之上,形成高效的空间系统,24米下的可建体积被全部利用,让几乎每寸空间都能够发挥其所能而产生活动效益(图7)。位于校园东侧三层标高平面上的运动场刚好与三层标准教学楼层的中间层相连,即便在极短的课间,孩童们也能从上层或者下层方便到达这个户外空间。在外观上,整个校园是一幢满占用地范围内可建区域的复合型建筑,空间单元的堆积由内及外反映在校园外立面上,构成一个既像城堡、但又见通透的城市界面,实现了在学校周边片区还在大量施工的状态下、维持校园里面相对安静和受保护的内在环境(图8)。
窗之辩
第三个议题被浓缩为教学单元的外窗,一个构造器物的尺度。这是一个构筑孩童们的“家”的起始尺度,是校园中实现所有交往和情感的想象源头。笔者希望在这个校园里实现一套灵活、独立且满足小朋友们交往的“班之家”模式,在创新过程中,设计既需不断挑战既有评判标准,也需回应和满足现行规范。在这个南方的“家”中,“窗”正是核心,但其实现过程极不容易。
在竞赛阶段,我们已有现在这个两两成对的异形教学单元的想法:把普通教室的标准适度放大并进行变形错位操作,争取室内外空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可变而灵活的隔断,成对组合的课室教学单元能够合并使用,获得可分可合的多功能空间。这个想法与校方改革教学模式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整合结构和实际使用要求后实现了“鼓形”平面的教学单元,它们被成对地布置于E形平面楼层(图9)。

图9.成对鼓形课室外观

图10.创新的格窗系统

图11.格窗前的阅读

图12.结构编织的高密度校园

图13.首层开放地景公园中的结构转换柱

图14.多功能风雨球场 ©张超

图15.校园东半区的架构架设 ©吴嗣铭

图16.山谷庭院中的空中连桥 ©张超

图17.与城市对望的空中连桥 ©吴嗣铭

图18.自然滋养中的校园 ©张超
设计试图打破传统建造系统中、把开启窗口当作实体隔断开洞的处理方式,而是把开启、维护和家居收纳整合在一个系统当中。三者的结合使室内外的界面成为有厚度的、体现某种类似生物学概念上的细胞壁的“有机壁膜构造”。这个壁体结构平面上“开”与“闭”两种状态相间并置,“闭”的部分利用壁厚可为课室提供存储收纳空间,“开”的部分则是通透地展示和实现内外交往的落地格窗。除了门扇外,我们把所有的通风要求集中于一扇尺度放大的中悬开启窗(图10)。每个“家”需要一个核心,西方传统中这个核心是家中的“炉台”;而在亚热带的中国南方,核心就是记忆和经验当中可以倚棂相望的一扇窗,这扇窗户既能带来通风和阳光,同时也带出邻里之间的交往(图11)。
结构之辩
红岭实验小学的“结”“构”就是如何在地景重塑的基础上、把地上部分的空间单元细胞连结并构织为一个大的结构体系,形成整体的校园聚落(图12)。为了保持地景花园的辨识度和完整性,在上部教学聚落与地景之间,设计进行了适度的结构转换,使用了类似鸡腿柱形的片柱结构形式(图13)。笔者也采用了模数化正方网格系统来控制平面上的场地建造和地景生成,清晰的网格里也会因空间环境变化而产生多种结构跨度。
校园建筑分为高度和形态都不尽相同的东、西两个半区。西半区的日常教学区就是前述的E形标准楼层,其竖向叠加的框架体系坐落于转换结构之上。在这个标准体系里,设计对面向“山谷”庭院的楼层边线做了大量错层的偏移,加上每个楼面的缓坡处理,标准楼层获得富有趣味的景观体验,楼层板的错动也让设计较为极致地利用深圳相对宽松的日照规则。东半区则以校园的集体性活动空间为主,结构转换与局部大跨度钢结构体系,有利于获取诸多不同尺度的空间;其中最大的跨度出现在东北方向、地下一层架空的多功能风雨球场空间,这里可供体育运动、音乐会和各种不同规模的集会(图14)。往南分别是架空于地景泳池之上的小礼堂和东南角的校园入口花园,位于三层标高平面上的操场平板采用大跨度的钢结构,架设在一系列由地景长出的刚性混凝土支撑体之上(图15)。
桥之辩
“廊”和“桥”、以及它们对建筑物进行串联而获得的动态漫行和游历,一向都是源计划回应岭南地区山水地理传统的空间策略;我们相信,无时不在的运动和变化是南方都市性的核心要素。因此,第五项抗辩的行动具体体现为对两个“山谷”庭院中四道景观连桥的坚持和争取。通过连桥的植入笔者将这种自由游赏串联到各楼层的结构性地景体验当中,在系统性的机能之上增加自由穿行的选项;然而,这个动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多次被要求更改甚至取消,而周旋、说服和继续细化的努力也从未停止,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山谷”中的穿行经历将是整个校园探访和生活经历中的高潮和点睛之处。最终四道景观连桥被艰难落实,为孩童们课间增添了许多身体和心理上的欢愉(图16)。“桥”的动作也为体验密度和关系描画出最后一笔,面对周边高达150米、甚至200米高的城市密度的巨大压迫,它们似乎为校园带来有效回应和抵御的从容(图17)。
植之辩
在所有前述的人工和机械建造活动之外,一个完整的南方校园聚落不能缺失孩童们最好的空间朋友——绿化和自然。理想之中的校园聚落除了包含学校本身的空间秩序外,还应包含现代城市之中所遗失的邻里聚落、以及附着其中的生活和园地。场地重塑后的地形自然容纳了微生态所需的覆土空间,同时将建筑退线与红线之间的距离作为内向的边坡绿化,为地下空间引入自然通风和采光。日常教学区的屋面为校园小农场,每个班都在农场中分得一片自留地。教学楼层内庭的边线错动为楼层空间引入立体绿化系统提供了实施条件,而南方的湿热气候也为绿化系统的成长提供了非常良好的生长条件。两三年时间,校园里面植物、不管是乔木、攀藤还是地被植物的茁壮成长,完成校园内部环境的最后滋养(图18)。
材之辩
在身边的速生城市中,笔者满目所见都是快速生产的工业材质,随着城市扩张,其空间品质似乎反倒在蜕化,大片新建城区仅剩下抽象空间的堆积和空洞的宏大景象。但是,校园的内外空间中需要容纳能促成人和植被交往互动的空间容器,塑造其质感的行动必不可少。类同于在大尺度场地上的地景重塑,我们的设计在细微尺度的表面肌理中同样追求一种粗糙感和操作痕迹,以消解掉商品城市的平滑冰冷。建筑立面最大量的材料应用是由陶棍编排的幕墙式系统,它所编排出的粗糙感结合曲面墙体,形成了独特空间背景氛围(图19)。地景公园中应用了不同材质的多种有机组合,占比较多的是与绿植匹配的一种深色水刷石和灰色水磨石,这些都是过去常用、且能和南方气候与地方性紧密结合的经济性做法。在这些整体塑性的材质当中,设计又渗入不同规格和色彩的马赛克、瓷砖等生活化材质以实现更为丰富的空间与情景体验,如此构成的校园中所有材质都能随之留下时间和被使用的痕迹(图20)。
红岭实验小学项目属于“新校园行动”的前奏项目,其设计和操作过程更接近一个重塑校园空间的纲领行动。回想当初,笔者带着许多问题对这片100米见方、连周边道路都仍仅存于规划蓝图中的抽象场地进行观察,敏感地注意到不远处的安托山在土石方开挖后的山体遗存,形象上有点像传说中的巴别塔。山体位于小学用地西侧不远处,而东侧则是一系列快速建造当中的超高层住宅群。为如此极端却又典型的深圳城区校园场地,我们做出了一个“立体地景”式的提案。笔者将这个提案及其实现过程和结果总结为上述七项辩思议题,在具体操作当中,这些议题并非并置或遵循某种线性的层级结构关系,它们更多贯穿于设计前后、且相互交织于空间的结构主义思考和现象学体验当中。从城市尺度“反平滑化”的地景重塑到表面材质肌理化处理之间的观念关联,从建筑复杂结构所构筑的微都市化系统、对大尺度无意识造城生产的逆向批判,再到校园经验尺度层级的建构、教学单元壁体的开放格窗、内庭院景观廊桥和绿植的情景对视、以及校园“微都市”之“城里”和“城外”的强烈空间经验反差,如此等等,这个进程化的设计体现出不同尺度的观念和行动交织,最终在这个本来平淡无趣的场地上编织出一片属于孩童们自由畅想的乐土,一处高密度城市的立体都市田园(图21)。
注释:
1 周红玫,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市和建筑设计处,四级调研员。

图20.校园材质的丰度 ©黄城强

图21.立体都市校园 ©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