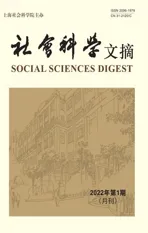“饭圈”观察:组织特征与圈内外关系
2022-10-26毛丹王敬雅陈佳俊
文/毛丹 王敬雅 陈佳俊
“饭圈”现象
“饭圈”十分醒目地集两极化社会形象于一身。一方面,“饭圈”经常有狂热的非常规行为,被视为“不良粉丝文化”,时不时引发社会质疑,引起监管部门和中央媒体的关注与严肃批评。另一方面,“饭圈”有时又表现出社会乐见的“正能量”,一度获得赞扬。“饭圈”组织慈善公益活动、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等行动,具有相当的社会接受度,而且还获得了央视和《人民日报》的热情表扬。“饭圈”为什么会呈现如此矛盾的社会形象?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如下视角和观察:(1)一个新群体能否被社会接纳,首先取决于有没有结构性机会。内地“饭圈”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与改革以来国家对娱乐业和娱乐群体进行政策改革,商业资本对文化产业的介入趋强,以及由此促成的社会成就标准趋多元化、趣味趋中产化密切关联,即,社会转型具备“饭圈”生长的结构性开放机会。(2)“饭圈”能部分理解社会转型给娱乐业提供的结构性开放机会,包括能部分理解来自社会的合法性要求并采取一些积极行动或降解社会批评的行动;但是,作为一种主要依赖文化纽带、感情规训并且接受商业资本介入的类组织人群,在理解政策约束和按照公序良俗标准组织圈内关系与协调圈外关系上存在明显不足,在理解和使用结构性机会方面存在偏差。上述解释建立在文献研究和田野观察的基础上。在文献方面,我们着重爬梳了改革以来的意识形态政策文本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田野工作选择A和B两个“饭圈”,进行了两年的观察(2018年7月—2020年7月)。
社会结构性机会及其特征
“饭圈”的结构性机会主要是指社会转型提供的系统机会。我们把我国改革以来的社会转型理解为从国家全覆盖型社会转向国家宽覆盖型社会。现代国家一般具备干预社会的能力和兴趣,所以现代社会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产物。依照国家干预的方式与结果,现代社会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国家全覆盖型社会,即由计划经济国家全面重组的社会;第二类是国家宽覆盖型社会,即国家大面积干预社会和经济事务;理论上也存在第三类国家窄覆盖型社会,即国家有限组织治安和军事,极少介入社会事务并且基本不干预经济。以上三种社会类型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第一类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对社会采取集束状管理,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基本重叠,社会结构也因此产生集束状特征,社会精英比较单一,社会成就标准与国家标准完全一致。国家出于避免治理成本过高等考虑,在一些领域和层面部分保留习惯性社会规则,但社会要素整体上由国家通过各类制度直接管理。第二类社会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具备自我维系和发展的空间,国家对社会保持广泛干预,但是采取非集束化的树状管理结构,社会精英群体和社会成就标准多元,社会结构也具备非集束化特征。第三类社会主要出现在前现代国家,许多地方和领域处于自治,国家管理社会主要集中于治安领域,按照政治中心与边缘的尺度渐次减少管理,管理结构具有某种圈层状特征。这三种社会类型或社会样态可能发生转型。动力主要来自国家对管理成本与合法性的衡量变化、精英取向变化,以及社会各领域组织运行的能力和要求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着眼于推动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丰富健全,并且通过政策和制度安排渐次调整了文艺与市场、政治的关系,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向树状型管理形态转变,表现为递进的三种管理区分。第一,不再简单用传统高政治标准统一衡量要求所有人与所有领域。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明确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自此以后,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化娱乐方面的政策一方面顺应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文化艺术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向市场企业化运营,激发文化的产业和商品属性;另一方面提出实现从“文艺为政治服务”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转变。广播电视等媒介在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转向举办各种有文化娱乐性的节目,争取更多听众、观众。第二,不再简单用传统高道德教化标准统一衡量要求所有文化娱乐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文化领域市场化改革中,“纯娱乐”内容出现并快速增多,出现了明星演唱会、卡拉OK、录像放映等市场化、“纯娱乐”类型;媒体进入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广播电视在节目内容形式上加速趋近群众文化娱乐消费喜好,《快乐大本营》(1997年开播)、《幸运52》(1998年开播)等“纯娱乐”综艺节目异军突起。这些新节目的娱乐性显眼,只要在国家管理框架允许的范畴内即可。第三,不再简单用传统官媒娱乐尺度去统一衡量和要求所有媒体。2000年以后,国家根据意识形态属性将娱乐体系及大众传媒进行分类管理,国家按照意识形态属性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了分类管理,对上星综合频道为主的官媒与网络自媒体在娱乐节目制作等方面采取不同要求,对于后者,国家主要明确不同题材类型制作的原则,要求节目内容与社会主流价值导向之间有契合度,对娱乐节目制作数量并不控制,后者在题材内容选择及制作标准上有很大的市场自由度。
上述改革意味着国家将大量文化资源释放给社会和市场,2005年后新出现的粉丝群体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生长空间。文化娱乐产业对于国家的经济效益回报非常显著,巩固了国家在这个领域的改革方向和信心。这些改革除了直接形成国家容纳“饭圈”这类新群体现象的框架之外,还促成两个重要的机会副产品。首先,商业资本大量流入文化娱乐业,对“饭圈”形成直接支撑是在国家对文化娱乐业改革过程中实现的,几乎是国家对文化娱乐业政策转向的副产品。其次,这个转向也促成了社会其他群体对于娱乐业和“饭圈”的态度变宽松,故而“饭圈”才有机会获得社会容纳。
国家改革文化娱乐业政策并不意味着放任,而是一直保持着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与价值的基本尺度。因此在树状管理结构上对包括“饭圈”在内的日常娱乐活动,国家一直通过党政途径引导和规范相应人群在价值理念、行动取向上不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的要求。该表扬的表扬,该规范的规范,国家对娱乐业管理既保持开放又保持基本约束,这是“饭圈”这类新群体所获得的结构性机会的基本特征。
结构性机会并不保证产生固定结果,“饭圈”能否行动自如又赢得社会接纳,取决于“饭圈”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机会。作者在田野观察中发现,“饭圈”部分理解结构性的开放机会,但是不善于理解结构性的约束要求,或者没有充分能力保障粉丝群体恪守约束。这种复杂表现与“饭圈”的类组织形态有关。
类组织的特征与强弱项
(一)类组织特征
A、B“饭圈”都有一些组织特征,包括圈层化等级、内部专业分工等。“饭圈”内部存着同心圆式的权力结构,位于核心圈层的是经纪公司首肯的后援会等组群、“反黑”站数据组等职能型组群以及一些有话语权的大粉。次一圈是一些资源产出型图站、影响力较小的组群以及忠实粉丝。最外圈才是数量最多的普通粉丝。“大粉”处于核心,是社交平台盛行以后由普通粉丝流动到圈层中心,其话语权主要来自技术赋权、人际关系赋权、信息赋权等。
尽管如此,A、B“饭圈”都更像一种“类组织”,虽然有上述组织形式与制度等,但既不是登记的社团,也不完全按社团运营,成员灵活流动性很强;有制度或隐性制度来固定重要规则,但是又比一般社团更依重文化和感情纽带。
“饭圈”明显不属于正式社团。它公开的组织方式与基本制度主要是“超话”论坛本身的规则。“超话”是新浪微博中的网络社区,是粉丝聚集互动的标志性场所,也是“饭圈”的主要活动点。“饭圈”的日常活动更多的是围绕特定目标采取自由聚集的方式。聚集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聚集形式是仪式型聚集。另一种聚集形式是临时任务型聚集,主要采取粉丝组织召集—核心粉丝联动—普通粉丝参与的模式。选择上述类组织的方式,兼有能聚集、低成本两种效用。用于A、B“饭圈”运行的成本微乎其微,几可忽略不计,但是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组织或维持粉丝集体行动,只不过组织力量尤其是约束能力不比社团。所以,“饭圈”还采取了以下办法:
1.依托制度但是更注重情感动员
“饭圈”试图用基本制度公开和监督公开的方式去增强内部公平感,增进内部黏力。但是,这类制度的约束力和团结功能不太强,主要原因是“饭圈”由粉丝自发聚集组织,加入与退出都相对灵活,成员流动性较高。“饭圈”仅能相对控制进口,对其他环节的监督较难。“饭圈”的内部秩序和团结很难完全依赖制度,所以注重情感联络,经常在网上频繁互动,以培养加强情感纽带,提升群体黏性,即强化粉丝群体的共同情感体验,激发其参与动力。情感动员在形式上比较突出使用本“饭圈”的独特符号,标识此圈、彼圈的界限,激发粉丝的身份感。“饭圈”的情感动员主要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虐粉”,即夸大偶像所处的不良境遇,制造悲情,激发粉丝同情欲,常常使用“哥哥只剩我们了”等句式;第二种则是通过成员关系更亲密的次级群组进行动员,粉丝个体很难不选择跟随。
2.日常规训
“饭圈”对粉丝的日常规训集中于教导粉丝“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粉丝”以及“合格的粉丝应该做什么”两个主题,或者说聚焦于准入标准与情感劳动两个环节,主要教育粉丝初步付出只是得到粉丝的资格,更高级别的付出才能维系粉丝的身份和品格,并享受相应权利。所谓付出,主要是指为偶像花费时间或金钱。“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粉丝”议题主要突出“饭圈”准入标准,强化粉丝的区隔意识。“合格的粉丝应该做什么”的议题聚焦于规训进入“饭圈”的粉丝继续为偶像付出,特别是基于情感为偶像自愿无偿付出。
(二)圈内外关系处理与突出弱项
“饭圈”的类组织性带来“饭圈”运营低成本化,既有某些组织效能,又避免了一般组织维系运转所需要的成本;既有一些较明确的制度,又持续关注成员黏性和情感规训带来的行动协调性。当“饭圈”具备一定内部协调性后,更多、更直接的问题通常来自行为模式与其他群体不同而面临社会合法性压力,“饭圈”如果不能协调外部关系,作为类组织就缺失了基本功能之一。“饭圈”的早期生存压力明显,因此对外部要求有一定意识。“饭圈”A、B都有注意到需要把外部合法性要求转为圈内规则,发展一些平衡圈际群际冲突、减少社会反感和设计“正能量”行动等增加社会接纳度的策略,甚至有意识到需要将主流群体认可作为“饭圈”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相比“饭圈”提升社会接纳度的“软努力”,粉丝对来自管理部门和社会舆论的社会约束性要求及其阶段性变化的感知远远弱于对社会开放性和宽松度的感知;“饭圈”作为类组织则缺乏向粉丝传导社会要求、约束成员不出格的“硬能力”,经常难以控制成员的过激言行相互传导而酿成各种社会事件。所以,A、B“饭圈”各种增加社会接纳度的行动的效果仍然显得不尽如人意,更多的是在自我约束上表现出两大问题:一个是圈内粉丝对社会约束性的感知一直普遍弱于对社会开放性的感知;另一个问题更为关键,即“饭圈”只是一种类组织,与任何组织都不相同。“饭圈”有圈层等级,但主要标识在圈内地位和影响的大小,而不是支配性权力的安排;它设立了各种内部组群,但主要出于职能专门化分工而不是科层关系安排;“饭圈”有一些制度规则,但其主干是平台网站的一般性规定,更主要依靠圈内粉丝的感性、感情纽带和尺度。所以,“饭圈”对粉丝的聚合力一直大于对粉丝的约束力,善于临事一呼百应聚集粉丝,不善于以组织制度约束成员;善于激发粉丝情绪,却无法在事先事中事后进行群体情绪管理。在“饭圈”实际上附着于互联网大平台以及粉丝进圈出圈较自由的情况下,如果作为组织的互联网大平台疏于必要的细致组织管理,作为类组织的“饭圈”很难单独防止粉丝一哄而起进入“类乌合之众”状态。
简短的讨论
“饭圈”是社会学观察的对象,同时又是一个公共话题。本文就此再作三点讨论:
(1)“饭圈”是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类组织人群。类组织水平的人群在与社会公序良俗保持一致方面只有相对能力,还无法像一个社团约束成员那样发挥约束力。“饭圈”要寻求提高社会容纳度,就需要全面理解社会要求及其特征,在类组织内部寻找和发展出对粉丝的正面约束力和协调力。
(2)我国保持着确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灵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而有社会主义价值观边界的娱乐消费文化所组成的基本结构,“饭圈”需要恪守在这个基本结构内活动,才可能有充裕空间。
(3)管理部门治理“饭圈”乱象的政策还要更多考虑类组织的对应性、适用性。在坚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和保持社会主义文化原则以及公序良俗的方向下,需要对应“饭圈”作为类组织实际上附属于互联网大平台组织的特点,更多增加互联网平台的组织责任,通过完善平台组织及其管理制度,向“饭圈”传导社会合法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