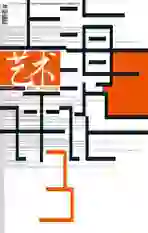王洛宾民歌的中华性和世界性
2022-07-05张春梅
张春梅
在当代民歌传播史上,论及数量、传播广度、受欢迎程度,怕是没有人能超过有“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他以一个人半个世纪的人生在青海、在新疆的草原、牧场和绿洲,以游吟诗人的姿态行走、歌唱,收获了全世界的目光。《在那遥远的地方》《可爱的一朵玫瑰花》《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汗》《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一个个名字平实而亲切,把遥远的“西部”、维吾尔和哈萨克以美好的情歌送进了世界的口与耳。
民歌改编如何呈现“中国哈萨克”
王洛宾是个很有意思也很有争议的人物。音乐家勉行发表在《人民音乐》1995年第6期的文章《做个堂堂正正的作曲家》就是这“争议”之中的典型。其主旨是王洛宾的《自选作品集》中有些曲子实为剽窃他人果实,还有他在不同场合编造出同一首曲子的不同传奇故事,并以《都达尔和玛丽亚》作为佐证。这些官司历经时间烟尘已渐渐散佚为“世界的中国民歌”背后模糊不清的斑点,文章中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新疆哈萨克人东迁至青海与宁夏的历史、50年代中国音乐界收集民歌尤其少数民族民歌潮,反而在这篇短短口诛笔伐小文中透露出重要的讯息:
其一,如果没有这些音乐家扎实的民间田野工作,像《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在那遥远的地方》一般美妙而旷远、亲切而悠长的歌曲,恐怕就会因为语言的隔阂而成为“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一江水》王洛宾词曲),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民族、跨地域的文化传播经过一首短小民歌的传颂实现了“中华一体文化”构建,其象征性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围绕民歌展开的“王洛宾们”是记谱者,还是填词者,是创作者,还是传播者,也就是这首曲子属于谁家,常常成为争议的焦点。相比于勉行先生的批评,讨论同一首曲子改编到底何者更能体现民族性,可能是更大范围、更强调差异性的问题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前者就变成基于同一“民歌整理”立场的内部争端,是知识分子伦理道德的问题,后者却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争夺民族遗产的话语权的行为。恰巧在这两方面,王洛宾都名列其中。
其三,勉行先生讲到“王洛宾热”,将时间线拉到了90年代初期。此时市场经济初初开始,港台流行音乐以更有利的态势进入中国,王洛宾的民歌也成为这一“流行”的一部分。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郭富城唱《沙里洪巴》、张学友唱《康定情歌》、黎明唱《虹彩妹妹》,最后刘德华以《青春舞曲》压轴,完成彼时中国最具影响力舞台的“四大天王民歌演绎”,使王洛宾的民歌进入“最流行”行列,一时间蔚为街头热唱的对遥远之地的想象和回忆。而携着“撒哈拉、骆驼和荷西”来到西部的三毛,加剧了王洛宾的“流行”,正是这样一种诗意、浪漫、跨越时空的联合将王洛宾拉出了一班“民歌搜集者”的历史行列,而进入到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从此方面看,“王洛宾”就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具有特定情境指示的表征。
其四,这里“争议”的几首曲子和王洛宾特别青睐的歌风集聚在一个西部民族——哈萨克族,这就将王洛宾与哈萨克民间音乐传播勾连起来,进而涉及到民族音乐如何世界传播的问题。哈萨克族的音乐是何风格,王洛宾的改编怎样成功建构了“遥远而亲切的哈萨克”,并以处处洋溢的“生机”和90年代中国站在一个精神平面上,就成为认识当代文化哈萨克的关键地带。
从《都达尔阿依》到《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都达尔阿依》是首哈萨克民歌,王洛宾改编曲中大概是最早的之一。勉行文章里并没有提到这首曲子,他着重讲述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有意思的是,他并没质疑王洛宾记谱改编的真实性,却指出他在不同场合提起这首曲子给出的创作经历太过随意,“我26岁,曾悄悄爱过一位千户长的女儿这首歌是坐在两个驼峰之间写成的”。1这里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王洛宾与哈萨克民歌的结缘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1939年左右新疆哈萨克人东迁,哈萨克文化开始进入所迁入地区;二是王洛宾的民歌改编曲具有鲜明的想象性和原创性,这在歌词中是可以感受到的。《都达尔阿依》正是这一情境下的产物。据王海成先生追溯,“王洛宾最早接触到这首哈萨克族歌曲,是上个世纪的1939年,那时一支新疆的哈萨克族部落迁居到了青海的海西地区,为了能在当地安居乐业,他们派了30多名代表,带着礼物前往西宁。想要与当时的青海省政府商议‘归顺’之事。当时,王洛宾正在西宁昆仑回民中学当音乐教师,他听说从新疆过来的哈萨克人要来西宁与政府商议‘归顺’之事,并且还带着能弹琴,会唱歌的民间艺术家。这个消息着实让酷爱搜集新疆各民族民歌的王洛宾兴奋不已”。2
《都达尔阿依》诞生于这次艺术交流,却经历了名称的三重转变:都达尔阿依——都达尔和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其变化逻辑充分体现了从创作到传播过程中的浪漫气质,勉行先生所说之“难以对历史、对众人圆说的蠢事”,反倒见证了民歌在口耳传唱中的传奇性。其作者为谁、其作为何,都没有“耳熟能详”的传唱来得重要,这大概就是民歌与文人创作之间最大的区别。《都达尔和玛利亚》是王洛宾的命名,其重点从哈萨克人“都达尔”转移到了男女青年双重主体。有趣的是,在哈萨克人中流传的《都达尔阿依》的吟唱主人公不是都达尔,而是那个痴情女子玛利亚,这就在名与实之间构成清晰的悖论:都达尔作为一个不在场的符号成为玛利亚的抒情对象,以“名”代“实”,俄罗斯人玛利亚就此依托都达尔活在不断“发誓”“我是为你一人而生的”语境之中,直到今天,和《在那遥远的地方》一同延续着人们对草原人的想象。到了《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則进一步于具化中虚化民族,坐实的却是人们对热诚、浪漫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的追求。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都达尔与玛利亚》流传到90年代时开始具名的又一表达。这一名称进一步成就了彼时的“王洛宾热”。具体时间无从考究,但从现有资料看,此名与江泽民同志有关,如珠丽杜孜·巴格达提的《哈萨克族歌曲〈都达尔阿依〉调查研究》,她照搬“百度百科”的科普:多次看到江主席“亲自弹着钢琴,高声歌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的镜头。可能是因为江泽民同志亲自将《都达尔阿依》取名为《可爱的一朵玫瑰花》”3这种推论,到了女高音歌唱家加米拉“在1997年全国第五届文化会,我向江主席献歌一曲《可爱的一朵玫瑰花》”,4则不留一点原歌名痕迹,已经自然而然是“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之间所有的千回百转落定在“可爱”二字。这样的歌名三重变奏,无疑极大丰富了民歌的蕴涵和想象。在内容上,王洛宾的改编与此并驾齐驱,也发生了从言语、主体到结构的系列变化。
维度:民间性与大众性
王洛宾记谱改编后的这首民歌,比之哈萨克版最不同的或许就在于“不仅仅是哈萨克”。他将词曲名为《都达尔与玛利亚》,是尊重了原曲的题旨:男女青年的恋情。他并没有关注他们的民族身份,而是将重点放在他们初见瞬间怦然心动的感觉,“那天我在山上打猎骑着马/正当你在山下歌唱婉转入云霞/歌声使我迷了路我从山坡滚下哎呀呀/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寥寥几句,就把彼时彼刻的情景勾勒出来,“歌声使我迷了路我从山坡滚下”,仿佛眼前所见只有这燃烧着的热烈情感,而人生理当如此真纯。辅之“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的反复咏唱,就把哈萨克人的不羁、洒脱而诗意纵横的一面汇入了听者、见者、唱者的想象图谱之上。这是非常高妙的起兴与叙述的结合,少了哪一环都会减损这首民歌的意趣和兴味。
整体结构则采取了对答式的情歌对唱结构,前有小伙子伊万都达尔见到姑娘激动而无措的模样,后有姑娘玛利亚大胆的邀约,这就打破了一人抒情的想象场景,在空间上拉近了对话者和听者之间的距离。这令我想起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刈麦者》,描写的也是一个在“高高的山岗上”唱歌劳作的姑娘,但听者、唱者和看的人三者之间始终保持着远观态势,每一方都很难进入对面的世界,如此方见“孤独之深”。我们来做个对比。开头,王洛宾上来就是反复咏唱这“玫瑰花般的姑娘”,这个玛利亚与其所在时刻构成了一个诗意的世界,这个世界饱含着看他的小伙子的全部情感;而华兹华斯却在同样的场景中用了“你看!”一词,骤然将看者和被看者放置在不同的世界。二者差别迥然!姑娘的歌声是吸引两首诗中看者的密钥,王洛宾将歌声形容为“婉转入云霞”,同时不忘带上小伙子的感受,还为其民族性不着痕迹地做了记号,这是个“山上打猎骑着马”的哈萨克小伙。怎么描摹歌声的效果呢,“迷了路”“从山坡滚下”就足以说明问题;但华兹华斯笔下的姑娘,“她独自在那里又割又捆,/她唱的音调好不凄凉”,这样歌唱的姑娘,是没法与行人形成对话的,只有独自一人咀嚼着的悲伤,“请你站住,或者悄悄走过!”于是乎,整个氛围便与王洛宾的民歌情趣盎然的场景形成鲜明反差,所有的声响似乎都化为无边的孤寂。于此,不同情境、不同主体、不同的书写方式造就了诗歌巨大的差异,一个属于个体“独乐乐”,一个则是“众乐”,凸显出中西审美差异。民歌的大众性质则更加深了二者的不同。
在这样的架构下,听众就有种熟悉中的异趣,这就保证了歌与不同地域、民族的人之间建立起适当的审美观照,其距离保证了普遍的欣赏和共情的发生。换句话说,王洛宾打破了单独的哈萨克领域,而将草原上的哈萨克带到了世间。当《都达尔与玛利亚》的名字换成《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响彻中国的时刻,就成为响当当的世界中国符码。在这个意义上,王洛宾是了不起的。
关于《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在哈萨克斯坦流传的有三个版本,也是一首深受哈萨克人喜爱的民歌。然所面对的受众不同,时代不同,歌词的面貌也大相径庭。略举一例。
第一段:玛利亚姆,俄罗斯人扎果尔之女,/已到了16-17岁,亭亭玉立。/想当年爱上都达尔,哈萨克青年,/献给他这首歌曲,表示爱意。/都达尔哟,我的都达尔/我是为你而生的/哎呀呀,都达尔,我的都达尔
第二段:阿西湖,与图西湖互相接连,/头上的帽子都是有着别样。/啊,都达尔,要来就请快一点来,/几多人娶不到我,与我变脸。/都达尔哟,我的都达尔/我是为你而生的/哎呀呀,都达尔,我的都达尔5
这两段词的主角都是这位“玛利亚姆,俄罗斯人扎果尔之女”,起手点明其民族属性:俄罗斯。紧接着介绍姑娘爱上的是“哈萨克青年”,这就清晰呈现了爱情诗的焦点,不在是否“爱上”,而在“让不让爱”“能不能爱”,其时代性、民族性和意识形态性尽皆包裹在名称隐喻之中。结构上,也不像王洛宾版是男女对话,从而营造双方投入的在场感。整首民歌采用叙述者交代前情:“想当年爱上都达尔,哈萨克青年,/献给他这首歌曲,表示爱意。”6也就是说,这是姑娘的心里话,全是说给都达尔听的,而“当年”也就自然带上了回忆的味道。于此,和王洛宾简简单单的“歌声让我迷了路”相比,爱情之光逊色不少。尽管后面姑娘不断呼喊“我是为你一人而生的”,也只能是多了些“爱而不能”的无奈,因为,那男主人公始终缺席,变成了一个被爱的影子。两首同一主人公、同一曲调的民歌似乎变成了两个故事。这首哈萨克斯坦民歌跟中国古代的《上邪》诗倒是很像,都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气魄,但就现代感和民族性表达而言,显然是不及王洛宾的《都达尔与玛依亚》的。
在前面提到研究《都达尔阿依》的硕士论文7里,言及“玫瑰花”的族属问题,哈萨克女孩在没结婚之前能否邀约男子约会问题,进而推知王洛宾的改编版与哈萨克传统相距甚远。此文以哈萨克斯坦流传的几个版本与王洛宾版比较,其音乐学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将文本分析重点落脚在是否为哈萨克传统,显然,距离艺术分析和文本的审美感受甚远。玫瑰花是否会用来形容哈萨克女孩,歌词中的都达尔和玛利亚是否在晚上月下相约成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般的姑娘,其美其神韵,在反复吟唱中如在目前;重要的是因唱着“婉转入云霞”歌儿的姑娘和“骑着马”的棒小伙心意相通,彼此向往和思念,表达上的泼辣和大胆不但不会有违道德伦理之感,反而显出情感的纯挚和热烈。我想,这就是这首曲子百唱不厌、动人心魄的地方。而若非要寻找哈萨克性质的话,整首曲子的声调、委婉抒情的情态,加上浑然于整曲的“带上你的冬不拉”,才是真正悠长蕴藉的哈萨克味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洛宾的民歌改编和传播具有了超越性质,它不拘泥于民族属性的限制,但又在音乐风格上忠实于民歌,他的歌词借重于曲调书写出蓬蓬勃勃的民间味;他在记录哈萨克,也在创造哈萨克,这些曲子是民族的,却在重新书写中成为世界的。一首民歌,却建构出阔大的世界文化共同體,这是艺术无远弗届的属性,也是艺术家的创造力。
作者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江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基地成员
1.勉行.做个堂堂正正的作曲家.人民音乐[J].1995(6):35.
2.王海成.流淌的歌声——“都达尔和玛丽亚”[J].新疆文艺.1995(8).
3.珠丽杜孜·巴格达提.哈萨克族歌曲《都达尔阿依》调查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5.
4.https://baike.so.com/doc/6969928-7192614.html2020-05-14.
5.哈伊萨尔.Дудар-ай这首歌的来源介绍,百读网[A].珠丽杜孜·巴格达提.哈萨克族歌曲《都达尔阿依》调查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5.
6.同上。
7.珠丽杜孜·巴格达提.哈萨克族歌曲《都达尔阿依》调查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