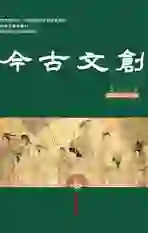品特后期代表作《尘归尘》中的修辞性叙事
2022-05-19吴迪周晓航
吴迪 周晓航
【摘要】在哈罗德·品特的后期代表作《尘归尘》中,品特将以往的戏剧主题与风格杂糅形成戏剧内情节发展的文本动力;叙述者与叙事读者、隐含作者与作者的读者构成二维叙事交流,通过读者一系列阐释判断、伦理判断以及审美判断,制造戏剧发展的读者动力。《尘归尘》是品特与熟悉其剧作的观众的一次修辞性叙事交流。品特通过引导观众对其戏剧的整体回顾向观众呈现谢幕。
【关键词】哈罗德.品特;《尘归尘》;修辞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8-0022-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8.007
完成于1996年的戏剧《尘归尘》(Ashes to Ashes,1996)是诺贝尔获奖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后期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戏剧生涯的集大成之作。融威胁,暴力,纳粹,嫉妒,爱情,权力,记忆等多重主题于一体,《尘归尘》多元混杂的意义与矛盾悖论的话语游戏引发评论界的热议。虽然国内外评论界对此剧的探讨涵盖以往品特研究的热点问题如权力、威胁、政治剧与女性主义等,但作为品特戏剧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戏剧,《尘归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集大成性。著名品特评论家耶尔·扎伊莱沃(Yael Zarhy-Levo)认为“《尘归尘》表达了作家对之前所有批评定位的回应,堪称是一次创新的尝试。它同时激活了品特早期和后期的戏剧模式,提纲挈领式地为品特整个创作轨迹列出一幅谜一般的戏剧地图。”[1]133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深入探析戏剧文本,从詹姆斯·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出发,通过分析《尘归尘》中戏剧情节发展形成的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最终揭示品特在此剧中综合以往戏剧主题与风格的戏剧创作修辞。在《尘归尘》中,品特通过独特的艺术修辞成功地在读者脑中唤起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品特戏剧语境。
《尘归尘》在情节上非常简洁,只有两个人物:妻子丽贝卡和丈夫德夫林。整个剧情是建立在两个人物围绕着妻子昔日的情人而展开的一场记忆式的对话,但此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看似私人的对白之间走向了人类暴力的宏大主题。本剧开始时,丽贝卡正在向丈夫德夫林回忆一个神秘男子如何一手抓住她的脖子,将她的头拉向他,让她亲吻他的拳头的情景。随后,身体上的暴力威胁转为夫妻婚姻关系中的“闯入者”威胁。通过德夫林的逼问,丽贝卡的躲闪,对神秘男子身份探究的情节在夫妻二人间的对话中伸展蔓延开去。
很快婚姻家庭中的暴力话题转化为二战纳粹暴力的集体记忆,丽贝卡讲述了令观众惊恐的意象,在她的记忆中,一群人在向导的引领下投海自尽,他们的行李四处漂浮在海上;同时那个她口中的神秘男子还走上城市火车站站台夺走母亲怀里的婴儿。一时间舞台上盈溢着无处不在的威胁感。而这一切意义的建构又在记忆话语的掩盖与自我否定的话语中变得若有若无,模棱两可。婚姻家庭、政治迫害与记忆剧等熟悉的品特式主题,荒诞派极简主义风格的舞台布景与真假难辨的戏剧对白等品特以往戏剧创作的元素的杂糅形成了该剧特有的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成功地建构了与读者的叙事交流。
《尘归尘》是一部基于叙事交流目的的修辞性叙事作品。品特的创作目的不在于构建连贯的情节和传递完整终结的意义,而在于通过调动读者反映而实现他与读者的叙事交流目的,从而引导读者做出基于作品整体艺术价值的审美判断。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映之间的交流互动是美国修辞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提出的文本分析模型。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认为,写作和阅读是一个复杂和多层面的交流过程,“作者通过叙事文本,要求读者进行多维度(审美的、情感的、观念的、伦理的、政治的)的阅读,反过来,读者试图公正对待这种多维度阅读的复杂性,然后做出反应。” [2]23这种以文本为中心,以读者反映为取向,强调作者意图的修辞叙事理论显然为解读《尘归尘》提供了有力的阐释框架。
在《尘归尘》之前,品特的戏剧创作一直践行着修辞叙事交流的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品特拒绝在戏剧中为任何社会意识形态服务,他曾断言:“我所写的东西不服从于其他任何东西,除了它本身。” ①但这并不等同于品特放任剧本意义的虚无,他强调作者在选择和安排上的作用,“我不认为我的人物是不受控制的,我所起的作用是选择与安排……这个过程,毫不夸张地说,是头等重要的。” ②在强调作者意图即作者代理的同时,品特更凸显了文本的重要性,“你创造了词语,词语获得了它自己的生命,他就以某种方式与你对视,它变得倔强了,多半会打败你。” ③然而尽管对语言内在含混意义的探索突出了戏剧文本的重要性,品特最终承认,“如果没有传递给观众的趣味、挑战与激动,那么就一无所成。” ④
综上,品特的上述观点和强调作者意图,凸显文本中心,以读者反映为取向的修辞叙事理论体系不谋而合。所以,本文将立足于修辞叙事的理论框架,审视《尘归尘》这部品特收笔大作的戏剧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最终揭示读者在品特戏剧修辞作用下形成的整体艺术审美判断,进而证明《尘归尘》继承并发展了品特戏剧创作风格,是一部集大成的封笔之作。
一、《尘归尘》中的文本动力
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Narrative as Rhetoric)一書中将叙事内在的文本动力定义为作品情节从开始到中间再到结尾展开过程的内在逻辑。文本动力通过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和人物自身内在的冲突形成 [3]56。在《尘归尘》中,品特通过杂糅以往戏剧风格的方式形成文本动力将情节推向前进,各种戏剧风格的并置形成了人物之间、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冲突,增强了《尘归尘》中的戏剧情节张力。
在《尘归尘》中,威胁喜剧与记忆戏剧的风格相交织,性、权力、家庭伦理、宗教、心理等主题杂糅形成《尘归尘》戏剧的文本动力。按照费伦对叙事进程中文本动力的划分,叙事开端的第一个方面是“说明”,即提供有关人物、场景的背景信息。品特借助以往威胁喜剧风格形成剧本开端的文本动力。在《尘归尘》的开始,观众仿佛置身于品特早期威胁喜剧的氛围中,感受到神秘的威胁的氛围充斥舞台,戏剧情节也在女主人公丽贝卡充满悬念与威胁的讲述中展开,这形成了最初的文本动力。
《尘归尘》中的两个人物是丽贝卡和德夫林,他们都在40岁左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背景信息。时间是黄昏,场景是乡间的一所房子,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在演出的过程中,房间内的灯光逐渐变亮,而房间却逐渐变暗。同时两个男女主人公的设置与品特第一部戏剧《房间》(The Room,1957)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房间》的时间设置在早晨,女主人公罗斯站着,男主人赫德坐着吃饭,罗斯不停地唠叨反衬出赫德的沉默,相比之下,《尘归尘》的时间在黄昏日落之际,女主人公丽贝卡坐着,而德夫林手里拿着酒杯站立,丽贝卡的记忆话语游离于德夫林的步步逼问的话语控制之外。《尘归尘》情节的开端呼应了品特的第一部剧作《房间》。如果《房间》是品特戏剧创作的清晨,那么《尘归尘》则象征品特戏剧创作的日暮。
《尘归尘》的开端唤醒了品特戏剧读者对《房间》《看房人》(The Caretaker,1960)等早期威胁喜剧的回忆,而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则在记忆戏剧的方式下围绕性别、权力、宗教、话语、大屠杀等一系列主题展开,其间品特以往戏剧的影子若隐若现。丽贝卡一开口就让观众陷入了性暴力威胁的情境之中,她讲述到记忆中的一名神秘男子正一手掐着她的脖子,另一只手握着拳头,对她暴力相加。这种威胁感与《房间》中赫德对罗斯的威胁一样令人不寒而栗。在充满威胁与悬念的开篇之后,丽贝卡又迅速化身为《回家》(Homecoming,1964)中的露丝般兼具圣女与荡妇角色于一身的形象,利用性魅力对丈夫德夫林构成压迫。她不仅对记忆中的施暴男子赞誉有加,还对德夫林冷漠无情,冷嘲热讽。凭借性别魅力,丽贝卡对德夫林构成了上帝一般的权力。在之后一段的情节发展中,德夫林妒忌的追问,丽贝卡的自说自话在升级戏剧冲突的同时将性别关系中的爱与被爱,男性的直线思维与女性的发散思维演绎的差异表现出来,令观众仿佛看到了品特另一部戏剧《风景》(Landscape,1967)的影子。在《风景》中,一对恋爱中男女追忆他们恋爱时所看到的风景,在性别的差异下,两人的回忆截然不同。在记忆戏剧的风格模式下,德夫林对丽贝卡私人内心空间领域的侵占与控制继续推进剧情发展。
“记忆戏剧”是继60年代威胁喜剧之后,品特在70年代戏剧创作的新转向,如《风景》(Landscape,1969)、《昔日》(Old Times,1971)、《虚无乡》(No Man’s Land,1975)等剧作。记忆戏剧其实质是威胁喜剧的另一种演变,“所不同的是,在这里人物争夺的不仅是生存意义上的空间,更是由‘过去记忆’所掩盖的内心世界和‘私人领地’” [4]82。在《尘归尘》中,丽贝卡内心世界的“私人领地”这一设置引起了德夫林和丽贝卡两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冲突,形成了由人物之间冲突引起的文本动力。作为丈夫的德夫林急切地探究由丽贝卡个人记忆构成的内心世界,而丽贝卡的含糊其词则暗示了对私人内心世界的防卫。德夫林不停追问道,“我非得问你这些问题不可。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不知道……所有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我两眼一抹黑。我需要些信息。那你认为我应该问这些问题吗?”[5]297“他是什么样子?你能够给我一个他的模样?”“是哪种工作?什么工作?”德夫林对丽贝卡的逼问是对其心理空间的侵占,品特曾在1962年《为戏剧而写作》的演讲中说道:真正的“思想交流常常使人感到害怕, 企图进入他人的生活则更有威胁性, 我们很怕向他人表露我们内心的空虚。”所以丽贝卡以含糊其词反抗来自德夫林的威胁或者干脆把话题转向别处。在《尘归尘》中,丽贝卡与德夫林在由丽贝卡记忆话语构成内心世界领域的空间之争成为文本内冲突的一维,进而构成文本动力。
在《尘归尘》中,德夫林对丽贝卡的记忆空间威胁构成戏剧文本动力的一维,而丽贝卡记忆空间与现实生活空间的转换则构成了由人物与环境冲突形成的文本动力。丽贝卡的记忆内容受制于记忆的准确性与公正性。所有的疑点在剧中都有所暗示。在丽贝卡的记忆叙述中,德夫林不断地引入现实生活中的因素,将情节从记忆空间扩展到现实空间。“现在瞧瞧,让我们再次开始吧。我们生活在这里。你不是生活在……多塞特……或是其他什么地方。你和我生活在这里。这是我們的家。你有一个很好的姐姐”[5]313。“我们为什么不出门,开车到市里去,看场电影?”[5]309“你去看金和孩子们了吗?”[5]310当被德夫林引入现实对话后,丽贝卡又总能从现实中回归到记忆世界中去。她打破德夫林为她描绘的幸福祥和的日常图景,径直插入一段可怖的回忆,她回忆道曾通过自家的窗户看到一群人在向导的指引下走入大海自杀,这个意象跳过德夫林的干扰话语,承接了她之前对记忆中男子的叙述,“他们(工厂里的工人)尊敬他信仰的纯洁,他们会跟着他翻过悬崖,走进大海。如果他要求的话[5]300。同时当德夫林提出开车到市里去,丽贝卡立即转入记忆的叙述中,“我走进冰冻的城市里……当我来到火车站……我看到了列车。有人在那儿。我最好的朋友,我付出了所有感情的那个男人,那个我一见钟情的男人,我亲爱的人,我最珍贵的伴侣,我看见他走过站台,从那些哭喊着的母亲的怀里把她们的婴儿抢走了。”[5]309通过在记忆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转换,品特打破戏剧中的单一空间逻辑,制造了文本内人物所处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形成了文本内部动力。
应该看到,由现实空间引入的《尘归尘》文本动力源于品特对之前家庭伦理主题戏剧的再现。在德夫林问到“你去看金和孩子们了吗?”这一打破丽贝卡记忆情节主线的插话之后,丽贝卡便叙述她去看望姐姐一家人的情节,她的姐夫陷入婚外恋而她的姐姐则不准备原谅。这种家庭伦理的探讨也隐约浮现在剧本的始末,德夫林就对夫妻关系伦理做过如下的陈述,“除非这一切发生在我遇见你之前。那样的话你就没有义务告诉我任何事情。你的过去不关我的事”。(306)婚姻以及两性关系间的私人性权力主题是品特早期与中期戏剧中的常见模式,如《房间》《回家》 (Homecoming,1965)、《背叛》 (Betrayal,1978)、《月光》(The Moonlight,1993)等。在《尘归尘》一剧中,婚姻与家庭的情节与丽贝卡记忆中的纳粹暴力情节次第出现,成了并行而不相容的两条情节主线。品特有意识地利用对话内在断裂的间隙,通过人物之间话轮转换得以重新开启话题的机会插入他想要表现的现实与记忆、家庭生活与大屠杀影射两条情节线索之一。
在家庭这条线索之上,丽贝卡接连讲述婚外恋男子、乡下别墅生活、城市电影院、探访姐姐等一系列情节,而在大屠杀暴力这条线索上,剧作家则总能通过丽贝卡话语中的关联回到大屠杀主题上来。丽贝卡控诉记忆中的男子抢夺母亲怀里的孩子,并曾带领一群人走向悬崖投海自尽。这个意象循环地出现在全剧始末,当丽贝卡在乡下别墅登高望远欣赏风景时,众人投海的一幕即出现在眼前的风景中。当丽贝卡在夜幕下的摩天大楼望街景时,一个怀抱妇女的小孩又引发男子火车站抢夺孩子的一幕再现。家庭情节与大屠杀情节的穿插交融暗含了品特戏剧创作从中期家庭系列到后期公共政治剧系列的過渡。《尘归尘》中的大屠杀情节唤起了观众对《生日晚会》《山地语言》《送行酒》等剧作中政治迫害的记忆。在尾声处,德夫林重新上演了剧首丽贝卡记忆中男子实施的暴力,从而令全剧首尾呼应,形成完整的叙事进程。
在《尘归尘》戏剧情节发展中,观众可以看到品特以往许多戏剧的影子,而剧中丽贝卡与德夫林的漫话杂糅宗教、心理与话语权力等主题讨论于一体,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下的众语喧哗。丽贝卡与德夫林针对上帝的存留,话语的性质与催眠等精神分析的讨论与对话形成情节枝丫蔓延开去,在主干情节脉络的发展之间造成情节延迟并增加了除主情节之外的戏剧文本张力。戏剧中的杂糅主题体现了话语权力下宗教、真理与秩序等形而上学趋于消解的现状。德夫林在劝说丽贝卡时因为丽贝卡的一句讽刺“你就像上帝”而对上帝大肆发表一套言论,他说,“不要随便谈论上帝,他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上帝。如果你把他赶走了,他就再也不会回来……缺席。僵持。瘫痪。一个没有赢家的世界。”[5]30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督教的信仰维度所能带给人们的灵魂救赎早已不在,对现代荒原社会深有体会的现代主义学者及思想家会对德夫林的台词产生共鸣。德夫林又通过理发师对丽贝卡头脑的按摩这个形象的隐喻来指涉心理精神层面的洗脑、催眠等意识形态控制,而罪魁祸首就是无限延宕的语言。德夫林的一句质问道出了《尘归尘》对话语权力主题的点睛,“没有什么清白的钢笔,你不知道它之前被谁握过。”透过《尘归尘》独特的对话交锋,后文化语境下的宗教、心理等主题在对话语权力的反思中融合杂糅,而戏剧情节也得以丰满、向前发展。
二、《尘归尘》中的读者动力
《尘归尘》中的文本动力通过拼贴以往戏剧主题与风格形成人物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以及情节不稳定而形成,但在剧本的结尾这些文本内冲突并没有终结,因此《尘归尘》的文本动力只提供了剧本的开端和发展。《尘归尘》的戏剧冲突不是通过文本动力内冲突的解决实现,而是通过读者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的完成实现。品特在《尘归尘》中通过精致巧妙的构思,复杂而又悬念惊讶迭起的情节安排,深刻的思辨冲突,令观众应接不暇,脑子飞速地转动从而积极地做出反应。“如果说文本动力是作者在故事层面的修辞,读者动力则是作者在话语层面的修辞安排。”[3]61读者在阅读中会对作品做出阐释判断、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通过制造读者在这些判断之中的张力,作者制造了作品中的读者动力。
丽贝卡是《尘归尘》中的人物叙述者,她的自言自语构成典型的同故事叙述(homodiegetic narrator),即叙述者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德夫林是故事层面的受述者,一边聆听丽贝卡的讲述,一边做出反应,即被修辞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成为叙事读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在话语层,隐含作者与作者读者的叙事交流则构成另一维叙事互动。人物叙事者虽然是隐含作者虚构下的产物,但却对隐含作者的叙事意图一无所知,“因此可以说,人物叙述者在叙述交流中表现出远离隐含作者、向文本内部无限退缩的倾向。”[6]4当作者与读者的交流通过人物叙述者与叙事读者的交流来进行时,叙事读者与作者的读者会产生不同的叙事判断,这构成作品的读者动力。
在丽贝卡的暴行叙述面前,与叙事读者德夫林的漠然态度相比,作者的读者产生会更为复杂的叙事判断。在事实轴上,德夫林只关注神秘男子的职业,样貌等表层信息,而作者的读者则会注意到丽贝卡话语中深层的象征意义。丽贝卡对记忆中的男子的叙述涉及主要事实有三点,一,他是一个向导一般的人物,拥有一个工厂,别人可以为他走上悬崖,跳下大海。德夫林对丽贝卡的叙述全盘接受,丝毫未注意到话语中的逻辑矛盾与自我否定。而作者的读者会产生质疑,向导如何成了操控别人生命的刽子手?同时,德夫林几乎断定丽贝卡是在讲述某种暴行,他制止丽贝卡继续讲下去,同时发表自己关于世界观,竞争法则,男性宣言等一系列言论。但在伦理轴上,作者的读者与德夫林的距离在扩大,因为作者的读者注意到丽贝卡在讲述暴行之后又被迫全部否认自己的讲述,这显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对言论自由压迫的表现。而德夫林却对丽贝卡的自我否定表示赞许。在读者的心中,德夫林完全成了反动的象征,他对丽贝卡叙述的判断与作者的读者的伦理判断由此产生隔阂。统观《尘归尘》全篇,作者的读者与叙事读者在叙事判断上的距离经历了多重的分分合合:从事实轴到伦理轴,二者的距离都在不断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读者的反应才会随着剧情的发展起落,这也成为《尘归尘》剧情引人入胜的原因。
例如,除了在常识方面的事实判断分歧,话语逻辑的矛盾也制造了阐释判断的裂痕。品特几乎在丽贝卡和德夫林的话语中都设置了频繁的自我否定话语并制造了矛盾悖斥的含义。丽贝卡评价警笛声时说,“我讨厌警笛消失。我讨厌警笛回荡。我讨厌失去它。我讨厌其他人占有它。”[5]304而德夫林说,“我在帮你脱身。”[5]304同时又说,“我掉进了陷阱里。[5]304”又如,丽贝卡说,“繁星布满天空” [5]306,同时又说“星星没有了”,“雪是白色的”,“它不是白色的,在上面有很多颜色。[5]306”阐释判断的悖论作者的读者对作家整体艺术安排的审美效果的进行解读。
对隐含作者而言,在矛盾对立的文本意义之后,一定有其审美的目的与意义。在文本的社会政治性意义方面,品特通过丽贝卡的暴行讲述与作者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传递出反对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一切暴力的声音;同时品特又通过设置隐含作者与作者的读者之间的交流传递自己一贯以来的创作审美观,即作者无法完全控制文本意义生成,这一点将品特和其他旨在通过戏剧作品传递某种确定意义的剧作家区别开来。
在《尘归尘》中,作者的读者在文本中发现关于暴力描写的字句贯穿剧本始末,从而构建了作者一贯的反对暴力的声音。例如对于在暴徒抢夺母亲怀抱里的孩子这一情节的设置中,品特融入了多重叙事视角,首先是丽贝卡对记忆中男人的叙述,“他总是去当地的火车站,走上站台,从那些哭喊着的母亲的怀里把她们的婴儿抢走。” 之后是丽贝卡以亲眼所见的方式呈现眼前发生的真实场景。她将自己置于市里的街道空间中,“当我来到火车站,我看见了列车。有人在那儿。我最好的朋友,我付出了所有感情的那个男人,那个我一见钟情的男人,我亲爱的人,我最珍贵的伴侣,我看见他走过站台,从那些哭喊着的母亲的怀里把她们的婴儿抢走了。” 最后在剧本的末尾,丽贝卡化身为了这些哭喊的母亲之一,“孩子在呼吸。我把她搂紧。她在呼吸。她的心在跳动。”[5]315至此,不管从何种角度,暴力、母亲、孩子的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一种连贯性,作者的读者可以觉察到作者这一设置中传递的某种确定性,即作者一贯地反对暴力的声音。
与此同时,在一贯性的声音之下,作者又插入了否定的话语,从而将建立起来的确定意义完全颠覆,在剧本的中部,丽贝卡在德夫林的压力下说,“我身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甚至我朋友的身上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我从未受到过迫害。我的朋友们也没有。”这句话否定了丽贝卡对所见的叙述,在剧末,当德夫林掐住丽贝卡脖子之后,丽贝卡更是否定了自己对亲身经历的讲述,“我说什么孩子,我没有孩子,我不知道什么孩子,我不知道什么孩子。”这里的颠覆并不构成意义的虚无,相反,读者看到的是品特艺术创作一贯的审美观。《尘归尘》之所以在事实和伦理层面呈现出意义上的矛盾,是因为品特一贯的创作审美观,即他对作者和文本意义关系的理解,“所有的剧作家都想创造一个世界,而对于我来说,X先生可以走他自己选择的道路,无须经过我的审查……我自己对于词语的感觉是互相矛盾的。在词语中漫游、推敲,看着它们出现在纸页上,我从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快感。” ⑤这一段话区别了品特与其他意在传递确定意义的作家的不同之处,品特于模棱两可的风格间表现了更深层次上的语言真相。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文学的魅力在于其中潜在的无穷尽的阐释可能。在品特看来,作家的设置无法完全控制文本意义生成,“你创作了词语,词语会获得了它自己的生命力,它就以某种方式与你对视,它变得倔强了,多半会打败你。”品特对创作的审美理解在于作品所可能具有的意义潜能和自身生命力。“语言,就是在其所说的东西之下,说了另外一种东西。”因此,在《尘归尘》中一切意义的生成都伴随着不确定性,作者通过一切手段将已建立起来的印象磨灭,令它们看起来含糊并值得商榷。作者的读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完整的审美判断。
“尘归尘”一句的典故来源于《圣经》《创世纪》中第三章第十九节中的经文,原意是说人本是尘土,死后仍要归于尘土。品特将“尘归尘”用于他封笔之作的标题显然有一种创作生涯完结留与后人评论的意味在里面。在这部封笔大作中,品特一方面融合了之前的戏剧风格形成文本中的不稳定性,同时又通过制造读者叙事判断上的张力来推动情节发展,剧本的完美落幕是通过作者的读者的审美判断实现。在剧本意义的不停建构与解构中,品特以往的话语风格一览无余,即模糊、含混、躲闪的谎言下面混杂着真言。其审美伦理也得到很好的阐释,即不确定性恰恰是生活中最真实的表现,因此品特的戏剧拒绝一切标签与定位。这正是品特戏剧艺术最大的魅力,也正是基于此,品特才在英国战后戏剧的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璀璨夺目。在《尘归尘》一剧中,品特通过巧妙的修辞性叙事将家庭空间中的背叛威胁与社会空间中的暴力威胁作为两条主线串起剧作家以往戏剧创作宝库里的点点珠翠琳琅,戏剧张力的光芒美不胜收,令读者与观众完整地感受到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功力与造诣。
注释:
①②⑤来自品特在1962年布里斯托尔国家大学生戏剧节上的演讲《为戏剧而写作》。
③来自品特1970年德国汉堡莎士比亚奖获奖演说。
④来自品特1995年戴维·科恩英国文学奖获奖演说。
參考文献:
[1]Zarhy-Levo,Yael.“The Riddling Map of Harold Pinter’s Ashes to Ashes”.Journal of Theatre and Drama.4(1998):133-146.
[2]王杰红.作者、读者与文本动力学——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的方法论诠释[J].国外文学,2004,(3):19-23.
[3]尚必武.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09:56.
[4]陈红薇. 《虚无乡》:品特式“威胁主题”的演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3,(1):81-87.
[5]Pinter.Harold.Ashes to Ashes[M].Trans.Hua Ming.Shanghai:Yilin Publishing Agency,2010.
[6]周静.《谁发的牌?》中的叙述者、受述者和叙事互动[J].外国文学,2014,(7):3-9.
作者简介:
吴迪,女,汉族,辽宁凌海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国当代戏剧。
周晓航,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信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