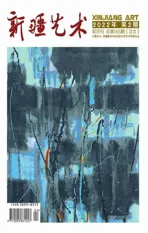论王族绿洲生态散文书写的美学特征
——以王族散文集《神的自留地》为言说中心
2022-04-23韦莎李博
□韦莎 李博

王族作品《神的自留地》封面
王族,新疆当代散文家、诗人。著有诗集《在西北行走》《高原的脉痕》,散文集《藏北的事情》《马背上的西域》《风过达坂城》《游牧者的归途》《从天山到阿尔泰》等,以及长篇散文《悬崖乐园》《图瓦之书》等。他的散文写意洒脱,文字简素而深挚,可以看作是诗的另一种形态。在内容上,王族一直以书写绿洲生态为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特别是其对动物生态的书写最具影响力,他也因此成为书写新疆动物生态的重要作家。
散文集《神的自留地》是王族对绿洲生态自然观和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生态精神的概括性审美呈现,王族以诗人的思维、散文家的笔调叙说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和生存精神。具体而言,王族在《神的自留地》中对山水草木等22 种绿洲自然物种进行分门别类地书写,将自然与人类、天地与历史融为一体,对新疆地域生态进行全景式的描绘,向读者展示一幅具有绿洲精神文化意蕴和美学风格的绿洲生物群像图。《神的自留地》中的艺术审美特征具体表现在继承性与创新性上,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对现代散文真实性与真情性、绘画美与意境美的继承,也是对现代散文在语言诗化、情节复杂化、情感深湛化的创新追求。
一、继承性:真与美的展示
对于散文的抒情性,汪曾祺曾言,“过度抒情,不知节制,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一切文学的)大敌……我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他强调散文要注意抒情的节制性。无独有偶,在新疆当代汉语散文中,大部分作家也善于使用节制的抒情,具体表现为叙事性抒情,把情感藏在叙事题旨中,把隐忍之痛用淡然平静的话语叙述出来。
(一)真实性和真情性的统一
散文的真情和实感,是在与“虚感”的冲突中建构起来的,是一种“想象的虚感”变成一种“语言的实感”。在此问题上,结合王国维的“性情说”和“所见者真,所知者深”即散文指向作者本我,强调自我情感表达的真实性的论点来看,王族的散文无疑有此特点。在《神的自留地》中,王族首先以“物说”来代替“我说”,沿袭了白话散文主观性的传统,以避免触碰散文走向客观性叙述的暗礁。以散文集中动物题材篇章为例,王族以事件为线索,将动物“人化”:如描写跟随在女人背后的狼、对子女“绝情”的雌鹰,一贯温顺却突然相互攻击的牦牛等。王族在序言中言,地域是对事物的支撑,但关注地域是危险的。因此,王族把目光从地域上转移,在书中将真实和真情重组,用平静的笔调叙述强大的情感,把真情向着生命的真实方向延伸。

作家王族
其次,作为新疆地域的行者,王族对新疆绿洲的记录细致透彻,使“边塞”摆脱既往已有的“想象的他者”的简单言说,从而显露其真实美。譬如“神的自留地”文集的命名,源于图瓦人居住的白哈巴和禾木两个村落;散文集中的《最好的树变成了纸》中桑皮纸的制作程序和老人对它的态度;《巨大的冬天》中人们对饥寒交迫的苦难记忆;《雨·最后一场雨》中老牧民警醒牧区人民在大雨中收拾毡房要保持秩序,这是源于绿洲民族传承几千年的游牧生活方式——牛羊进场后的缓急。这些细节叙述集中展现了绿洲人民对待自然万物的心态,即他们认为自然比人类更值得尊敬。正如巴尔扎克“艺术以最小的面积表达最大的思想”的观点一般,王族避开对地域的简单描摹,从对小事物的细节描述中窥见绿洲人民的生命思考。
最后,王族还以汉语音译的词语形式表现新疆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其中包括人名称谓、日常用语、生活用品等类别。比如在《水过村庄》中对索伦格、龙达的称谓;《歌》中地域性歌谣的记载、对“想望呼”等听歌感想的描述、对那仁牧场、钐镰、坎土曼等具有明显地域标识的风物的称谓、在交谈时偶尔出现“都洼尔(请允许吧)”等音译词的表述……王族极力还原语言的真实面貌,勾勒出游牧者真诚和朴实的待人处事态度。如此,在凸显王族游记性散文的信息真实性的同时,又让读者“零距离”感受绿洲生活,也增强了散文的“陌生化”效果。
总之,在散文集中,王族以“物说”代“我说”的方式展现语言的主体化、以细节囊括绿洲人民的思想、以音译记录绿洲生活,最大限度地再现绿洲地域的游牧生活和文化习俗。这些既是王族通过散文表现绿洲人民自然生态观的语言实践,也是他继承散文书写传统的一种重要体现。
(二)绘画美和意境美的统一
美是散文写作的重要特征,古往今来,研究者们都曾对散文美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释,如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朱光潜认为“美在于心与物的关系”。王族的散文在记录绿洲地域生活时,不自觉地呈现出绘画美和意境美的统一。在《神的自留地》中他活用绘画、诗歌等创作技巧来展现新疆绿洲的自然生态美,以平静的叙述给读者带来视觉的震撼并留下想象的空间。尽管王族在文中不强调事物的地理性,但在他以散文的形式记录绿洲生命时,离不开对地域景观的直接记述,比如对冰川巍峨壮美、草场和转场游牧习俗、山水雪树等超自然性的描写,以及对绿洲人面对自然生态的基本态度如何影响其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描写。
绘画美和意境美风格的统一同样是王族对传统散文书写的继承。一方面,王族通过对色彩和景致的精雕细刻展现绘画美。在山水题材的篇章中皆有着笔。如《冰山之父》一文中,阳光在高山冰面上反射出“刚烈的光洁”,让王族联想到战场上兵刃对峙的场面。《水过村庄》一文中,王族描写河岸上高大笔直的松树,齐整地勾勒出河流流经之处,充满画面感。山和水是绿洲生命的维系,是绿洲一切生命的根源,故而,王族用绘画技法描摹新疆地域的山水之美,让人生发出对自然万物生命的惊叹和敬仰,从而在绿洲生态观念的视角下重新审视自然力量。
另一方面,王族以情景交融的方式实现对绿洲人民和绿洲生活意境美地营造。王族的叙述聚焦那仁牧场、牛羊、风雪,游牧生活中的游戏、宴饮等,再现了绿洲游牧生活迥异于其他地域生活的差异美。在以“山”为题材的篇章《凝视》中,王族细致描写了如同用石头雕刻出的群山、全身涌现出生命气势的戈壁,展现了山川景色的动人之美。再如《神山在上》一文中,形容山的王者气势直抵人心,那因终年积雪而通体洁白的冈仁布波齐山,让众山“跪拜”,洋溢着圣洁之气。《冰山之父》一文中王族将慕士塔格峰的王者之气与老人“火不能灭”的敬畏相关联,表现出绿洲人民对雪山的尊敬,对万物生灵的敬仰。王族将自我情思融于笔端,以描摹绿洲图景的方式重释绿洲自然生命的壮阔。
在该散文集中,他通过对新疆绿洲地理、山川景致的细腻描写和对人与环境情景交融的意境艺术呈现,最“真实”地逼近绿洲生活内核。

静静的玛纳斯河
二、创新性:诗事思的合唱
正如公刘在《天山诗丛》的序言中所言,新疆的生活既是开拓者的生活又是正在不断开拓着的生活……新疆的诗人理所当然的应该是开拓者的气质。公刘认为新疆诗人在艺术上具有开拓性。在王族身上,诗人和散文家的双重气质相互影响,他的散文在继承传统散文内涵的同事,又在语言言说、情节结构、哲思表达上有一定的开拓创新。
记得王族曾在接受访谈时表示,散文家的心灵装得下的并不是我的宇宙和我的世界,而是世界中的我。由此观之,王族作为绿洲生态记录者对散文书写的创新性开拓,既是王族自身对创作的一种追求和提升,也是对充满人与生态谐存的绿洲地域空间影响下的一种主体回应,具体表现为质朴和诗性统一的语言特色、故事性和戏剧性相统一的情节特点、赞美性与悲悯性相统一的情感特质等三方面。
(一)语言特色:质朴性和诗性的统一
王族的散文将语言的质朴性和诗性巧妙融合,以诗性语言构成散文的美学意义。所谓诗性语言,即语言诗化,指的是散文语言具有诗歌的精致、凝练、优美、丰蕴等语言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王族摒弃了散文语言质朴性的笔调,而是一种简素与诗意的融合与交织,这正是王族所持有的“好散文家总是将激情化为温度,牵着猛虎嗅蔷薇,让一切都不动声色”的创作观点的重要例证,也就是说,王族冷静的语言背后反映的是诗性情感的内蕴。
具体而言,一是语言质朴性和诗性的统一,主要体现在散文集中书写语言的主体化和诗化。比如在《夜遇阿克巴哈河》中,王族描写“河水的内层被月光照亮,很深,也很重”。日常所见的河水在其诗性的视角中具有分明的层次,在月色笼罩下一点点透亮,意味深远。这里的“深”和“重”是视觉上的感受,也是内心的触动。自然之美从外界向内心传递的过程也是自然与人间互动的过程。又比如在《向大地觅食》一文中,“我”、沙丘、草丛和石头皆被抛弃在背后,万山以高大的身躯站立,变成寂静世界中的沉默者。这种从“物”到“心”的转移叙述,都给予我们一个自然而然打量和观察绿洲自然生态的视线顺序,符合人与物情景交融的现实感知。
二是地方民歌谚语等地域性言语在文中的穿插,也体现了散文语言质朴性和诗性相统一的特色。譬如,在开篇《水过村庄》一文中,王族引用“马跑得再快,也比不上缓慢流淌的河水”,以简素的论调阐明绿洲民间智慧,词约义丰,揭示绿洲人民对水的崇敬心理。再如新疆蒙古族的敬酒歌、哈萨克族的《送你一朵玫瑰花》等歌谣在文本中的穿插出现也体现了这一特色。如在《听歌》中,巴哈台唱出的蒙古族民歌,其歌词复叠在变化的音调上,以不同歌词唱出自然中最伟大的母爱,这种爱是与风雪、牛羊、夕阳等地域景物交织在一起的,是由“心”到“物”的一种心绪渲染。
整体而观,王族的生态书写篇章精简,单篇篇幅多为两三千字,虽以事物为类别,以事件为主要脉络展开叙述,形成“物说”私语性的客观化,但在作品结尾处,王族的书写语调又陡然以富含诗性、哲理性的短句叩击人心,反映出王族受到绿洲民谚歌谣的感染,也表现了绿洲自然生态对王族的生命启示。
(二)情节特点:故事性和戏剧性的统一
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认为,为实现“陌生化”,诗的语言是对“日常语言施加有组织的暴力”。在《神的自留地》中,王族一方面以动态为主描写场面,另一方面,王族引用绿洲民间故事阐述景物背后的文化内涵,这让散文产生故事性和戏剧性的“陌生化”效果,表现出情节上故事性和戏剧性相统一的特点:
一是王族在文中借小说技法对场面进行细致刻画,呈现人与自然间的互动关系。《雪崩》一文写雪崩发生时雪从山顶自上而下的塌落,王族并没有以单纯、简略地笔调去描写雪崩是如何的壮美,而是插入雪崩时雪的凝聚、扩散、飞扬等细微状态,并使之成为散文的言说中心和主体,让读者仿若身临其境、目睹雪崩的发生过程。同样,王族在对宴饮、放牧、聚会等特定生活场景进行书写时,还注重从视觉与听觉上对现场进行描写,使故事如同由一帧帧镜头组成的大场面,张弛有度,呈现出动态的场面美。正如丁帆所言,“生动的场面描写,流畅的情节发展线,都使作品显得晓畅流丽,从而一扫以往作品里某些沉闷之气,获得了流畅的动态美。”总之,这些场面描写调度有方,声色兼具,真实地再现了绿洲生活的本来面目,将绿洲人民与自然谐存的感悟展露无遗,引发读者对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的思考。
二是王族自觉引用绿洲民间故事干预叙事。譬如,在以“水”为题材的篇章中,王族引用了关于河的故事,如小羊饮水、河水“搬家”以及人与河水的故事等等。在这些故事中,动物与山河被“人格化”,饱含传奇色彩,同时,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在绿洲民间故事的干预叙事中起伏转折,颇具戏剧性。人类与河水维持着一种“相对静止”的地理位置和心理位置,书写出自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使故事挣脱了单调地引用,被赋予了新意。这些细节的处理是王族对绿洲民间故事文化的时代性阐释。如上所述,作为散文家,王族在写作中沉醉于绿洲民间故事所反映的绿洲文化哲思;作为诗人,王族又对细节地观察和书写细致入微,这为散文情节增添了故事性和戏剧性的特色,突显出绿洲人民对自然生命的哲思和理性叙说,表现出王族对文体认知地创新与开拓。

王族作品《沙漠中的骆驼》封面
(三)情感特质:赞美性与悲悯性的统一
记得曹文轩在《曹文轩文集·小说门》(文学研究卷)中指出:“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又有学者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这种意象在王族的笔下,被分为树、石头、猎人等23 个类别,通过对它们的描述,我们可以关注到绿洲人民对自然生命的关注,也可窥见王族对绿洲生命生存的赞扬和悲悯,对人与动植物的生存命运的忧思。
王族的散文中表现出对万物旺盛的生命力和对绿洲人民生态观的赞扬,这种赞扬是王族对生命谐存关系的赞美。对自然生命的坚韧体现在《根比树长》《枯树的温暖》等文章的描写之中,文中描述松树将地表戳破,又受着时间的施恩与摧毁,活着时挺拔,死后仍带着香。就连枯树、草地、牧道也忍受着时空更迭的考验,表现出王族自然观和生命意识的精神性提升。在水、动物等题材篇章中,王族着力于对绿洲人民自然生态观的生动刻画,比如在《水过村庄》一文中,图瓦人敬水,不会把脚踩入河中;龙达洗净马鞍子后,会把石头上的泥土也洗去。王族在文中由衷赞美,认为绿洲人民尊重自然的态度是一笔精神财富:“什么是真正的财富,物质终归只能是精神安慰,如果直接体现出精神,也许就是难能可贵的财富。”
王族散文情感赞美性和悲悯性的统一,还体现在对人和动植物的生存忧思之中。一方面王族感叹命运对绿洲人民的考验。这一点在水、猎人、歌题材篇章中处处可见,由于河流“搬家”,人们也一直处于不断搬家的状态,这是绿洲地域上游牧生活的另一种呈现。无论是记叙为了延续生命而进行的打猎,还是叙述动物猎捕者的残忍,亦或是叙述动物摄影者的救赎行为,这些篇章中对人物活动的描写始终与绿洲生灵交织在一起。概括而言,王族通过描写人与自然的交往互动,以一种审美的态度记叙了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
另一方面,王族对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复杂情绪,同样也是其散文情感的赞美性与悲悯性的统一。比如在《雪崩》一文中,王族通过描写大羊面对洪水的冷静和小羊在河中嬉戏的欢乐,阐发“苦难一旦不被视为苦难就会变成幸福”的观点,展现了王族对自然万物有喜有忧的心态。而在动物题材篇章中,王族所描写的跟在女人身后的狼、“狠心”的雌鹰以及最后一头犟驴等,也表现出王族对这些人格化的生灵对生的追求、对梦的执着的敬佩之情。
王族的散文生态书写中,有一种“大我”与“小我”关系的切换,王族将“小我”自身的悲悯性与“大我”对生命的赞美融为一体,反映出一种主体隐秘的期待与渴求,一种对现代生活渗透进绿洲自然生态环境的担忧,一种由绿洲血脉而产生的对生命意识的情感皈依,一种对散文书写的地域性探求。